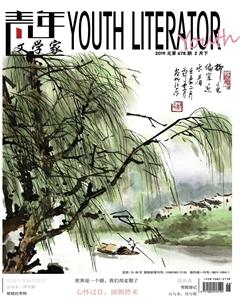讀謝桃坊先生《國學論集》一文有感
周淑怡
摘 要:謝桃坊先生的《國學論集》主要講的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和煩瑣高深學術(shù)的考證,它是獨立純粹的學術(shù)。其為學術(shù)史提供了真實可靠的依據(jù),有助于促進我國各科學術(shù)發(fā)展。國學研究的水平體現(xiàn)了先生學術(shù)的高度境界,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先生獨特現(xiàn)代的思想價值,對后學者具有啟發(fā)引導作用。
關(guān)鍵詞:國學起源;特點;治學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6--01
謝桃坊先生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的館員,他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著名專家,他的許多論著在學術(shù)界影響頗大。謝桃坊先生雖出生農(nóng)村,卻自小研讀各種書籍,1960年畢業(yè)于西南師范大學,1981年進入四川省社會科學文學院研究所,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1]。先生一生涉及學術(shù)領(lǐng)域有客家文化、國學、蜀學和新儒學,著有《宋詞概論》、《宋詞辨》、《詞學辨別》、《蘇軾詩研究》、《中國市民文學史》、《四川國學小史》等,發(fā)表論文達170余篇,其中近30篇是關(guān)于國學的[2]。2011年12月出版的《國學論集》收錄了先生26篇精華文章,包括自1991年以來所發(fā)表的國學研究文章。先生以認真和冷靜的態(tài)度,通過歷史和理論結(jié)合對20世紀初國學的產(chǎn)生、性質(zhì)、發(fā)展和重要的國學家做了深入的探討。
一、先生國學的特點
先生早年間經(jīng)歷過政治迫害的生活,煉就了他獨立堅韌的人格,對虛偽和不端的行為充滿了排斥。他一直堅守純學術(shù)的信仰,對熱炒國學的商業(yè)操作和政治倫理導向大為反感,在對國學的歷史研究上大力的批判了倡導儒學等的庸俗學術(shù)。對蜀學的解釋也是一樣,他辨別分析了巴蜀文化歷史源頭的學術(shù)史料,點出了蜀學興始儒家文化后,僅帶了某些地域特點,抨擊了某些學者為了文化建設(shè)和地方經(jīng)濟盲目傳神巴蜀文化的行為。
二、先生治學論
(一)先生治學的方法
先生在大學時期就開始吸收西方近代理論的學術(shù)方法,在其學術(shù)研究中就體現(xiàn)了科學考證的方法。先生利用自己的學術(shù)優(yōu)勢和習慣,形成了自己獨特理解學術(shù)問題的特點。學術(shù)的成就大多受學者發(fā)現(xiàn)學術(shù)問題的制約,先生的《國學論集》中,每一篇論文都以自身獨特的意識視角發(fā)現(xiàn)理解問題,對每一篇都進行了學術(shù)問題的解決。其中,國學討論解決了國學的概念性質(zhì)問題;王國維紀念碑解決了學術(shù)的獨立和自由問題;評章太炎的學術(shù)思想方法解決了國粹主義理念正確詮釋國學的概念及內(nèi)涵;胡適開啟國學研究的新方向 解決了國學研究的定位問題;胡適的國學觀念與其白話小說考證解決了國學的范圍和外延問題;對古蜀史料辨?zhèn)?解決了蜀學和中原文化的關(guān)系。從中發(fā)現(xiàn),先生對學術(shù)問題的選擇,都是核心難題,是該學術(shù)領(lǐng)域的高深點,隨著先生學術(shù)問題的解決該學術(shù)研究達到更高的層次。
(二)先生治學的視角
先生都是持著機動靈活的視角考察和解決學術(shù)問題,體現(xiàn)了先生的人文立場,又堅持了對歷史的客觀態(tài)度。在新儒學定名為理學過程中,先生以細致的文獻考證為切入點,確定了理學能準確反映新儒學的性質(zhì)特點,解決了學術(shù)概念的問題;辨別古蜀史料時,以史料疑古為切入點,將盲目建立古蜀世系者的理論基礎(chǔ)推翻;對儒家與宗教-論西方的儒教觀念及相關(guān)的問題中,以西方學者的分歧觀念和宗教的基本特征為切入點,解決了儒教概念問題;對明清時調(diào)小曲考原中,從民眾位置包容調(diào)笑淫邪的粗鄙內(nèi)容,解決了對此文化的態(tài)度問題。
(三)先生治學的依據(jù)
先生極其注意尊重原始資料和罕見史料,收集其并加以深入分析。在對四川國學運動進行評述時,先生采用了許多四川的史料并自行收集了許多四川特有的民間資料。在論蜀學的特征中,不僅引用了司馬相如、李白、蘇軾、郭沫若等大學者史料外,還使用了唐甄、李宗吾、吳鎮(zhèn)、龍昌期等不熟知的學者史料。在敦煌藏經(jīng)洞之沙州都督府文獻中,先生根據(jù)政府的檔案資料、外交資料以及史書、民間契約和宗教棄卷等,并結(jié)合政治管轄特點和沙洲都督府缺乏紙張等特點,推斷出是沙洲都督府的檔案,此觀點依據(jù)可靠可信度高,已引起敦煌學術(shù)界的重視。先生對史料的深入研究,開辟新點、險點已經(jīng)成為先生治學的典型特征。
(四)先生的治學境界
先生對學術(shù)境界的追求從未懈怠,且以崇高境界和拓新為追求目標。在先生的自傳中,其不斷強調(diào)對目標的不懈追求,并強調(diào)七年一變,其變就是指對學術(shù)境界的更高追求和自我超越。縱觀先生的學術(shù)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先生不斷的拓新精神。在對國學的概念和性質(zhì)界定后,先生轉(zhuǎn)向?qū)鴮W家們在國學運動中的轉(zhuǎn)折性作用進行研討,之后又對四川國學運動進行考察評論,在解決了蜀學性質(zhì)和來源問題后又以現(xiàn)實的眼光對蜀學的地方文化進行研究;在解決了新儒學的定名后又開始了觀念修整和對傳統(tǒng)文化的質(zhì)變影響;在確立了明清時調(diào)小曲文化意義后又把人文精神賦予了明清時代的禁毀小說上。
參考文獻:
[1]王懷成.學術(shù)思想與方法的啟示——讀謝桃坊先生《國學論集》有感[J].社會科學研究,2012,(6):208-209.
[2]湯君.試論謝桃坊先生之學術(shù)思想和方法-讀《國學論集》有感[J].蜀學,2012,(0):204-215.
[3]湯君.獨鐘詞學成系統(tǒng),別富插曲亦華章——謝桃坊研究員訪談錄[J].文藝研究,2016,(9).
[4]郭一丹.當代詞學的發(fā)展與詞體規(guī)范的建構(gòu)——謝桃坊詞學理論述評[J].社會科學研究,2017,(6):184-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