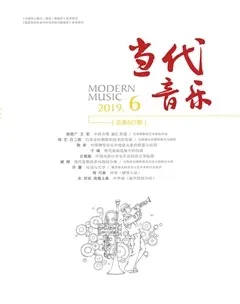對話與互學(xué)
許馨
[摘 要]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時期,文化藝術(shù)多元發(fā)展。2018年12月21日,“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研討會”在北京長白山國際酒店隆重召開,與會代表圍繞魏晉南北朝音樂制度、考古與文化交流、思想觀念與總體發(fā)展等議題,展開了比較深入的討論,促進了多學(xué)科對話合作、互鑒互學(xué),共同推進了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研究。
[關(guān)鍵詞]魏晉南北朝音樂;多元文化;多學(xué)科互學(xué)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7-2233(2019)06-0029-03
2018年12月21日,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云岡石窟研究院、《中國音樂學(xué)》雜志社聯(lián)合主辦的“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研討會”,在北京長白山國際酒店召開。來自華中師范大學(xué)、廣州大學(xué)、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云岡石窟研究院、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學(xué)院等十多所院校和科研單位的二十多位專家學(xué)者,參加會議。專家們從文學(xué)、歷史、宗教學(xué)、樂譜學(xué)、音樂學(xué)等多個學(xué)科出發(fā),運用開放視野,對魏晉南北朝文化研究提出了諸多新見解,拓寬了魏晉南北朝研究的道路。多學(xué)科學(xué)者的不同思想、視角和方法,交流激蕩,既促進了彼此之間的友誼,也有力提升大家共同合作探討發(fā)掘、弘揚優(yōu)秀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的自覺。
一、打破壁壘,構(gòu)建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研究多學(xué)科對話平臺
本次研討會討論的課題跨越文史學(xué)、音樂學(xué)各領(lǐng)域,還有來自不同學(xué)科的專家們攜帶多年深入思考和研究心得參與,因而搭建起各大學(xué)科交流、溝通的新平臺。首先感謝來自云岡石窟研究院張焯院長的致辭,為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研究開拓思路,展示更多實例資料。
張焯院長指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混亂時期,也是一個偉大時期。歷史由此邁向大唐,走向中國文化的巔峰。同時,佛教及佛教藝術(shù),經(jīng)魏晉南北朝階段的發(fā)展走向成熟,在未來上千年,占據(jù)中華文化的半壁江山。恰是云岡石窟中反映佛教音樂、樂舞的相關(guān)雕刻為古代音樂研究保存了最華美的實物!云岡石窟中的雕塑表現(xiàn)吹奏樂、打擊樂、彈撥樂三種音樂形式。梁朝僧人慧皎(497—554)在《高僧傳》中講到,印度管弦之音,帶給人們靜悟、歡悅的氣氛,云岡石窟表現(xiàn)的天宮伎樂,具有雙重功用,既育佛,也育人。從曹植開始,佛教音樂多創(chuàng)新少守舊。由于語言、歌詠方式不同,來自印度的佛教音樂逐漸消失在中國大地。所以云岡洞窟雕刻樂隊組合名實、特點以及承載音樂等問題亟須解決。云岡石窟在建筑方面集中體現(xiàn)出希臘、羅馬、印度等多種外來藝術(shù)特征;美術(shù)上再現(xiàn)了犍陀羅藝術(shù);佛學(xué)上,是中華大乘佛教誕生并走向藝術(shù)化的里程碑式建筑。云岡石窟不同于中國早期小乘佛教的藝術(shù)形式,也不同于印度中亞的既有石窟。特別是中期洞窟,是彌勒信仰盛行下,對彌勒天宮的理解,將彌勒天宮在人間的空想變成現(xiàn)實。把天宮搬到了人間,這是一次巨大的創(chuàng)造。那么作為天宮之樂的云岡石窟的音樂形象,到底創(chuàng)造的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張院長呼吁,云岡石窟是中國甚至是世界佛教建筑形式上的一個特例,是中西文化音樂的最高薈萃。希望各界學(xué)者一起走進云岡石窟,研究云岡石窟,共同挖掘與復(fù)活云岡石窟。
馬良懷的《魏晉文人與音樂》從文化史、思想史與中國古代社會階層三方面入手,他認為,在人的發(fā)展過程中,經(jīng)歷了兩次飛躍:第一次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人從萬物中獨立;第二次在漢魏之際,個體從群體中獨立。戰(zhàn)國時期,中國文人從士人階層走出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真正形成一個社會階層,重要特點便是人的覺醒。人的覺醒帶來了藝術(shù)的覺醒。在魏晉之前,藝術(shù)形態(tài)經(jīng)歷了兩個階段:公用階段和教化階段。儒家強調(diào)“移風(fēng)易俗莫善于樂”,音樂(藝術(shù))本身沒有獨立的生命,是為政治、教化而服務(wù)的。魏晉時期,文人階層重視自我的主體感受,追求個體生命的真實存在。漢魏之際,隨著建安年代鄴下文人集團的出現(xiàn),中國文人階層活躍于歷史的舞臺,藝術(shù)開始擁有獨立品格。例如三國曹魏時期的嵇康,從藝術(shù)角度思考音樂。嵇康認為,音樂本身沒有喜怒哀樂之情,但不同音樂對人的情緒有不同感染力,音樂是二者之間的媒介,這正是音樂作為藝術(shù)而體現(xiàn)出來的作用。嵇康《聲無哀樂論》的主要貢獻便是使音樂(藝術(shù))掙脫社會束縛,擁有生命力。他將音樂從教化百姓的工具,轉(zhuǎn)變?yōu)橐粋€獨立的生命存在。判斷音樂好壞,不是社會影響大小,而是自身是否和諧。嵇康遭奸人所害,臨終仍以《廣陵散》一曲,表現(xiàn)、宣泄內(nèi)心情感,將生命和藝術(shù)同時切入美的意境中,使二者成為永恒,亦表現(xiàn)出中國文人與音樂的密切關(guān)系。
吳相洲以《談雅樂來源問題》為題的發(fā)言指出,現(xiàn)代學(xué)人多用雅樂、清樂、燕樂三個概念描述漢唐音樂史發(fā)展歷程,造成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宋人將唐樂簡單地分為雅樂、清樂、燕樂,造成后世的訛誤。故雅樂來源問題至關(guān)重要。從漢到唐,雅樂基本有三個來源,一是周宮廷音樂留存,所謂的“先王之樂”;二是依古法重建,根據(jù)典籍所載前代音樂再造雅樂;三是以新聲為雅樂,吸收流行音樂制作的雅樂。由此得出三點結(jié)論:一是雅樂不以音樂特點命名,而以功用命名,專指朝廷郊廟祭祀音樂(少量用于燕射)。其中有“先王之樂”留存,有依先王樂理之重建,也有以新聲之創(chuàng)制,一概看作“先王之樂”很不準(zhǔn)確。二是歷代皆有雅樂,只有隋代把清樂當(dāng)作雅樂,總體上得不出清樂取代雅樂之結(jié)論。三是雅樂曾取資于俗樂、胡樂等,但雅樂僅供朝廷郊廟祭祀之用,傳播范圍十分有限,很難成為流行音樂,談不上被流行音樂取代。從音樂發(fā)展及音樂志書記載看,清樂和燕樂在出現(xiàn)時間上幾乎不分先后,無替代關(guān)系。雖然初唐樂府清樂曲目表演越來越少,但并未徹底消失,一些清樂曲目變成法曲,繼續(xù)用于宴饗。所以“清樂衰落后燕樂興起”說法不太確切,且唐代燕樂與清樂也不是對立關(guān)系。例如唐代雅樂除了用于郊廟祭祀,也用于宴饗,燕樂指宴饗音樂,燕樂包含部分雅樂。另外,《破陣》《上元》《慶善》等燕樂樂舞也曾入雅樂之列。從《舊唐書·音樂志》載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石奏請修訂已入雅樂三大舞事宜可以看出唐代燕樂與雅樂是并存關(guān)系而非先后替代關(guān)系,是相互借用關(guān)系而非對立關(guān)系。故雅樂被燕樂取代的結(jié)論也不準(zhǔn)確。出現(xiàn)這些問題,是由于當(dāng)下學(xué)科劃分過細,學(xué)科間交流有限,造成層層的學(xué)科壁壘。故要加強學(xué)科交流,打造互通共鑒。
二、多視角切入,挖掘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研究新價值
范子燁的《喉囀與胡笳:中古時代的喉音藝術(shù)》立足于個人長期的藝術(shù)實踐與田野調(diào)查,以漢魏時代著名詩人繁欽(?—218)在建安十七年(212)正月寫給曹丕(187—226)信中的匈奴車子為核心(《昭明文選》卷四十的《與魏文帝箋》),切入到整個中古時代即漢魏南北朝喉音藝術(shù)領(lǐng)域,他認為,喉轉(zhuǎn)就是呼麥,胡笳就是莫頓·潮爾。就整體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而言,車子的呼麥更偏向于深沉的抒情性的那一類型。在他自由、輕靈、緬邈、哀怨的呼麥聲里,在“日在西隅,涼風(fēng)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的無限美好的自然背景中,人們或“仰嘆”,或“俯聽”,無不為之“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車子的呼麥所具有的藝術(shù)感染力真是令人遐想不已!曹操西征的赫赫功業(yè)已消失在歷史中,但大軍中小小的車子卻以自己的呼麥之音穿越歷史長空,帶著草原氣息走來。所以,車子(198—?)是偉大的,是不朽的。“喉囀引聲,與笳同音”這八個字相互印證,喉音的歌唱技巧和胡笳具有同質(zhì)性。通過對相關(guān)文獻的清理與闡釋,將古代文獻與現(xiàn)代活態(tài)相印證,音樂學(xué)分析與詩學(xué)解讀、美學(xué)分析與歷史學(xué)解讀、豐富的第一手材料與現(xiàn)代性的闡釋相結(jié)合,揭示藝術(shù)的真實與感染力。
項陽的《重新認知兩晉南北朝對中國音樂文化的價值》通過對近些年的研究內(nèi)容梳理與回顧指出,學(xué)界常以漢唐論中國音樂文化,將兩晉南北朝涵蓋其中,影響后世國家音樂文化發(fā)展的樂籍制度;禮樂文化新發(fā)展和雅樂重新定位;佛教音聲對中原音樂文化的重要影響;周邊國度特別是西域諸國音樂文化對中原實質(zhì)性的影響,大多形成于兩晉南北朝時期,有些甚至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能夠改寫中國音樂文化史。學(xué)界應(yīng)對這一歷史時期音樂文化現(xiàn)象深入探討,重新認知兩晉南北朝時期音樂文化的重要價值。例如,樂籍制度確立對中國音樂文化發(fā)展影響深遠,《魏書·刑罰志》等多種文獻明證,此前沒有明確專設(shè)樂籍歸之。樂籍制度的源頭為北朝時期,官屬樂人設(shè)置專門戶籍,文獻涉及三種人:刑事犯罪人員的眷屬,陣獲俘虜及其眷屬以及因政治獲罪者的眷屬入籍,以樂戶稱之,逐漸形成專業(yè)、賤民、官屬樂人群體,承載國家禮制儀式用樂和俗樂的為用。正是與國家禮樂制度緊密關(guān)聯(lián),彰顯了這個專業(yè)群體存在的必要性。周代確立國家禮樂制度,樂與禮制儀式相須。禮樂面對特定對象、特定儀式和儀程、樂人群體性存在、樂之形態(tài)在儀程中固化為用。俗樂類下,隨時代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一系列音聲技藝類型,諸如說唱、歌舞、戲曲、器樂等,同樣形成一條主導(dǎo)脈絡(luò)。儀式與非儀式為用、禮樂和俗樂兩條主導(dǎo)脈絡(luò)不斷發(fā)展且一以貫之,成為國家用樂的整體樣態(tài)。在歷史語境下,禮樂、俗樂為用必定活態(tài)承載,由此加深對國家用樂深層認知,感知樂這種音聲為主導(dǎo)技藝形態(tài)與禮樂制度和樂籍制度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此外,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交往引發(fā)了音樂的一系列變化,諸如國家音樂傳播制度、雅胡俗三分禮樂為用現(xiàn)象、佛教洞窟音聲認知等。魏晉南北朝時期應(yīng)引起音樂學(xué)界足夠重視,拓展開來會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發(fā)展的認知有極大助益。
秦序的《南北朝文化藝術(shù)的多元發(fā)展及兩極端現(xiàn)象的繼起與并存》認為,費孝通“多元一體格局”思想給文化藝術(shù)研究,帶來非常重要的啟迪:中國歷史上有在多元化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逐漸實現(xiàn)一體的時代,即多元前提下追求一體化為主線的時代——“多元一體發(fā)展”時代。另外,也有某個一體化的結(jié)構(gòu)下,多元逐漸發(fā)展,導(dǎo)致舊的一體分化解構(gòu),再經(jīng)多元進一步發(fā)展后,逐漸形成新的一體化建構(gòu)的時代,即“一體多元發(fā)展”時代。西周時代封邦建國和制禮作樂,秦朝在郡縣制基礎(chǔ)上推行書同文、車同軌、形同倫等舉措。漢代又進一步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決策。因此,秦漢王朝建構(gòu)的是新的多元一體格局,是在前一種西周建構(gòu)的多元一體格局基礎(chǔ)上,經(jīng)由春秋戰(zhàn)國多元發(fā)展之后,建構(gòu)起來的多元一體新格局和新階段。它繼承和發(fā)展了前一種多元一體格局,但不是復(fù)舊,而是實現(xiàn)了多方位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是一種螺旋性的上升。魏晉南北朝,是秦漢大一統(tǒng)專制集權(quán)社會之后出現(xiàn)的分裂割據(jù)時代。它既是長期大動蕩、大沖突、大分裂的時代,也是多民族進入中原地區(qū)與漢民族大交流、大融合而激烈互動的時代。秦漢大一統(tǒng)王朝的文化藝術(shù),是“一體化”為主、多元化發(fā)展為次的新高點、頂點、端極,實現(xiàn)高度的“文化統(tǒng)一與思想統(tǒng)一”;魏晉南北朝則是文化多元發(fā)展為主、一體化發(fā)展為次為后的另一個新高點、頂點、端極,是“亂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可謂兩大極端之間的一次來回大擺動。因此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出現(xiàn)了中華文化史上不多見的思想、文化和藝術(shù)的“兩極端并起”,或“兩極端并存”的奇特景象。諸如過去經(jīng)學(xué)為主干、以儒學(xué)為獨尊的文化模式,魏晉以后進入低谷。玄學(xué)、佛教、道教種種宗教和異端思想則大興,由此形成了儒學(xué)、玄學(xué),二教道教佛教相互結(jié)合、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蕩格局。文化的多重碰撞融合,使文化呈現(xiàn)了多樣性、豐富性,文化得到多向度的豐富發(fā)展;戰(zhàn)亂頻仍、災(zāi)難慎重,局部地區(qū)或短暫時間,又有相對安定和繁榮的局面出現(xiàn);佛教大興和滅佛;政治黑暗混亂,社會充滿苦難,文化藝術(shù)卻多元、自覺發(fā)展;傳統(tǒng)中原漢民族的禮樂文化,值此亂世,遭到嚴重大破壞、大擠壓,但在南方地區(qū)則得到尊重和傳承,甚至變俗為雅。種種矛盾的評價、種種兩極端事項的出現(xiàn),正反映這一時代思想文化上的兩極端繼起,或兩極端并存,非常值得關(guān)注。
孟凡玉、韓啟超、柏互玖、周靜婉、吳夢雅基于深厚的文獻功底,從微觀具體入手,考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相關(guān)音樂儀式、機構(gòu)、制度、樂器等方面。趙昆雨、辛雪峰、劉曉偉、李榮有借鑒考古學(xué)、圖像學(xué)等研究方法與理念,將研究目光從紙質(zhì)文獻擴大到實物、活態(tài)中,不斷地為中國古代音樂研究補充新材料。孫云、金溪探討了佛教音聲與儀式對音樂研究的重要意義。學(xué)者們圍繞魏晉南北朝文化的研究內(nèi)容與方法、理念與意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觀點和判斷,并嘗試突破現(xiàn)有研究的局限,對魏晉南北朝文化做更深入的探索與解析,全面挖掘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文化蘊含。
結(jié)?語
習(xí)近平總書記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xué)互鑒、互利共贏精神為指引,倡導(dǎo)打造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中國自古重視對外交往,中華文化在繁榮交流學(xué)習(xí)中形成了“美美與共”的多元特色。多元的文化互動,成就出燦爛的絲路文化。所以,保持開放包容、互學(xué)互鑒思想,才能更好地收獲璀璨文化。習(xí)總書記對外訪問的講話思想為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次與會專家學(xué)者從各自研究領(lǐng)域出發(fā),從廣闊的視角對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進行了深入討論,為音樂學(xué)此時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視野,拓展了相關(guān)論題研究的路徑與方法。秦序先生在會后總結(jié):“這次研討會不是音樂界關(guān)起門來自說自話,而是將不同知識結(jié)構(gòu)、思維方式的學(xué)者匯集,討論和研究共同關(guān)心的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提出新的見解,迸發(fā)出創(chuàng)造的火花,形成異質(zhì)綜合的優(yōu)勢。另外,這次研討會也提醒我們關(guān)注各學(xué)科之間的結(jié)合互動關(guān)系,以及各分支學(xué)科總方向的一致和整體的統(tǒng)一;提醒我們注意采用更多方法、選取更多視角,來揭示研究對象——音樂藝術(shù)及其相關(guān)行為、事項、思想、意識、文化等多層面復(fù)雜結(jié)構(gòu),進而總結(jié)中國音樂藝術(shù)的特色、獨立的發(fā)展道路及體系。”
黃翔鵬先生曾提出“三個斷層”[1]說法,中國歷史在每一次斷層都經(jīng)歷著劇烈的時代變革,春秋時期周天子及其諸侯政治地位的衰落,禮崩樂壞引發(fā)的社會格局及秩序的變化,使中國思想文化步入轉(zhuǎn)型,繼而迎來第一個黃金時代——諸子百家爭鳴時期。魏晉南北朝戰(zhàn)爭頻仍、動蕩分裂,但思想?yún)s自由創(chuàng)新,文化成果輝煌,史學(xué)家曾將魏晉南北朝比作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時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化藝術(shù)呈現(xiàn)出多元的發(fā)展。音樂、繪畫、雕塑等文化因子的融合,儒、道、佛三教信仰的共存,胡、漢文化的沖突與交流,都加速了人性的覺醒與藝術(shù)的自覺。
當(dāng)下魏晉南北朝音樂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是我們前行與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項陽主張,要從不同視角把握時間節(jié)點前后的情狀,辨析相通性和差異性,再挖掘重要歷史節(jié)點的價值意義。德國哲學(xué)家萊布尼茨說過,唯有相互交流我們各自的才能,方能共同點燃我們的智慧之燈。通過會議,與會代表交流學(xué)術(shù)研究視角與方法,多學(xué)科對話中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資料再共享與研讀,極大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文化研究的繁盛新局面。
注釋:
[1]黃翔鵬.黃翔鵬文存[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05):94—95.
(責(zé)任編輯:張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