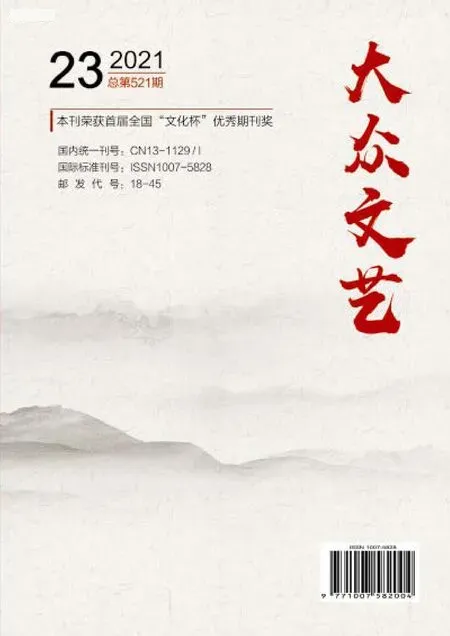尋找庇護所的旅行:伊麗莎白?畢肖普詩歌中的景觀
(上海理工大學 外語學院 200093)
伊麗莎白?畢肖普,繼艾米麗迪金森之后美國最著名的女詩人之一,在美國詩歌史上一直享有盛譽。目前,國內外學者對畢肖普詩歌中旅行和景觀這兩個主題分別都有涉及,國外學者馬里特?麥克阿瑟(Marit MacArthur)認為畢肖普的無根使她趨向旅游,同時引出畢肖普詩歌中房屋總是被“遺棄”這一觀點;撒伽利亞?皮卡德(Zachariah Pickard)則轉而提出,畢肖普事實上是在“就旅行提出一個特殊的負面解釋”。而國內對和旅行相關的景觀主題的討論,主要來自米家路對詩歌中地理海景和畢肖普旅行中的“四種自我”的闡釋,以及包慧怡對畢肖普這個“地圖繪制者”的闡釋。
這篇文章在繼承前人堅實研究的基礎下,對畢肖普詩中有關旅行的景觀做研究。以此說明畢肖普雖然沒能在這場心靈的旅行中找到永久的物理性庇護所,但在對不同種類的景觀再現中,獲得了代償;在現實與想象之間置入安全距離,調和了兩者之間的沖突。
一、在路上:小徑、地理與人
畢肖普在旅途中對所見所聞進行描摹,用以展現她“在路上的”的狀態。這些描寫中,小徑常常是荒涼的,甚至有時是致命的;同時,地理往往令人迷惑、難以分清方向。
(一)道路景觀:致命與拒絕
通過對不同交通工具以及與交通相關的事物的描繪,例如小徑、鐵路、碼頭等,畢肖普表現了她希望路途終能通向庇護所的愿景。但事實上在建構景觀時,她無意識選擇性地表現它們荒涼、拒絕與致命的特質。
在《鐵路》中,“我”走在荒涼的鐵道上去尋找隱士,可鐵道“枕木彼此靠太近/或許又太過疏遠”。火車可能與“我”相撞,太近或者太遠的枕木更是增加了小徑的不穩定。此外,街道在詩人的詩歌中出現的頻率也很高,例如在詩《粉紅狗》《瓦里克街》和《我們前往街角的暗穴......》等詩歌里都對街道做了相應的描繪,著力呈現出街道的陳腐、拒絕和危險的一面。
對這些道路景觀的消極描寫,也是畢肖普對作為客體的自我書寫,表現了作為外來者被更“安全”的地方拒絕的傾向,別處的庇護所對她呈現的并非包容的態度,繼續旅行仍然成為畢肖普繼續的事。
(二)地理景觀:孤獨與迷失
而對于地理景觀,畢肖普也有自己的描繪方式,時常使用對比,通過不同論述之間的張力達到表情達意的目的。雖然她很詳盡地描繪地圖的顏色和形狀,其中方向往往不定。
畢肖普的地理詩中,說話者與景觀之間大都缺乏有效的聯系和互動,處于非流動狀態,繼而營造被隔絕感與無方向感。《奧爾良碼頭》中,畢肖普就展示了關于碼頭的凝滯景觀。碼頭孤零零且安靜地佇立著,雖然開口的外部是廣博的海洋,說話者可以走向的方向卻是四面八方。畢肖普通過詩中落葉流動的方向和說話者的無方向感,表現了她在路途中的孤獨迷失。與此類似的對立同樣出現在詩人的《海景》中,詩中“燈塔”將海景一分為二,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獄。天堂正是畢肖普在旅途中想要尋找的庇護所,但是伴隨著疑惑“看起來的確恍若天堂”,這種構建的、存在于想象中的庇護所,最終解體、消解,天堂與地獄互相溶解、相互置換。
要之,畢肖普在悖論式的地理景觀的描述中展現出來的是旅途中的孤獨與迷失。這處于詩人潛意識中的情感往往被詩人以間接的方式表達出來,通過詩歌中由對立帶來的空間分割和置換不斷強化旅途中的孤獨與迷失。
二、未知的目的地:不是庇護所的房屋
畢肖普不斷地旅行,尋找庇護所來安置她的身體與靈魂。然而,庇護所難尋。她的詩歌中的房屋往往缺乏跟庇護所相似的性質,相反,它們總是倒塌或者存在于夢中。正如加斯東?巴什拉認為的那樣,房屋并不單單只是一件物品,它是“人類靈魂的分析工具”。借助于房屋,我們有可能找到通往畢肖普內心世界的入口。
(一) 倒塌的房屋景觀:易壞的庇護所
畢肖普詩歌中倒塌的房屋因為不可抗的外部力量傾覆,通過外形的消失加劇了詩人旅行途中的孤獨無助感。
《耶羅尼莫的房子》則提供了這么一個范本。正如加斯頓?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指出的那樣,一個房屋“要求人單純地居住其中,簡單性給人以巨大的安全感。”。被耶羅尼莫當做“童話宮殿”的房屋雖簡單,但是擁有一個美好的庇護所的重要性質:美麗、舒適。房屋 “紅紅綠綠”的,“有一個/木花邊曬臺”,還有音樂、舞蹈。耶羅尼莫的房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家”,一個“愛巢”。然而,詩中的 “容易腐爛的”揭露了殘酷的事實,一場颶風后,只留下樂透彩的數字,曾經的庇護所,最終歸于廢墟。
在房屋呈現逐步消逝下,畢肖普渴望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的庇護所也逐一消散。傾覆的房屋不再具有庇護所的功能,宣告她再次嘗試的失敗。
(二)夢中的房屋景觀:想象的庇護所
巴什拉相信,“家宅庇護著夢想,家宅保護著夢想者,家宅讓我們能夠在安詳中做夢。”
如果一個人擁有一間房間,她/他就能成為一個平和的做夢者,因為房屋能夠保護她/他。如果沒有擁有房屋,她/他就會在白日夢里夢到房屋。
在《三月末》中,畢肖普描繪了她“原夢”里的“夢幻屋”應該是什么樣的。但是這樣的庇護所只存在于幻想中,那日“海風過于凜冽”,“走不到那么遠”, “房子一定封上了木板”。而《站著入眠》里則涉及到真正的夢。夢中的小屋代表著對永久的庇護所的渴望,然而小屋既在眼前也遠在他方。有時跟隨著“碎礫和卵石”去尋找小屋,可它們卻“在青苔中溶解”。直至即使“徹夜駕駛直至破曉”,我們“連房屋的影子也沒有找到”。
現實中的庇護所難以尋找。然而正如巴什拉認為的那樣,“家宅是一種強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考、回憶和夢融合在一起。在這一融合中,聯系的原則是夢想。”夢,可以向做夢者提供強有力的精神上的房屋。毫無疑問,對于畢肖普來說,詩歌的書寫成為一種夢,并借此尋找到了永久的庇護所。
三、結語
畢肖普詩歌中的景觀雖然有時在解構旅行的意義,旅行路上的景觀總是骯臟、壓抑和無方向,然而它們也有自己實際上的意義。作為一種“視覺引導物”,給詩人提供了一個安全距離,在這個距離下,她能夠有效與自己的記憶交流,緩解記憶與現實、個人所失與藝術創新之間的張力,因此某種程度上寫詩的行為和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做夢,成為詩人不休、無根的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失去的在藝術的創作中得到補償。藝術即是她生命中最終永恒的庇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