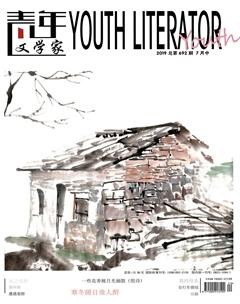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養一齋詩話》視野中的《楚辭》研究
摘? 要:潘德輿作為傳統儒家詩教的繼承者,以傳統的“溫柔敦厚”為詩教原則,在《養一齋詩話》中所論“必求合于溫柔敦厚、興觀群怨之旨”,他認為《楚辭》與《詩》均為后世詩歌創作之根本原則,但《楚辭》的地位低于《詩》。并把《楚辭》與《詩》共同作為“詩之源”,強調“賦比興”三位一體的詩歌表現形式,表現出一種兼收并蓄的文學態度。
關鍵詞:清代;《養一齋詩話》;《楚辭》
作者簡介:盧宇寧(1995-),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詩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02
楚辭是公認的與《詩》并峙的一座詩的豐碑,歷朝歷代以來,對“楚辭”的研究都層出不窮,清代是“楚辭學”的集大成時期。在乾嘉學派的推動下,各種《楚辭》著作和注本層出不窮,創造了清代楚辭學的繁榮局面。而清代詩話對《楚辭》更是進行了全方位的闡釋,彌補了專著與注本的不足,豐富了楚辭學的內容,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清代楚辭學的發展風貌。[1]
潘德輿是晚清重要詩人,他的《養一齋詩話》始終遵循儒家思想,所論“必求合于溫柔敦厚、興觀群怨之旨”,同時他又重“性情”,贊揚直抒個人胸臆的情感,所以他追求的應當是一種熱烈真摯而又“不逾矩”的情感狀態,而《楚辭》就剛好符合,因此他以《詩》和《楚辭》為源頭,作為研究詩歌創作、審美、批評理論的標準和模范。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研究一下這一位傳統的儒家繼承者心目中《楚辭》的形象。
一、與《詩》相較,言其地位
清代詩論家普遍認為《楚辭》是受《詩三百》的影響,開后世詩歌之源流,潘德輿自然也不例外。首先,他引用《學齋占畢》的觀點,“……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為變風矣。”[2]對《楚辭》是“變風”,是在《詩》的基礎上進行的革新表示贊同,而后始終將《詩》與《楚辭》并列作為詩歌發展的源頭及作詩的典范,如“泰徒以六朝隱約意思為《風》、《騷》遺響,而不知樂天、文昌樂府之可貴,此以皮毛相詩者。”
盡管潘氏將《楚辭》與《詩》同樣都視為詩歌創作之根本準則,但《楚辭》都是伴隨著《詩》順帶而提的。潘氏作為一個恪守儒家思想道德規范的傳統詩教者,他眼中這二者的地位自然一目了然:
嚴羽《滄浪詩話》,能于蘇、黃大名之馀,破除宋詩局面,亦一時杰出之士思挽回風氣者。第溯入門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于《離騷》,恐尚非頂<寧頁>上作來也。
魯直不甚服坡詩可也……謂以此自負而刺坡,則楚《騷》亦不易到,而魯直平時之詩,豈真能與《國風》抗衡,而敢以之自負哉?以晚近文人相輕之心測度古賢,予不以為然。
杜紫薇謂李長吉詩“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夫“奴仆命《騷》”者,惟《三百篇》耳,長吉為《騷》之奴仆而不足者也。
首先,他雖然贊同嚴羽于宋詩說理之外別開生面,不假妙悟,但仍對嚴羽詩歌入門于《離騷》而非《詩三百》顯示出懷疑的態度,但此時的態度比較委婉;第二則態度鮮明地認為《國風》深于《離騷》;第三條更是指出《離騷》乃《詩》之奴仆,而李賀即使作為《離騷》之奴仆也不能夠,立場已明顯確立。
因此可以看出在潘德輿的心中,《楚辭》雖與《詩》均為詩歌藝術的兩座豐碑,對后世詩歌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詩》的地位始終根深蒂固,《楚辭》只是次之而已,這也是清代學者對《楚辭》普遍態度,“無論是古文派還是今文派, 也無論是漢派還是宋派, 其楚辭研究成就均不及經學。尤其是今文派, 楚辭研究方面甚至與經學成績截然相反。”[3]
二、作“詩之源”,言其影響
鐘嶸在《詩品》中首次將詩人追根溯源,最終都歸結為《詩》與《楚辭》,開后世追溯詩源之先河。而后凡論詩歌創作之源頭及詩人風格淵源皆效仿之,都是按照《詩》、《楚辭》、漢、魏,唐、宋、元、明、清的順序,已然形成一種傳統。潘德輿就極力贊揚朱熹的論述:
朱子論詩,謂“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后,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欲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后,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矣”。
潘氏評價“詩之源流得失,實盡此數十言之中”,可以看出他對《詩》與《楚辭》并峙地位的認同。《詩》與《楚辭》都是純性情的文學元典,開后世詩歌創作之源流,只有以《詩》與《楚辭》為詩歌創作之根本,并重“性情”與“學問”,“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才是“能詩之士”。
探討《楚辭》對后世詩人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唐代詩人,清代詩論家多認為李白是承襲《離騷》之浪漫主義,“太白宗《國風》,又兼《離騷》,其樂府古詩往往有沉著入微處,謂其純蹈虛,則窺太白亦淺矣。” 潘德輿不僅李白是《離騷》之苗裔,杜甫也受到《楚辭》影響,“而終以子美為堂奧歸宿,方與《風》、《騷》、漢、魏有息息相通處”。
潘德輿在品評詩歌作品時以詩人人品居于詩歌才華水平之上,尤其強調“忠義愛國”,他認為《楚辭》是繼《詩》之后能夠代表“忠義”的作品,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委婉地勸諫君王親賢臣遠小人,“忠義”是屈原最優秀的品質。他在詩話中屢次斥責陳子昂背信棄義,諂媚新皇,置忠義于不顧,背棄《詩》《騷》之正道,態度鮮明地反對杜甫、韓愈等人對陳子昂的贊賞:
杜公尊子昂詩,至以《騷》、《雅》忠義目之,予烏得異議?曰:子昂之忠義,忠義于武氏者也,其為唐之小人無疑也。其詩雖能掃江左之遺習,而諷諫施諸纂逆,烏得與曲江例觀之?杜、韓之推許,許其才耳。吾不謂其才之劣也。若為千秋詩教定衡,吾不妨與杜、韓異。
杜甫把陳子昂看作《騷》、《雅》的繼承者,以“《騷》、《雅》忠義目之”。這主要是針對陳子昂提倡的“風雅興寄”和“漢魏風骨”提出來的,而潘德輿主要從家國情懷出發,認為陳子昂的忠義是對新主的忠義、對舊主的背板,他雖有才氣,然人品卑劣不足道,是傳統詩教倡導者所不容的。潘氏對陳子昂“不忠義”進行的批判與對傳統愛國詩人陸游“忠義”的贊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放翁詩學所以絕勝者,固由忠義盤郁于心”,一個是“唐之小人”,一個“忠義盤郁于心”,二者相較,高低立見。
三、強調“賦比興”三位一體
在指導詩歌創作方面,潘氏始終將《詩》與《楚辭》看作詩歌創作的根本準則,他并標舉“賦比興”三位一體的詩歌表現形式,“蓋只知意在詞表為《三百》、為《離騷》,而不知《風》、《騷》之暢敘己懷,鋪陳亂始,直詆匪人者,固指不勝屈也。大抵詩知賦而不知比興者,則切直而乏味;知比興而不知賦,則婉曲而無骨,三緯所以不可缺一。”潘氏認為“比興”能夠使詩歌作品婉曲不貧乏;“賦”能夠使詩歌作品切直有骨氣,三者需要相互配合才能產生有情感有意味的真正的作品。《楚辭》繼續延續《詩》的表現形式,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在詩歌創作中注意體現審美的規律和結構原則,講究情感情節、語言文字的相互變化,以賦、比、興三種形式相互穿插,增添了詩歌的形象性和抒情性,更具有審美韻味。
潘氏在“賦比興”的基礎上更注重“比興”,即帶給人“深曲有味”的審美感受,讓讀者獲得更深入的情感體驗。“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平鋪直敘的詩是平淡無奇的,只有一波三折才能夠蕩起讀者的漣漪,如撞鐘般清音有余,連綿不絕。
綜上所述,潘德輿雖身為儒家傳統詩教的倡導者,不單純尊崇《詩》,而是能夠發現《楚辭》與《詩》相似的地方,提取出有利于儒家詩教的部分并大力宣揚,體現出兼收并蓄的文學態度。潘氏始終以《詩》為詩歌正統,《楚辭》只是順帶提及,這也是清代文學家的普遍現象,這毫無疑問是楚辭學的一大憾事。
參考文獻:
[1]施仲貞:《清詩話中的楚辭評論》,《北方論叢》,2009年06期,第12頁。
[2]本文所引《養一齋詩話》均為:(清)潘德輿著,朱德慈輯校:《養一齋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
[3]毛慶:《復興與創新--試論清代經學對楚辭研究之影響》,《漢江論壇》,2010年01期,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