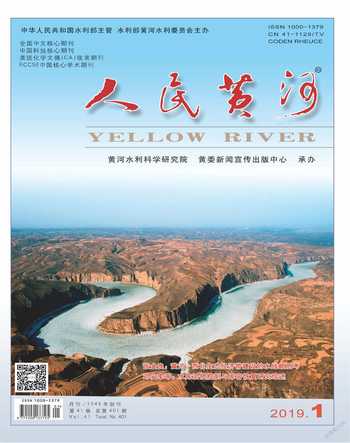水利工程施工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三方博弈探析
安慧 劉暢 王思樺





摘要:為促進(jìn)水利工程施工過(guò)程中減少環(huán)境污染、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分析了政府、建設(shè)單位、施工單位三方博弈模型的均衡解,以尋求激勵(lì)施工單位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措施。首先,分析水利工程項(xiàng)目環(huán)境治理現(xiàn)狀,對(duì)建立模型的前提條件進(jìn)行假設(shè);其次,建立政府、建設(shè)單位、施工單位三方博弈模型,分析隨著各影響因素的變化,模型均衡解是否會(huì)向著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方向發(fā)展;最后,根據(jù)對(duì)模型均衡解的分析,提出政府完善監(jiān)督激勵(lì)政策等激勵(lì)施工單位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主動(dòng)不偷排的措施。結(jié)果表明:有效的監(jiān)督、合理的環(huán)保合同條款以及適當(dāng)?shù)莫?jiǎng)懲機(jī)制有利于施工單位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從而減少環(huán)境污染,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將綠色理念貫穿水利工程建設(shè)始終。
關(guān)鍵詞: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激勵(lì)作用;博弈策略;水利工程
中圖分類(lèi)號(hào):TV-9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doi:10.3969/j .issn.1000- 1379.2019.01. 031
水利工程施工會(huì)對(duì)周?chē)h(huán)境產(chǎn)生大量污染,例如噪聲、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以及揚(yáng)塵等,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目前,我國(guó)政府為監(jiān)督或鼓勵(lì)企業(yè)加強(qiáng)環(huán)境保護(hù),已頒布一系列相關(guān)法律、政策,對(duì)企業(yè)產(chǎn)生的環(huán)境污染收取政府綜合治理環(huán)境的相應(yīng)費(fèi)用。這些政策對(duì)促進(jìn)企業(yè)加強(qiáng)環(huán)保建設(sh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Druckman等[1]認(rèn)為,個(gè)體企業(yè)缺乏實(shí)施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動(dòng)力,由于政府收取的治理環(huán)境費(fèi)用是依據(jù)監(jiān)測(cè)機(jī)構(gòu)測(cè)出的污染物排放量來(lái)計(jì)算的,且監(jiān)測(cè)機(jī)構(gòu)往往沒(méi)有精力對(duì)施工單位進(jìn)行全程監(jiān)控,所以一般只能監(jiān)測(cè)已知排放點(diǎn)的排污量,很難監(jiān)測(cè)到施工單位是否采用其他排放方式偷排以及偷排的量。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來(lái)自政府、社會(huì)、環(huán)保部門(mén)等的監(jiān)督形成了促進(jìn)企業(yè)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外部壓力。因此,如何禁止施工單位偷排、實(shí)現(xiàn)企業(yè)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從而減少對(duì)環(huán)境的污染,是一個(gè)值得探討的問(wèn)題。
如何促進(jìn)企業(yè)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眾多學(xué)者進(jìn)行了相關(guān)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李創(chuàng)[2]對(duì)環(huán)境成本進(jìn)行分類(lèi),從提高企業(yè)競(jìng)爭(zhēng)力角度,提出減少環(huán)境污染的建議:金友良等[3]基于產(chǎn)品各生命周期階段將環(huán)境成本分為內(nèi)部與外部成本,從設(shè)計(jì)研發(fā)、原材料獲取、產(chǎn)品生產(chǎn)等各個(gè)階段分別提出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措施:安志蓉等[4]建立政府間、企業(yè)間、政府與企業(yè)間及顧客、媒體等其他環(huán)境保護(hù)利益相關(guān)者與企業(yè)間的博弈模型,分析提出可使環(huán)境績(jī)效與企業(yè)績(jī)效正相關(guān)的措施:劉佳佳等[5]分析國(guó)內(nèi)外對(duì)環(huán)境成本的分類(lèi),將環(huán)境成本分為選擇性成本、損耗成本及社會(huì)成本,運(yùn)用三者間的關(guān)系建立“漏斗模型”:汪龍生[6]建立港口污水處理過(guò)程中的企業(yè)與政府間演化博弈模型,得到動(dòng)態(tài)演化趨勢(shì);章輝美等[7]分析政府、企業(yè)、社會(huì)三方動(dòng)態(tài)博弈求出的均衡解,進(jìn)而分析各影響因素對(duì)均衡解的影響,提出增加社會(huì)監(jiān)督等措施促使企業(yè)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
上述研究運(yùn)用不同方法,分析了如何促進(jìn)企業(yè)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并提出許多很有價(jià)值的措施。另外,也有學(xué)者如王麗等[8]研究分析了施工質(zhì)量對(duì)環(huán)境成本的影響;張智慧等[9]通過(guò)建立環(huán)境評(píng)價(jià)模型,對(duì)項(xiàng)目施工的環(huán)境友好性進(jìn)行系統(tǒng)評(píng)價(jià),從而改進(jìn)項(xiàng)目環(huán)境管理。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在企業(yè)和施工單位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方面的研究對(duì)于促使水利工程施工單位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具有一定借鑒意義,但均缺少針對(duì)水利工程特征以及現(xiàn)階段政府針對(duì)水利工程施工單位偷排現(xiàn)象的治理研究。為此,筆者針對(duì)水利工程施工的特點(diǎn),建立政府、建設(shè)單位與施工單位之間的三方動(dòng)態(tài)博弈模型,并計(jì)算得出均衡解,通過(guò)分析影響均衡解的相關(guān)因素,嘗試?yán)媒ㄔO(shè)單位對(duì)施工單位進(jìn)行全過(guò)程監(jiān)督,促進(jìn)施工單位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以減少施工單位偷排現(xiàn)象,從而減輕施工環(huán)境污染。
1 政府、建設(shè)單位及施工單位三方博弈模型
1.1 模型假設(shè)
政府請(qǐng)的監(jiān)測(cè)機(jī)構(gòu)往往無(wú)法做到對(duì)施工單位施工全過(guò)程進(jìn)行監(jiān)控,否則需要投入的精力太大,因此政府可以借助本身就要對(duì)施工全過(guò)程進(jìn)行監(jiān)督的建設(shè)單位進(jìn)行全程監(jiān)督(這里將監(jiān)理單位歸屬于建設(shè)單位一方[10])。為此,政府需要針對(duì)施工單位的環(huán)境治理效果,對(duì)建設(shè)單位進(jìn)行獎(jiǎng)懲,從而使建設(shè)單位加入監(jiān)督施工單位環(huán)境治理效果的行列。這里作如下假設(shè)。
(1)政府、建設(shè)單位、施工單位均為理性人。
(2)若政府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存在偷排現(xiàn)象,將對(duì)建設(shè)單位及施工單位追究連帶責(zé)任,并且建設(shè)單位及施工單位都需要繳納一定數(shù)額的罰款。
(3)政府有權(quán)對(duì)任何水利工程進(jìn)行監(jiān)督,建設(shè)單位及施工單位須無(wú)條件配合政府對(duì)工程環(huán)境治理情況的督查。
(4)建設(shè)單位與施工單位之間制定了有關(guān)環(huán)境治理的相關(guān)合同條款,建設(shè)單位可選擇是否對(duì)施工單位進(jìn)行監(jiān)管,施工單位也可選擇是否偷排污染物,但若被建設(shè)單位發(fā)現(xiàn)存在偷排現(xiàn)象,建設(shè)單位可上報(bào)政府,從而免除政府對(duì)建設(shè)單位的懲罰。施工單位須無(wú)條件配合建設(shè)單位對(duì)工程環(huán)境治理情況的督查。 基于上述假設(shè),設(shè)定如下參數(shù):S為政府(/=1)、建設(shè)單位(i=2)、施工單位(i=3]的支付函數(shù),其中j(j=1,2,…,8)表示不同博弈行為結(jié)果的集合;W為施工單位投資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不成功,使政府治理環(huán)境額外增加的費(fèi)用;J1為政府監(jiān)督施工單位是否偷排所需的監(jiān)督費(fèi)用:F為政府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偷排,對(duì)建設(shè)單位以及施工單位的罰款之和;J2為建設(shè)單位監(jiān)督施工單位是否偷排所需的監(jiān)督費(fèi)用:A為政府監(jiān)督后對(duì)工程項(xiàng)目環(huán)境保護(hù)優(yōu)秀的表彰評(píng)優(yōu)給建設(shè)單位帶來(lái)的效用:T為合同中約定,若建設(shè)單位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有偷排現(xiàn)象,建設(shè)單位對(duì)施工單位的罰款,但該罰款不能超過(guò)政府對(duì)建設(shè)單位的罰款數(shù)額:w為施工單位不偷排需增加的費(fèi)用:K為政府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偷排,對(duì)建設(shè)單位和施工單位罰款的分配比例,即對(duì)建設(shè)單位的罰款為FxK、對(duì)施工單位的罰款為Fx(1-K)。
1.2 模型構(gòu)建
在政府、建設(shè)單位和施工單位三方博弈中,各博弈方的行動(dòng)具有先后順序,且后行動(dòng)者可在行動(dòng)前通過(guò)觀察先行動(dòng)者的行為來(lái)選擇自己的策略,該博弈屬于不完全信息動(dòng)態(tài)博弈。借鑒其他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11],構(gòu)建政府、建設(shè)單位和施工單位三方動(dòng)態(tài)博弈模型,繪制博弈樹(shù)(圖1)。節(jié)點(diǎn)G表示政府( Government)、0表示建設(shè)單位(Owner)、C表示施工單位(Contractor);該三方動(dòng)態(tài)博弈的假定如下。
(1)參與人集合:政府、建設(shè)單位、施工單位。
(2)參與人行為順序:假定該博弈中,參與人行為順序?yàn)檎⒔ㄔO(shè)單位、施工單位。政府制定相關(guān)環(huán)境監(jiān)督政策,并根據(jù)對(duì)建設(shè)單位及施工單位行為的預(yù)測(cè)選擇是否進(jìn)行監(jiān)督:建設(shè)單位根據(jù)對(duì)政府決策行為的觀察及理解,以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決定是否對(duì)施工單位進(jìn)行監(jiān)督:施工單位再根據(jù)對(duì)建設(shè)單位決策行為的觀察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選擇是否偷排。
(3)參與人的行為空間:政府可以選擇對(duì)建設(shè)單位及項(xiàng)目實(shí)施監(jiān)督或不監(jiān)督,建設(shè)單位可以選擇對(duì)施工單位及項(xiàng)目實(shí)施監(jiān)督或不監(jiān)督,施工單位可以選擇不偷排或偷排。
(4)參與人的信息集:政府監(jiān)督與不監(jiān)督的概率分別為α和l-α.建設(shè)單位監(jiān)督與不監(jiān)督的概率分別為盧和1-β,施工單位不偷排與偷排的概率分別為y和1-γ。
1.3 博弈模型的支付函數(shù)構(gòu)造
基于以上博弈模型假設(shè),對(duì)應(yīng)圖1中三方博弈樹(shù)的8個(gè)分支,分別給出各博弈參與者的支付函數(shù),見(jiàn)表1。
1.4 動(dòng)態(tài)博弈均衡解分析
通過(guò)博弈模型得出的均衡解,分析政府、建設(shè)單位及施工單位的決策行為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1)由γ*=1一J1/F可知,施工單位選擇不偷排的概率γ與政府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偷排后的罰款F正相關(guān),與政府監(jiān)督施工單位是否偷排所需監(jiān)督費(fèi)用J1負(fù)相關(guān)。其含義表明,施工單位為了避免繳納高額罰款,會(huì)更愿意選擇不偷排:而若政府監(jiān)督施工單位是否偷排所需要的費(fèi)用很高時(shí),施工單位會(huì)由此推測(cè)政府選擇監(jiān)督的概率會(huì)很低,因此會(huì)選擇偷排。
另外,由于γ不可能為負(fù),因此必有J1≤F。這與事實(shí)相符,對(duì)政府來(lái)說(shuō),若監(jiān)督費(fèi)用高于罰款,則監(jiān)督無(wú)法帶來(lái)效用,因此政府不會(huì)選擇監(jiān)督。為了更加直觀感受y如何隨J1、F的變化而變化,本文將J1、F具體化,假定二者取值范圍為0~5萬(wàn)元,可得三者的變化關(guān)系,見(jiàn)圖2。
(2)由式(9)可知,建設(shè)單位選擇監(jiān)督施工單位的概率β與施工單位因不偷排所需付出的額外費(fèi)用w、建設(shè)單位承擔(dān)的罰款費(fèi)用比例K、政府對(duì)于工程未偷排而給予建設(shè)單位的嘉獎(jiǎng)對(duì)應(yīng)效用A正相關(guān),與政府發(fā)現(xiàn)偷排后對(duì)施工單位的罰款F(1-K)、政府監(jiān)督費(fèi)用J1以及建設(shè)單位監(jiān)督費(fèi)用J2,負(fù)相關(guān)。其現(xiàn)實(shí)意義為,施工單位不偷排所額外付出的費(fèi)用越高,則施工單位更可能傾向于為了不付出這筆費(fèi)用而選擇偷排,而建設(shè)單位監(jiān)督獲得施工單位繳納的罰款的可能性越大,因此選擇監(jiān)督的概率會(huì)加大。建設(shè)單位承擔(dān)罰款的比例越大,說(shuō)明在施工單位偷排后,建設(shè)單位需要繳給政府的罰款越多,建設(shè)單位為了不繳高額罰款,將傾向于監(jiān)督施工單位;如果施工單位偷排了,建設(shè)單位也可以因監(jiān)督施工單位,發(fā)現(xiàn)其偷排從而獲得施工單位繳納的罰款,作為自己繳納給政府罰款的補(bǔ)償。另外,對(duì)建設(shè)單位來(lái)說(shuō),獲得政府嘉獎(jiǎng)的欲望越強(qiáng),即效用越大,越可能對(duì)施工單位采取監(jiān)督。政府對(duì)施工單位的罰款越高,施工單位更傾向于不偷排,則建設(shè)單位會(huì)選擇不監(jiān)督來(lái)節(jié)省監(jiān)督費(fèi)用。同時(shí),政府的監(jiān)督費(fèi)用越高,建設(shè)單位通過(guò)分析可知政府將傾向于不監(jiān)督,因此自己不易被罰款,也就會(huì)傾向于選擇不監(jiān)督。而建設(shè)單位過(guò)高的監(jiān)督費(fèi)用也會(huì)使建設(shè)單位監(jiān)督概率減小。
(3)由式(7)可知,政府選擇監(jiān)督施工單位是否偷排的概率α與建設(shè)單位監(jiān)督施工單位所需費(fèi)用.J2正相關(guān),與合同內(nèi)約定的對(duì)施工單位偷排的罰款T、未偷排時(shí)政府給予建設(shè)單位的嘉獎(jiǎng)所帶來(lái)的效用A以及政府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偷排后的罰款F負(fù)相關(guān)。其含義表明,建設(shè)單位監(jiān)督施工單位所需費(fèi)用越高,建設(shè)單位越傾向于不監(jiān)督,以省下這筆高昂的監(jiān)督費(fèi)用,政府在分析得出該結(jié)論后更傾向于選擇監(jiān)督。建設(shè)單位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偷排,根據(jù)合同約定對(duì)施工單位的罰款越高,則建設(shè)單位更有積極性去獲得這筆罰款,因此更可能傾向于監(jiān)督,政府在分析得出該結(jié)論后更傾向于不監(jiān)督來(lái)節(jié)省監(jiān)督費(fèi)。另外,政府對(duì)建設(shè)單位的嘉獎(jiǎng)帶給建設(shè)單位的效用越大,則建設(shè)單位更可能采取監(jiān)督,政府同樣會(huì)傾向于不監(jiān)督來(lái)節(jié)省監(jiān)督費(fèi)。政府高額的罰款會(huì)促使施工單位選擇不偷排,政府在分析得出該結(jié)論后也會(huì)選擇不監(jiān)督來(lái)節(jié)省監(jiān)督費(fèi)。
2 案例分析
2.1 案例演算
某大型水利工程項(xiàng)目屬于政府重點(diǎn)建設(shè)項(xiàng)目,政府對(duì)該工程項(xiàng)目是否偷排的監(jiān)督費(fèi)用為J1= 11 500元,但政府可選擇對(duì)工程是否監(jiān)督。若監(jiān)督后發(fā)現(xiàn)偷排,根據(jù)嚴(yán)重程度確定罰款金額,罰款金額F由前文可知,應(yīng)大于政府監(jiān)督費(fèi)用J1,因此F最低為11 500元,另設(shè)有罰款上限,最高16 000元。其中對(duì)建設(shè)單位的罰款占比為K= 60%.而偷排帶給政府治理環(huán)境額外增加的費(fèi)用W= 50 000元:若因工程項(xiàng)目的環(huán)境保護(hù)效果明顯,政府對(duì)建設(shè)單位進(jìn)行表彰,設(shè)其帶來(lái)的效用為20 000元,即A= 20 000元。建設(shè)單位對(duì)施工單位是否偷排的監(jiān)督費(fèi)用J2 =10 000元,合同約定若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偷排,對(duì)其懲罰T=8 000元,另外有FK≥T。施工單位不偷排所需增加費(fèi)用w=7 000元。其中,運(yùn)用MATLAB繪制動(dòng)態(tài)博弈均衡解(a*,β*,γ*)中α與γ之間的變化關(guān)系,見(jiàn)圖3。
2.2 影響因素分析及啟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Jl、J2、F、A、T、w、K等因素會(huì)導(dǎo)致政府、建設(shè)單位選擇監(jiān)督以及施工單位選擇不偷排的概率發(fā)生變化。假定三方的信息都是完全對(duì)稱(chēng)的,那么當(dāng)上述影響因素取定值時(shí),可由式(10)求出政府、建設(shè)單位選擇監(jiān)督以及施工單位選擇不偷排的確定概率值。其中,Jl、J2、w屬于客觀值,隨項(xiàng)目復(fù)雜程度及進(jìn)展而改變,不因政府、建設(shè)單位或施工單位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因此在不考慮技術(shù)層面改進(jìn)的前提下,無(wú)法通過(guò)改變這三個(gè)因素來(lái)影響概率值的變化。那么,為了使模型均衡解向著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方向發(fā)展,即施工單位選擇不偷排的概率增大,可以考慮以下措施。
(1)政府加大懲罰力度。由圖2可見(jiàn),隨著政府對(duì)施工單位偷排現(xiàn)象的罰款力度加大,即F值越大,施工單位選擇不偷排的概率γ也會(huì)變大,換句話(huà)說(shuō),此時(shí)施工單位為了避免高額罰款,更傾向于選擇不偷排,即向著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方向發(fā)展。但罰款F只能適當(dāng)增大,不能無(wú)限增大,由圖3可見(jiàn),在概率γ增大的同時(shí),政府的監(jiān)督概率α?xí)p小,在長(zhǎng)期發(fā)展中會(huì)引起惡性循環(huán),最終導(dǎo)致環(huán)境成本外部化。
(2)合理分配建設(shè)單位與施工單位的罰款比例。K值的變化會(huì)直接影響建設(shè)單位選擇監(jiān)督施工單位的概率盧,K值越大,則建設(shè)單位所承受的罰款越多,此時(shí)建設(shè)單位會(huì)傾向于選擇監(jiān)督。但K值的增大意味著施工單位所承受的罰款降低,當(dāng)施工單位被罰款的費(fèi)用低于偷排節(jié)省的費(fèi)用時(shí),施工單位仍會(huì)傾向于選擇偷排。此時(sh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政府選擇監(jiān)督,即有β[F(1一K)+T]+(1 -β)F(1-K)≤w;另一種是政府選擇不監(jiān)督,則有βT+(1-β)×0≤w。在這兩種情況下,施工單位都會(huì)選擇偷排。另由假設(shè)可知,T≤FK,可得K的取值應(yīng)滿(mǎn)足:
3 結(jié)論與建議
環(huán)境安全不僅是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也是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政治問(wèn)題,而水利工程建設(shè)過(guò)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較大導(dǎo)致政府環(huán)境成本增加。以政府、建設(shè)單位、施工單位的博弈為切人點(diǎn),通過(guò)對(duì)動(dòng)態(tài)博弈均衡解的分析來(lái)研究促使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措施。結(jié)合水利工程環(huán)境治理現(xiàn)狀及相關(guān)政策,通過(guò)建立政府、建設(shè)單位、施工單位三方動(dòng)態(tài)博弈模型,分析隨著政府監(jiān)督費(fèi)用J1、政府罰款F、建設(shè)單位罰款T等各影響因素取值的變化,動(dòng)態(tài)均衡解的變化,進(jìn)而采取措施,改變影響因素,推進(jìn)模型均衡解向著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的方向發(fā)展。
根據(jù)以上研究成果并結(jié)合實(shí)際情況,提出如下建議:①政府根據(jù)實(shí)際的監(jiān)督費(fèi)用適當(dāng)增加罰款可以減小施工單位偷排的概率,但是需要注意罰款的臨界上限;②若施工單位不偷排所付出的費(fèi)用較大,建設(shè)單位應(yīng)積極監(jiān)督施工單位的規(guī)范排放,并且政府可以提高對(duì)建設(shè)單位收取罰款的比例來(lái)激勵(lì)建設(shè)單位實(shí)施有效的監(jiān)督措施:③政府可以通過(guò)合適的表彰以及獎(jiǎng)金的形式來(lái)提升建設(shè)單位發(fā)現(xiàn)施工單位偷排現(xiàn)象的效用,以此激勵(lì)建設(shè)單位更好地對(duì)施工單位進(jìn)行監(jiān)督。
本文為促進(jìn)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提出一種新的思考角度.為了方便計(jì)算,博弈模型的假設(shè)相對(duì)理想化。通過(guò)增加參與方以及參與方的策略集可以使博弈結(jié)果更加符合實(shí)際,為水利工程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提供進(jìn)一步的措施和建議。
參考文獻(xiàn):
[1] DRUCKMAN A, BRADLEY P,PAPATHANASOPOULOUE,et al.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s Carbon Reduction inthe UK[ 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6(4):594-604.
[2] 李創(chuàng),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及其在工業(yè)企業(yè)間的差異分析[J].價(jià)格理論與實(shí)踐,2015(12):86-88.
[3] 金友良,李晶晶,基于生命周期的企業(yè)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探討[J].西安財(cái)經(jīng)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28(3):49-52.
[4] 安志蓉,丁慧平,環(huán)境績(jī)效、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與環(huán)境保護(hù):一個(gè)研究綜述[J].中國(guó)科技論壇,2013(1):126-131.
[5]劉佳佳,曾月明,環(huán)境成本最優(yōu)化決策模型構(gòu)建:基于環(huán)境成本內(nèi)部化視角[J].財(cái)會(huì)月刊,2015(9):37-40.
[6] 汪龍生,港口工業(yè)污水處理監(jiān)督的演化博弈分析[J].大連海事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4):26-29.
[7] 章輝美,鄧子綱,基于政府、企業(yè)、社會(huì)三方動(dòng)態(tài)博弈的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分析[J].系統(tǒng)工程,2011(6):123-126.
[8] 王麗,王志祥,建筑工程綠色施工質(zhì)量與環(huán)境成本分析[J].施工技術(shù),2016,45(12):103-106,137.
[9] 張智慧,鄧超宏,建設(shè)項(xiàng)目施工階段環(huán)境影響評(píng)價(jià)研究[J].土木工程學(xué)報(bào),2003,36(9):12-18.
[10] 周建亮,佟瑞鵬,陳大偉,等,我國(guó)建筑安全生產(chǎn)管理責(zé)任制度的政策評(píng)估與完善[J].中國(guó)安全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20(6):146-151.
[11]劉長(zhǎng)玉,于濤,綠色產(chǎn)品質(zhì)量監(jiān)管的三方博弈關(guān)系研究[J].中國(guó)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5(10):17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