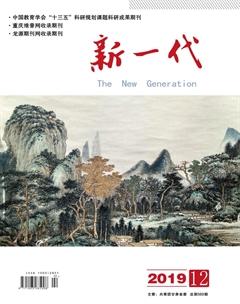悲喜劇比較探析
蔣敏敏
摘 要:悲劇歷來被人稱為是戲劇之冠,叔本華也曾經說過“悲劇是藝術的最高峰”。如果說喜劇是“小橋流水人家”,給人一種輕松的愉悅感,那么悲劇則是“滾滾長江東逝水”,震撼直抵人心。人們在欣賞藝術時,總會不自覺地發現,相比較喜劇而言,悲劇給人的印象更為深刻,更能夠直擊心靈。那么筆者將從以下三個方面比較悲劇與喜劇的不同,試圖從中探析悲劇比喜劇更震撼人的原因。
關鍵詞:悲劇;喜劇;審美效應;審美特征
一、悲劇與喜劇的本質特征
歷史上許多人都對“悲劇”這個概念曾做出界定,亞里士多德是藝術史上最早對悲劇的本質做探討的人,他在《詩學》中提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德國古典主義美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認為“悲劇是‘兩種對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之間的沖突與調節”。這相互沖突對立的兩個方面,各有其合理和片面的一面,在矛盾沖突的過程中,雙方各執一面,最終導致毀滅。矛盾雙方在激烈斗爭的過程中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價值的毀滅,會引起極大的觀感刺激,并且在戲劇結束之后,人們還是會對此進行思考和反思。
與此相反,喜劇是用一種荒唐的藝術表現形式形成“悖謬”,從而引人發笑,來鞭撻、征服丑。喜劇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否定型喜劇、肯定型喜劇和含淚型喜劇,含淚型喜劇是一種悲喜劇,界限模糊,筆者在這里不做過多解讀。就前兩種喜劇而言,否定型喜劇是“用諷刺嘲諷的手法撕破偽裝,揭示丑陋的本質”,肯定型喜劇是“用幽默詼諧的手法將人民內部矛盾中的一些不良現象作為批評的對象,寓莊于諧達到喜劇性效果”,這兩者都是將“人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人們在欣賞喜劇的過程中不會產生價值觀的巨大矛盾沖突,反而是會抱著一種理所當然的姿態去俯視劇中人物。
二、悲劇與喜劇的審美效應比較
“審美效應”是指文學接受活動對主體所產生的審美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共鳴、凈化和領悟。
亞里士多德指出悲劇能夠“借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情感得到陶冶”。中國當代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對其中的“陶冶”二字做了解釋,他認為“陶冶”包括道德進化和情感宣泄。由此可見,對悲劇的欣賞會給人帶來“審美效應”,“共鳴”就是在藝術鑒賞中,鑒賞主體在審美直覺和審美體驗的基礎上,進而深深地被藝術作品所感動、所吸引,以至于達到忘我的境界。悲劇更具有切身性,觀眾在欣賞悲劇的時候,總是人為地將自己想象成其中的悲劇主人公,因此悲劇能夠很大程度上引起人的共鳴。而喜劇則是恰恰相反,觀眾在觀看喜劇時總是站在道德至高點上,是具有旁觀性,無關痛癢地批判者劇中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使自己和劇中人區分開來。“凈化”是指鑒賞者通過藝術鑒賞而達到的調節精神、排遣情緒的效果。悲劇人物的遭遇會讓人們的內心感受到一種悲傷和壓抑,但也正因為如此,在欣賞的過程中,人們的悲傷情緒可以借這這種悲傷的氛圍加以釋放。在欣賞喜劇的過程中,人們雖然會不自覺地對人物的行為發笑,但是這種笑或許并不能帶來情感上的愉悅,而只是對丑的輕蔑和嘲笑。“人之所以發笑,是因為突然發現了可笑的事物的某種缺陷或弱點,從而意識到自己的優越”
“領悟”是指在欣賞藝術作品時對世界奧秘的洞悉,人生真諦的徹悟,以及精神境界的升華。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審美效應。悲劇將真善美以一種十分殘忍地方式撕碎在人們眼前,人們會不自覺地對悲劇人物產生一種憐憫,這種憐憫的心態會使人產生強烈的“嫉惡如仇”,思想上受到悲劇人物的反抗行為牽引,被他們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及其反抗邪惡的精神所感染。同時,對悲劇人物的憐憫還會促使人們去思考造成這種悲劇的深層次的原因,給人思想上的啟迪,這樣人的思想境界在欣賞悲劇的過程中就會得到升華。而喜劇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社會現狀,并對此進行諷刺,試圖通過鞭笞丑引發人們的思考,但是其撕碎的終究是無意義的東西,同時也由于觀眾與劇中人始終維持著一種距離感,因此思考是難以升入的,無法給思考者帶來精神的升華。
三、悲劇與喜劇的審美特征比較
悲劇中的人物必須具有正面素質,他們是正義、美好、善良的代表,憑借自己的力量和惡勢力抗爭,但最后往往不得善果,反映了人在時代中的無力感,因此魯迅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像中國古代四大悲劇之一的《竇娥冤》中的竇娥,她善良、孝順,為了能夠使婆婆免遭酷刑,寧愿簽下砍頭罪狀,即便是在赴刑場的時候仍對婆婆一腔柔情,沒有對她產生絲毫怨恨和不滿,對待張驢兒父子這樣的惡勢力,竇娥也是積極地去抗爭,毫不妥協,可是最后竇娥仍然判死。竇娥對代表著封建皇權的天地進行辱罵,可是最后又不得不把死后昭雪的希望寄托于天地。哈代筆下的苔絲也是如此,苔絲純潔美麗勤勞,敢于反抗道德和虛偽的宗教,但是十九世紀的英國鄉村正處于現代與傳統的交界地帶,傳統的價值觀念在她心中并沒有完全淪喪,她內心充滿著掙扎,最終走向毀滅。
而在喜劇中,人物常常是乖謬錯訛、自相矛盾的,喜歡通過自炫來獲得別人的關注,人物具有丑態,在戲劇中通過夸張的方式將這種丑態展示出來,從而引起觀眾的嘲笑。就如《變色龍》中的奧楚蔑洛夫,為了在百姓面前展示自己的威嚴和公正而多次進行自炫,可是在每一次自炫之后他又會迅速變臉,因為威嚴和公正只是他對百姓的一種展示,他本質上見風使舵、媚上欺下的性格特點并沒有發生變化,戲劇在這樣的自我矛盾中達到喜劇效果。
參考資料:
[1]李建東,《藝術觀審中的“距離”生成》,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1月
[2]祁志祥,《論悲劇與喜劇——美的范疇研究系列之四》,人文雅志,2015年第07期
[3]彭吉象,《試論悲劇性與喜劇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