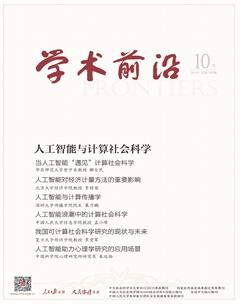從平等到對等:刑法平等原則的教義學深入
谷超
【摘要】刑法的平等原則應當以社會倫理作為支撐以實現和諧之目標,因此,需要通過身份構建對等進而彌補平等原則的倫理缺陷,從而展現社會倫理中不同角色的對等形式。對等是刑法實質平等的體現,可以表達刑法實質合理性之追求;是刑法自足性之內在需求;是存在于社會群體或者個體中的“集體無意識”。為了實現對等并加以適用,刑法立法應肯定對等的價值,并通過立法加以展示。通過刑事司法展示對等,刑法應肯定并期待適用對等后的社會效果。
【關鍵詞】平等? 對等? 身份? 社會倫理
【中圖分類號】D924?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0.0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條規定了刑法的平等原則,該原則規定了刑法在“所轄范圍”內適用主體的平等性。在理想狀態下,該原則保證刑法適用時排除了所有非刑法要素之干擾,諸如:財產、頭銜等。此理想狀態雖是刑法孜孜以求之目標,但因為刑法必然需要以社會為依托,刑法的適用無法完美達到這種“真空”的狀態。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如何使刑法平等原則獲得足夠的社會倫理支撐,為刑法平等原則的社會倫理化提供理論支撐。
刑法平等原則社會倫理困境
當下刑法中的平等原則雖以成文形式展現,但其內在價值仍回避社會倫理,即刑法的平等原則于適用時排除所有非刑法的差別性因素,即在不考慮犯罪人任何身份、地位差異的前提下求取“絕對值”式之相等。在“絕對值”式的對比之下,刑法衡量的方式僅僅強調人與人之間“量”的相等,而非人與人社會價值、社會屬性之間的對等。在此種衡量方式下,刑法的工具意義被不斷突出,即在定罪量刑時,平等原則只是作為一種衡量罪、賦予罰的工具。于此而言,平等原則于適用時不斷展現的是自身的工具價值,而非展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及社會秩序維護者之地位。在此種理念之下,刑法有可能在規則主義的窠臼里越陷越深,以致背離社會倫理基礎,刑法越發存有“刑罰不中”[1]之傾向。
刑法作為法規范的一部分,其實質是社會倫理規范。[2]因而,寄望和諧共處的刑事法律不應該要撇開社會倫理標準,而應當以社會倫理作為支撐以實現和諧之目標。[3]但是,當下社會倫理在刑法評價理念和評價體系之中不斷被弱化,刑法的平等原則亦是如此,導致諸多立法、司法理念無法吻合公眾樸素的刑罰觀,致使刑法評價或者刑法司法結果無法與社會價值產生共鳴。因而,為了走出當下的“共鳴”困境,平等原則對于自身乃至刑法的社會倫理屬性不能視而不見,而是應當以社會倫理為切入點,使刑法規范與社會倫理規范充分銜接,減少人們認知刑法規范的難度,[4]最終實現刑法公眾認同之目標。
刑法平等原則社會倫理之突破
刑法作為社會的“倒影”,理當“倒映”社會倫理及其價值取向,刑法的平等原則概莫能外。換言之,刑法的平等原則應體現對合理范圍內社會倫理秩序的肯定與維護。因而,平等原則欲走“現實性”缺陷,需以倫理為支柱。但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倫理要素,為實現平等原則與社會倫理的完美貼合,刑法的平等原則需選擇重要“點”,這其中就是社會倫理中的重要元素——身份,因為身份在社會倫理觀念中無處不在且如影隨形;并就平等原則之價值擴展而言,因身份的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之對象性可以被一般社會公眾明確感知,從而有助于刑法平等原則的內涵乃至刑法規范的傳播,亦有利于刑法理念在社會公眾中的根植,進而有助于社會公眾進一步理解和尊崇刑法的規范理念。于此,刑法的追求方可獲得社會公眾的遵從,刑法蘊含的法秩序亦會被社會公眾自覺維護。
當身份這一要素與刑法的平等原則結合之時,便會顯現基于身份之對應性,進而衍生為基于身份的平等——對等。當然,通過對等可以彌補平等原則的倫理缺陷,進而展現倫理軌道中不同角色間的對等形式。舉例來說,虐待罪中被保護的“家庭成員”與施虐的“家庭成員”間即展現出社會倫理概念下刑法平等原則中的對立屬性,例如,兒子之于父親,丈夫之于妻子等。這種社會倫理概念之下,適用對等價值,可以充分體現平等原則中的倫理秩序,進而于具體法條適用時展現犯罪人與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之間社會倫理秩序的地位,實現“婦孺所能曉者”[5]之目標。一言以蔽之,身份的引入能夠引導公眾對刑法的理解與接受,社會中每個角色的地位可以于刑法中完全展現,便于公眾通過平等原則“丈量”倫理的刑法價值,進而滿足公眾對于刑法的期待和對刑罰結果的“企盼”。
刑法對等內涵引入之法理考量
在刑法語境下,似乎基于身份構建的對等與當下刑法的平等觀相去甚遠,但這種對等形式下的平等卻是權利義務的真實展現,此也是康德、黑格爾提倡的“法權人格”的體現,即通過“法權人格”的塑造,將身份價值融入刑法條文的內涵中,表達之實質恰恰是公正。同時通過身份對等價值的構建,可以避免社會公眾對刑法價值以及司法目的、司法結果產生前提性懷疑。具體而言如下:
首先,基于身份的對等恰是刑法實質平等之體現,也是對刑法實質正義內在的拓展。刑法對犯罪的設置遵循著必要性和合理性原則,基于身份對等之考量可以使平等原則在適用之時有效辨別犯罪人身份差異性和社會危害性,進而明確處罰力度,排除不該處罰的行為,以展現刑罰的人道主義和文明性,確保高效實現法益保護之目標,以保障罪刑均衡目標之實現。
其次,經由對等可以表達刑法實質合理性之追求。刑法的實質合理性是指刑法“合乎自然法的公正、平等、美德、善良等實質正義的價值內涵”。[6]刑法平等原則演變為蘊含倫理要素的對等,此是刑法吸收社會公平正義觀念并將社會觀念貫徹司法實踐的過程,基于此而構建的對等理念可使刑法平等原則符合社會公平正義觀念,也有利于限制非必要司法,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實現實體正義之追求。同時可以使刑法平等原則的精神與社會觀念得以緊密結合,規范平等原則在個案適用時符合實質正義內涵,進而限制不確定因素的進入,確保刑法的穩定性和適用的平等性,以最終實現刑法的正義價值。
再次,基于身份之對等是刑法自足性之內在需求。“刑法的自足性就是要求刑法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和運作是自覺自為的。”[7]對于刑法而言,需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把握社會和倫理的脈搏,才可成為貼合公眾價值觀和實際需要的刑法,此應是刑法“本自具足”之品質,刑法的基本原則——平等原則也概莫能外。身份作為社會生活中的普遍存在,每個個體或者群體的身份作為社會有序運行組成之部分應當在刑法中實時體現,此為社會秩序之基石,亦是刑法自足性需感受的元素。
最后,身份是存在于社會群體或者個體中的“集體無意識”,是人類社會發展傳承的結果。用身份對等補足平等原則,可以吻合“集體無意識”以體現群體價值觀,也可以妥善地處理當下刑法與社會發展傳承之間的矛盾。如果在平等原則中拋棄對等,注定刑法必須選擇性地忽視社會倫理,也注定刑法之價值取向必然選擇性地回避社會“倒影”之事實。因此,用對等概念補足平等原則的內涵符合社會的情感因素,刑法于實踐活動時可產生持久的穩定性,社會秩序在刑法活動中可以得到維護,刑法也可以在社會活動中實現穩定。
刑法對等實現之現實措施
欲展現刑法平等原則中的對等,以及展現刑法中的倫理價值和社會價值,故而應作出如下措施:
首先,刑法立法應肯定對等的價值,并通過立法加以展示。當下因為社會倫理要素之欠缺,致使平等原則的社會根基偏于薄弱。依照刑法條文“一律平等”之規定,“人”在立法中僅僅被當作一種被刑法裁量“物”而存在,而非為被刑法評斷之“人”。因而,刑法立法之時就需確定對等的存在,以打破這種評斷桎梏,還原刑法與社會之間的價值互動。同時在立法之時應當肯定并引入身份要素,將平等原則的內核拓展為對等,進而在刑法的立法維度中增加社會要素,即從二維(刑法和人)拓展到刑法、人和社會三維維度。最終在對等的價值評斷體系中實現刑法、人和社會三要素的互動。如此而言,三要素之間可以通過對等這座“橋梁”實現刑法、社會和“人”的三維交互性關系,進而拓展平等原則乃至刑法的價值,最終保障刑法的社會功能得以更好發揮,實現刑法維持、形成和發展國民的人倫文化秩序之狀態。[8]當然,刑法立法時也應當維護平等原則不可觸碰的底線,即違背倫理秩序價值和平等實質的倫理內容當被刑法立法否定,例如,由身份尊卑引申的權利義務不對等。如果刑法立法無法遵守此等底線,那么人際關系和個人道德之中會產生針對刑法的不服從阻力,刑法會失去在公民心中的道德信譽。[9]
其次,應當通過刑事司法展示對等。刑法司法階段應當基于對等需求,考察犯罪人的身份,并基于犯罪人不同的身份給予有差異的刑法評價。這種評價結果并非僅表現在外化的刑期上,也應當包括通過刑法司法展現對犯罪人社會身份之否定。例如,在“殺害尊親屬”行為中,司法結果在展現對犯罪人殺人行為進行評價的同時,也應當對犯罪人“卑親屬”身份給予否定性評價。如此而言,刑法便可以通過對等引入社會倫理責任,將社會心理的負擔引入犯罪后果之中,增強刑法的威懾力,進而拓展刑法懲罰,以及預防效果的邊界。同時在對等要求下,刑法司法判斷應轉向實質價值判斷。因為不同的犯罪身份導致犯罪時的支配能力和犯罪行為危害程度大相徑庭,因而,基于身份的差異考量不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輕重程度也是對等的應然之意。[10]因此,只有在刑事司法中展現對等,社會中的個體才會擴大自己的刑法自覺性和社會自覺性,珍視基于社會身份之義務,刑法尊嚴才會通過身份價值在刑法司法過程中的構建得以維護,社會公眾也可以更好地通過刑事司法結果了解刑法的社會邊界。
最后,刑法應肯定并期待適用對等后的社會效果。盡管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數量和種類的犯罪,[11]但因為對等的存在,刑法對犯罪行為的否定即存有對犯罪人身份之否定,也含有對犯罪人社會價值之否認,刑法的平等原則可以成為考量受損法益與刑事責任間是否對等的標尺,以利于達成價值調和之目標。具體而言,對等可以調和犯罪人與被害人和社會之間的法益博弈關系,即于微觀中通過刑事責任實現對犯罪人身份否定的“量”與受害人受損的“量”之對等,于宏觀中實現重塑犯罪人之社會價值,同時實現對已損社會秩序的合理彌補。最終使犯罪人、被害人和社會皆具備調和的主體性地位,進而通過對等使得犯罪人和受害人的利益在刑事司法的過程中得到完整地保護,實現“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結合”,[12]促使社會秩序之創傷得以愈合。同樣,基于身份的對等強調的是社會倫理中的寬恕,即無論何種身份之間講求的為共存,在身份視角下實現對犯罪行為的合理原諒、實現包容性共存以盡可能恢復已損的社會關系成為身份的實質要求。于此而言,刑法可以期待對等會在社會倫理之中產生寬恕之心并以“責人薄”[13]為寬恕標準。在寬恕之心下,犯罪人與受害人的權益范圍被限縮在合理的范圍內,避免權益范圍無限擴大,以及基于權益的訴求無限延伸。
結語
將刑法的平等發展為對等,看似只是將身份這一要素引入刑法平等原則之中,實質是將社會觀念中身份的“柔性”因素引入刑法價值體系中,“更直接地再現公眾的想法,使公眾深刻感受刑法規范的形成過程,有利于公眾更好地理解和遵守法律,從而促進法律更好實施”。在這一過程中,平等乃至刑法展現了“共識”的凝結和體現,社會公眾的主體性在刑法中得以展現,同時社會倫理中的正義感和包容性可以通過社會公眾的“共識”在平等原則乃至刑法中得以體現,實現犯罪人、受害人、社會間的共存,乃至實現共贏。刑法通過對等價值的構建完善了自由價值要素與秩序價值要素,進而實現自身結構的穩固性。在刑法的穩固性下,社會中每個個體都能意識到身份這一“標簽”的重要性,進而尊重并維護刑法,同時每個個體的價值都能夠通過對等的存在得到成長與發展,從而保證正義的穩步實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刑法修正的理論模型與制度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6ZDA061)
注釋
[1]鐘茂森:《論語講記》,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第198頁。
[2]周光權:《刑法學的向度》,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21頁。
[3]陳偉:《人身危險性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11頁。
[4]袁彬:《刑法的心理學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頁。
[5]梁啟超:《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第60頁。
[6]劉艷紅:《理性主義與實質刑法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7]馬榮春:《刑法公眾認同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8~149頁。
[8]張乃翼、崔紅:《刑法總論講義》,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頁。
[9][美]羅賓遜:《刑法的分配原則——誰應受罰,如何量刑?》,沙麗金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00頁。
[10]袁登明:《行刑社會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5頁。
[11]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29頁。
[12]《四庫家藏》,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213頁。
[13]郭澤強:《刑事立法政策與公眾認同論綱》,《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責 編/肖晗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