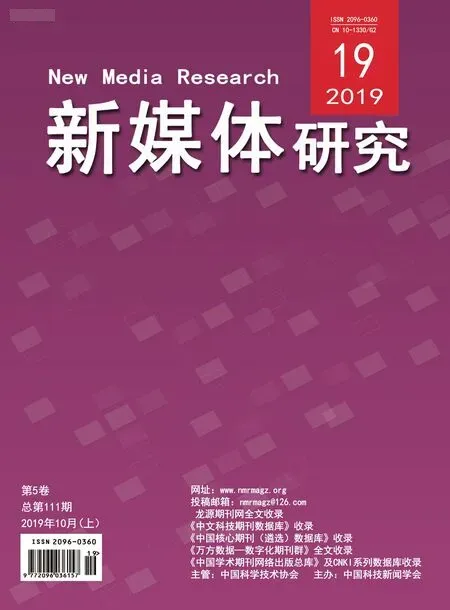新媒體語境下非遺題材紀(jì)錄片的嬗變
閆宏宇 宋雪
摘? 要? 新媒體的發(fā)展不僅極大拓展了非遺題材紀(jì)錄片的傳播渠道,也使其在敘事策略、制作方式、傳播理念上發(fā)生了立體化的嬗變。借力時(shí)代發(fā)展的潮涌,探尋新媒體時(shí)代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影像敘事和話語表達(dá)的新動(dòng)向,以期為非遺題材紀(jì)錄片的精品化創(chuàng)作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傳播提供啟示和思路。
關(guān)鍵詞? 非遺;紀(jì)錄片;新媒體;傳播
中圖分類號(hào)? G2?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 ? 文章編號(hào)? 2096-0360(2019)19-0085-03
依托于數(shù)字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新媒體以傳播交互的即時(shí)化、傳播內(nèi)容的碎片化,接收內(nèi)容的移動(dòng)化深刻影響著媒介話語環(huán)境。以鳳凰視頻、騰訊視頻、優(yōu)酷土豆、愛奇藝網(wǎng)絡(luò)視頻為代表的新媒體紀(jì)錄片播放平臺(tái)悄然改變著過去以電視臺(tái)為首的記錄片播出陣營。從網(wǎng)臺(tái)聯(lián)動(dòng)、到網(wǎng)絡(luò)首播、再到網(wǎng)播平臺(tái)制作,非遺題材紀(jì)錄片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價(jià)值引領(lǐng)下,積極適應(yīng)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的媒介特點(diǎn),主動(dòng)進(jìn)行自我調(diào)適以贏得觀眾,成為傳承與拓展非遺生命力的有效形式,呈現(xiàn)出頗具有時(shí)代風(fēng)格的文化景觀。
1? 故事至上——體量微小,敘事短平
中國非遺題材紀(jì)錄片在制作初期帶有民族志紀(jì)錄片的明顯痕跡,以客觀、完整、準(zhǔn)確地再現(xiàn)非遺項(xiàng)目的產(chǎn)生淵源、歷史傳承、工藝技法為主要目標(biāo),也就是“手持鏡子去映照世界,承載著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表征任務(wù)”,[1]通過影像空間的建立來講述國家、民族、社會(huì)的歷史動(dòng)態(tài),在影像書寫方式上運(yùn)用人類學(xué)的整體性思維,敘事呈現(xiàn)出一種宏大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話語范式。這類早期的紀(jì)錄片自有其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和文獻(xiàn)價(jià)值,但因過分“高冷”在審美消費(fèi)和傳播上呈現(xiàn)劣勢(shì)。
新媒體時(shí)代紀(jì)錄片由電視媒體時(shí)代45分鐘/集的標(biāo)準(zhǔn)片長,下降到一般10分鐘,最長不超過25分鐘。一方面十幾分鐘的輕體量顯然無法支撐起宏大敘事,另一方面新媒體用戶的審美期待也更加傾向于個(gè)人和情感而非歷史與時(shí)代。故此,紀(jì)錄片普遍采用了開門見山講故事、直抒胸臆訴感情的敘事表達(dá)方法。紀(jì)錄片或者從開始就單刀直入地切入時(shí)間、地點(diǎn)人物、和事件等敘事要素,通過解說幫助影像敘事,快速推動(dòng)人物和故事的發(fā)展。《了不起的匠人》中林志玲的解說詞就起到了這個(gè)作用。或者使用非遺傳承人口述直抒胸臆的“真實(shí)電影”模式,以非遺傳承人、手工從藝者個(gè)人的言說和講述將故事漸次展開,珍惜受訪者在講述過程中情感流露,在碎片化的、有限的、流動(dòng)的、多元的主人公口述中,推動(dòng)故事片段的粘合與發(fā)展,“以非遺當(dāng)事人的個(gè)人化視角重在表現(xiàn)‘人的主題”[2],從而作為指認(rèn)“集體記憶”和“大眾記憶”的縮影。《了不起的匠人》之《高考狀元的皮影夢(mèng)》開頭主人公陳雪月就講“我也曾以696分的成績考入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了不起的匠人》之《唐卡世家新勢(shì)力》以“我是旦增平措,我曾經(jīng)相當(dāng)一名當(dāng)代藝術(shù)家,我繼承了父親的唐卡學(xué)校……”開啟。紀(jì)錄片《了不起的匠人》創(chuàng)造了以主持人快速引出——主人公口述開啟——正片的基本結(jié)構(gòu),在總共15分鐘左右的時(shí)長中,通過具體微觀的工藝展示和工匠故事的敘述,滿足人們對(duì)工藝的好奇和人物情感的體會(huì)及共鳴。《了不起的匠人》在優(yōu)酷播放量超過6 500萬次,單集播放量超過300萬次,創(chuàng)造了優(yōu)酷紀(jì)錄片播放量新高。與之類似以非遺和傳統(tǒng)手工藝為題材的紀(jì)錄片《講究》《尋找手藝》《百心百匠》等都將短平敘事作為不二的敘事策略。
2? 視效至美——技術(shù)加持,畫面唯美
2.1? 畫面拍攝唯美化
當(dāng)下,傳播領(lǐng)域正發(fā)生著以新媒體為引領(lǐng)、以圖像消費(fèi)為主導(dǎo)的變革,“整個(gè)社會(huì)文化轉(zhuǎn)向以形象為中心、特別是以影響為中心的感性注意形態(tài)”[3]。新媒體時(shí)代觀眾每天接受海量的視覺信息刺激,感覺閾值有日漸提高之勢(shì),所以想得到觀眾的關(guān)注和認(rèn)可,非遺拍攝每一個(gè)鏡頭都需經(jīng)過精心設(shè)計(jì),從而實(shí)現(xiàn)從容不迫、行云流水般地優(yōu)雅呈現(xiàn)。精致細(xì)膩的視聽畫面,不僅可以實(shí)現(xiàn)對(duì)非遺項(xiàng)目或產(chǎn)品的完美呈現(xiàn),更主要的是精致的視聽形象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觀眾,震撼他們的審美感知、滿足他們的審美體驗(yàn),進(jìn)而達(dá)到良好的傳播效果。很多非遺項(xiàng)目、尤其是傳統(tǒng)美術(shù)類非遺,如剪紙、皮影、泥面塑、雕刻、糖畫、木版年畫等本身就具有唯美而奇觀化的視像效果,選用適合其作品類型的景別、角度、鏡頭運(yùn)動(dòng)方式,善于捕捉光影變化,使其得以藝術(shù)化唯美化的表達(dá)和呈現(xiàn)。
2.2? 情景再現(xiàn)藝術(shù)化
“藝術(shù)真實(shí)是一種實(shí)體存在,是一種主觀選擇,也是一種文本建構(gòu)”[4]。《指尖上的傳承》系列之《泥人張》一集中,在講述已故泥塑大師張明山的成長和習(xí)藝故事時(shí),使用了搬演式情景再現(xiàn)的方法,用演員扮演年輕時(shí)代的張明山,著古裝,在古城的背景中觀察、練習(xí)、捏塑。在《蘇繡》一集中,在敘述蘇繡主人公鄒英姿小時(shí)候的所思所做時(shí)也使用了同樣的方法,以江南院落中的小女孩扮演主人公。紀(jì)錄片是基于現(xiàn)在時(shí)態(tài)展開的影像表述,但非遺題材的紀(jì)錄片經(jīng)常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已故的人和過往的事,比如介紹泥人張就不可能略過泥人張世家名望集大成者——張明山,因其生活的年代又不可能留有影像和圖片文獻(xiàn),僅靠解說也難以彌補(bǔ)畫面信息的缺失,搬演式情景再現(xiàn)就顯得非常實(shí)用和適用了。搬演式情景再現(xiàn)一方面能夠變靜默的歷史素材為逼真的現(xiàn)場(chǎng)氛圍,以戲劇表現(xiàn)之美彌合重要影像不足所造成的時(shí)空斷點(diǎn);另一方面也與主人公的口述呼應(yīng)成為層進(jìn)式的故事結(jié)構(gòu),增加故事化敘事的張力;此外,情景再現(xiàn)在不斷流變和適應(yīng)的過程中,或可形成非遺題材紀(jì)錄片獨(dú)特的美學(xué)藝術(shù)因素,且推動(dòng)非遺題材紀(jì)錄片文化面貌的不斷創(chuàng)新。
2.3? 虛擬現(xiàn)實(shí)仿真化
數(shù)字動(dòng)畫、虛擬現(xiàn)實(shí)技術(shù)應(yīng)用于紀(jì)錄片已不足為奇,包括三維場(chǎng)景的仿真和還原、3D制作與實(shí)景拍攝相結(jié)合、二維及三維動(dòng)畫的演繹等。紀(jì)錄影片《超碼的我》(2004),以實(shí)拍導(dǎo)演自己一個(gè)月只吃麥當(dāng)勞食品的經(jīng)歷為主線,其中穿插了大量動(dòng)畫片段,用以呈現(xiàn)各種關(guān)于飲食健康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和相關(guān)科學(xué)原理。系列紀(jì)錄片《故宮》(第一集《肇建紫禁城》)中,編導(dǎo)運(yùn)用虛擬影像技術(shù)還原展示了與今故宮不同的明朝紫禁城的空間布局和建筑式樣,同時(shí)也有采用3D制作與實(shí)景拍攝相結(jié)合的方式。
在非遺題材的紀(jì)錄片中,數(shù)字技術(shù)的恰當(dāng)應(yīng)用則能營造出獨(dú)特的效果,幻化出豐富的文化意蘊(yùn)。《昆曲六百年》運(yùn)用數(shù)字動(dòng)畫技術(shù),將古代經(jīng)典繪畫作品中的人物用動(dòng)畫技術(shù)還原活化,并創(chuàng)作出大量水墨風(fēng)格的自然山水場(chǎng)景,為觀眾營造出一個(gè)視覺和心理上的夢(mèng)境江南,以一種審美體驗(yàn)的方式接通觀眾對(duì)昆山腔曲詞典雅、行腔婉轉(zhuǎn)、表演細(xì)膩美學(xué)認(rèn)知,使單純枯燥知識(shí)介紹變得富有美感易于理解。《指尖上的傳承》之《泥人張》中徐悲鴻對(duì)泥人張作品的評(píng)價(jià)的文獻(xiàn)資料“其比例之精確、骨骼之肯定,與其傳神之微妙,不足多也”,以文字動(dòng)畫特效的方式著落于花黃底紅豎格的紙簽之上,一如歷史之筆的書寫,嚴(yán)謹(jǐn)而莊重、唯美且真實(shí)。而在片尾,泥人張作品展架上的兩個(gè)男童泥塑作品經(jīng)由三維動(dòng)畫師的制作,成為兩個(gè)歡笑著奔跑著放風(fēng)箏的活靈活現(xiàn)的男孩,以動(dòng)畫這種種獨(dú)特的視覺語言深入演繹著對(duì)傳統(tǒng)造型藝術(shù)“惟妙惟肖”的最高褒獎(jiǎng)。
3? 傳播制勝——跨界融合,場(chǎng)域開放
傳統(tǒng)紀(jì)錄片是一個(gè)封閉的場(chǎng)域,強(qiáng)調(diào)客觀記錄。新媒體時(shí)代促使傳統(tǒng)封閉的結(jié)構(gòu)被徹底打破、非遺題材紀(jì)錄片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和融合,開創(chuàng)了新媒體紀(jì)錄片的嶄新形態(tài)。在這種形態(tài)中,“視頻不再是唯一的敘事主體,原本的線性編輯被打破,敘事更加靈活、更富有吸引力”[5]。
3.1? 由娛樂體驗(yàn)到文化認(rèn)同
這種新的形態(tài)體系以跨界主持人和嘉賓的選用做為傳播制勝的法寶,以名人效應(yīng)吸引年輕觀眾,嘗試介由“娛樂體驗(yàn)”達(dá)到“文化認(rèn)同”。《百心百匠》邀請(qǐng)業(yè)界名人精英探訪民間匠人,李亞鵬、李泉、孫楠、柯藍(lán)、李艾、許亞軍、吳曉波、馬艷麗、喻恩泰等一對(duì)一向匠人拜師,學(xué)習(xí)蔡侯紙、昌黎皮影、宮毯、唐卡古琴、哈薩克馴鷹、唐卡、武夷山巖茶等傳統(tǒng)技藝,片子通過記錄名人深度體驗(yàn)傳統(tǒng)手工藝項(xiàng)目的故事,實(shí)錄非遺項(xiàng)目的主要工藝和發(fā)展現(xiàn)狀,在娛樂偶像、時(shí)尚明星與傳承上百年、數(shù)百年的傳統(tǒng)技藝的跨界碰撞中,彰顯非遺的獨(dú)特魅力,揭示傳承匠心的時(shí)代價(jià)值。《了不起的匠人》選用林志玲作為主持人并擔(dān)綱解說,在極富工藝感場(chǎng)景的演播室里,用不超過30秒的簡練語言引出匠人及所從事的工藝領(lǐng)域,隨后在片中作為解說與主人公第一人稱的口述相互結(jié)構(gòu),設(shè)置懸念、迅速推動(dòng)故事的發(fā)展。2017年12月7日出版的《人民日?qǐng)?bào)》刊發(fā)時(shí)評(píng),“以現(xiàn)代的視角、用很‘燃的方式,致力于讓傳統(tǒng)文化‘活起來”[6]。
3.2? 由線性傳播到交互傳播
新媒體平臺(tái)為紀(jì)錄片帶來了全新的傳播模式。AIDMA模式是美國廣告學(xué)家E·S·劉易斯在傳統(tǒng)媒體時(shí)代提出的營銷法則,即注意(Attention)—興趣(Interest)—欲望(Desire)—記憶(Memory)—行動(dòng)(Action)。日本電通公司針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與無線應(yīng)用時(shí)代消費(fèi)者行為分析將模型發(fā)展為AISAS,即Attention(注意)—Interest(興趣)—Search(搜集)—Action(行動(dòng))—Share(分享),后者雖然添加了互聯(lián)網(wǎng)行為的兩個(gè)典型模式:搜索和分享,但依然視圖使用線性的思維厘清消費(fèi)者的接受過程。新媒體時(shí)代秉承“媒介即訊息”、并且升級(jí)為信源即受眾,傳播形成一張具有若干信源點(diǎn)的無限發(fā)散的大網(wǎng),關(guān)鍵點(diǎn)之間的鏈接則靠共同的文化認(rèn)同。《百心百匠》的冠名合作伙伴是網(wǎng)游《王者榮耀》,二者以傳統(tǒng)文化作為基本契合點(diǎn),提煉出“王者匠心、榮耀傳承”的立體化傳播核心理念。《王者榮耀》數(shù)以億計(jì)的游戲用戶基數(shù)及專家顧問團(tuán)等專業(yè)力量,必然為《百心百匠》帶來良好的傳播價(jià)值,更重要的是將《王者榮耀》培養(yǎng)起的網(wǎng)絡(luò)新生代代入到以非遺為代表的傳統(tǒng)手工藝中。《了不起的匠人》在片子結(jié)束時(shí)可直接通過鏈接購買牦牛絨圍巾、唐卡、皮影等相關(guān)的傳統(tǒng)手工藝品,為觀眾提供由文化訊息到原創(chuàng)手工藝產(chǎn)品購買的便捷渠道,也為傳統(tǒng)手工藝贏得了更加廣泛的社會(huì)體認(rèn)和更加廣闊的市場(chǎng)空間。
3.3? 由始自非遺到不拘非遺
2015年7月,非遺題材紀(jì)錄片《指尖上的傳承》通過新媒體全網(wǎng)首播,正式開啟了非遺題材紀(jì)錄片的新媒體征途,《指尖上的傳承》拍攝對(duì)象主要是省級(jí)以上非遺項(xiàng)目名錄及代表性傳承人。時(shí)至2016年底開播的《了不起的匠人》,定位于亞洲首部治愈系匠心微紀(jì)錄片,其拍攝對(duì)象已不拘囿于一定級(jí)別的非遺名錄,地域范圍也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中國內(nèi)地,在一個(gè)更廣闊的傳統(tǒng)手藝領(lǐng)域里挖掘故事、致敬匠心。這并非對(duì)非遺的用心不專,而是通過回避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或年事已高、身體狀況欠佳,或不善言談、不適合上鏡,抑或一些項(xiàng)目拍攝周期較長等主客觀因素,將傳統(tǒng)手藝以一種最適合新媒體言說的方式恰到好處的呈現(xiàn)出來,在全社會(huì)形成一種熱愛傳統(tǒng)、尊重手藝、崇尚匠心的文化癥候,身處其中的非遺自然受益其中。
4? 結(jié)束語
非遺作為根植中華民族土壤、凝聚傳統(tǒng)文化記憶、彰顯匠心精神的活態(tài)文化,它是民族文化與心理結(jié)構(gòu)中“最有回憶性或進(jìn)一步交流意義”[7],是民族影像的文化識(shí)別碼。它標(biāo)注了影像獨(dú)特的風(fēng)土人情、審美趨向,凝聚成民族文化的同理心,接通、延續(xù)了族群記憶。新媒體時(shí)代賦予了非遺題材紀(jì)錄片嶄新的文化品格,這就要求從業(yè)者不僅要對(duì)非遺項(xiàng)目、作品、傳承人及相關(guān)的文化事象等影像進(jìn)行選擇、概括與提煉,用富于影像邏輯的視聽語言進(jìn)行重新編碼,還要深諳紀(jì)錄片新媒體傳播之道,建構(gòu)起具有獨(dú)立審美價(jià)值和傳播價(jià)值的視像文本。
參考文獻(xiàn)
[1]保羅,亨利.敘事:民族志紀(jì)錄片深藏的秘密[J].莊莊,徐菡,編譯.思想戰(zhàn)線,2013(2).
[2]張芊芊.“口述歷史”的電視化呈現(xiàn)[J].電視研究,2010(1).
[3]周憲.圖、身體、意識(shí)形態(tài),文化研究(第3輯)[M].天津: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2.
[4]劉如文.紀(jì)錄本性·藝術(shù)真實(shí)·藝術(shù)表達(dá)——紀(jì)錄片基本理論問題的新思考[J].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藝術(shù)版,2006(3).
[5]王之月,俞哲旻,彭蘭.新媒體背景下的網(wǎng)絡(luò)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以澳大利亞SBS廣播公司的紀(jì)錄片節(jié)目為例[J].新聞界,2015(15):51-55.
[6]“一眼千年”,與文化長談[N].人民日?qǐng)?bào),2017-12-07.
[7]艾柯.電影符碼的分節(jié),外國電影理論文選[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6: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