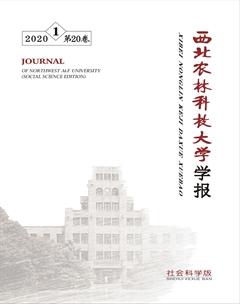精準扶貧主體的行動邏輯
摘?要:扶貧資源在從上到下的傳遞過程中極易出現“瞄不準”和“瞄不久”現象:村民在扶貧實踐中處于被動接受地位,導致扶貧資源在傳遞過程中層層偏離;縣鄉政府追求自身政績和經濟效益最大化,依托資源優勢影響扶貧信息及資源傳遞;村干部為完善鄉村治理利用親緣關系影響貧困戶識別結果。因此,探索長效脫貧機制激發貧困者的內生發展能力;優化貧困者在資源分配過程中位置;轉變基層政府在扶貧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為扶貧實踐工作中的協作者;健全多元扶貧監督機制及扶貧績效評價體系成為了新時期推進精準扶貧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精準扶貧;行動策略;資源傳遞;瞄不準;瞄不久
中圖分類號:C913.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0)01-0019-07
收稿日期:2019-04-09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0.01.03
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專項(18JK0037);寶雞文理學院校級重點項目(ZK14048)
作者簡介:柳晨(1987-),女,寶雞文理學院經管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經濟。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扶貧工作不斷有序地開展,貧困狀況有效改善,但是扶貧工作難度逐漸加大,貧困問題逐漸呈現出新現象:(1)貧困人口多分布在農村地區,并呈現出“插花式特征”。農村貧困戶及貧困人口分散在非貧困地區,但按照現行的貧困標準,他們的收入水平處在貧困標準線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告》顯示,截止2018年,按照每人每年2 300元的貧困標準計算,我國還有1 660萬貧困人口。(2)農村貧困問題異化特征明顯。農村貧困問題由改革開放初期大規模貧困逐漸轉變為少數弱勢群體的多維貧困問題。(3)隨著扶貧工作的不斷深入推進,投入的大量扶貧資源呈現邊際效應遞減趨勢。扶貧資源利用效率降低,扶貧效果不明顯,真正的窮人以及貧困村很難獲得國家扶貧資源,甚至出現越扶越貧和返貧現象[1]。總之,在如今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中,扶貧資源的傳遞及瞄準等問題亟待解決。
雖然我國扶貧工作中,扶貧瞄準對象不斷調整和聚焦,從區域到縣到村落再精準到貧困戶,試圖將有限的扶貧資源更加精準地傳遞到貧困人口中去,但是在基層的扶貧實踐中,扶貧資源的分配卻經常有所“變通”[2],基層干部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和自身工作需要,在執行上級政策時進行變通,這使得扶貧政策初衷與執行結果背道而馳的現象常常發生,有限的扶貧資源很難傳遞分配到真正需要的對象手中,扶貧資源并沒有因為扶貧對象的不斷調整和細化而瞄準。
要分析扶貧資源瞄不準的問題,必須深入到國家的扶貧資源從上級政府到基層社會傳遞和分配過程進行分析,是怎樣的分配格局使得有的村莊、農戶能夠優先得到大量扶貧資源,而一些貧困村、貧困人口卻得不到或者得到很少的扶貧資源?扶貧資源是具有社會公益性、福利性的國家幫扶投入要素,扶貧資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導致了其分配及獲取具有一定的競爭性,不論對于各級政府還是貧困戶本身來說,想要得到扶貧資源需要憑借自身的能力去爭取。新時期國家賦予了縣級政府較大自主權,將扶貧資源分配權力下放至縣級政府,因此縣級政府在扶貧資源投向哪些鄉鎮地區起著主導作用,有著絕對的話語權,是扶貧實踐中重要的行動者。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在扶貧資源分配過程中也能發揮一定的主觀能動作用,利用自身資本積極運作,爭取更多的扶貧資源。因此,本研究著重分析扶貧資源傳遞和分配過程中縣級政府、鄉鎮政府、村莊和貧困戶各行為主體的行動策略如何對扶貧資源的分配格局產生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精準扶貧的理論研究
黃承偉等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扶貧治理體系變遷過程的分析,提出精準扶貧是提高扶貧開發效果的必然路徑選擇;我國扶貧開發目標呈現多元化特點,扶貧治理體系圍繞片區精準和個體精準建立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扶貧戰略格局[3]。左停等認為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在技術層面的靶向是扶貧資源瞄準目標偏離和精英捕獲問題,從理論層面對精準扶貧的理解和反思可以從中央-地方關系、社會控制理論以及“社會成本”等視角進行[4]。鄭瑞強等通過對精準扶貧生成邏輯進行分析,提出精準扶貧是新時期我國扶貧開發的戰略導向,是對接經濟新常態要求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和發展質量提升的政策回應[5]。
(二)扶貧資源瞄準偏離的研究
汪三貴等認為基層政府難以獲取農戶家庭收入的真實信息,使得村莊內基層民主評議成為貧困戶識別的主要方法,但識別的結果往往不能反映村民的真實貧困程度,導致精準識別偏離目標[6]。李博等認為扶貧資源瞄準偏離的主要原因是精準扶貧過程中國家邏輯與鄉土社會的矛盾,農村復雜的關系網絡、不規則的鄉土社會以及農村社會“不患多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不健全的基層民主都阻礙著扶貧工作目標靶向的精準度,將國家的貧困識別標準與農村社會文化相融合是精準扶貧實踐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7]。 邢成舉認為扶貧工作與鄉村治理聯系密切,扶貧工作要與鄉村社會的變遷相互對接。村莊內的社會關系結構、權力結構、社會分化和信息傳遞、精英俘獲、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體行動的缺乏等都是扶貧工作目標發生偏離的重要原因[8]。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研究,精準扶貧政策的提出與實施是我國扶貧歷程中的必然選擇,代表了我國扶貧的最新理念。近些年,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精準扶貧和扶貧資源的瞄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針對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路徑提出了政策建議。本研究深入M縣A鎮進行調研,分別對縣級、鄉級政府、村干部及農戶的行動邏輯進行考察,試圖探究扶貧資源在從上到下的傳遞過程中逐層偏離的原因。
三、扶貧資源分配中基層扶貧實踐者的行動邏輯
筆者在2018年3月至2018年9月對M縣A鎮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M縣,位于B市東北部,M縣下轄7個鎮,66個行政村,410個村民小組,常住總人口922萬人,人均生產總值77 268元。M縣不僅是六盤山連片特困地區縣,也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A鎮經濟發展底子薄弱,鄉鎮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土地貧瘠,難以發展多樣化產業,產業結構較為單一,貧困程度深,脫貧致富腳步緩慢,也一直是縣政府扶貧工作開展的重要地區。2016年B市扶貧辦調研結果顯示,導致M縣貧困最主要的三大原因分別是因病致貧,缺少資金和缺乏技術與勞力。
(一)縣級政府扶貧資源分配的精英俘獲
1.制定地方性政策措施走過場。縣級政府在扶貧資源的分配過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根據上級扶貧政策制定細化的地方發展規劃或相關扶貧政策和措施[9]。但在這次調研過程中,筆者發現縣級政府在決策時缺乏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深入調研,大多情況下是通過相關部門或單位內部討論征求意見等形式形成最終決策,這種程序化征求意見方式往往流于形式“走走過場”,對于具體政策的制定并不會產生實際影響。調研期間,筆者有幸參加過一次M縣扶貧工作座談會,會議主題是征求鄉鎮政府、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對《M縣產業扶貧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主管扶貧工作的縣長、縣扶貧辦工作人員、各鄉鎮領導和扶貧工作負責人、各村干部以及部分村民代表參加了此次座談會。代表們分別從地方實際情況出發,對實施方案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議。鄉鎮扶貧工作負責人大多提出了工作具體開展過程所遇到的問題,如:上級扶貧政策大多是原則性要求,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政策模糊、不夠具體,可操作性不強;扶貧工作時間緊、任務重、工作量大,但工作人員少,“5+2、白加黑”也忙不過來,希望増加扶貧人員編制。村干部在會上反映了一些更加具體的問題,如貧困農戶想要發展產業卻資金不足,扶貧項目和扶助資金少,小額貸款難以辦理,村民沒有承擔風險的能力等問題。會上縣扶貧辦針對代表們提出的問題只是進行了簡單答復,并沒有給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措施,在會后制定的《實施方案》中也沒有涉及座談會收集的意見,只是結合了M縣基本情況后照抄照搬了上級實施方案中的指導意見。會后,筆者與縣扶貧辦相關工作人員交談中得知他們在制定政策措施時一般是上級文件怎么說,他們就怎么寫,一是因為工作任務繁重,沒有精力和時間深入調研并制定政策;二是縣扶貧辦工作人員在制定政策措施的能力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擔心自己制定的政策跑偏,被追究責任,常年來的習慣性工作模式就是照搬上級方案。由此可見,縣級政府雖然以座談會等形式調研基層對于扶貧政策措施的意見,但卻流于形式,座談會中談到的問題得不到相關部門的關注,也沒有為基層扶貧實踐者解決實際問題。
2.結對幫扶資源分配不公平。在扶貧工作實踐中,由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結對幫扶駐村扶貧是一種普遍制度,這種制度可以充分調動各部門或單位資源,也是地方政府和鄉村高度認可的幫扶方式。幫扶單位為貧困村帶來扶貧資金和項目的同時,幫扶單位往往通過自身信息優勢和關系網絡為村莊帶來更為廣泛的資源。
M縣,現有幫扶工作隊17個,其中省級工作隊2個(一個是省屬國有大型企業,一個是省屬高校),市級工作隊6個,均為市級部門,縣級工作隊9個,為縣級部門、事業單位,每個工作隊都有一名縣級領導聯系包抓對應的幫扶村。
調研中筆者發現,并不是所有幫扶單位都能為幫扶村帶來“可觀”的項目資金。例如,由省屬大型國有企業X集團幫扶的丈村,僅2017年就直接收到幫扶單位扶貧專項資金40余萬元;由市財政局幫扶的Q村,也收到了美麗鄉村建設專項資金、人畜飲水改造工程資金等176萬元;而由縣計生服務站幫扶的泉村,并沒有獲得“真金白銀”的“可觀收入”,幫扶單位僅送來了職工捐款2 350元和兩次義務診療活動。由此看來,幫扶單位的級別高低、經濟實力和權利大小是能否為幫扶村帶來“可觀收入”的關鍵所在。因此,那些級別高、經濟實力強、權力大的單位被鄉村視為“香餑餑”。
在筆者對M縣扶貧辦主任的訪談中,扶貧辦主任坦言:“在進行幫扶資源分配中,一是將優勢資源分配給縣主要領導聯系包抓的村莊,這些幫扶單位資金支持力度大,村莊工作容易干出成績和亮點,這樣主要領導工作有面子,也是對扶貧辦工作的肯定;二是將優勢資源分配給工作基礎好、工作積極性強、容易出效益和成果的村莊;三是出于人情將優勢資源分配給和本部門聯系多,私人關系好的村莊,也是對村莊和人情的一種‘照顧。那些經濟基礎不好,人際關系一般的村莊往往被分配到‘清水衙門的幫扶之下。”由此可見,縣級政府在扶貧資源分配中出于自身政績、人際關系等因素的考慮,并不能實現資源的均衡配置,反而造成了精英俘獲。
(二)鄉鎮政府的選擇性信息傳遞
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府要將有限的扶貧資源在各村莊之間進行分配,是扶貧實踐中重要的參與者,在行動過程中有著自身的行動邏輯。
現行扶貧項目和資源分配有兩種模式:一是根據精準識別結果扶貧資金直接分配入戶,這種分配方式基本不需要鄉鎮政府介入,但資金數量相對較少;而另一種則是以扶貧項目下發的形式分配扶貧資源,由鄉鎮向各行政村分配扶貧項目,對村莊的產業發展給予資金支持[10]。但鄉鎮政府在分配扶貧項目時,往往利用自身信息優勢,根據各村莊的經濟基礎和產業發展情況,有選擇性地進行信息傳遞,僅僅將項目信息有針對性地傳遞給能夠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和扶貧成果最大化的村莊。
雖然國家對于產業扶貧項目的操作流程都有明文規定,必須公開透明,但鄉鎮政府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卻有所“變通”。在訪談中A鎮扶貧辦主任對于這種“變通”行為也很無奈:“如果把扶貧項目信息公開,每個村都來申請,一方面加大了我們的工作難度,另一方面資金不給誰都會得罪人。對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分配指標的時候首先考慮哪個村需要相關建設,把項目放在真正需要的村莊;而產業扶持項目的分配首先考慮村莊是否具有產業發展基礎和前期投入,選擇最合適的村莊進行項目投入。桑村原來種植烤煙,就把千畝示范基地項目指標下發給桑村,支持桑村的烤煙產業發展。如果沒有產業基礎,即使投入幾萬塊錢也看不到效果,會影響鄉鎮年度考核的成績,上級部門來檢查驗收我們也沒法交代。”
由此可見,鄉鎮政府在分配扶貧資源時是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的。一方面希望投入的扶貧資源能夠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為村民帶來更高的收入,形成產業特色;另一方面鄉鎮政府在分配扶貧資源時考慮自身發展需要和政績等因素,為了打造工作亮點、完成脫貧任務,將扶貧資金投向“非貧困村”,嚴重影響了扶貧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公共性,違背了精準扶貧政策的初衷。
(三)村莊扶貧資源分配瞄不準
1.村干部借助關系網絡獲取扶貧信息。村干部在扶貧實踐中作為一個積極的行動者,為了爭取更多的扶貧資源也具有自身的行動策略。在調查中筆者發現,為了從上級部門獲取扶貧資源,村干部會積極的運用人際關系資本占據有利條件。信息不對稱是影響村莊獲取扶貧資源的一個嚴重障礙,相關信息大多時候也是由一些非正式渠道傳遞獲得的,尤其是一些具有競爭性的惠民項目,申請后獲批的幾率非常高,獲取項目信息就意味著獲得扶貧資源,而能否通過非正式渠道獲取信息就取決于村干部利用自身人際關系資本進行運作的能力,村干部維護相關人際關系的能力直接影響著扶貧資源分配的格局。
2.親緣關系影響貧困戶識別結果。精準扶貧就是強調將識別單位細化,精準到戶地識別貧困人口并具體分析貧困戶的致貧原因進行扶貧資源傳遞。因此,識別是否精準是精準扶貧政策實施過程中關鍵的一步。
A鎮政府為了平衡各村的關系,按照M縣的貧困發生率在各行政村之間分配貧困戶指標,對貧困人口建檔立卡。但各村的經濟基礎不同導致了部分行政村的實際貧困人口和上級分配的指標不一致。在一些相對富裕的村莊,為了完成貧困戶指標,非貧困戶進入了貧困戶系統建檔立卡;而在一些貧困程度高的村莊,部分貧困村民由于指標少無法進入貧困戶系統得不到國家的扶貧資源。2017年泉村按照23%的貧困發生率共分配到88戶貧困指標,在訪談過程中村干部表示很為難,村支書告訴筆者:“貧困指標有限,但人人都想爭取,經濟條件懸殊不大的村民如果識別結果不同,會來村里鬧事,有些甚至還去鄉鎮或者縣上鬧事,每次上級領導來檢查都提心吊膽,而且還會影響干群關系。去年在評選的時候,一位老人子女在外務工條件較好,但不贍養老人,老人經濟條件拮據,村委會鑒于這種情況,將老人納入貧困戶范圍。但有條件相當的村民為此鬧事,對于這種情況,我們只能安撫情緒,告知指標有限,承諾明年納入貧困戶范圍。”
貧困戶識別的一般程序是:宣傳告知信息摸底農戶申請入戶核實村民民主評議名單公示、鄉鎮政府審核縣脫貧攻堅小組入戶調查、審核市脫貧攻堅小組抽樣核查省脫貧攻堅小組隨機抽查等[11]。(1)識別程序的確定。在各村莊具體實踐過程中,村內貧困戶的識別程序根據各村人員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方式。在調研中,Q村是將貧困指標按照各小組的人數分配到組,由小組內部商議并確定本村組的貧困戶名單;泉村和丈村沒有將權力下放,由村干部對全村貧困狀況摸底后進行排隊,選擇貧困戶;口村、桑村和石村由村民代表會議和黨員代表會議討論決定。(2)上級政府審核。在村委會將貧困戶名單提交后,鄉鎮政府、縣扶貧攻堅小組扶貧工作人員會和村委逐戶排查,進行審核。有村民告訴筆者,2017年在Q村的排查審核過程中,一農戶家中有小汽車,還住著新蓋的二層樓,審核小組工作人員了解到此戶是村支書的侄子,在投票前給每戶村民打電話拉選票,鑒于他的特殊身份村民都不愿得罪村領導才給他投票,審核小組當場對該戶進行除名。桑村已經去世的前村支書為村里做出了不小的貢獻,聲望較高,留下患病的妻子,雖然子女條件都不錯,但村干部提議將前村支書列為貧困戶,也算是村上對老領導的照顧。在評議會上大家一致通過,審核小組在排查時也沒有提出異議,這種“人情貧困戶”在識別過程中并不是偶然現象。
由此看出,不論是以何種方式確定貧困戶,村干部掌握著較大的權利,一方面完成上級政府分配的扶貧任務,另一方面平衡各方關系。村干部的行為在鄉村這個關系錯綜復雜的親緣社會中難免有失公正,無形中增加了扶貧資源精準傳遞的風險。
(四)鄉村內部扶貧資源分配的親富性
在扶貧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參與者也是最終受益者都是農戶。農戶普遍認為“這些錢是國家的,不拿白不拿”,也通過和村干部進行“關系聯絡”“攀親戚”“哭窮”“說情”等行為爭取被納入貧困人口范圍,提高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
納入貧困戶范圍建檔立卡只是扶貧工作的第一步,而扶貧資源是否能夠傳遞到這些貧困戶手中,有多少扶貧資源能夠到達貧困戶還需要到具體的扶貧實踐中來看。目前M縣針對貧困戶的扶貧資源有很多,如危房改造項目、移民搬遷項目、產業發展項目、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在筆者進行調研的A鎮,針對貧困戶主要有兩類幫扶措施:一類是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發放,一類是產業項目幫扶。產業幫扶模式的運行方式為“合作社+互助組+農戶”,鎮村成立專業合作社,以村為單位,對有勞動能力和發展產業意愿一致、居住較近的貧困戶,每十戶左右建立一個互助組,“十戶一體”組織帶領貧困戶發展特色產業,實行集約化經營[12]。上級政府支持Q村發展肉羊養殖產業,由上級政府牽線引進養殖企業統一建設標準化養殖場,由合作社統一管理,企業和農戶按2:8的入股比例,每戶入股3萬元。經過調研筆者發現,入股專業合作社的大部分為鄉村的村干部或者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農戶,也就是鄉村中的精英階層,他們具有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經濟實力,對政府的政策敏感度高,對政府提出的產業扶貧政策積極響應。但是,貧困戶確大多采取消極“反抗”的行動策略,并沒有積極地參與到發展產業的行列中。一方面,入股需要交納3萬元的資金,真正的貧困戶是很難一次性拿出3萬元;另一方面,發展產業具有一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貧困村民也不具備相應的抗風險能力。
在扶貧實踐過程中,扶貧資源也具有親富性,鄉村中的精英憑借自己的經濟和社會資源更容易獲取扶貧資源,參與到扶貧實踐中,而真正的貧困戶確往往因為無法在項目前期投入,無法支付獲取扶貧資源所必須的成本而失去本該獲取的扶貧資源。
四、精準扶貧資源瞄不準的深層次分析
國家扶貧制度設置的初衷:(1)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對社會財富再分配,實現全國各地區、全體人民的均衡發展,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2)扶貧資源作為一種社會公共資源,在分配和使用中應該更加注重公平性、公開性,更加具有傾向性,體現社會公平正義[13];(3)國家將扶貧項目和資金投入貧困地區,提高村莊公共基礎設施水平和公共物品供給質量,更重要的是通過技術和知識的投入,提高貧困群體的生產、生活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自己動手從根源解決貧困問題。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國家的政策初衷并沒有實現,各基層政府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行為目標弱化了扶貧政策的公共性,使得鄉村內部的貧富差距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有加劇的趨勢,加劇了農村內部不平等的現象,扶貧資源呈現邊際效益遞減現象,非目標群體大量獲得扶貧資源,増加了貧困群體脫貧致富的難度,與國家政策設定的初衷背道而馳。
國家扶貧資源層層傳遞的過程并非是一個簡單的政策執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級政府、村干部和農戶為了自身利益爭奪扶貧資源展開互動和博弈,每個行動者利用自身關系、經濟等資本選擇的行動策略都會影響扶貧資源的分配和傳遞,在各個相關利益的行動者行為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最終的扶貧資源分配格局[14]。在扶貧資源分配過程中,縣、鄉鎮政府作為科層內部行為主體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是上級政策的執行者又是基層扶貧資源的分配實踐者,一方面要根據上級政府的扶貧文件制定更加具體化的扶貧政策,另一方面對基層扶貧實踐具有絕對的決策權和支配權,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根據各地的差異性采取變通的行為。首先,扶貧工作是中央下達的一項政治任務,扶貧任務的完成情況直接和地方政府的政績以及相關負責人員的政治仕途掛鉤,能否出色完成扶貧任務,直接影響官員的政績,因此,在基層的扶貧實踐中,政府官員通過打造亮點工程、建設示范村莊的方式提升政績。其次,每一個扶貧工作相關人員都是“理性經濟人”,在扶貧具體實踐過程中會摻雜個人意志,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弱化上級政策目標。村莊和農戶作為扶貧實踐的最終受益者是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行為目標,被評為貧困村或被識別為貧困戶都會得到國家相關的政策傾斜和扶貧資金補助,因此,村干部在扶貧實踐過程中運用人際關系資本爭取扶貧資源,去上級主管部門跑項目、拉關系,不僅利于村莊的經濟和產業發展,改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也能夠提升自身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政治威信。而貧困農戶由于缺乏經濟和社會資本,在基層扶貧工作實施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難以具有話語權為自己爭取利益[15]。
扶貧資源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使得在分配過程各鄉級政府間、不同的村莊間及同村農戶之間形成競爭關系。同一層面的不同行動者會利用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和優勢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影響著扶貧資源的分配格局和分配結果。因此,扶貧政策在從上到下的執行過程中層層偏離導致 “扶富不扶貧” 扶貧資源無法瞄準和無法長效發揮作用的現象發生。
五、政策啟示
(一)建立長效脫貧機制激發貧困戶內生發展能力
扶貧不意味著單純的給貧困戶資金,更為重要的是從源頭治理貧困,從根源上解決扶貧資源瞄不準、瞄不久的問題,激發和提升貧困戶內生發展能力。在調研中筆者發現,貧困人口“等、靠、要”思想嚴重,大部分貧困戶都在等著政府今年又有什么扶貧措施,能給多少錢,缺乏主動脫貧的意識,沒有充分利用政府給予的扶貧資金和資源。因此在扶貧工作中要引導貧困戶將“要我干”的意識轉變為“我要干”意識,建立長效脫貧機制,鼓勵并帶動貧困群眾主動參與扶貧工作。探索“科研機構+政府+農戶”聯合行動“三位一體”的科技脫貧道路,由科研機構研發農產品新品種,派專業技術人員對貧困戶指導種植,政府給予相應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為貧困戶打造發展平臺,加強貧困農戶的自身素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讓他們最大限度地去使用扶貧資源,用自己的雙手脫貧摘帽。
(二)優化貧困者在資源分配過程中位置
由于不同村莊在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差異較大,關系網絡也各有不同,并且村莊內部各農戶在收入水平、人際關系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結構性差異,使得真正的貧困群體在扶貧資源配置過程中處于不利的末端位置,難以獲取與之匹配的資源。要讓貧困者獲得充分的扶貧資源并有效的利用,就要讓貧困群體在扶貧資源分配中處于優先位置。
(三)轉變基層政府在扶貧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扶貧資源配置過程中,貧困群體作為精準扶貧政策的最終受益者應當成為扶貧實踐的主導者、執行者,擁有一定的話語權,而基層政府應該轉變自身的主導者角色,切身從貧困者利益出發,充分發揮自身的權力和能力,協助貧困群體減貧脫貧,成為扶貧實踐工作中的協作者。制定相關政策支持農產品企業在貧困地區安家落戶,為貧困村民提供技術培訓和就業機會,提升村民個人發展能力從而實現持續增收;另外,在筆者調研的A鎮,50%以上的貧困群體受教育程度都是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個人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投入,提升貧困戶文化素質是扶貧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四)健全多元扶貧監督機制及扶貧績效評價體系
現有的扶貧監管體系重視扶貧資金使用和貧困戶信息管理,但在具體扶貧實踐中環節眾多,從扶貧信息傳遞,到貧困戶的精準識別,再到扶貧項目的分配和實施,任何一個環節缺乏監督都會導致扶貧資源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因此,建立健全多元化扶貧監督體系,完善精準扶貧各環節的監管是確保各類扶貧成果真正的受益者是貧困戶的關鍵。
建立科學的扶貧績效評價標準,不單單以脫貧率為標準衡量扶貧工作,對于不同的工作主體和不同的扶貧資源建立與之匹配的評價標準。要加強對扶貧工作人員的考核評價,以精準扶貧政策目標為標準對基層扶貧實踐者進行考核,將考核的結果作為其獎懲和晉升與否的依據,使得基層扶貧工作人員與國家政策目標一致,糾正扶貧資源在傳遞過程中發生的偏離。
參考文獻:
[1]?汪三貴,李文,李蕓.我國扶貧資金投向及效果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04(5):45-49.
[2]?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華北B鎮收糧個案研究[C].北京: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1,2000.
[3]?黃承偉,覃志敏.論精準扶貧與國家扶貧治理體系建構[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5(1):131-136.
[4]?左停,鐘玲,楊雨鑫.精準扶貧:技術靶向、理論解析和現實挑戰[J].貴州社會科學,2015(8):156-162.
[5]?鄭瑞強,王英.精準扶貧政策初探[J].財政研究,2016(2):17-24.
[6]?汪三貴,郭子豪.論中國的精準扶貧[J].貴州社會科學,2015(5):147-150.
[7]?李博,左停.誰是貧困戶? 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的國家邏輯與鄉土困境[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4):1-7.
[8]?邢成舉.村莊視角的扶貧項目目標偏離與“內卷化”分析[J].江漢學術,2015(5):18-26.
[9]?邊燕杰,張磊.論關系文化與關系社會資本[J].人文雜志,2013(1):107-113.
[10]?李文,汪三貴.中央扶貧資金的分配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8):44-48.
[11]?陜西省扶貧開發辦公室.陜西省扶貧開發辦公室關于印發《全省扶貧對象核實及數據清洗工作方案(試行)》的通知[EB/OL].(2017-04-09)[2019-03-08].http://www.shaanxifpb.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29014928&chid=100203.
[12]?孟民.“互助組+”幫咱來脫貧[EB/OL].(2017-06-15)[2019-01-18]. http://www.linyou.gov.cn/info/1013/7858.htm.
[13]?楊亮承. 扶貧治理的實踐邏輯——場域視角下扶貧資源的傳遞與分配[D].北京:中國農業大學,2016:98.
[14]?吳曉燕.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原因及其完善——以公共政策的運行為分析視角[J]. 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56-64.
[15]?丁建彪,張馨月. 我國精準扶貧政策中公眾權益的保護與建設研究[J].行政論壇,2019(1):39-46.
Action Logic of Subjects i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LIU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Shaanxi?721013,China)
Abstract: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are prone to the phenomenon of “inaccurate targeting”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from top to bottom.The villagers are in a passive acceptance posi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County and township governments seek to maximize their own achievements and economic benefits,and rely on resource advantages to influence poverty alleviation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transmission;village cadres use kinship to improve rural governance to affect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poor households.These lead to the devi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and eventually the phenomenon of “poor targeting” and “short-term targeting” appears.Therefore, exploring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poor,optimizing the position of the poor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giving priority to the poverty-stricken groups,changing the role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truly becoming the coautho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and improving the multi poverty alleviation supervisory mechan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have becom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promoting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action strategy;resource transmission;poor targeting;short-term targeting
(責任編輯:馬欣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