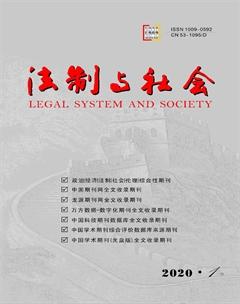高校保衛部門治安管理行為的法律屬性探析
關鍵詞 高校 治安管理 行政受案范圍
作者簡介:徐放,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1.144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2010-2020)》的實施,進一步推動了高等教育法治化的進程。高校管理過程中與師生、以及校外人員之間產生的糾紛如何借助法律途徑得到實質性解決是實現高等教育法治化的一大重要議題。同時,厘清校內安保部門履行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法律性質也為高校保衛部門的日常工作提供更加明晰、合法的工作思路。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具體列出了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的各種行政案件,其中第一款即為對行政處罰不服的。第十二款又做了“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的補充。在實踐中,1999年“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行政訴訟案” (以下部簡稱為“田永案”)開創了高校成為行政訴訟中被告的先河,從此之后,高校成為被告已為常態。高校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資格,但是當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時,高校與管理相對人之間就不是平等的民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它們之間因管理行為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有利于化解是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因此高校可以成為被訴行政主體 。由此,可以從判例推定出高校行使諸如開除學籍、不授予學位等管理行為的性質是行政行為。那么高校內保衛部門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行為又是什么性質呢?是否適用行政法和行政訴訟的調整范圍呢?本文從以下幾個典型的案例判決為視角來進行探析。
一、高校保衛部門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職責是否具有行政管理屬性
何志蘭訴清華大學案 中,2016年10月8日,何志蘭在清華大學萬人大食堂平臺散發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的競選材料,10月17日,清華大學保衛處對正在進行競選活動的何志蘭出示校規,并聲稱其宣講行為違反了校規,隨后,清華大學保衛處人員將其抬下萬人大食堂平臺,塞進轎車,送到中關村派出所。何志蘭認為,清華大學保衛處沒有執法權,即便其違反治安處罰法,清華大學也只能勸阻,或報警由派出所處理。故起訴至法院,要求確認2016年10月17日在清華大學萬人大食堂平臺保衛處人員把正在發放人大代表競選資料的其抬下萬人大食堂平臺、強行塞進汽車送往中關村派出所的行為違法。一審法院經審查認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起訴應當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符合法定的起訴條件。清華大學并非國家行政機關,因維護校園秩序將何志蘭強制帶離校園交與公安機關的行為并非行政行為,何志蘭所訴事項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不符合起訴條件。
何志蘭的主要上訴理由是,清華大學雖非國家行政機關,但其屬于國家授權的“組織”,其“組織”內部包括“行政職能部門”,這些行政職能違法,理應在行政訴訟的范圍內。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四十九條規定,提起訴訟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四)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就本案而言,清華大學并非國家行政機關,且其維護校園秩序的行為亦非行政行為,故何志蘭對清華大學提起的訴訟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不符合行政起訴條件。何志蘭的上訴理由缺乏法律依據,對其上訴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清華大學并非國家行政機關,且其維護校園秩序的行為亦非行政行為,故何志蘭對清華大學提起的訴訟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何志蘭”案中,法院對高校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行為認定態度不同于“田永案”,從實質主義的判斷方法來倒推的話,如果法院認為清華大學保衛處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那么由此可以推定出高校維護校園秩序的行為的性質就不是行政行為,那么高校保衛部門行使維護校園秩序的職權也并非行政職權。
二、高校保衛部門在履職中確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權”
在張曙光案 中,校外人員張曙光在人民大學校園內有拍攝校內女學生特定部位照片的嫌疑,第三人將此情況報告給人大保衛處。學校保衛處接到學生反映的情況后,派巡邏保安到達事發現場對該事件進行處置,并讓雙方當事人到保衛處值班室解決爭議問題,進行調解。隨后,張曙光家屬以人大保衛處違反了《治安處罰法》第四十條第(三)項、第四十二條第(三)項的規定報警。那么高校保衛部門作為負責維護校園秩序,處理校內糾紛的部門,是否有權讓雙方當事人到保衛處值班室解決爭議問題是本案的爭議焦點。法院判決的意見是:人民大學保衛處指派保安員進行處置并要求原告配合前往保衛處值班室協調解決問題,也是其履職行為,并無不當,不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形。從“張曙光”案中可以看出,雖然法院判決中并沒有明確高校保衛部門在校園治安管理中的職責到底是何種法律性質,但是法院認可高校保衛部門在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職責過程中有權要求當事人在特定時間、到特定地點配合調查、調解糾紛。
而另一個案例——“白曉龍案” 從另一方面印證這個觀點。“白曉龍案”中,當事人白曉龍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一名物業人員,因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接待省領導,安排白曉龍等物業工作人員維持領導視察區域的秩序,行政相對人白曉龍等人在勸說逗留在領導視察區域的李周姜離開無果后,白曉龍指使四名物業工作人員將李周姜抬離領導視察范圍至該校家屬樓7號樓下,并與另一物業工作人員在7號樓下繼續勸說李周姜直至省領導視察結束。后第三人李周姜以物業人員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報警。公安部門經過調查事實后認為,白曉龍等物業人員并非國家公務人員或者具有行政職務人員,故當時并非是實施職務行為,且其確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故對白曉龍做出了治安處罰決定。與張曙光案不同的是,本案中執行維護校園秩序任務的物業人員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受到了公安部門的行政處分,并且一審法院認為,原告白曉龍與該校四名物業人員將第三人李周姜抬離該校院士樓至家屬院7號樓并以勸說的行為方式,在客觀上限制了第三人李周姜在省領導視察時間段內的人身自由,且原告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物業人員,其造成第三人李周姜行動受限的行為不應包含在其職責范圍內,故認定白曉龍等物業人員的行為屬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在實際操作中,雖然物業單位在某些場合也有維護秩序的職責,但是上述兩個案例的判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即法院及公安部門均認可物業人員不同于高校保衛部門,并沒有要求他人在特定時間到特定地點配合調查、調解糾紛的權限。
三、由案例裁判界定高校保衛部門的性質和職能
從上述案例中可以推定出高校保衛部門不僅是校園安全管理過程中最直接的職能部門,還扮演著社會基層安保維護者的重要角色,是治安維護工作的主體參與者之一。
其一,對高校來說,保衛部門作為高校的職能部門,其法律性質是事業單位的內設機構,歸屬于高校領導,與高校之間是上下級的領導關系。從行政主體的概念范疇來看,高校某些場合又是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主體。高校保衛部門要執行學校的命令,服從學校的指揮和監督,所做的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行為的法律性質并非行政行為。
其二,對公安機關來說,隨著改革的深入,公安機關與高校保衛部門的領導關系已經逐漸演變為指導關系。在指導關系中,公安機關及其派出機關作為指導方的行政主體,擁有指導高校保衛部門的“指導權”,但沒有干涉安保機構具體工作安排的“命令權”,即公安機關沒用強制更改以及撤銷校內安保機構行政決策的權利,在指導關系層面,相關派駐機構應該通過給出具體建議、履行勸告職能、施加權利影響等手段督促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安保部門的日常工作。并且在高校保衛部門實際的日常工作中,其維護校園治安秩序的行為也并不屬于公安部門(行政部門)的授權行為,因而其法律性質不屬于行政行為。
綜上,雖然高校因為其適用了1989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舊法)第25條第4款前句“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的規定。2017年6月27日修正后的新法,在其第2條沿用了這一制度,規定“行政行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被認定為“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而能成為行政訴訟法的被告。 然而,高校保衛部門是高校的一個職能部門,其法律性質是內設機構并不是國家行政機關,而且也沒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一般的工作環境里,高校保衛部門并不能夠從自身的名義作出行政行為,也不能以自身名義承擔行政行為的后果。曾經擁有“刑事偵查權”和“治安管理權”的高校保衛部門現今已隨著“政事分離”的大環境而慢慢消逝,到目前而言已消失殆盡。
注釋: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4).
葉必豐,王誠.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頁.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2016)京01行終1113號.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17)京02行終626號.
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16)陜0113行初7號.
崔卓蘭,王景斌.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頁.
朱芒.高校校規的法律屬性研究[J].中國法學,2018(4).
參考文獻:
[1]莫于川.行政職權的行政法解析與建構[J].重慶社會科學,2004(1),第74-81頁.
[2]芮雪晴.高校行為行政可訴性的法理依據與審判趨勢研究[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