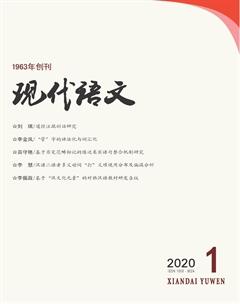賈樟柯電影對話藝術探析
張文心 翟耀
摘? 要:賈樟柯電影高超的對話藝術與人物對話關系的巧妙設定,是其電影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有時利用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權力關系,表達人物之間的疏離與冷漠;有時通過人物的肢體語言表達人物豐富的內心活動;有時通過靜默與失語,使人物之間的對話出現障礙,達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
關鍵詞:賈樟柯;電影;對話藝術
德國浪漫主義戲劇理論家A.W.史雷格爾(1767—1845)認為,對話是產生于兩個或兩個以上人物之間的語言交流,是一般人物語言的主要形式。它既可敘述、評論已經發生的事件,也可表現人物的個性、意愿、思想和情感,同時也可以使對話的另一方產生影響和沖擊,從而使其產生行動,并使人物關系和戲劇情節不斷向前發展。史雷格爾很好地闡釋了戲劇性對話的內涵。具體到電影門類而言,由于其言語形式和內容包含著創作者的個人思想與情感,具有歸屬于不同人物主體、不同身份指向等特點,因此,它擁有戲劇性對話的沖擊力,又貼合著影像的畫面感,從而構成了獨特的電影對話藝術。賈樟柯作為中國當代最著名的導演之一,他在電影中對對話藝術的巧妙運用,豐富了電影對話規則的同時,也提高了電影的表現力,形成了獨屬于自身風格的電影藝術特點。
一、方言與普通話搭建的交談模式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山西方言與普通話在賈樟柯電影中形成共生這種形式,構建了導演或影片與觀眾之間的一種動態、開放的對話方式。”[1]方言美學最重要的深層意義在于相同地緣環境下,展現同語言結構群體之間的關系,增加身份認同、喚起親密情感,并在無形中拉近交談者的距離。在異地環境中遇到同鄉者用方言進行親密交談,還能引起“他鄉遇故知”的情感體驗。
在賈樟柯的電影中,山西汾陽方言是人物語言機制的主體,汾陽話作為了一種身份的標簽,所有的人都在這層方言語境營造的身份下密切地交談著。而普通話作為國家規定的交流語言,在賈樟柯電影中更多地展現了官方、大眾特征。在對話關系的情感層面,普通話則使交談者蒙上了一層距離感,缺失了方言語境下的親密,在交談對話中顯得正式和客套,無法達到與同一話語體系下對談者相交相融的親密關系。當方言與普通話搭建起一種溝通的橋梁時,語言機制在交流中則會出現不對等的情形,這樣就使得某一方為了達成對話同一性而主動做出順從或屈從,此時的交流關系會變得格外復雜與耐人尋味。
在賈樟柯的電影《山河故人》中,沈濤與兒子到樂的一段對話,便凸顯了這種不對等情形。在方言與普通話所搭建的交談機制下,一個母親努力喚起孩子心中對故鄉的情感,在遇冷后為了拉近與兒子的交談距離,又主動轉變為普通話。在沈濤父親離世后,兒子張到樂回到山西老家奔喪,沈濤無意識地用山西方言對兒子說:“到樂,咋不跟媽說話了呀?叫媽。”幼小的到樂對陌生的方言表現出不適與排斥,猶豫良久后怯弱地叫了一聲“媽咪”。十分洋氣的“媽咪”在地域性十足的方言面前顯得格格不入,而“到樂”這一名字則是美元“Dollar”的諧音,體現出到樂洋里洋氣的身份及其與土生土長的山西人的不同特征。同時,方言與普通話是由不同語言構成的不同的“身份”,通過到樂的反應可以看出,他能聽懂母親所說的山西方言,但猶豫過后仍是選擇用自己的語言習慣作出應答,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到樂對自我身份的堅持。導演賈樟柯在此處通過兩者人物語言的分歧來暗示母子兩人情感上的距離。“媽咪?甚人教你這樣的叫了?爽快點,叫媽!”并一把扯下到樂洋氣的黃絲巾。沈濤的憤怒來自于親生兒子口中對“母親含義”的陌生稱謂,對于生長在山西方言環境中的沈濤來說,兒子的陌生口吻是一種與方言母體的象征性分離,自己的兒子已經和腳下的這片土地沒有了任何聯系,自然而然地也將會對自己產生陌生感。沈濤努力甚至用粗暴的方式試圖喚起兒子的方言話語機制,是為了遏制到樂對故鄉情感的疏離與淡漠。沈濤的強烈排斥,也使到樂更加怯弱和畏縮,無奈的沈濤為了兒子也只能選擇“漠視”自己的方言,并對兒子的語言行為做出協同。在隨后的對話中,沈濤用普通話對兒子說“回家吧”,她在對話言語上作出妥協,并構建了與到樂相同的語言規則。從方言到普通話的轉變,是為了縮短母子之間的距離隔閡的讓步表達,也是一個母親想要順從兒子情感所作出的讓步。
在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中,巧巧出獄后四處尋找斌斌,落魄無援的她只身漂泊到四川奉節,向當年的小弟“大學生”林家棟尋求幫助。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一向以方言為“母語”的巧巧,在林家棟公司里便選擇了用普通話與他交談。林家棟說道:“這不是巧巧嗎,歡迎歡迎!”巧巧十分恭順地用普通話回應:“打擾你了!”這里也同樣是一種話語讓步的表示。而五年之前,在山西初見林家棟兄妹時,那時山西方言才是人物對話中的主流“話語權”。當年的巧巧從容地坐在斌斌身旁,依靠著“江湖大哥”斌斌也獲得了主體位置,可以散漫隨意地用方言與林家棟兄妹對話。面對林家棟送來的雪茄煙,一句玩笑又帶有火藥味的方言隨口而出:“大學生,你這是讓額們家斌斌升級啊!”以無可置疑的主體力量脅迫著說普通話的林家棟與說香港話的林家燕做出屈從。方言主體在當時環境下甚至有決斷他者姓名的權力,斌斌:“家燕?我給你改個名字吧,就叫林間燕。”如今權力結構的置換顛覆了主流話語的選擇,此時落魄的巧巧以被動的客體身份出現,只得做出順從林家棟普通話的語言選擇。在不同的情勢與地緣環境下,從方言到普通話交談模式的遷移成為了主客體情感關系轉變的表現。因此,方言和普通話的關系,在賈樟柯電影中就構成了某種權力關系,生動地反映出人物關系的變化以及人物復雜的心理活動。
二、形體、動作構成的對話關系
及“無意義交流”
人類學家道格拉斯提出人的身體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生理的身體,另一方面是‘社會的身體,在這兩種身體經驗之間,存在著意義的不斷轉換,任何一種經驗都強化著另外一種。”[2]賈樟柯電影世界中的對話藝術,不僅僅是停留在演員的對白、臺詞中,更超越了語言的界限,構建起了形體、動作的多重對話關系,并通過身體的對沖表達人物劇烈的內心活動。
在賈樟柯的電影《任逍遙》中,描述了喬三與巧巧在公交車上撕扯這一場景。巧巧不斷地想掙脫出去,卻被喬三一次次地甩回到座椅上,兩者互不妥協。在整個過程中,人物沒有出現一句對白和交流,而是通過動作張力構成了整段戲碼。巧巧和喬三用動作上的沖突架構了另一種特殊的對話關系,即沉默過程中的身體對話。人物在沉默的過程中不需用言語上的對白,就能感受到彼此情感的交流。他們依靠肢體的對沖,宣泄心中復雜的情感狀態。賈樟柯在電影《任逍遙》放映后接受采訪時說道:“他們用不斷的撕扯和反抗,用一種傷害和受傷,來證明、提醒自己還存在著、生活著。”[3]導演將人物在此刻設置成緘默,借助動作的張力性完成了特殊情形下的“交流”,來表達此刻分崩離析的人物關系。
在電影《天注定》中,趙濤飾演的小玉也是一樣,猛烈地反抗非禮她的桑拿客人,即使遭到百般毆打羞辱,也仍不屈從。小玉身為他人家庭的破壞者,在“小三”這樣一個身份標簽下,使她自我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同時,大眾關系中看待第三者的眼光,也讓小玉陷入了自我懷疑,她需要用毫不妥協的抗拒方式來證明尊嚴的尚存。暴力與抗拒的身體對話,在電影中表現出的不僅僅是憤怒的情緒,對于構建對話關系的人物而言,它更多的是一種提醒,提醒著迷惘的個體還存在著自我情感,并且擁有對情感進行釋放的權力。他們并沒有被拋棄,還能一如往常地敢愛敢恨,有尊嚴地活著。這恰恰反映出生命個體始終處于空洞、迷惘的狀態之中。
在電影《任逍遙》中,舞女巧巧與追求自己的少年混混小濟,在面包車里展開了對話。巧巧輕蔑地反問小濟:“你怎么泡我?”小濟隨口回答道:“就像開水泡方便面一樣泡啊。”人物對話的荒誕感呈現出了喜劇效果,猶如語言學家巴赫金所提出的對話理論,兩個聾子對話的情境——有實際的對話交往過程,但對話之間沒有任何意義上的交流[4]。小濟與巧巧的對話關系正是如此。渴望占有與愛情讓兩人坐在一起交談,但無知與沖動又使得事與愿違,讓交流變得毫無意義。巧巧毫無意義的設問“你怎么泡我?”,更像是一種特殊的期盼,期待收獲到自我渴望的愛情,但她自身對愛情的想像卻又是一片空白。于是,她便將這種解答疑惑的權力轉讓給追求自己的小濟,希望通過他的回答獲得對愛情的認知。對于愛情,在小濟心中也只是迷惘下的沖動,“泡姑娘”這一詞匯只是簡單出現在電影里營造的幻想性對話中,渾噩的少年通過幼稚的模仿,將這一不甚清晰的行為轉換成主體的語言帶到了現實中。但當被巧巧追問起“你怎么泡我”時,想要展現成熟與實力的小濟也只能硬著頭皮,根據自己淺顯的直觀解釋作出回應。小濟空洞的回答是可悲少年的思想投射,在啼笑皆非的回答背后,隱藏著人物主體精神空洞的悲哀。可以說,兩人在這一交談中,暴露了各自對待感情的方式。正是由于雙方都一無所有,因此,他們對待心中“不甚清晰”的愛更接近于一種填補式的占有,以這種“占有”的方式相互慰藉,來彌補心理情感的匱乏。就此而言,空洞思想下的對話導致了雙方語言交流的“無意義”。
三、失語狀態下的特殊表達
失語狀態是指在人物在進行交流與對話過程中,因受某種特定情形的影響而產生的默不作聲,當語言行為受阻時,主體往往尋求另一種替代語言表達方式來回達自身的情感態度。在面臨文化因素多元雜糅的現實具象時,人們難免會手足無措,陷入難以自拔的“失語”境地[5]。這便構成了失語狀態下的特殊表達。
在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中,斌斌與巧巧在老式迪廳中盡情地狂舞,便是失語狀態下用以替換的表達方式。人們在表達最強烈的情感時,常常是以無法言說的方式來進行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是對情感最濃烈的釋放,在那樣一種狂歡中沒有人用言語來互訴衷腸,卻又人人明晰相互之間熾熱的情感狀態。沉默的狂舞是人物失語狀態下的特殊對話表達,人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宣泄無處釋放的情感躁動。愛情在迷惘的一代人身上,等同于想強烈的擁有對方,企圖通過熱烈的方式來證實心中模糊消逝的本我還依然存在,依然有血有肉。賈樟柯電影善于利用演員身體上的對沖來構建新的動作言語體系,身體動作的張力和沖突是失語狀態下的特殊表達方式,用沉默的狂舞來彌補人物主體無法言說的空洞情感。
在《江湖兒女》中,巧巧回家探望父親,則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在煤場工作的父親,由于礦務局老板拖欠員工工資,父親便跑到廣播臺,通過廣播向礦友們慷慨激昂地吶喊:“礦場劉金明,是誰給你的權利,讓你把國家資產流失,我們堅決不答應!正義永遠戰勝邪惡,光明永遠戰勝黑暗!”但現實生活中的父親卻是安分老實、沉默寡言的。在現實里“失語”的巧巧父親,借助喇叭將無法宣之于口的話語宣泄出來,這是失語狀態下表達話語權力的特殊方式,也是一種無奈的方式。話語是一種權力,然而礦場中不為人知的權力結構關系“壓抑”了父親遭遇不公時的發聲,限制了老人隨心所欲的表達權力。面對權力壓迫下的失語,老人只得采取另一種更特殊更能使人所知的“廣播”方式來控訴遭遇的不公,選擇另一種的發聲方式進行替代表達的同時,也構成了人物主體失語狀態下的特殊表達。
在電影《天注定》中,四處漂泊的少年打工仔小輝,在夜總會里與小姐蓮蓉通過平板看新聞的過程中,產生了以下的交談:蓮蓉說:“山西煤礦爆炸,死了十幾個人呢!”小輝說:“跟個帖。”蓮蓉說:“回復什么?”小輝說:“TMD,他媽的。”這段富有戲謔意味的對話,展現著真實的社會原貌。小輝與蓮蓉的特殊身份猶如被主流社會所“拋棄”的邊緣群體,他們身居與主體社會“相去甚遠”的邊界,在命運最初就已經與社會整體出現了斷裂式脫軌。“這群人長期處于社會底層,接觸到的往往是常人的唾棄,所以不少邊緣人都存在孤單落寞的心理。”[6]沒有社會地位意味著失去了話語權,即便是發聲也無法獲得主流的回應與認可,這樣的情形便造成了邊緣人處于被動的“失語”狀態。主流世界無法傾聽邊緣人的訴說,邊緣群體也漸漸退出參與交談。在這樣的雙重“拒絕交談”下,在沒有話語權的失語狀態和不受關注的現實情境下,邊緣人只能通過電腦、手機等“窗口”來窺探社會的巨變與自身相隔甚遠的主流。蓮蓉手中的平板電腦,是他們與主流社會接觸的唯一接口,是自身所處的現實泥潭與真實世界唯一的對話途徑。“跟帖”則給予他們發聲的權力,在這一過程中所完成的回復是被動失語狀態下的特殊表達。不過,由于久居邊緣,一旦擁有了同正軌對話的機會,也只能用一句含混不清的“TMD”來做出回答而已。邊緣人與社會對話的可悲之處,不只是被動失語下通過“窗口”做出的特殊表達,而是一旦擁有發聲的權力也只能是模糊含混的無話可說。
四、身份鴻溝下的跨越式交談
賈樟柯的電影群像中,造成人物處于失語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人物之間的身份差距使得對話關系出現扭曲和障礙。若想完成對話過程,則必須選擇越過鴻溝,發出跨越身份層級的對話,但最難跨越的往往是人物的內在情感和自尊。
在《任逍遙》中,斌斌的女友正面臨高考,穿著校服的高中女孩和混跡社會的不良少年斌斌相戀,兩人盡管年紀相仿,卻即將面臨命運的分野。女孩即將參加高考去北京上大學,將要插上翅膀離開這片貧瘠狹窄的小城,而斌斌的未來則是前路迷茫黯淡無光。分野的人生轉折意味著即將形成的身份差距,從而誕生了不同身份之間的對話。“快考試了我就因為看了WTO挨了罵。”“你看孫悟空多好,沒爹沒媽沒人管,多自在,也不用管什么鳥蛋的WTO。”兩人談論著“WTO”之類的社會大事,卻對自身的生活無話可說。年齡相仿的兩人都陷入了對自由的渴望,女孩是希冀于高考壓力之后的解脫,而渾噩的斌斌則是尋找著生活的出路。最后一次K歌廳相遇,女孩換下了校服穿上了白色襯衫,兩人的感情亦突破了拉手的界限,這卻是即將告別命運的再難重合,跨身份的命運分野即將降臨:
女孩:“考完試了你都不去接我。”
斌斌:“我是混社會的,學校的事我哪知道?”
女孩:“全國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這幾句頗顯局促的對話,顯示了斌斌對自我的設定,“混社會”這一身份標簽深入其心。與其說斌斌不知高考時間,不如說這是他從心底的不愿面對,考試學業早已與他無關。但這個少年的心中是否對高考生活有著一絲向往與羨慕呢?現實卻是令人失望的無奈與頹唐。雖是戀人,雖屬同齡,但斌斌與女孩未來的身份將截然不同,自己渺小的“街頭混混”身份讓他開始無顏面見擁有美好未來的女孩,在身份鴻溝的落差面前斌斌是那樣的無地自容。
最終選擇發起跨越身份對話的人還是斌斌,只不過他選擇了從頭至尾的沉默。高考結束后,兩人在空曠廢舊的電影錄像廳約會,女孩打扮得明麗鮮艷,已經沒有了往日的沉悶壓抑。斌斌看到她后眼里寫滿了自卑,將貸款買的手機交給女孩后不發一言,悄然等待著女孩的心情由欣喜慢慢變得枯萎。始終無法得到應答的女孩,騎在自行車上問了最后一句“你跟我一起走嗎?”得到的仍是沉默。在對話關系中,話語發出的目的是被人聆聽,讓人理解并得到應答,但斌斌的選擇性“失語”破壞了對話關系。這種貌似對話實則是一人獨白的對話關系又被賦予了雙重的表現功能:它在展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受阻和其中一方的內心孤獨的同時,也被用于呈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即同齡之間“大學生”與“社會人”的社會身份鴻溝。斌斌明白坐在自己面前的漂亮姑娘擁有了不一樣的人生,女孩的一句有雙關意味的“你跟我一起走嗎?”更是讓斌斌無奈。他深知自己已然被命運拋下,最終將無法追趕前往大城市讀書的女孩,只能獨自停留在這孤城混跡和頹唐,“在百無聊賴的度日中找尋那無可奈何的逍遙”[7]。
在賈樟柯的電影《山河故人》中,也同樣存在著身份鴻溝之下的對話。窮困潦倒的梁子重回故鄉,身染重病四處借錢時,在老屋里再次遇到了沈濤。此時的沈濤已成為外人眼中風光無限的“沈總”,光鮮的衣著與梁子破落的平房顯得極不協調,尊嚴再一次受挫的梁子與她交談時始終未露出正面。現實之中的“失意者”在面對身份落差下的舊愛,更多的是一種“無顏面見”的掙扎與自卑。在影片《江湖兒女》中,江湖中的迷失者斌斌落葉歸根重回故土時,輪椅上的他“累累若喪家之犬”。斌斌被迫“失聲”的同時,卻發現話語權已經悄然置換在巧巧身上。曾經的戀人此刻已然接替自己的位置,成為江湖圈層里規則的執掌人,而作為曾經江湖規矩的決斷者,斌斌此時卻寄人籬下,僅存的尊嚴被撕扯盡碎。斌斌的處境產生出一種蒼涼的“挫頹感”,在身份的落差下他沒能邁出跨越的一步,最終留下一句毫無情感波瀾的留言“我走了”,便淡出人來人往的江湖。在賈樟柯電影中,身份鴻溝帶來的距離感使人物主體難以發聲,這種無法構成的跨越式交談則突破了傳統的對話模式。
總之,賈樟柯電影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其中對人物對話藝術的巧妙運用以及對人物對話關系的匠心設定,為其電影的成功提供了重要助力,值得認真研究與總結。
參考文獻:
[1]孫宏吉,路金輝.《山河故人》對白特征及表意探析[J].電影文學,2019,(11).
[2]張祥.《窈窕淑男》:身體與權力的對話[J].美與時代(下),2019,(5).
[3]賈樟柯講《任逍遙》.https://v.qq.com/x/page/h0533c36gou.html?2002.
[4]張葵華.言語狂歡下的隔膜——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的多重對話關系[J].新鄉學院學報,2018,(11).
[5]戴瑋.多重文化認同下的陌生人——當代人“失語”狀態的三種解讀[J].傳播力研究,2019,(27).
[6]呂湘毅.論邊緣人形象在21世紀大陸電影中的多維展現[J].電影評價,2017,(17).
[7]謝明志.賈樟柯電影《任逍遙》中無奈的逍遙[J].大眾文藝,2014,(1).
A Study on the Art of Dialogue in Jia Zhangkes Films
Zhang Wenxin1,Zhai Yao2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The extraordinary art of dialogue in Jia Zhangkes films and the clever setting of the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through dialogue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success to his films. Sometimes he uses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alects and mandarin to show the alienation and indifference among people; sometimes he uses the characters body language to express their complicated mental activities; and sometimes he creates barriers through silence and aphasia during the dialogue of characters to achieve the effectthat “silence speaks louder than the noise now”.
Key words:Jia Zhangke;film;the art of dialo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