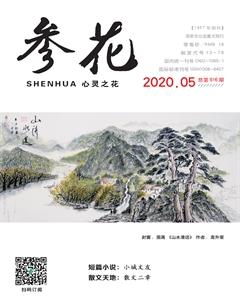敘述的世界:《去往第九王國》的文化認同書寫
摘要:彼得·漢德克的《去往第九王國》通過講述菲利普的尋根之旅,展現出獨特的文化認同觀。首先,小說有著深厚的歷史意蘊和自傳色彩,通過不斷追問,明確文化認同是將人類聯系在一起的深層原因;其次,小說通過主人公菲利普·柯巴爾與“小敵人”的沖突,探討了文化對話中的暴力因素;最后,菲利普越過即有文化成見,直接將生命體會注入語言文字中,建構起“自我—敘述—世界”的文化認同方式。
關鍵詞:彼得·漢德克 《去往第九王國》 敘述 文化認同 身份認同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是奧地利當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包括《左撇子女人》《緩慢的歸鄉》《去往第九王國》等,被譽為“德語文學活著的經典”。在漢德克的創作中,“尋找”是一個永恒的母題。[1]長篇小說《去往第九王國》通過講述主人公菲利普·柯巴爾的文化尋根之旅,深入探討文化認同的原因和文化交流中的暴力因素,拋棄傳統的文化認同方式,以敘述為媒介連接自我與世界,顯示出獨特的文化認同觀。
一、漢德克的文化認同觀
漢德克作品的主要中文譯者韓瑞祥認為,文學是漢德克不斷明白自我的手段,尋找自我與文化尋根是他的重要母題。[2]《去往第九王國》承襲這一母題,描繪了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多民族的德國、各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家庭、碎片化的回憶;在這相互離間的世界上,主人公菲利普·柯巴爾踏上文化尋根之旅。由此,小說向傳統上以國家、民族、地域為依據的文化認同觀提出質疑,從文學角度出發來關照這一問題。
文化認同(culture identity)理論發端于20世紀50年代。其中,“identity”有兩層內涵:第一層是身份認同;第二層是社會認同。“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中,從人類的主體性出發考察文化,提出文化始于人類超越自身繼承自自然之物的那一刻,而且身份問題是文化研究的核心。[3]對文化認同的作用,卡斯特認為多重身份及文化認同與國家權利、國家機器的絕對權力和其他組織共同分享權力,是形成國家的必要因素。[4]伊格爾頓認為,文化不僅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一切,還是我們為之生活的一切,[5]文化認同推動“共同文化”誕生。[6]總而言之,文化認同是人歸屬于某一民族、國家、地域的深層邏輯,對文化認同的考量,要從身份認同開始探究并最終回到聯結個體與世界的文化本身。
在斯德哥爾摩的獲獎演說中,漢德克坦言《去往第九王國》是一部糅合了家族故事、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文化交流的種種矛盾在小說中被寄寓了深刻的思考,因此,《去往第九王國》可視作文化認同研究的典范作品。在小說中,菲利普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斯洛文尼亞族,哥哥在二戰中失蹤,姐姐則精神錯亂;國家、民族、戰爭等問題混雜在柯巴爾家族中,重重矛盾甚至阻斷了血親關系,在菲利普的夢中,他們“在這空蕩蕩的屋子里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既不能相互接近,也不能相互接觸,垂掛雙臂”。[2]意味深長的是,柯巴爾家族中流傳著“第九王國”的傳說故事:“要是我們大家失散后有一天又重聚在一起,乘坐上披著節日盛裝的四輪單駕輕便車,前往第九王國,參加第九代國王的婚禮。”[2]在國家與民族之外,文化是使人跨越時空相聚在一起、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深層原因。漢德克將文化認同視為人存于世的重要命題,它超越國家、民族等限制,在開闊的文化立場上賦予人身份,也據此將人們聯系在一起。
二、文化中的“流浪者”
漢德克對文化認同的探究始于對文化身份的懷疑。在《去往第九王國》一書中,主人公菲利普拒絕以民族、國家為依據認知文化,也拒絕被任何既有文化定義,于是他重新審視個體的身份問題,卻陷入了文化“流浪者”的境遇,即徘徊在世間難以融入任何既有文化,也拒絕融入任何既有文化。菲利普認為只有不含期待、沒有暴力因素、平等的文化交流可以被接受,對“流浪者”的身份甘之如飴。
“流浪者”的身份在旅途開始便伴隨著菲利普。穿越國境時,耶森尼克邊防士兵一眼認出了“Kobal”是個斯拉夫名字,便將菲利普歸為斯拉夫民族,用斯拉夫語言與他搭話。但是“自然用他的語言跟我搭上了話”“受到如此一番教誨之后,我才獲準……進入那個南斯拉夫的北方城市”,[2]一系列敘述傳遞的卻是菲利普被動、無奈的心理與對憑姓氏區分族屬的不滿。事實上,祖先格里高爾被流放,柯巴爾家族不斷遷移,這使菲利普認為自己所屬的民族“壓根兒也不是那個特有的斯洛文尼亞民族……而更多是一個不確定的、永恒的、超然于歷史之外的民族”。[2]在旅途中,菲利普極力破除民族、國家、地域的局限,他為自己的每一段故事都加上主觀性的定語:傳說中的格里高爾、不值得敘述的學校生活、再也無法融入的林肯山村,試圖以自己的邏輯來組織回憶,尋找文化歸屬。
與此同時,“流浪者”也是菲利普的主動選擇。在個體與他人的對話中,菲利普敏銳地意識到文化交流中隱含著文化暴力因素,即為了維持交往,一方向另一方靠攏,逐步接受對方文化規定的現象;唯有“流浪”的文化心理能誠實地感知自我、認知文化。通過菲利普與“小敵人”的交手,小說討論了個體在文化對話中能否維持忠于真實自我,而不被任何文化“暴力”影響的問題。菲利普的小敵人是鄰居的兒子,他與菲利普玩影子游戲,故意學菲利普的樣子惹怒菲利普。菲利普起初試圖通過虛晃擺脫小敵人,但不僅沒有成功,反而使“我成了自己影子的俘虜”,持久地陷入“自我急切擺脫自我”的怪圈。細究其中關系,模仿是一種企圖消滅兩個主體間差異的行為,其中一方的行為逐漸接近另一方的同時,另一方為了抵抗則陷入“我不是什么”的思考,迫使自己做出不符合真實自我的行為,再難認知真實自我的感受,如此往復,雙方都沉迷于制造虛偽外殼,而真實自我已在漸漸消解。所謂“敵人”,是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他人,企圖抹平兩者間文化差異的人,不論以何種方式,其中都隱含著文化暴力的因素。因此,菲利普渴望成為“流浪者”以保持自由身份來行走于世。
菲利普細致地考量每一次交流的意味,他欣賞的文化交流沒有索取或要求,而是保持距離的、自由的相互感知,否則,他寧可做不為他人所動的文化“流浪者”。
三、敘述中的“第九王國”
在傳統文化認同理論中,相同的語言、宗教信仰、文化景觀、節日慶典等都是文化認同的依據。《去往第九王國》則另辟蹊徑,將個體生命體驗注入語言文字,解構了其中蘊含的民族意味,并以敘述為媒介建構了“自我—敘述—世界”的文化認同觀。
語言文字承載著一種文化的思想精神,也劃分出了不同文化的邊界,雷蒙德·威廉斯認為“一個文化的范圍,它似乎常常是與一個語言的范圍相對稱”。[7]但在菲利普眼中,語言文字并不反過來被某種文化局限,而直接與現實世界相連,于是他從更廣義的角度認識自身與世界的文化聯系。在菲利普翻閱哥哥的大詞典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建立這一聯系的過程:“我呼喊著那些陌生的詞語,讓它們融入這片天地里”[2]“我隨之感受到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和形象同它們的空間間隙都顯現了出來”,[2]斯洛文尼亞文字的字形、音韻與林肯山村的圖像對應起來,形成了菲利普自童年起就缺失的詞語——聯系自我與生存環境的詞語:“在我眼前聚合成一個民族,家鄉的村民清清楚楚地出現在其中”。[2]在往后的敘述中,菲利普熟練地給語言文字注入自我生命體會,例如在劈木頭時用新造的“分裂光明”一詞表述“制造麻煩”。對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菲利普在喀斯特的旅行中稱:“不僅是個尋根問祖的人,而且也是個打短工的、新郎、酒鬼、鄉村錄事、守尸人”,[2]超脫政治與世俗對自我身份的定義,賦予自己觀察者身份從而得以在世界上自由地探索自我的多重文化身份,即自己為自己命名。對個體而言,這才是最真實的文化身份,它與現實的生命體驗緊緊貼合。
菲利普越過既有文化的限制,直接通過自身生命體驗來認知世界,使敘述和世界直接相連。在這種視角下,敘述可以支撐柯巴爾家族內部形成文化認同,人們可以通過敘述相互理解、相互靠近,形成不受制于世俗的、忠實于生命經歷的文化認同。小說中,菲利普的旅行軌跡在敘述中多用自然地理名稱標記,他以卡拉萬肯山脈的位置變化表示跨越國界,以火車站連接不同空間,通過體驗來認知世界,也通過體驗將敘述片段連接起來:“終于又要像當年那個光著腳的孩子與父親并肩走在田野上一樣……這時,他重復的不是同父親一起走過的童年之路,而是當兵的哥哥拖著艱難的步子穿過不毛之地,去參加一場預先注定要失敗的戰斗。”[2]柯巴爾家族的祖先格里高爾出生在伊松佐河上游,菲利普的父親在伊松佐河度過一戰,哥哥亦曾走過這條行軍之路,這些在開頭被碎片化處理的故事片段由此聯系了起來,三代人的記憶也在這里交匯。正如“第九王國”傳說所說的“我們失散又重聚”,菲利普抵達了心中的“第九王國”,文化交匯之地。在筆者看來,只有家族世世代代的經歷是最真實的,它埋藏在每一代人的心底,并隨著生命體驗的豐富逐漸生動起來。“柯巴爾”這一姓氏始終在提醒我們這是一個行走著的民族,不屬于任何既有文化,我們無法定義它,只能透過它的蹤跡在歷史流變中不斷感知它。
四、結語
《去往第九王國》的德文書名為“Die Wiederholung”,意為“重復”,點明尋根之旅是一次文化回溯,民族、國家、區域的文化內涵會隨時間流逝不斷地變化,個體的文化身份會隨人生經歷不斷變化、豐富。通過菲利普的尋根之旅,小說建構起“自我—敘述—世界”的文化認同方式,站在人類生活的高度為文化認同拓展出新的路徑。
參考文獻:
[1]賈晨.一部 “尋找” 與 “自我反思” 的小說——評彼得·漢德克長篇小說《試論蘑菇癡兒》[J].名作欣賞,2018(20).
[2][奧地利]彼得·漢德克.去往第九王國[M].韓瑞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Routledge.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M].1999: 68.
[4][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夏鑄九,黃麗玲,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78.
[5][英]伊格爾頓.文化的觀念[M].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131.
[6]韓偉,徐蔚.文化的危機與彌合——讀伊格爾頓的《文化的觀念》[J].文藝評論,2010(01).
[7][英]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M].吳松江,張文定,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399.
(作者簡介:邢若蘭,女,本科在讀,河北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文學理論)(責任編輯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