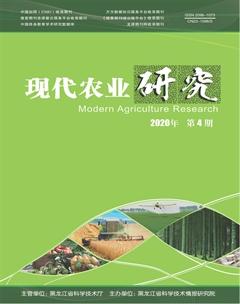變遷中的廟會文化與鄉土重建
王亞軍
【摘? ?要】 與全國大多廟會相異,川南天心廟會應其福澤范圍有限,并不具備商業性質,故而更為傳統。通過對川南天心廟會前世今生歷史變遷的回顧以及廟會場景的展示,得出廟會生死與鄉村共同體繁榮與式微之間的互構關系,歸納出林村天心廟會的三大特征,并認為復興廟會文化本身就是鄉村公共性與鄉村共同體的重建之路。
【關鍵詞】 天心廟會;歷史變遷;共同體;鄉土重建
[Abstract] Unlike most of the temple festivals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Southern Sichuan Tianfu Temple has a limited range of Fukuzah and does not have commercial properties. Therefore, it is more traditional.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Tiananshui Temple in southern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display of the temple scen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temple and the mutual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rural community, summarize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anxin Templ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holds that the temple culture itself It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ity and r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tianxin temple fair; historical changes; community; local reconstruction
1? 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廟會作為一種原始的傳統文化,搭載著人們最原初的信仰和追求。對于傳統中國農民而言,廟會的舉辦,能夠直接與神靈對話,通過對神靈的尊敬和愛戴,換來風調雨順和家人的康健。正是廟會在人民心中所固有的重要性,使得學界對廟會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縱觀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廟會概念的界定研究。如小田認為,廟會是以祠廟為依,在特定時間舉行的祭祀神靈、交易貨物、娛樂身心的集會 。吉發涵則向前追溯廟會的由來,認為今世的廟會與上古的廟會并不相同,上古的廟會是“廟”與“會”的結合,“廟”主要是帝王的宗廟,而“會”也不是當代所指的平民百姓的集會,而是帝王與諸侯之間的會面,是一種政治外交活動。由此“廟會”也就成為以祭祀逝去帝王為目的的政治外交活動。直到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道教發展成熟后,廟會的祭祀對象才逐漸轉移到對佛陀、各種神仙之上 。進而具有了今世的廟會含義。二是廟會的社會功能研究。如李永萍、杜鵬在對關中金村廟會的考察后指出,廟會發揮著社會整合的功能,這種整合功能主要表現為,宗教整合、交往整合、文化整合以及市場整合等功能 。陸益龍則通過對河北定州廟會的研究強調了廟會的經濟功能,并認為從華北鄉村集市繁榮發展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廟會和集市的綜合性功能在逐步消失,并逐漸演化為功能單一的農村低端消費市場 。三是國家霸權影響之下的廟會研究。如張祝平通過對浙北黨山雷公廟會的考察中指出的,廟會作為一種傳統民間儀式和文化,其繁榮深受國家文化政策的影響和強力干預 。
縱觀既有對廟會的上述研究,既分析了廟會的歷史發展,也從功能的角度進行了分析,甚至與將廟會納入到“國家——社會”的框架之中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逐漸形成了以廟會為核心的知識譜系。不過,學者們所研究的廟會太過于“現代”了,無不涉及廟會的市場和經濟功能。然而,作為一種原生的精神信仰和生活追求,對傳統的、未市場化的廟會公共性及其價值的研究卻稍顯不足。本文則以非市場化地、以公共性為核心價值的川南林村天心廟會為研究對象,以區別于學界已有研究中的研究對象。
然而,正如吳理財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社會歷經了與西方社會不同的兩波個體化,第一波個體化由國家開啟,個體從“總體性社會”中的集體中“脫嵌”出來,重新回歸地緣共同體、家族、家庭,而隨著市場化、全球化的沖擊,第二波個體化開始了,個體再次從地緣共同體、家族,甚至于家庭中“脫嵌”,越發成為“為自己而活” 的“無公德的個體” 。伴隨中國社會兩波個體化的,是象征公共性的鄉村公共生活的日漸式微和消解。廟會本身就是一種以相似信仰為基礎的公共活動,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同時廟會的舉行能夠吸引同村村民的聚集,進而形成以廟會為中心的公共空間。由此觀之,廟會依托公共性能夠建構鄉村共同體。盡管當前有學者提出了廟會的社會整合功能,但關于廟會對鄉村共同體的建構作用的詳細研究亦稍顯不足。
本文通過對林村天心廟會這一特殊案例的生死流變及其表演場景的深描,探究其與川南林村鄉村共同體繁榮與式微之間的互構關系,并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探究廟會與鄉土重建間的關系。
2? 天心廟會的生死流變與表演場景
天心廟會的生死流變。通過與“破四舊”之后首次廟會的組織者的訪談,大體可以將天心廟會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
2.1? 天心廟會的初生階段
川南林村的天心廟會始于19世紀20年代,因為天心廟本身始建于此期間(具體的承建歷史已無人知曉)。由于年代久遠,且無文本資料可以考究,僅能夠從村中老人的回憶中模糊描繪天心廟會的初始景象。“我們都還沒出生的時候(根據老人年齡推測為19世紀20年代中期),就有天心廟了,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廟會了。
2.2? 天心廟會的消亡
建國后的“破四舊”運動轟轟烈烈在全國開展時,天心廟也遭到了“滅頂之災”,廟內的佛陀被民兵排長帶人全部摧毀,寺廟也被拆除了。由此觀之,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支持下,廟會這一傳統文化作為傳統舊風遺俗、迷信被統一廢除了,盡管林村村民害怕以菩薩為首的神靈的怪罪,但在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的壓迫下,也顯得無力反駁。
2.3? 天心廟會的復興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在文化上也更為包容開放了,廟會作為一種傳統文化開始復興。復興后的第一次天心廟會舉辦于1980年,正好由筆者的訪談對象為核心之一的4位“文化人”組織。
2.4? 天心廟會的再消亡
據老人回憶,2015年為天心廟會幾十年來的首次停辦。其原因主要出于三個方面,其一原先的舉辦人已有兩人分別于2004年和2008年離世,一人年紀已達78歲,行動困難,一人隨其子于2015年搬入縣城居住,幾乎不再回村;其二在往常的廟會選舉中,不再有人愿意承擔廟會的組織者;其三,村中大多家庭已經搬入城市,或中青年長期在外務工,村莊空心化愈發嚴重,廟會所需經費難以籌集且參加人眾逐年變少。
整個廟會的表演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寺廟的重建,以及為佛陀重塑金身。二是4位“文化人”開會,商議廟會的議程及分工。三是宣傳、動員以及“功過(即參會經費)”的收集和物資的借去。四是請道士(民間認為能連接神人之間的異能人士)念經祈福并做道場。最隆重的環節就是道士做道場,因為這是人們覺得能直接向神靈祈福的方式和時機。五是做齋飯。齋飯從1980年開始,直到2008年,一直在寺廟旁邊的羅家制作。六是善后工作(包括物資的歸還、剩余“功過”的存儲、下一屆組織者的選舉)。齋飯之后,是會眾自費請道士“打保卦(即抽幸運簽)”,如果能順利打過則代表這一年家庭平安,風調雨順,否則便多災多難,需要請道士重畫靈符以便“破災”。
3? 生死之間的廟會與繁榮、式微中的鄉村共同體
通過對林村天心廟會的歷史變遷、過程的描述以及對其自身特征的歸納,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生死之間的天心廟會與鄉村共同體的繁榮、式微之間的互構關系。
建國之前,林村生產十分落后,且常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據林村老人回憶,19世紀30-40年代的林村一共有3個地主,因為林村耕地實在太少了,糧食產量,特別是水稻產量太低了,且常受到干旱氣候的影響。不得已,林村地主和佃戶將目光和希望轉向了天心廟,期盼通過與神靈(特別是菩薩)的神意交匯,以保護一方水土風調雨順。在這樣的期望下,天心廟會成為林村信仰的歸宿
建國后,由于“破四舊”,林村天心廟被拆除,象征著林村人精神信仰的佛陀也被推倒、摧毀。傳統的林村人,特別是林村老人對以生產隊長和民兵排長為首的“破四舊”執行者敢怒不敢言。原本集體生產所建構的集體生活和共同體也因為對“破四舊”態度的差異而產生了裂縫。
改革開放后,國家對傳統文化持發掘和保護的政策,這為廟會的重生創造了條件。以4個“文化人”為代表的組織者于1980年復興了林村天心廟會。從1980年開始,天心廟會逐漸為制度化了。同時,從廟會的規模來看,從1980年開始,會眾激增,不過進入21世紀以來,會眾人數開始減少。由此可以總結出生死之間的廟會與繁榮、式微中的鄉村共同體之間的互構關系:廟會生則鄉村共同體興盛、廟會死則鄉村共同體衰敗。
4? 廟會與鄉土重建
城市與鄉村是伴生的一對兄弟,在城市飛速發展的今天,鄉村卻走向了衰敗的另一端。為此,政界和學界就鄉村何去何從展開了多維度的論爭,不過鄉土重建和鄉村復興到十九大提出全面鄉村振興取得了最終勝利。近來,關于鄉土重建的研究也不斷增加。如陸益龍認為鄉土重建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解決鄉村轉型中的文化矛盾,重建鄉村社會秩序 。閆麗娟、 孔慶龍則認為,鄉土重建的使命是重構一個能夠提供生活保障、價值賦予和身份認同的村莊共同體 。吳理財則從個體化的視角,認為鄉土重建的題中之義應有鄉村公共性的建設 。總而言之,以公共性為核心的鄉村共同體的重構是當前學界的主流觀點。
本文亦認為鄉村公共性的重建和鄉村共同體的重構乃是鄉土重建的核心命題。而對于鄉村公共性與共同體的重建媒介或途徑,學界也觀點眾多。如張良將鄉村公共性建設的重心放在賦予村級組織相關資源的配置權力、以公共文化活動搭建公共交往平臺,建構村民之間互動與溝通的公共空間;需要發展民間組織,營造熟人社會的氛圍;需要重視村規民約的重要作用等幾個方面 。江桂英則認為鄉村公共經濟是農村社區公共性建設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詳細第建設路徑 。
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可以提出眾多的重建媒介,然而真正能夠落到實處加以實施的卻并不多見。因而,從可行性的角度,筆者認為村莊廟會也是重建鄉村公共性和共同體的良藥。誠如上文所指,我們可以歸納出林村天心廟會的三大特征:
第一,公共性。這主要表現在“功過”的收集、齋飯材料來源以及廟會組織者的選舉三個方面。就“功過”的收集來看,出多出少全是自愿的,不會強制性地要求繳納多少才能參會,并且最后的“功過”清單也不會根據多少進行排序并張貼在寺廟堂前進行公示;就齋飯材料的來源來看,起初由于林村地處山區缺少耕地,水稻種植產量不高,因而大米通常通過“功過”進行購買,而其他菜類則大多由會眾自愿帶來,或多或少,全屬自愿,會眾亦不會計較得失。
第二,非市場性。與全國其他地區廟會相異,林村廟會并不具備經濟性,不會產生市場交易。盡管“打保掛”和請道士做道場需要花費一定的金錢和“功過”,但其額度卻是極少的,林村人認為這是對道士辛勤勞作的補償和對其職業的尊重,道士也不會要求過分的工費。當然,林村天心廟會缺乏市場性也許還與林村人認為的與神靈相通的場合不適于做買賣、天心廟會福澤范圍有限(大體僅覆蓋林村8、7、6等三個臨近組,當然其他組也有村民慕名而來,不過人員較少)有關。
第三,制度性。從1980年林村天心廟會復興到2015年的再次覆亡,天心廟會每年于農歷六月十九固定舉辦一次,并形成了上述六個固定的行程步驟,以4個“文化人”為核心的組織者等不成文的規定,從而將自身自度化了。
由此觀之,以川南林村天心廟會為代表的更為傳統的廟會因其自身的公共性、非市場性和制度性與鄉村公共性和村莊共同體的重建不謀而合。總而言之,在市場化、村莊空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復蘇傳統廟會本身就是一種鄉村公共性和村莊共同體的重建之路。
參考文獻:
[1] 小 田.“廟會”界說[J].史學月刊,2000,(3).
[2] 吉發涵.廟會的由來及其發展演變[J].民俗研究,1994,(1).
[3] 李永萍,杜 鵬.鄉村廟會的社會整合功能及其實踐特征—基于關中金村廟會的考察[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 ? 2016,(4).
(編輯:李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