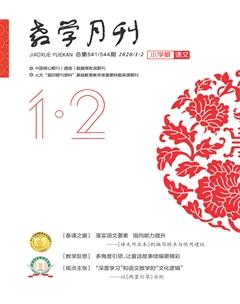順學而導,讓提問策略的學習更有效
高小蓮
【摘 ? 要】《一個豆莢里的五粒豆》作為統編教材新入選的課文,承載了閱讀策略單元的學習任務。教師在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上,需要充分關注新的學情及教學生成,順學而導,幫助和引領學生解讀文本,學習提問策略。
【關鍵詞】提問;閱讀策略;童話
統編教材四年級上冊《一個豆莢里的五粒豆》是童話大師安徒生的作品,編入學習提問的閱讀策略單元。提問對學生來說雖然不陌生,但作為閱讀策略這種語文要素來展開學習,還是第一次。作為該單元的第一篇精讀課文,其課后練習安排學習的內容有二:一是敢于提問,二是針對全文與課文的一部分內容提出問題。如何有效達成提問策略的學習呢?
不能含糊的“地位”
教學中,在安排學生讀完課文后,筆者要求學生試著把自己提出的問題寫下來并在小組內進行交流。結果有個學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課文重點寫了五粒豆中的哪一粒豌豆呢?”小組內討論時意見分歧嚴重,一方認為是“最小的一粒”,另一方認為不是,雙方互不相讓。問題提交全班討論時,筆者讓雙方說出具體的理由。反對的一方認為“最小的一粒”和“最后的那一粒”不是同一粒。細細掂量,才覺得這涉及故事中五粒豆的“地位”,還真是一個不可含糊的問題。于是,筆者決定引導學生帶著問題深入課文進行探尋。
故事開篇寫道“有一個豆莢,里面有五粒豌豆”“豌豆按照它們在家庭里的地位,坐成一排”。這里雖然只用了一句話進行交代,但對后續出現的豌豆的不同表現與歸宿影響很大。畢竟故事里的五粒豌豆不是平均用力描寫的,真正影響故事中小女孩成長的是“最后的那一粒”。也就是說,“最后的那一粒”才是故事的主要人物。那么,“最后的那一粒”到底是這個豌豆家庭里的哪一粒呢?
學生聯系實際說,豆莢里的豌豆數量是五顆,樣貌都是圓溜溜的,不易排序也不易辨認,按照“在家庭里的地位”,本來可以用豆老大、豆老二、豆老三、豆老四和豆老小來稱呼它們,然而課文中并沒有出現類似的排序。從豌豆還在豆莢里時的想法和說法中,能夠找到的指稱是“它們”“豌豆們”或者“它們中的一個”,只有一次出現了有單獨指稱意味的“最小的一粒豌豆”。這個“最小”是從體積上來說的,而且對于其他豌豆,再也沒有出現與體積有關的表達。下文出現了關于豌豆的順序,有“第一粒”“第二粒”“接下來的兩粒”和“最后的那一粒”。這是從豌豆被一個孩子從玩具槍里射出去的先后順序來說的,與它們在豆莢這個家庭里的地位沒有特定的關系。也就是說,那個頑皮的孩子在用玩具槍射出五粒豌豆前,絕對不可能也沒有辦法事先把五粒豌豆按照它們在家庭里的地位進行排序。由此斷定,“最后的那一粒”與“最小的一粒”是從不同的角度說的不同時空里的豌豆,雖然都是“最后的”,但無法確定是不是同一粒豌豆。
課文一開始強調豌豆在家庭里的地位。與兄弟眾多的家庭相似,豆老大所得的養分要優于其他豌豆,長得更飽滿、壯實,其余豆兄弟的生長情況類推,輪到豆老小往往都是“拖著長大的”。課文中出現“最小的一粒豌豆”可能正是由此造成的。這樣的地位必然會影響這些豌豆走向未來的志向,或者說是對“走得最遠”的理解。“現在我要飛到廣闊的世界里去了!”“我將直接飛進太陽里去。”“我們才會飛得最遠呢!”這些說法都體現了一種心理優勢,應該與豌豆在家庭里的地位有一定關系。而“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吧”這一說法展現的卻是一種質樸、實在的心態,與豆老小的地位、境遇相當。可惜的是,課文并沒有以明確的語言來表示這句話就是豆老小說的。
如何確定課文中豌豆的“地位”呢?那就需要對文中的豌豆兄弟予以適當的排序,如用豆老大、豆老小等進行指稱,以使“家庭里的地位”得到具體落實。這樣一來,當它們還在豆莢里發表想法和說法時,就能明確誰在想什么或說什么。在被孩子從玩具槍中射出時,“第一粒”“第二粒”“接下來的兩粒”也應依次改為豆老大、豆老二、豆老三和豆老四,“最小的一粒豌豆”和“最后的那一粒”自然就是豆老小了。因為豆老小在家庭里的地位最低,即便它落在頂樓夾縫里這種缺少養分和水分的惡劣環境里也能夠頑強地生長,進而影響那個住在頂樓、生病躺在床上一年的小女孩,讓她慢慢好起來。探尋到這里,筆者再讓學生想一想:“這個問題是針對全文提的,還是針對部分內容提的?”學生都肯定這是針對全文提出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理解全文的一個關鍵。
安徒生童話是作為經典安排學生學習的。如果翻譯或編輯沒有妥善處理相關的語言表述問題,導致學生理解課文出現偏差,不僅會影響學生學習課文的效果(這種課文內容理解上的偏差可能使他們提出的學習問題偏離閱讀策略學習的要求),而且會打消學生后續閱讀與安徒生有關的整本書的興趣。所以,看上去“地位”不清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問題,但對于學生學習經典來說,也絲毫含糊不得。畢竟學生在學習每一部經典的過程中,只有汲取包括語言在內的豐富營養,才能逐漸形成敬畏經典、致敬經典的良好的閱讀心態,進入由經典營造的美好的閱讀空間,在里面自由翱翔。
問豆?問人?
應該說,確定五粒豆的“地位”還不是課文學習的關鍵所在。這篇課文比較長,先講述了一個豆莢里五粒豆的想法和遭遇,再講一個病重的小女孩在一顆豌豆的陪伴下漸漸好轉起來,最后交代了五粒豆的去向。以這樣比較長的文本來承載“提問”這一閱讀策略的教學,再加上故事內容之間的連貫性看上去不怎么緊密,導致學生在針對全文提問時,不知是就其中的豆來提問,還是就文中的人來提問,同時還出現了“瑣碎問”和“隨便問”的現象。這便是本課學習提問策略需要突破的難點所在。
首先,豆與人,誰才是主要對象?
初讀課文,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故事講了一個豆莢里的五粒豆和住在頂樓的母女,誰才是主要的描寫對象?”從閱讀教學來說,這是一個關于課文內容理解的最基本的問題,不搞清這個問題,后續的學習就無從談起。從提問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針對全文理解提出的問題,回答了這個問題,有助于從整體上把握全文內容。
先從課文題目看。安徒生作為童話高手,非常講究給文章擬題。他的許多童話一說到題目,馬上就讓人想起了其中精彩的內容,如《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鴨》。《一個豆莢里的五粒豆》也是一個容易吸引讀者的題目,原因在于題目中“豆莢里的五粒豆”不是容易發生故事的對象,因此當它成為故事的題目,自然引起讀者關注。換句話說,從題目看,豆應該是故事描寫的主要對象。
再從人物在故事中的表現看。豆從豆莢里成長時,就不斷有自己的想法,如“得做點兒事情”“誰會走得最遠”等,后來被一個孩子當作玩具槍的子彈射出去,落在不同的地方。其中,落在頂樓窗子下面的一個裂縫里的那一粒,在春天里發了芽,長出了嫩綠的豌豆苗,不斷生長之后還開出了紫色的花兒。小女孩出現在故事中時,身體虛弱,躺在床上一整年了(安徒生原文中,她媽媽對她好起來已經沒有信心了),后來窗外長出來的豌豆苗引起了她的關注。豌豆苗不斷生長,給了小女孩信心,并且慢慢陪伴小女孩漸漸好起來(爬起來、坐在床上)。最后小女孩臉上洋溢著健康的光彩,注視著豌豆花,快樂地微笑。不難看出,是故事中的豌豆苗影響了小女孩,小女孩的身體狀況是隨著豌豆苗的生長而變化的。由此可以確定,豆是課文描寫的主要對象。
其次,寫豆,其實也是寫人。
在課文中,既寫了豌豆,又寫了人物。故事中的五粒豆“按照它們在家庭里的地位,坐成一排”,這里需要特別引起注意的是“家庭里的地位”,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說法,但其中包含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畢竟在一個兄弟眾多的家庭中,兄弟之間肯定會有一定的秩序,尤其是老大與老小之間的區別很明顯。在課文描寫的豆兄弟之間,也存在這種區別,“最小的一粒豌豆”無疑是家庭中老小的角色,往往處在一種被忽視的地位,而它的哥哥們都互相爭著出人頭地。雖然“我倒想要知道,我們之中誰會走得最遠”的說法是豆老小提出的,但是,豆哥哥們在被射出玩具槍時紛紛說“飛到廣闊的世界里去”“直接飛進太陽里去”“會飛得最遠”,顯示的正是那種躊躇滿志、志在必得的心理優勢,只有豆老小說的話講求實際:“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吧!”在被射到頂樓、落進長滿青苔的裂縫里并被包裹起來時,它還是這么說。在這種對比中,安徒生把豆老小定位成很腳踏實地的人。也只有這樣的豆,才能在沒有土壤、幾乎沒有養分也缺少水分的頂樓裂縫中求生存。這種生存狀態讓處于人生低谷、艱難生活的小女孩感同身受,并由此產生“好起來”的信心和希望。豆和人就這樣合二為一。
有了以上的理解,可以弄明白的是,課文中無論是豆的故事還是人的故事,都是講逆境中的成長。在成長的主題下,學習運用策略來閱讀課文,所提的問題自然也需要圍繞成長。具體地說,可以從整體和部分兩個不同層面進行提問。學生開始提出的問題不能聚焦主問題或關鍵問題。對此,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行梳理與歸并,使其最終指向能夠促進學生在閱讀中深度思考的主問題。
針對整體內容可以這么提問:“豆莢里的五粒豆中,哪一粒對小女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為什么?”學生帶著這樣的問題閱讀課文,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就能夠把握故事的主要內容,體會課文的思想感情,進而理解童話中的人物形象。
針對部分內容則可以這么提問:“課文為什么重點寫最后一粒豆?小女孩為什么那么關注豌豆苗的生長?”學生在解決這種局部問題的過程中,從不同角度關注故事中人物的命運,厘清人物成長的心路歷程,進而深入理解課文表達的重點,達到以部分聚焦整體的學習功效。
總之,《一個豆莢里的五粒豆》作為統編教材新入選的課文,承載了閱讀策略單元的學習任務。教師在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上,需要充分關注新的學情及教學生成,順學而導,幫助和引領學生解讀文本,學習提問策略。
(安徽省安慶市宿松縣破涼鎮中心小學 ? 24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