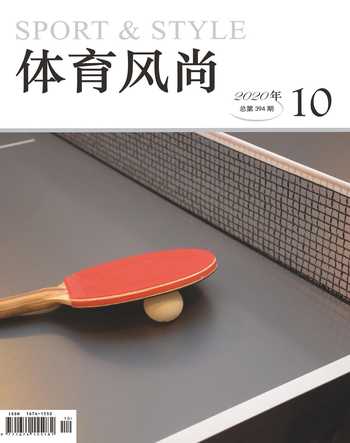高校籃球運動員的體能訓練方法研究
豆林帥
摘要:當前,體能訓練是高校進行籃球運動訓練的基礎工作,通過科學高效的體能訓練能夠有效加強高校籃球運動員的賽場表現,也能有利于提升其競技水平,因此對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方法進行深度研究和創新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文章首先對高校籃球運動員加強體能訓練的必要性進行了闡述,而后對開展體能訓練的具體項目內容和適用方法進行了探討,以期為促使高校籃球運動員的體能水平得到高效提升提供一些參考幫助。
關鍵詞: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
高校籃球運動是一項需要對運動員進行體力訓練和技能提升還有加強其心理素養的綜合型競技項目。籃球運動最吸引人的莫過于賽場上的運動員在競賽過程中通過敏捷移動的步伐和完成各種難度系數大的技能動作來與對方進行周旋、對抗,在變幻莫測的賽場上能具備較強的反應能力,并運用其智謀來及時做到應對解決。體能水平不僅是提升高校籃球運動員技能水平和運動素養的重要基礎,也是體現球隊精神面貌與競技能力的物質前提。高校籃球運動員只有擁有很強的體能才能在賽場上體現出真正的實力。因此,不管是對于籃球專業運動員還是校園運動員來說,在進行訓練活動時應要將體能訓練作為重點項目。但是,通過對近年來高校籃球運動賽場上大學生運動員的場上表現進行觀察,能夠直接看到大多數大學生籃球運動員的體能明顯薄弱,進行長時間的比賽之后明顯體力不支,因而在運動場上難以將自身的技能水平發揮出來,同時也嚴重影響了團隊成績。基于此,本文對改進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的具體內容還有方式進行了深入分析,力求高校籃球運動員的體能水平得到高質量地提升。
一、開展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工作的必要性
(一)強化體能成為運動員參與運動競賽的重要保障
基于生物學的視角下,日常在對高校運動員進行運動訓練時經常增加一些適量的運動負荷刺激,能夠有利于對高校籃球運動員的身體機制進行一些生物改造,通俗來說就是指教練通過長期性和科學性的負荷刺激來促使高校籃球運動員的機體產生一些生理變化,讓其體內身體器官的機能能力得到優化提升,以此來幫助其體能水平得到高效提升,從而從容應對超負荷和超激烈的籃球運動賽事。與此同時,由于高校籃球運動員的體能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因而其身體對負荷刺激的需求量也在逐漸擴大,所以說,開展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的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在查閱大量體育競技運動的實踐資料后能夠得出更堅定的結論,即對籃球運動員施行科學合理和適度的負荷刺激,還有不斷完善其身體機能,都將十分有助于促進籃球運動員的身體體能得到顯著提升。在籃球運動賽場上若是運動員的體能水平十分低下,那么將致使其在競賽過程中難以順利進行防守和攻擊,一旦到了賽事尾聲,有限的體力將難以支撐其堅持繼續比賽,并且還會產生比賽失誤,最后嚴重影響到賽事成績。當然,如若高校籃球運動員具備超強的體能,在比賽過程中就能將技能和運動技巧很好地運用起來,可進行快速移動和搶奪,還將有著很強的反應能力來應對緊急狀況,一旦敵方體力不支,籃球運動員就可憑借自身的體能來占得最大競賽優勢,在籃球賽場上積極抓住機遇來贏得勝利,總而言之,一場籃球比賽到了賽事尾聲拼的就是兩方運動員的體能狀況。
(二)強化體能成為提升高校籃球運動員技術與戰術的基礎保證
眾所周知,美國NBA的競技水平在國際上是一流的,究其原因,除了具備超強的籃球技能之外,就是其擁有非一般的體能和超強的身體素質。NBA的籃球隊伍中有著很多技能高、體能強的優秀隊員,例如赫赫有名的籃球中鋒張伯倫和有著“飛人”稱號的喬丹還有素有“強盜”之稱的博克斯等等,這些優秀的籃球運動員不僅獲得了優異的比賽成績,也收獲了國內外無數的籃球粉絲。與美國NBA的球員相比,我國籃球運動員的體能要明顯薄弱很多。目前,在我國很多高校都尚未重視對籃球運動員進行針對性的體能訓練,例如,高校球隊教練在日常帶隊訓練時,總是會擔任很多工作,除了要教導運動員提升籃球技能,還要帶領其進行身體素質的加強鍛煉,另外籃球運動員的生活雜事也要由其負責,因而無暇抽身也沒有充足的時間對高校籃球運動員進行專業的體能訓練。此外,當前對高校籃球運動員進行體能訓練時所樹立的目標和采用的訓練手段都較為不科學,并且不適用于高校籃球運動員的運動需求,平時對于球隊的訓練力度也過弱,對其體能檢測的相關工作也未合理開展,還有對運動員體能的不足之處也沒有制定行之有效的彌補方案,因而難以促使高校籃球運動員的體能得到高質量地提升。
二、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的詳細內容和有效方式
體能訓練是所有運動訓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指的就是對運動員身體機能進行完善加強和對運動能力進行提升的訓練,通常可劃分成基礎體能訓練還有專項體能的提升訓練,并且將進行專項體能訓練作為主要部分。基于運動訓練的視角下,體能訓練可分為身體形態和身體素質還有人體機能,能夠看出其與身體素質訓練是不太相同的,但是需將身體素質訓練作為整個訓練工作的核心內容,也就是泛指借助科學合理的身體素質訓練來激發出運動員的運動潛能,從而促使運動員充分發揮出最大限度地運動水平。因此,就高校籃球運動員而言,其體能訓練的內容可分為身體素質和機體能力兩大部分,這里面的身體素質包含了力量和彈跳還有速度以及靈敏等幾種訓練內容,基于此,本文展開了論述。
(一)力量素質訓練
對高校籃球運動員進行力量素質訓練時,通常所采取的訓練手段為:(1)最大力量的訓練,即將擴充其肌肉生理橫斷面和提高肌肉內部的協調能力作為訓練目標;(2)負重與不負重的訓練,即激發籃球運動員的速度和力量作為訓練目標;(3)綜合性能力的訓練,即激發運動員的力量承受力作為訓練目標。這些訓練手段的使用方法和關鍵之處也有著很大的差異化,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可劃分為五大種類,即提高最大力量和建設性力量還有將力量提升為爆發力的訓練以及過渡與保持的訓練。在這之中,對運動員進行針對性力量訓練的第一階段應當是建設性力量的訓練,能夠有效為之后訓練工作的開展奠定下夯實基礎,只要高質量完成這個階段的訓練內容就可順利進行下一階段的訓練。提高最大力量的訓練將有利于促使高校籃球運動員肌肉應對最大阻力能力水平的高效提高,也能成為之后為提升運動員快速移動能力和彈跳能力打下堅實的基礎,還可有助于促使高校籃球運動員將其本身具有的力量升級為特定的運動爆發能力,并且通過結合該項運動特征和訓練需求來體現出籃球運動員的極限力量。
保持訓練是指高校籃球運動員進行完以上所有訓練之后能夠將所獲取的力量保持與發展下去,而過渡訓練是指指導高校籃球運動員逐步消除疲憊,以此來讓其身體系統得到有效訓練。因此,高校籃球運動員進行訓練時一定要在一個星期內抽取4天來完成力量訓練,還可將舉重和蹲跳等作為訓練內容,同時也需要進行持續性的對抗阻力的專項訓練。
(二)彈跳素質訓練
籃球比賽是一項變化極大的競技運動,籃球運動員在賽場上需結合實際情況來及時移動位置,以此來爭取得到進攻和投籃的機會,例如在有限的場地里進行前后跑動和左右側換位還有垂直移步等等,這些通常是每個籃球運動員在賽場上要做的移動。通常來說,對籃球運動員進行彈跳力訓練的練習內容主要為跳和連跳還有單腿跳以及全力跳等等,但是在進行真正的訓練活動時,可通過同一位籃球運動員來選擇同一位置,并且采用要與運動風格相符合的移動方式,例如向前移動和筆直移動與向后方移動和向兩邊移動還有不同的轉身移動等等,而且還要讓各項動員進行充分結合,從而來進行訓練。同時,彈跳力量的訓練活動還會被多種因素所制約,例如籃球運動員本身的綜合能力和其潛能認知等等,所以在訓練過程中,要盡力為高校籃球運動員提供很多如同比賽模式的訓練機會,如此一來,既能有利于避免高校籃球運動員滋生厭倦心理,也能有助于其應對一些因重復訓練而產生的問題。除這些之外,雖然大多數運動員都能適應彈跳力訓練,但是針對那些體能很弱的球員,高校籃球教練應結合其特點來合理選用訓練方案。
(三)速度素質訓練
當前,高校籃球運動不僅要求球員在賽場上能夠快速正確的移步,也要求其擁有后退和滑步還有變換方向的綜合能力,在競賽過程中特別是要擁有快速移步的能力來進行攻與防互換。除此以外,高校籃球運動員還要擁有一定的速度耐受能力,在進行這類體能訓練時也包含了快速移動和沖刺跑動。其中快速移動一般都是由400米的距離縮減為100米,并且快速跑動的速度需在沖刺跑動和一般速度跑動這兩者之間,通常沖刺跑動距離大都是控制在60米之內。還有,對加強高校籃球運動員無氧能量供應系統最好的訓練手段即為場地訓練和爬樓梯,這要求各個球員要全力完成這項體能的訓練。此外,在進行速度訓練時還應注意不同訓練模式和移動距離還有反復訓練以及兩組訓練的相隔時間,從而來避免導致高校籃球運動員身體陷入高亢奮狀態。
(四)靈敏素質訓練
在籃球運動中靈敏素質是無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通俗一點來說就是指籃球運動員在賽場上能夠快速移動位置和改變動作,在比賽過程當中需具有很強的反應能力和應變能力,同時也是多種身體素質集中體現出來的綜合能力。因而可以認為,在進行籃球運動的過程之中,基本上所有的籃球技巧都是需以靈敏素質作為前提來發揮出來的,例如移動技術和投籃技術還有防守技術與突破技術以及傳球技術與接球技術等等。所以,高校籃球運動教練在進行日常訓練活動時,應強烈要求和倡導高校籃球運動員多多參與靈敏素質的訓練,以此來提升其賽場反應能力和應對能力還有判斷能力以及轉變能力,另外,通過靈敏素質的訓練還可有效提高運動隊員之間的戰術配合能力和召喚能力還有回應能力等等,以此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投籃機會,從而來贏得優秀的比賽成績。
參考文獻
[1]李立堅.我國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研究[J].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10,18(32):71–73.
[2]蘇程.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研究[J].科技信息,2012(30):320+318.
[3]高亞東,孟麗梅.高校籃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研究[J].才智,2014(12):75.
[4]楊淑英.基于高校籃球運動員的體能訓練研究[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5(01):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