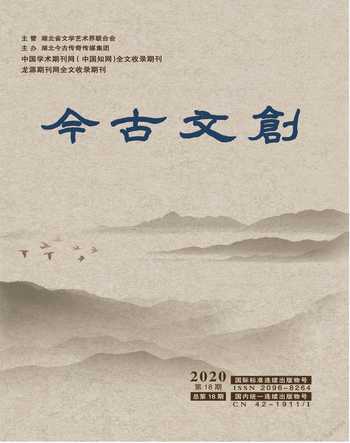古人今論 故事新述
【摘要】 《歷史人物縱橫談》在寫人和敘事兩方面既繼承了傳統史學經典的優點,又能夠結合當代視角和表述習慣進行有益的嘗試。本文主要以此為切入點對這部叢書的史學價值和藝術價值做出簡要分析。
【關鍵詞】 史書;通俗化;寫人;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8-0034-02
龔弘《古人今談》最初在紐約《時代周報》連載,后在臺灣結集出版,與錢穆的《中國歷史精神》、余英時的《史學與傳統》一起被選為臺灣高三以上學生必讀的課外歷史書籍。這部叢書后經齊魯書社在內地刊印,重新定名為《歷史人物縱橫談》,推出后獲得了廣大讀者的認同和喜愛。
《歷史人物縱橫談》語言融通俗和典雅為一體,人物個性鮮明,事例安排得當,既能夠尊重原著典籍的客觀性,又能夠照顧到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仔細探究,其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突出個性 隱寓褒貶
自《史記》出,以人物傳記為主的著史模式便成為中國史學典籍最為重要的創作傳統之一,《歷史人物縱橫談》在這一點上有所繼承亦有所演變。與傳統的史學著作相比,龔弘塑造歷史人物時更注重其主要個性特性并在大量篇章中以此作為標題和主線。如《劉邦的“能忍”與“用詐”》一文,跳出傳統人物傳記以時間為線的模式化寫法,著重突出了劉邦在奪取天下的過程中對“忍”與“詐”的運用。全文分為四個小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劉邦用計娶得富家女子,并和自己的妻子合謀演繹了“天命所歸”等若干傳奇故事。第二部分則描繪了楚漢相持廣武時劉邦要害受傷卻假裝傷的是足趾以安定軍心的細節。這兩個故事都是為論證劉邦的善于“用詐”服務的。第三部分以鴻門宴和“坐視父難”為例說明了劉邦的“能忍”。第四部分綜合論述劉邦“忍”與“詐”相濟為用的“機變靈活”,并以張良對劉邦的評價作為佐證。全文精煉短小,但因人物個性鮮明又在各個部分分別以具體歷史事件作為例證,故顯得客觀而豐滿。
再如,正統史書對漢武帝的書寫大多集中于其好戰與好神仙方術,龔弘則集中論述了他的“多欲”。因多欲而寵幸衛子夫帶出衛氏外戚中的衛青與霍去病,同樣因多欲寵幸李夫人便連帶著重用其兄李廣利、李延年,這兩部分作者雖未明確剖析卻也是隱含有褒貶之意的。同樣出自外戚之家,前者功彪史冊,后者遺臭萬年。同樣源自“多欲”,從結果而言,一個是功,一個是過。那到底是功是過呢?若究武帝本身的動機而言,他的親疏好惡原本與家國大事無關,只不過是對身邊女子好惡的延伸而已,因而也就不能以結果論功過。最后一個部分,作者重點講述了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從而進一步點明了武帝一生行徑“多欲”的本質,既一切從自身欲望出發,衛氏家族悲慘的結局便順理成章。之前的寵幸源自女子的美貌和武士的功勛,而非帝王的真情和睿智,那么當他們成為阻擋武帝滿足更多欲望的勢力時,覆滅就是必然的結局。正因如此,文中事件的選擇實暗含著對武帝“多欲”的譏諷之意。
二、兩兩相對 各有千秋
自《史記》始,合傳的形式便在史書中運用甚廣,龔弘沿用了這種形式并加以擴展和延伸。《歷史人物縱橫談》中直接以兩位相關人物作為傳主命題的篇目甚多如《佐劉興漢蕭何張良》《降與不降李陵蘇武》《一莊一諧汲黯東方朔》《黃霸張敞各有千秋》等等。相對《史記》中生平經歷互相關聯的合傳標準,龔弘的角度則顯得更為開闊。
蕭何張良合傳既是因為他們同是輔助劉邦追逐天下的重要謀臣,又同樣深諳功成身退的謙抑之術,因此方能在劉氏大規模誅殺功臣的背景下得以善終。如果說《佐劉興漢蕭何張良》一文更多選取的是傳主的一致之處,《降與不降李陵蘇武》則從相反的角度入手。李陵投降匈奴原有許多不得已處,加之司馬遷和李廣一門的遭際,故世人多給予同情。然本文從深層次的內在價值追求對二人進行比較,得出李陵“功利觀念太重”而蘇武“爭的是一個國格”的結論,高下立現。
汲黯和東方朔在《史記》中并沒有太多直接關聯,作者卻能從他們同樣“好為諫言”入手加以辨析。汲黯是耿直切諫,既不懼權貴亦不曲意迎合上意,東方朔的進言方式則靈活多變,顯得既富于生活情趣又蘊含著保全自身的智慧。治世需要勇于進言的諫官,同時也需要能夠納諫的明君,汲黯和東方朔合傳正見證了武帝英明寬廣的一面。
衛青與霍去病同為武帝時名將,同為外戚,又都是私生子出身,卻在行軍戰略和為人處事上有許多不同處,作者從他們一個久居人下一個生來貴胄的角度加以辨析,便使得讀者可以在了解二人個性差異的同時又能夠明白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
除了上述這一類直接可從標題中看出比較之意的作品外,書中尚有一些比較是潛藏在文本之中的。《項羽短促的一生》結尾處用劉邦的《大風歌》和項羽的《垓下歌》作比,揭示項羽的個人英雄主義婦人之仁正是導致他失敗的深層原因。《幸運兒司馬相如》一文開頭從同姓的角度入手對同為武帝朝重要人物的二司馬進行比較,點出司馬相如“幸運兒”司馬遷“背運人”的不同遭際。雖未直接嚴明,讀者卻也可以從他們不同的人生經歷中見到偶然性對人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生本身包含的荒誕性,寓情于事,正是從“史”向“文”過度的必然選擇。
三、古人今論 直指內心
除了對人物個性重點提煉以及通過對比突顯其主體特征外,摻入當代因素剖析人物內心世界亦是《歷史人物縱橫談》一書的重要特性。
《多欲的漢武帝》在上文中已做簡要分析,這里面就包含著不以成敗論英雄和不以結果看功過的較為當代歷史觀。
除了不同于古人的歷史觀之外,龔弘還在很多篇章中套用現代心理學中的“情意結”解讀古代人物。“套句現代語,項羽的情意結,不過是夸耀自己,榮譽感失,生命亦可失”,對項羽而言,這正是切中痛處。
從垓下突圍到“欲渡”烏江來看,項羽的種種行徑明顯地是有求生欲望的,既如此,何以到了生機已現的烏江邊上,又是“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的絕好條件,項羽反倒放棄了生存的機會主動選擇了死亡。正如龔弘所言,項羽是一個把榮譽感看得比性命重要的人,如果即將面對的是天下人同情可憐的目光,對他而言正是無法忍受的屈辱,如果“能忍”,項羽也就不是項羽了。后文中的以烏騅馬“賜”烏江亭長,又以自刎的形式而將自己的頭送于“故人”呂馬童,并點明“吾為若德”,正是為反轉自身被動處境而激發出的主動行為。李清照詩曰“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不肯”二字正是項羽人格的流光溢彩處。
如果說,項羽個人英雄主義的“情意結”是從貴族出身、少年得志、前半生過于順利而來的話,王莽喜好作偽的“情意結”則是從“幼年的自卑情緒發展出來的”。由于父親早逝,自己又有相貌上的缺陷,王莽只能靠偽裝自己來謀奪地位,“他的偽裝和自我宣傳做得非常成功,后來果然使他做到了大司馬。朝廷上對權勢的諂媚,和民間盲目的崇拜,讓他跌進了自己虛妄的偽像之中,而竟信以為真。”這正是“自欺欺人”的典型注解,以至于篡奪帝位之后,王莽的復古改制便表現為種種不合時宜的悖逆。依靠表演可以獲得一時的成功,但當一切行為必須落到實處時,越是身處高位,自身的虛空越是會被歷史無限放大。
四、刪繁就簡 故事新述
閱讀古史原典的過程中,篇幅浩繁是一個明顯的障礙,以至于許多人有立志讀書的欲望,卻沒有堅持讀書的勇氣。加上史書為了遵循客觀性的原則,必然有些流水賬般的內容,這些內容作為專業研究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作為普通大眾的閱讀對象而言,大多枯燥乏味,讀來如同嚼蠟虛耗時光。故而在古史通俗化的過程,對內容進行有效的裁剪便是一項比較重要的工作。
史書中的傳記大多是以時間發展為線索的,加上群體利益和個人價值的雙重標準之間很多時候又必須以后者服從前者為標尺,所以內容上的重復與對塑造個人形象無意義的羅列在史書中屢見不鮮。本書作者在述史過程中對流水賬式的記述大多棄之不用,而對重要事件則進行了二次篩選和加工。如劉邦在書中就分為“平民皇帝”和“能忍與用詐”兩個獨立篇章來塑造,而王莽則用了“一生作偽”“情意結”“假社會主義者”三個角度來綜合展示,這樣把傳主提煉為若干個性特征的綜合體,既有助于讀者快速認知,也容易為傳主一生中的相關事件找到內在聯系。
如此一來,不僅可以使我們“知事”而“知得失”,更可以“知人”而“知因果”,兩相結合相濟為用,對我們解讀包括《史記》在內的古史原典多有助益。
五、結語
龔弘《歷史人物縱橫談》對傳統史書處理“事”與“人”的手法加以繼承和發揚,使得“事不繁雜”而“人格凸顯”,加之語言文白相雜,古雅與新意并存,從而獲得了古史通俗化的成功經驗。這部叢書在講述歷史故事、解析歷史人物的過程中,既有史學著作最基本的客觀與嚴謹,又有通俗作品應該具備的簡潔與新穎,兩者疊加,正是史學著作推廣的不二途徑。
參考文獻:
[1]龔弘.歷史人物縱橫談[M].濟南:齊魯書社,2005.
[2](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清)姚祖恩.史記菁華錄[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
趙玲,女,漢族;學位:碩士;學歷:研究生;職稱: 副教授 ;研究方向:古代文學、詩詞。單位:遵義師范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