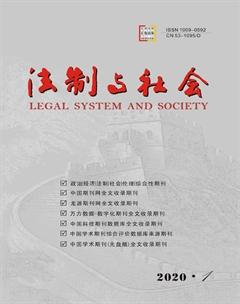《國(guó)際法學(xué)》SPOC和MOOC模式教學(xué)實(shí)效對(duì)比研究
孫傳香 姚彩云
關(guān)鍵詞SPOC MOOC 教學(xué)實(shí)效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及其他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的發(fā)展,傳統(tǒng)教學(xué)模式面臨愈來(lái)愈多的技術(shù)瓶頸與挑戰(zhàn)。作為“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兩種主要新型教學(xué)模式,MOOC(大規(guī)模開(kāi)放在線課程)與SPOC(小規(guī)模限制性在線課程)極大地促進(jìn)了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的變革與創(chuàng)新。基于高校教育改革的宏大背景,以實(shí)證方式對(duì)前述兩種教學(xué)模式的教學(xué)實(shí)效進(jìn)行對(duì)比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jià)值與實(shí)踐意義。
一、對(duì)比實(shí)證研究的目標(biāo)及前期準(zhǔn)備
(一)對(duì)比實(shí)證研究的目的
作為兩種不同的教學(xué)模式,SPOC和MOOC在其本質(zhì)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但同時(shí)亦存在不少區(qū)別。其聯(lián)系表現(xiàn)為兩者均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均需借助于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實(shí)施;區(qū)別則體現(xiàn)在產(chǎn)生時(shí)間、受眾范圍、資源建設(shè)、師生互動(dòng)以及教學(xué)實(shí)效等方面。為了從實(shí)證角度辨析SPOC和MOOC的區(qū)別,筆者在湖南人文科技學(xué)院組織開(kāi)展了此次對(duì)比研究項(xiàng)目。
(二)對(duì)比實(shí)證研究的前期準(zhǔn)備
為保證實(shí)證研究結(jié)論的客觀性,筆者在實(shí)施本項(xiàng)目前做了充分的前期準(zhǔn)備。首先,本次實(shí)證研究爭(zhēng)取到了湖南人文科技學(xué)院教務(wù)處以及法學(xué)院的大力支持,教務(wù)處為本次實(shí)證研究提供了實(shí)施本項(xiàng)目的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法學(xué)院提供了部分經(jīng)費(fèi);其次,為了取得完整的客觀對(duì)比數(shù)據(jù),本次實(shí)證研究分別組建了MOOC組和SPOC組研究團(tuán)隊(duì);再次,湖南人文科技學(xué)院信息中心與信息學(xué)院為本次研究組建了一個(gè)3人技術(shù)小組,專門負(fù)責(zé)本次實(shí)證研究所需的視頻制作和網(wǎng)絡(luò)維護(hù);最后,為了使學(xué)員能夠全程且完整地參與本次活動(dòng),從而得出客觀真實(shí)的研究結(jié)論,本次實(shí)證研究決定將教學(xué)內(nèi)容確定為《國(guó)際法學(xué)》中“國(guó)際法淵源”的中英文雙語(yǔ)教學(xué),實(shí)驗(yàn)時(shí)間為一周,包括注冊(cè)、教學(xué)實(shí)施及實(shí)效測(cè)評(píng)等全過(guò)程。
二、具體實(shí)施
(一)招生
MOOC組:為了突出MOOC教學(xué)模式的“大規(guī)模”的特點(diǎn),更廣泛的吸引學(xué)員申請(qǐng),MOOC組研究團(tuán)隊(duì)在本次實(shí)證研究中進(jìn)行了充分的前期宣傳,一方面,通過(guò)法學(xué)院網(wǎng)站發(fā)布了MOOC招生公告,另一方面,研究小組在學(xué)校學(xué)生食堂、致遠(yuǎn)樓以及陽(yáng)光公寓等學(xué)生主要集散地進(jìn)行了海報(bào)宣傳。至報(bào)名截止日,共有327名學(xué)員完成申請(qǐng)并注冊(cè),這些注冊(cè)者既有校內(nèi)的,也有校外的,甚至有少量外省學(xué)員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報(bào)名參加。盡管MOOC組未要求學(xué)員的注冊(cè)門檻,但為了便于研究并盡可能得出客觀結(jié)論,我們要求注冊(cè)者如實(shí)填寫基本情況。從學(xué)歷結(jié)構(gòu)來(lái)看,注冊(cè)學(xué)員包括在校中學(xué)生、本科生、碩士研究生以及部分社會(huì)在職人員。
SPOC組:為保證學(xué)員質(zhì)量,SPOC組決定“就地取材”,將招生范圍限制在湖南人文科技學(xué)院校內(nèi),主要面向法學(xué)院法學(xué)專業(yè)學(xué)生,同時(shí)考慮吸納其他專業(yè)或其他院系少量綜合素質(zhì)較高的學(xué)生。經(jīng)過(guò)為期一周的報(bào)名工作,SPOC組本次活動(dòng)共收到62份申請(qǐng),依據(jù)此前設(shè)定的入學(xué)條件,包括要求申請(qǐng)者英語(yǔ)水平至少為通過(guò)大學(xué)英語(yǔ)四級(jí)、大學(xué)二年級(jí)以上以及人文社科類學(xué)生等,最后有36名學(xué)生符合條件,獲準(zhǔn)參加本次SPOC教學(xué)實(shí)證研究活動(dòng)。
(二)教學(xué)實(shí)施
1.周一周二(2019年下學(xué)期第7周):學(xué)員平臺(tái)學(xué)習(xí)
雖然本次實(shí)證研究分別建有MOOC教學(xué)網(wǎng)站和SPOC教學(xué)網(wǎng)站,但為了凸顯MOOC與SPOC的共性與特性,兩個(gè)比對(duì)研究小組利用的網(wǎng)絡(luò)教學(xué)資源完全相同,同時(shí),我們均要求MOOC學(xué)員和SPOC學(xué)員對(duì)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的內(nèi)容進(jìn)行學(xué)習(xí)。不同的是,按照SPOC課程教學(xué)理念,我們?cè)诎才臩POC組學(xué)生進(jìn)行自主學(xué)習(xí)前進(jìn)行了針對(duì)性的指導(dǎo),要求SPOC學(xué)員在學(xué)習(xí)平臺(tái)資源時(shí),注意分辨學(xué)習(xí)內(nèi)容的重點(diǎn)與難點(diǎn),對(duì)理解不夠到位的內(nèi)容進(jìn)行標(biāo)識(shí),要求帶著問(wèn)題走進(jìn)教室。與此形成對(duì)比的是,由于MOOC組教學(xué)規(guī)模過(guò)于龐大,無(wú)法在正式教學(xué)前組織面對(duì)面的線下課堂環(huán)節(jié),因此未對(duì)MOOC學(xué)員作出類似SPOC學(xué)員的課前學(xué)習(xí)指導(dǎo)。兩組學(xué)員的平臺(tái)學(xué)習(xí)時(shí)間均定為2019年下學(xué)期第7周周一周二兩天時(shí)間。
2.周三周四(2019年下學(xué)期第7周):MOOC學(xué)員繼續(xù)線上學(xué)習(xí);組織SPOC學(xué)員參加線下教學(xué)活動(dòng)
隨后兩天,MOOC學(xué)員繼續(xù)在線上學(xué)習(xí)平臺(tái)資源,SPOC學(xué)員則按事先安排到致遠(yuǎn)樓208教室參加線下教學(xué)活動(dòng)。36名SPOC學(xué)員趕到指定教室后,教師將36名學(xué)生分成六組進(jìn)行分組討論,討論結(jié)束后主講教師要求每組將本組學(xué)員反映的問(wèn)題進(jìn)行匯總并上交。教師對(duì)學(xué)員提出的問(wèn)題進(jìn)行匯總歸納后,將學(xué)員問(wèn)題總結(jié)為三個(gè)主要問(wèn)題:(1)在所提供的案例“普魯士拿捕三艘丹麥商船案”中,清朝政府為什么能以惠頓的專著作為主張權(quán)利的依據(jù)?(2)《國(guó)際法院規(guī)約》第38條規(guī)定是否窮盡了所有國(guó)際法淵源?(3)國(guó)際法淵源是否像國(guó)內(nèi)法淵源一樣具有位階性?除上述三個(gè)帶有普遍性的問(wèn)題外,還有七個(gè)只有個(gè)別或少數(shù)同學(xué)提的問(wèn)題。
針對(duì)前述三個(gè)問(wèn)題,主講教師首先從有與無(wú)、抽象與具體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引導(dǎo)學(xué)生思考而并不急于正面回答,進(jìn)一步激發(fā)學(xué)生的思維興趣。在主講教師抓住學(xué)生的興趣后引出“國(guó)際法的淵源”,繼而引述《國(guó)際法院規(guī)約》第38條的規(guī)定。其他不具有共性的問(wèn)題則在課堂講解中順帶解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課堂教學(xué)實(shí)效,彰顯SPOC教學(xué)模式的優(yōu)勢(shì)。
(三)周五(2019年下學(xué)期第7周):測(cè)評(píng)
本次測(cè)評(píng)共設(shè)置了10個(gè)題,其中六個(gè)單選題,兩個(gè)多選題以及簡(jiǎn)答題及案例分析題各一個(gè),滿分為100分,時(shí)間為4Jo分鐘。出于可比性考慮,MOOC組學(xué)員與SPOC組學(xué)員均在相應(yīng)的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上完成測(cè)試。測(cè)評(píng)結(jié)束后按統(tǒng)一評(píng)分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評(píng)分。
三、實(shí)施效果分析及啟示
評(píng)分結(jié)束后統(tǒng)計(jì)發(fā)現(xiàn),327名MOOC學(xué)員有261名參加了考試,最高分為8=3分,最低分為24分,平均分為52.7分,及格人數(shù)為129人,占參加考試人數(shù)的49.4%;36名SPOC學(xué)員全部參加了考試,最高分為89分,最低分為66分,平均分為71.3分,36名學(xué)員全部及格。從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來(lái)看,SPOC教學(xué)實(shí)效明顯優(yōu)于MOOC教學(xué)模式,其原因可歸結(jié)為以下幾點(diǎn):首先,從學(xué)習(xí)態(tài)度來(lái)看,MOOC學(xué)員由于沒(méi)有相關(guān)制度約束,松懈散慢現(xiàn)象十分嚴(yán)重,導(dǎo)致只有占總注冊(cè)人數(shù)的79.8%的學(xué)員參加考試,有超過(guò)20%的學(xué)員沒(méi)有放棄了測(cè)評(píng)考試;其次,從學(xué)習(xí)效果來(lái)看,MOOC學(xué)員及格率不到參考人數(shù)的一半,而SPOC學(xué)員及格率高達(dá)100%。最后,從卷面分?jǐn)?shù)的構(gòu)成來(lái)分析,MOOC學(xué)員與SPOC學(xué)員的選擇題得分相差較小,而包括簡(jiǎn)答題和案例分析題的差距則較大。此外,MOOC學(xué)員在主觀題中有較明顯的抄襲痕跡,而SPOC學(xué)員在主觀題中更多地表達(dá)了個(gè)人觀點(diǎn)。
四、差異性分析
從上述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可以看出,無(wú)論是學(xué)員學(xué)習(xí)態(tài)度、學(xué)習(xí)效果還是測(cè)評(píng)卷面分析,SPOC學(xué)員均優(yōu)于MOOC學(xué)員,反映出較明顯的差異性。要明確存在這種差異性的原因,需要洞察SPOC與MOOC兩種不同教學(xué)模式的差異性。應(yīng)該說(shuō),SPOC經(jīng)由MOOC發(fā)展而來(lái),因此,SPOC與MOOC具有一定的共性,譬如,兩者均基于課程與教學(xué)論,均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和移動(dòng)智能技術(shù)發(fā)展而來(lái),都要利用現(xiàn)代化教育技術(shù)與手段。一般來(lái)說(shuō),共性不是導(dǎo)致結(jié)果出現(xiàn)差異性的原因,經(jīng)過(guò)團(tuán)隊(duì)成員的全面分析后發(fā)現(xiàn),上述差異化的結(jié)果主要源白以下幾個(gè)方面:
第一,MOOC平臺(tái)在追求資源共享的同時(shí)無(wú)法兼顧教學(xué)質(zhì)量。“不設(shè)先修條件”以及“沒(méi)有規(guī)模限制”是MOOC締造者的得意之處,但MOOC這種寬口徑入學(xué)模式直接導(dǎo)致其注冊(cè)率高而完成率低的嚴(yán)重弊端。與之不同的是,SPOC對(duì)學(xué)生的注冊(cè)嚴(yán)格把關(guān),控制注冊(cè)人數(shù)的規(guī)模,因此,SPOC注冊(cè)學(xué)員一般均能保障一定的學(xué)習(xí)時(shí)間并能自始至終堅(jiān)持下來(lái)。
第二,MOOC平臺(tái)的授課教師以及授課方式并未嚴(yán)格按MOOC理念執(zhí)行。有些教師仍然沿用傳統(tǒng)方法,不愿在教學(xué)資源上下功夫,到頭來(lái)是換湯不換藥,正如學(xué)者所言,基于認(rèn)知主義的傳統(tǒng)學(xué)習(xí)方式依然盛行,而建構(gòu)主義和行為主義的學(xué)習(xí)理念無(wú)法得以貫徹與實(shí)施。由于規(guī)模較小,SPOC的授課教師均通過(guò)“精挑細(xì)選”后產(chǎn)生的,其課件、教學(xué)視頻等教學(xué)資源均有較好的質(zhì)量保障。
第三,線下討論與面授環(huán)節(jié)相結(jié)合是SPOC的制勝法寶。在MOOC教學(xué)模式中,學(xué)員的中心任務(wù)就是通過(guò)MOOC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進(jìn)行學(xué)習(xí),由于相關(guān)教學(xué)資源可以反復(fù)播放或閱讀,學(xué)員沒(méi)有學(xué)習(xí)壓力,有些學(xué)習(xí)任務(wù)一壓再壓,“明日復(fù)明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SPOC模式則不一樣,除了線上學(xué)習(xí)環(huán)節(jié),SPOC學(xué)員還要參加線下討論環(huán)節(jié),如果不完成線上學(xué)習(xí)環(huán)節(jié),線下討論環(huán)節(jié)也就無(wú)計(jì)可施。特別是,MOOC學(xué)員由于沒(méi)有機(jī)會(huì)與教師面對(duì)面交流,線上學(xué)習(xí)環(huán)節(jié)的疑問(wèn)可能得不到解決,最終只能“蒙混過(guò)關(guān)”,而SPOC學(xué)員可以利用線下交流學(xué)習(xí)的機(jī)會(huì)與學(xué)員一起討論,向教師請(qǐng)教,從而提高學(xué)習(xí)實(shí)效。
五、結(jié)語(yǔ)
本次實(shí)證研究充分表明,作為MOOC的“替代產(chǎn)品”,SPOC顯露出了諸多優(yōu)勢(shì),除其他外,嚴(yán)格的管理制度與線下交流討論環(huán)節(jié)應(yīng)該是SPOC在與MOOC較量中勝出的主要原因。本次實(shí)證研究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gè)意外收獲,那就是,學(xué)校教育的重要性在這次實(shí)證研究中得到了實(shí)證,互聯(lián)網(wǎng)教學(xué)平臺(tái)雖然有其優(yōu)勢(shì),但終究無(wú)法替代教師與學(xué)生“面對(duì)面”的課堂討論與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