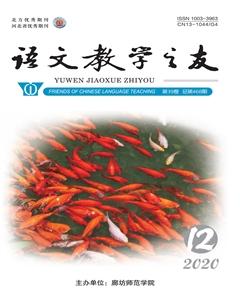核心素養視域下建構審美語言的質感
吳豐強 朱華華
摘要:“語言的建構與運用”是語文學科的核心素養之一,建構又是運用的前提,這就涉及到建構什么樣的語言、如何建構語言的問題。語文教師應該引導學生開放自己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在富有質感的文字中與世界零距離接觸,在體悟中建構自己的語言質感,進而調動五感,用富有質感的語言來呈現世界。
關鍵詞:核心素養;建構;審美;語言;質感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新增了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即“學生在積極的語言實踐活動中積累與構建起來,并在真實的語言運用情境中表現出來的語言能力及其品質;是學生在語文學習中獲得的語言知識與語言能力,思維方法與思維品質,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綜合體現。”新課標還明確指出:“語言建構與運用是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基礎,在語文課程中,學生的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都是以語言的建構與運用為基礎,并在學生個體言語經驗發展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引導學生有效地建構與運用語言是培養學生語文核心素養的基礎與根本,而建構又是運用的前提,這就涉及到建構什么樣的語言、如何建構語言的問題。
語言不只是傳輸信息的工具,還應具備動人心弦的美感。語言的美感有很多特征,而質感則是不可忽視的特征之一。《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質感指藝術品所表現的物體特質的真實感。”也就是說質感是借用語,“若從專業角度講,質感是指視覺或觸覺對不同物態如固態、液態、氣態的特質的感覺。在造型藝術中則把對不同物象用不同技巧所表現把握的真實感稱為質感。”簡潔地講,質感就是“指雕塑、繪畫等藝術品所表現的物體的物質真實感。”質感比狹義的形象更形象,更具真實感。繪畫雕塑依靠視覺,最早依靠形象來表達,隨著藝術探索的深入,真實性已由形象的逼真進入物質的逼真。繪畫雕塑使用的媒介就是物質,充分發揮媒介的物質特性是藝術實現質感,也即實現真實感的重要途徑。而語言是非物質的,要想實現質感就必須捕捉物質經由感官所引起的感覺經驗。所以語言的質感最基本的涵義就是語言的感官化,如語言的音響感、色彩感、觸摸感等等。
一、借助音響感建構審美語言的質感
在描繪人物時,學生往往提筆就是眉、眼、嘴、臉地一一道來,這其實是一種思維的惰性。真正高明的作家一定尊重生活的真實,注重審美質感的追求。
蕭紅是追求語言質感的高手,在《呼蘭河傳》中她這樣展現王大姐的形象:“她是很能說能笑的人,她是很響亮的人。”王大姐,在“我”的院子里是個響亮的人物,這個“響亮”一詞傳神,非常富有質感。表面看起來,“響亮”似乎是指王大姐說話聲音清晰洪亮,但這個詞實際上把王大姐整個人的特點寫了出來。王大姐健壯、開朗、熱情,身上有一股勃勃的生氣。而且王大姐在這個院子里得到人們的夸贊,名氣也響亮。蕭紅用一個音響詞語把一個人物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活靈活現。
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在《寫于安娜·阿赫瑪托娃100周年誕辰》中寫道:“嚴酷的脈搏猛擊著,血液的激流鞭打著,鐵鍬均勻地敲打在它們之中,通過溫柔的繆斯產生。”布羅茨基高度稱贊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并指出女詩人詩歌中還有一種異樣的聲音,用“嚴酷的脈搏猛擊著,血液的激流鞭打著”兩句詩來形容可謂非常形象,但是因為不能產生物質性的聲音,不能讓我們感受那是一種什么樣的聲音,而“鐵鍬均勻地敲打在它們之中”,迅速讓我們真切聽到了阿赫瑪托娃這溫柔的繆斯,有時為了抵抗黑暗,不得不發出鐵鍬敲打一樣的剛硬的聲音,那種比寶劍更原始質樸的金石之聲,布羅茨基借助音響感讓盛贊之辭充滿了質感,充滿了撞擊心靈的力量。
學生龍樂昕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喜歡在慢跑的時候聽書,塞上耳機,讀書聲緩緩地淌進耳朵里,雙手在夜風中吹得有些冰涼。”筆者建議其將“緩緩地”改為“潺潺地”,此時寫的是聲音,用“緩緩地”缺乏語言的質感,缺乏語言的聲響感,而改為“潺潺地”以擬聲詞寫聲音,能增加語言的質感。
借助音響感能很好地建構審美語言的質感,因為聲音是在空間中流動的,有利于增加語言的空間感,營造意境。中國詩人喜歡“以聲寫靜”亦可以說明這一點。“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是“以聲寫靜”的名句,詩人將人類通過聲音更深地感受寧靜的感覺經驗寫了出來,使得整個詩句透露出寧靜的美感,特別是這個“幽”字,不僅是靜,而且有深邃的空間感,詩的意境也因這空間感而生成。
二、借助色彩感建構審美語言的質感
許多心靈的感覺非常抽象,必須通過物質化地呈現才能讓人感受得到,而借助充滿色彩感的畫面則能化抽象為具體,增強語言的質感。
楊萬里的《八月十三日望月》開頭兩句寫道:“才近中秋月已清,鴉青幕掛一團冰。”“鴉青”是鴉羽的顏色,黑而帶有紫綠光,用鴉羽的顏色比喻天幕,不僅色彩有層次,而且表現出了天幕的羽絨質地。用“冰”比喻月亮,不僅表現出潔白的色彩,而且傳達出一種寒意。中國詩人喜歡以物色模仿色彩,不僅為了形象逼真,更是為了傳達一種質感,使色彩詞語意義超出色彩。比如“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這個“銀”和“冰”一樣,不僅僅是比喻色彩,還傳達出心靈的感覺,這種抽象的心靈感覺因為物色而有了某種質地。
卡爾杜齊的名句“那田野綠色的寂靜”,博爾赫斯對其曾經有過精彩的解讀:“卡爾杜齊改變了形容詞位置,他應該這樣寫:‘綠色田野的寂靜。”有一點是博爾赫斯沒有表達出來的,那就是“那田野綠色的寂靜”并不等于“綠色田野的寂靜”。“綠色田野的寂靜”沒有任何創造,而“田野綠色的寂靜”則增加了讀者對于寂靜的經驗。用綠色形容寂靜,這種田野的寂靜就變得可視,并且從綠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寂靜的和平、生機以及美。
巴爾扎克的《驢皮記》中這樣形容桌布:“白得像一層新落的雪”。如果只說桌布像雪一樣的白,就沒有語言的質感,因為這里的“雪”是抽象的,“一層新落的雪”才使“雪”具有了實實在在的物質性,而且顯得那樣清新,那樣潔白。
色彩詞語經常用來增強抽象事物的物質感,比如我們在評價時代時,會用“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這些富有色彩的詞語,使我們對于時代有了一種類似于物質性的認識。
三、借助觸摸感建構審美語言的質感
中國文人喜歡觀照世界,其實僅僅通過“觀”的方式感知外界是不夠的,我們還可以調動更多的感官去體察萬事萬物,比如撫摸世界,與世界零距離接觸。
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的《晚安》中寫道:“門閂撥開,一窩鋒利的光/剖開了庭院。”希尼詩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景,一家人在廚房吃飯,有人在院前叫門,母親打開廚房門準備去開院門,廚房里的燈光一下子鋪展到黑暗的庭院。希尼對此時這種光與影的對比非常有感覺,于是其選擇“鋒利”這個帶有觸感的物質性詞語將燈光在庭院黑暗中的強度和力感傳達了出來,并以“剖”這個動詞暗示燈光的鋒利近似一把刀。
洛爾迦在《西班牙憲警謠》中寫道:“黑橡膠似的寂靜/和細沙似的恐怖。”寂靜是心靈的感覺。很多詩人寫過寂靜,而洛爾迦寫的寂靜首先賦予寂靜以物質性的顏色——黑色,讓人感覺這種寂靜的黑色恐怖,但這還不是洛爾迦高妙的地方,洛爾迦把寂靜物質化為無法洞穿的黑橡膠,把恐怖物質化為無處遁藏的密密的細沙,如此則把寂靜、恐怖的感覺具象化了,從而使語言充滿了質感。
美國詩人加里·斯奈德在《八月中旬在蘇竇山瞭望臺》中寫道:“我記不得我曾經讀過的東西/幾個友人,可他們都在城里/從鐵皮杯中飲著冰冷的雪水/透過高爽寧靜的空氣/極目眺望遠方。”在斯奈德筆下,冰冷的雪水和高爽寧靜的空氣都是極為新鮮的體驗,它們使詩人忽略了八月的暑熱。怎么表達雪水的冰冷呢?僅靠“冰冷”這個形容詞是不夠的。詩人有意識地用“鐵皮杯”這個具體之物使冰冷的感覺物質化,使人從中感受到一種堅硬之冷,一種厚重之冷,一種具有審美質感的冷。
日本詩人喜歡在細微的事物上深入體悟,借助身體的觸摸感建構語言的質感更是其慣常使用的途徑。比如,尾崎紅葉的《黃鶯》中寫道:“竹里黃鶯足脛寒”。很多詩歌寫黃鶯時注重色與聲,讀者獲得的是外在的美感。而尾崎紅葉用身體去感受,所以其感受到黃鶯露出的足脛,在竹枝上接觸到的寒冷,借用一個成語,那就是“感同身受”。這種感受讓讀者獲得與物血肉相連的體驗,由審美進入了情懷。
中國詩人也不乏借助身體的觸感建構語言質感的佳作。比如,馮延巳的《拋球樂》中寫道:“波搖梅蕊當心白,風入羅衣貼體寒。”溫庭筠的《商山早行》中寫道:“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這兩句詩,都是寫寒意,一個通過身體,一個通過腳板,形成觸摸的感覺經驗,這樣的寒意完全是身體的,不是想象的,具有質感。
除了調動聽覺感知聲響、調動視覺感知色彩與畫面、調動觸覺感知冷暖軟硬,作者還可以調動嗅覺感知芳香。比如,王安石的《梅花》中寫道:“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作者可以調動味覺感知酸甜。還有楊萬里的《閑居初夏午睡起·(其一)》中寫道:“梅子流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亦有很多的詩文在追求語言的質感時打通了五感,綜合性地調動各種感官,甚至打通感官之間的界限,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通感”。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學習語言也是如此。但何為上乘的語言,學生未必清楚。絢爛華美、新奇異質的語言通常被學生奉為上乘,這無疑是窄化、甚至矮化了語言。作為語文教師,需要引導學生開放自己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在富有質感的文字中與世界零距離接觸,在體悟中建構自己的語言質感,進而調動五感,運用富有質感的語言來呈現世界,徹底地把語言從粗糙的、抽象的、概念化的泥淖中拯救出來,讓語言呈現出審美的、具體的、富有質感的真實滋味,才是建構與運用語言的正途,才是落實語文核心素養的正道。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2]茅盾.《呼蘭河傳》序[M].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
[3]吳豐強.文字內部風景[M]. 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9.
【基金項目:本文系東莞市立項課題“基于學習任務群的‘思辨性閱讀與表達的實踐研究”(課題編號:mskt201906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吳豐強(1965—),男,廣東省東莞中學松山湖學校高級教師,主研方向為文本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