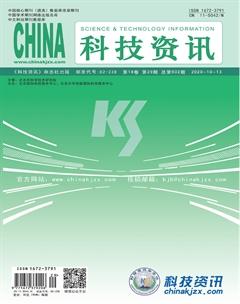民族地區非遺產業化發展探究
李許寧靜
摘 ?要:民族地區迫切需要解決高質量發展,使自身經濟發展契合綠色發展理念。非物質文化發展意義重大,如何實現非遺產業化發展是民族地區面臨的現實難題。數字經濟高速發展背景下,實現民族地區非遺保護與產業化互動發展至關重要。民族地區非遺產業化程度不高,在產業化過程中呈現了缺乏創新意識、產業定位不明確、產品集群優勢不顯著等問題。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民族地區應重視非遺產業化發展。
關鍵詞:民族地區 ?非遺 ?產業化 ?發展探究
中圖分類號:G122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672-3791(2020)10(b)-0003-03
Abstract: Ethnic areas urgently need to sol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that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fits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how to realiz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practical problem facing ethnic reg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is essential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thnic areas is not high.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innovation awareness, unclear industrial positioning, and in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product clusters have emerged. In order to forg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nherit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ethnic region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Ethnic areas; Intangible heritage; Industrialization;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由于我們缺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征把握以及它的價值的界定的標準,會讓很多人在短期利益的驅動下形成“泛文化遺產論”,從而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發展泛濫,不利于產業和地區的發展[1]。因此,非遺產業化發展的研究對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底蘊,增強該地區民族對于文化認同感,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產業都具有十分重大深遠的意義。
1 ?非遺保護和產業化發展的關系
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來說,往往蘊藏著一個民族傳統文化最深的精髓,是一個民族在漫漫歷史長河發展的見證者。它保留著一個民族最原始的歷史狀態以及該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以及生活習俗,是一個民族團結和對該民族文化強烈認知感的最好體現[2]。產業化的發展則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另一種保護形式,以發展經濟和非遺保護行為導向,以實現效益為目標。通過產業化的發展,最終反作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上,實現一種閉環的有利循環。對經濟發展以及非遺保護起到了往復不間斷的作用。
2 ?大理地區非遺產業化發展問題
2.1 缺乏創新意識
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分豐富,僅從本土情況來看,就有大理白族的繞三靈和扎染、劍川的石寶山歌會和木雕工藝、鶴慶的“天子廟會”和銀器煅燒等。盡管大理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蘊藏量豐富且形式多樣,但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發展卻缺少創新意識。比如白族扎染技藝,作為大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代表,雖然早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是根據有關數據,目前注冊在案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僅剩1位。這樣一種民族瑰寶,陷入了后繼無人的局面,也正是因為如此,扎染技術傳承多以家庭作為單位,以老人為主要傳承人。扎染通常只能出現在衣服、圍巾等一系列棉織品上,各自的家庭有自己的勾線技術,且不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款式的固定、各自技藝的不互通性并不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以及產業的發展[3]。
2.2 產業定位不明確
工業化制造雖然大幅度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的生產效率,卻使部分手工環節缺失或淘汰。傳統博物館展出方式雖能滿足人們了解傳統非遺文化需求,卻只停留在靜態層面,難以滿足非遺文化傳承。旅游在為文化提供產業發展平臺的同時,也帶動非遺產業的積極創新發展,但究其本質,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都有自己的發展方向以及市場空間,沒有明確的界線[4]。這樣一來就不利于各個產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發展方向的不明確不利于政府進行統一管理,加劇了企業之間的不合理競爭。
2.3 產品集群優勢不顯著
大理國歷史文化、南詔歷史文化以及各種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盡管文化種類眾多,但存在開發過于淺顯、不集中、零散的問題。沒有一種整體性的發展氛圍,非遺產品零散分布,缺乏一種統領性的民族非遺文化遺產產品品牌。對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對消費者的消費品位缺乏領導,對不同層面的消費者需求沒有進行差異化的分析,消費者的精神文化層面產品消費水平普遍不高,對消費者真正需要的文化產品了解不深入,文化產業發展缺乏強有力的市場支撐。
3 ?大理地區非遺產業化發展建議
3.1 創新引導,政策扶持
政府通過政策優惠、人才培養等政策積極鼓勵年輕人在“一帶一路”的大方向下,在深入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后,結合自身經驗,不斷創新,向多方向、多角度進行創業,政府可成立相關部門,為相關人員提供技術指導和資金幫助,與相關企業溝通,加大幫扶力度,促進非遺產業多角度進行發展。建立文化人才培養政策,儲備人才。整理非遺傳承人名單,通過走訪等形式,鼓勵傳承家庭進行創新。消除相同技藝之間的傳承隔閡,開設非遺技藝培訓班等。大理作為一個旅游城市,消費者主要具有兩方面的消費需求:第一是本土人民對世界潮流文化的需求,第二是旅游者“原汁原味”的文化需求。大理非遺產業化發展的契機就是滿足這兩類不同消費者的需求,更重要的則是通過不斷地進行整合和創新,找到一種能夠同時滿足這兩類需求者的產品。
3.2 明確產業化發展方向以及改進政策
政府在整理一系列名單之外,應該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單位,比如博物館、保護中心等制定靈活的幫扶政策,避免同等化、籠統化,對相同類別的非遺產業進行整合,對不同的非遺項目傳承手法以及內涵進行分類,根據不同的非遺項目,圍繞一個總的產業發展方向,鼓勵不同企業根據自身情況在保持總方向不變的情況下,不斷創新,鼓勵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衍生出新產業。對不同產業之間進行明確的界定,大理的旅游業較為發達,國際旅游勝地,少數民族較多都能夠帶動非遺產業的蓬勃發展。旅游業可以將不容易以具體形式呈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通過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借助旅游業的發展,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一體化的發展。通過產業化發展,創立出屬于該民族的本土品牌,起到龍頭帶領的作用,之所以未能創立本土品牌,就是在對非遺文化的發掘的過程中,停留在了表面,沒有深層次地對非遺文化進行理解,進而未發掘到其底蘊,因為鼓勵人才對非遺的不斷發掘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5]。
3.3 促進產業聚集化和可持續性發展
產業聚集化發展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產業旅游、餐飲影視、會展形成產業鏈,從而形成產業聚集區域,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延伸性的發展。針對一個固定的非遺,可以衍生出許多相關聯的產業發展,這樣使產品得到了很大的銷售助力,人們在向傳承人學習有關技藝的同時也能夠體會到非遺文化的文化內涵,從而提升了大理的城市品牌,又反向作用于產業鏈,實現了一個積極的循環,使傳承能夠得到可持續的發展[6]。結合不同地區非遺文化發展特點,在已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對其進行整理,根據不同的特點,找尋不同的商機,比如對于可以進行具體形式呈現的非遺,可通過線上和線下兩種方式進行發展。線上,通過目前大多數人接受的新型傳媒方式,對非遺進行宣傳,以達到讓更多的人知道并且感興趣的程度,針對這一部分人群,采用線上推廣商品的方式,而如果是表現出極大興趣的人群,利用線上宣傳隊非遺以及大理進行強有力的宣傳,以達到這一部分人能夠實際到達大理,如此一來,對大理的經濟起到了積極引導的作用。建設特色非遺產業園,培育和不斷發展非遺產業集群發展[7]。
參考文獻
[1] 胡凌.去產業化:大理劍川白族木雕的非遺生產性保護[J].云南社會科學,2018(1):104-110.
[2] 萬金店,包家官.“兩聚一高”視野下非遺產業化發展研究——以江蘇省級非遺項目連云港貝雕為例[J].江南論壇,2018(12):41-43.
[3] 周波.非遺保護與鄉村振興的文坡實踐[J].文化遺產,2019(4):26-34.
[4] 陳育義.論少數民族地區非遺保護——以“安順戲案”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19,40(7):101-104.
[5] 陳思琦.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創意產業融合發展路徑研究[J].四川戲劇,2018(10):54-56.
[6] 左丹.少數民族地區非遺扶貧經驗研究——以貴州省“錦繡計劃”為例[J].改革與開放,2019(18):26-28.
[7] 李江麗,趙艷秋.大理旅游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中外交流,2018(12):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