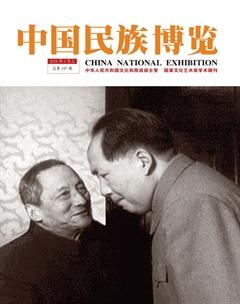“有、無”之間:論王弼音樂美學思想
【摘要】魏晉文人音樂美學在玄學思潮的推動下,脫離、超越了傳統對音樂自身的局限與束縛,以王弼為代表有了對音樂自身審美的回歸。王弼音樂美學通過玄學的理性思辨,以儒道匯通的思維方式,對“有”與“無”的問題,“體”與“用”關系的問題的提出,進行《老子》《論語》中音樂思想的再度詮釋。其音樂美學思想深深的撥開并證明了音樂本身“自然”“情理”的合理性的存在。他的玄學理性思辨在音樂美學思想中的運用,深遠啟發,影響了后世文人音樂美學的發展。
【關鍵詞】王弼;音樂美學;音樂自身;理性思辨;再度詮釋
【中圖分類號】J6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01-123-08
【本文著錄格式】郭思言.“有、無”之間:論王弼音樂美學思想[J].中國民族博覽,2021,01(01):123-130.
音樂本身作為一種人心、人情交流的特殊方式,魏晉文人在音樂中安頓心靈,為超越現實生活中的物累。由于玄學以理性思辨、理論性的徹底性來探索宇宙人生之本體和規律,使人的主觀玄思達到高度敏銳,同時,人的審美重心的轉移,回歸于個人精神的滿足。王弼將玄學自然觀中自然、無為的本質貫徹進音樂美學思想中,并以儒道哲學的互通,對傳統音樂美學思想進行了合理的調整,使問題的探討不僅限于音樂自身,還上升到了哲學本體論層面。通過對“本末”“有無”等問題的深入辨析,使音樂的本質、審美、價值和形式特征方面得以被探討。
由于漢代經學敗落,王弼在不脫離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貴無論玄學體系,想使本體與現象,自然與名教結合,并力圖將理論與實踐,內圣與外王相結合,從《老子》中凝練出了本體論思維模式。其實,從老莊到王弼美學對于“有”與“無”的問題,一直是一種現象和本質、形式和內容、象和意的辯證關系問題。“有”即為實,“無”即為虛,“有”是“無”的具體表現,它們在“有”“無”“虛”“實”的辯證中,呈現出對事物理解的美學價值觀念。
道家在音樂中“道”的體現,如《莊子·天下》中“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再有“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道”深邃寂靜,在沉寂中鑒照萬物,金屬或石頭脫離它就無法發出聲響。它可與萬物交接,但自己卻一無所欲,還供應著萬物的需求。莊子的音樂美學更靠近音樂自身,在《天運》里對音樂的描述“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能引出人“懼、怠、惑、愚”之情感。還認為“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這種帶有虛無主義的哲學思想,即一切外在可試聽之區都是虛幻,無法體現正真的“道”的本質,同老子“大音”“大象”“無物之象”這種虛無境界非人的視聽所能認識或達到的意思一樣,都代表著生命本原的“道”。“道”即是美的最高境界,外在的音聲只會對其破壞,所以老莊否定現實中實物音聲的美。對于老子《道德經》中“有無相生”的理念,在音樂中就是想從有聲之境進入無聲之“大音”,但離開音聲而直接獲得希聲之大音從實際上看并不太可能,所以也可將老莊的“道”看作是一種無形無為的絕對精神,一種“境界形態”。只靠一種神秘的體驗讓人對客觀世界認識、把握,這種離開五音進入人心中的“虛無”之境的不切實際性,是無法對日常經驗論證或描述的。
一、音樂本體的“回歸”
玄學的探討雖屬形而上,但它強調立足本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用“無”與“有”去探索宇宙本體的思路在先秦哲學中就有出現,但我們并不能完全認為這是對傳統天人之學的延續,而廣理解為一種推陳出新的發展與超越,為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需要。湯用彤先生概括王弼“無”與“有”的理念:“蓋萬有非獨立存在,依于無而乃存在。”“未有不以無為本也。此無對之本體,號曰無,而非謂有無之無”“未有非于本無之外,另有實在,與之對立”,所以,王弼的玄學本體論是“體用一如”的,不是空洞、虛無、神秘,脫離實際的。從他對于“有”回歸到“無”的解釋,理性、清晰而富于邏輯性。如貴無論玄學就是以人的主體性認識作為構建宇宙本體論的重要環節,“萬物雖貴,以無為用”,有即現象,無即本體,以無為本,以有為末,本末作為基本范疇,世間萬物都可概括于此中。在貴無論玄學影響下,有聲、有形、有色的音聲、語言文字、圖像能夠向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無”轉化。
陳來先生從共相和殊相,一般和個別的角度來看貴無論玄學,并比作將宇宙從總體看,其本體為“無”,從部分看,宇宙每一領域又以該領域特定的“無”作為直接根據。只有不宮不商才是大音,不溫不涼才是大象,即“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音、大象超越了宮商或溫涼的界定,則“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傷”[1]。音樂作為典型的審美意象而非形象。在老莊看來,豐富多彩的社會萬物都只是“道”的外化,而任何事物都只是“道”的局部,而不是全部。老子用音樂作比喻,體現“道”的一種超感性特征,它“無形”“希聲”“無呈”“可得而不可見”是絕對的存在,同莊子《人世間》中“唯道集虛”的理念一樣。只有沒有任何限定或規定的東西才能成就絕對的價值,“大音”作為“道”的音,即是無聲,它屬于感覺范圍但又超越感覺的存在。音樂離不開聲音,但聲音只是作為將我們引領向音樂所表現的意境的媒介,單靠人耳無法聽見這種意境,要借助人的思維、聯想、情感等因素,借助內心的領悟與體知,這顯然已超出了對音聲單純的感知。一般人對于音樂的鑒賞,都是經由“有”到“無”這樣一種復雜的心理活動過程。王弼在老子中凝練出“無”作為宇宙萬物存在的根據和形而上的本體范疇,并未否定具體音聲的存在,認為“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不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涼,不炎則寒”。“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故隱而無名也。”[2]這里“分”指局部,“眾”指整體,有聲只包含局部,無聲則包含“音”的整體。人為的音聲只能表現部分美,而失去整體的自然美。
他繼續解釋“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為音也則希聲,為味也則無呈。故能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經也[3]”。“無”既有抽象的意義,又有本體的意義,即“品物之宗主”。“無”作為萬物宗主,苞通天地,卻又無形無聲,不可聽聞而得,“萬物宗主”必須達到“無形”“無聲”“無味”的狀態才能成為根本。由于王弼認為“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于無也”[4]。又說“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5]。所以,他“萬物之宗”的“無”并非完全不存在,而是無形、無聲、無味的存在,先有“無”,再有“有”,以“無”為根本,“無”即是萬物的本體,同時無法用具體感視把握它,這就是最真實的存在。“始”則是萬物長成自身樣子的過程,但根據是無法看見的,因而“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6]。“名號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7]。他的“萬物之宗”又絕對不能得而“形名”。因為道就是萬物產生于“無形無名”。他從本體“無形”同時又不可對本體有“名號”的角度解釋,認為“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名生乎彼,稱出乎我”[8]。任何具有特定規定性的“形”都只能成就“我”,而不能互相或成就“彼”的價值。由于不能對事物命名,否則無法恰當地表達事物,反而破壞了世界的完整性。“無”本身就不依靠任何具體特性而顯現,即為“無性”。若某物有了稱呼,帶有個人主觀性在里面,以此下去,就會被“名言(稱)”的世界掌控。“名”是人對物的命名,由人發出的命名叫作“稱”,所以只有無聲之域才能辨別出音聲。“名”與“稱”都不能完全通過事物本質而達于本體,否則就會限定“萬物之宗”的意義。“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以名”[9],“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10]有“分”而不能“兼”,說明不具有恒定與絕對性。“形”作為特定性質,本身帶有限定性,有限定就會有“分”。“形”可視作“分”的根由,所以某“形”的“名”是不能指稱另一“形”的,同時也不能兼有對各個不同“形”的描述。
可見王弼超越老子的地方就在這“所以成”上。“道”不再同老子的本源,“道”富于萬物以它存在的方式的根本過程,不管控萬物,不對萬物作具體事情,讓萬物各適其用。“無”作為萬物的絕對本體和規律,他用“名”與“稱”進行對本體“無”的解釋,并為之證明“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11]。就是如果一個本體有“溫”這樣的屬性就不能有“涼”這樣屬性的根據,音樂同樣若本體有宮音這樣的屬性,它就只能是所有有宮音這樣屬性的根據,而不能成為有商音這樣屬性的根據。所以不溫不涼,不柔不剛,只有沒有任何具體屬性的東西,才能成為有具體屬性的“宗”和“主”。當萬物有一個共同的本體,這個共同的本體要想成為所有事物存在的根據,那它就不能擁有任何事物的具體性和特殊性,而一旦擁有,那它就不能再擁有相反事物特殊性存在的根據。“宗”強調事物的根據,“主”強調這個根據能富于所有萬物統一性,為了把所有萬物統一聯系起來,而形成一種合力,這個合力即為物存在的根據。他的“本”“無”“宗”“主”即為“道”,“道”有路或是通達的意思,即每個事物都有它的路徑,“道”是所有事物必經的,是“無不通也,無不由也”的,所有萬物存在并長期存在,都要經由這個道,才能獲得它的存在。可見王弼對“無”的本體化表現。
從“有”的方面來看,王弼認為,“無”并非在“有”之外存在。“萬有”就是事物外在的存在狀態。“有以無為用”,“無”只具有邏輯和抽象概念,“將欲全有,必反于無”,對有的理解,必要回歸到“無”上。樓宇烈先生認為,“王弼無和有,既不能在時間上分先后,又不能在空間上分彼此。無不是在有之先,與有相對存在的某個實體,無和有只是一種本末、體用的關系。”[12]可見王弼“體用一如”的本體論,能使老子的“大音”“大象”等自然消失。因為“有”能被我們日常經驗生活所把握,而“無”作為抽象,是我們從哲學層面上對事物本質、本體的一種理性認識。“無”與“有”的體用關系,證明了我們必須依靠理性的思維才能進行抽象的把握,所以要回歸于具體的音、象中,才能把握大音、大象,這完全不帶有神秘主義的成分。“無”作為萬物之有的本然屬性,“四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13]。音聲雖未是有形有象之物,卻源于無形無限之本體的孕育苞通,因而與此一本體直接相通。因老子將“物”自身的觀念去除,如無聲的大音,無形的大象,“物”本身作為一個依賴于主體而存在的狀態,這里老子虛無主義體現的更加明顯。牟宗三先生認為,不論王弼的“無”或是“有”,都是從作用上來講的,只有天地萬物的“物”才真正具有存在性,而王弼對“無”關注的重點并不在這“無”的屬性上,而是在“無”的發用上。正因為“無”的發用功能,才始“道”能養萬物、成萬物。同樣,當人的內心有了“無”的狀態,則能順天地萬物之性,人與社會才能和諧。所以,正是“無”的功用才有了萬物本性的存在。
由于老子的“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莊子也認為并非言不能傳意,而是言不能傳達“意之所隨者”,這“意之所隨者”就是道家美的本源的“道”。莊子《知北游》中認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即語言的極大局限性是不能反映心靈深處的本質。所以《外物》中又認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是“道”的領悟,要把握好“道”,就要處理好“言”與“意”的關系。“言”的目的是“得意”,前者作為工具,后者作為目的,不能拘泥于工具的“言”,而忽視“得意”的目的。王弼又引入“象”之意,認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得意在忘象”。“象”既包括主體知覺中的表象,又包括記憶中的表象。“意”是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投射流變的產物,是意識境界的心靈化,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是一種復雜的心理活動內容。“象”是“意”之象,“意”因象而生,二者相互交融、滲透,意蘊深邃、不確定又模糊,“言”“象”是表達“意”不可或缺的條件。如黑格爾認為,音聲“是在藝術中最不便于造成空間印象的,在感性存在中隨生隨滅,所以音樂憑聲音的運動直接滲透到一切心靈運動的內在發源地”[14]。一種無聲之外的音聲美。音樂的美既有聲又無聲,當人沉浸在音樂的美的意境中,就會出現一種無法言表的聯想和感受。言、象作為達于言外、象表之意的媒介,不執著于言辭,而應宣心寫妙、言短意長或意余言外,若執著言、象本身,則無法領悟言外、象外之意,音樂也是如此。王弼解釋“無聲”之美,就是以無聲之處求音,如同僧衛所說:“扶弦節于稀,暢微言于象外。”僧肇說:“窮心極智,極象外之談。”意思一樣。
其實,“得意忘言”有學者認為主要在于“名”和“稱”的不同,而不是為了否定掉什么。“得意忘言”作為王弼對無形無名之道論述的方法論說:“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15]比如當音聲作為具體存在時,可以用名來指稱它,但對于“無物而不由,無妙而不出”的萬物之極,則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所以音聲是沒有名稱可以匹配的,一旦被冠名號,就會失其旨,因為稱謂不能盡其極。由于“道”以無為用,它給所有存在物提供一種對自身統一的否定環節,才為所有存在物提供了實現自身的機會。王弼一方面認為萬物之本是不能用“名言”來把握的,另一方面又必須通過“名言”來表達,這里是否矛盾?他該如何表達?就是通過這“名”與“稱”。
王弼認為,雖然不能用“名”來對“物之極”予以“稱”,但卻可以意會。意會是通過言辭的體驗,能用語言來“稱”之的東西。“名也者,定于彼者也;稱也者,從于謂者也。”[16]凡可名之名皆“定名”,不可名之名則非“定名”。“名生乎彼,稱出乎我。”“名號稱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17]。名以對象為根據,稱以“我”為根據,一個主觀性,一個客觀性。“名”是定義形的,它必須跟事物的形狀,具體規定性相結合來以此為根據,是具體的事物產生。而“稱”是一種認識的過程,不能達于事物本質,要靠人主觀性給予,為虛意。“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后謂之道。”“無稱不可得名”[18]。因為我們在探萬物背后那個存在的根據時,要經過“無不通也,無不由也”的“道”。“道”,是指稱性的,作為過程的表現形式,它還可以有無數的表現形式,那他又是從哪里看出這個道的?就是從“有”中。“凡有皆始于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19]無形無名是道之“無性”,有形有名是道之“有性”,前者為天地之始,后者為萬物之母。以道之“無性”始萬物,以道之“有性”成萬物。“有”作為虛飾詞,被王弼用作道之“有性”。“然則道、玄、深、大、遠、微之言,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20]皆屬稱謂之詞,不能定名,若以名責者,就會違其常、離其真、敗其性。所以,王弼有把希聲之“大音”意會為“體無”的意思,就是因物之極,難以形容描述,則稱“無”了。
王弼解釋:“恍惚,無形不系之嘆。以無形始物,不系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21]“無形無名,則為萬物之始。”不再簡單把“道”作為萬物生成發展的“根據”,這里他思考了一事物成為一事物的緣由,突出“無形無名”,作為創生的方式,“道”就是通過“無”的方式創生了萬物。那他的“不知其所以然”又從何而來?雖然萬物本身由自然而來,但王弼與老莊對于“而來”的“根據”或“始源”的出發點不同。王弼萬物邏輯原點是“無”,萬物“本無”且生成萬物,然又必回歸于“本無”,“本無”可看作無數美的東西之所以為美的邏輯根因和規律,與“反者,道之動”意思差不多。“本無”要超脫語言、音聲這種有限、有形的具體事物,給“無”根本性地位,好把握無限抽象的本體。語言、音聲等都只是作為工具,最終目的是盡可能拋棄這些,所以“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音至矣”。他并未否定音聲的存在,而是將“無”看作具有統攝萬物的作用。萬物回歸自身、自我實現,都有賴于“無”,“無”是使音聲成為可能的最終保證,作為一種實然概念。“有”指有形有象的現象,“無”指形無象的本體,無形無象的本體又是形成有形有象現象產生的根由與存在的根據以及最后的歸宿。只有先不認定任何觀念或意義,才能反思一切,無限追求,就是現象之美不在本身,而在其所象征的本體上。這種把天地萬物的多樣性和作用都歸為“無”的統攝,即為他“舉本統末”的理念。
“無”既要離開具體的事物而抽象,又要求不離開具體事物而有具體意義這樣一種生成意,即“萬物始于無而后生”。那王弼的“無”是否又帶有天地萬物出于“自生”的想法?他解釋道:“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22]這里“一”即為“無”,“一”數,本身就有初始或開始構成之意,作為“物之極”,“一”產出“無”,“無”產出萬物即“多”,但世界的統一性不在于現象的多,而在于本體的“一”,由“一”到“多”,只有把握本體,才能統帥現象,這樣一種由本體到現象的認識路徑。當萬物從母體中生出,有了自己的形體,開始各自變化的過程就是“無”生成性的表現。“無”既有抽象又有生成的含義,看似矛盾,則是王弼玄學本論的體現。他應該看出二者之間的矛盾性,若不抽象,不是大音或大象之類,它就不能“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經也”,若只是抽象那“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大音”必須要存在于具體的大音中,所以王弼“無”的本體論思想中又包含著抽象與具體的矛盾。名、形、聲、色是人認識事物的普遍特性,而“無”不帶有具體特性而又能使這些特性顯現出來。無名才能命名出“有”與“無”,無聲才能辨別出宮或商,無形才能呈現出大或小。無名、無聲、無形與物的具體特性之間,也可看作為顯與隱的關系。
二、音樂中的“自然”與“情理”
“自然”作為道家美學的基調,老子“道法自然”,即“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于乎人之力而萬物生矣”[23]。老子視宇宙的本體為“道”,“道”即是自然,即以自然為存在狀態。“道”貫穿于天地萬物和社會人生之中,“道”可以無所不容,無所不包,也被稱為“大道”。“道”即是“無”,是物象無法以語言進行傳達,也無法被主體的感覺經驗和理性認識所把握的,只能借助超越語言和邏輯的心靈體驗觸及。以“大”的“道”比之于“音”,此音乃至大之音以至于音不成音而為“希聲”之音,“音”為可稱之名,但“大音”非“音”。因“道”以其“大”即“彌綸而不可極”[24],而無名可稱,如果指稱它就破離了它的本真,棄離了它的本意。正是這無名可稱而唯可嘆之“大”的“道”來成全著庶物,從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老子提倡“無為”“無欲”使人心性達于“道”,即實現“自然”的內化,以天道自然觀為其美學基礎。認為“五音令人耳聾”,就是對音樂給人帶來的自然的情感反映予以否定。莊子認為,如同“大音希聲”,無聲之樂作為同萬籟相協調的聲樂,在“無聲”中散發和諧之美。莊子從音樂美學角度關照天地之大美,借“自然”之力而彰顯音樂的“自然之和”和合“萬物之體”“萬物之性”,而達“天籟”,美好的音樂就是宇宙本體和自然之道的體現,這是一種超越理性尺度的審美標準。
老子說:“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王弼解釋:“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25]認為音聲相互協調應和前后相伴,只有回歸于自然無為的狀態,音與聲之間才會相和,會通合一則和矣。以回歸本無,回歸自然,而達到內在平和、獨立的圣人精神。老子說:“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要任萬物順自然。”“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26]王弼也認為圣人治世“自然已足,為則敗也”。“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智者,謂之為也。”[27]即為老子“無為無不為”的概括與贊同。他通過老子“五音令人耳聾”作了對圣人精神的詮釋,說:“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為目也。”[28]因為老子認為心會因耳聽到五音而聾掉真心,“五音”刺激,令人耳聾,這不符合自然生命之道,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五音只能提供人感官享受,無法達于“道”至善至美的音樂境界,應被徹底否定。而王弼的“為腹”即往內,就是人不該因外物所累,被困于“以物役己”中,同時他又并不否定“外物”的存在。由于老子“少私寡欲”“滌除玄覽”“致虛極,守靜篤”的養生觀,反對一切與客觀自然萬物相對的倫理秩序,否定人情感的自然。但王弼并沒有這樣,他的自然觀使他認為人類社會需要合理、規范的等級制度,也就是名教與自然的一致性。在他看來,“名教”不是憑空出現的,也是由“道”的自然生成而來,是由自然產生出的一套社會等級倫理制度、規范,次序法則不可被否定,同時對于人的自然情感也不可被否定。如他提出“圣人有情”就是一種對自然人性的肯定,認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哀樂以應物。然則,圣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29]。圣人也同為人,是不可能沒有自然人性的,“萬物以自然為性”就是承認人的自然情感。他又從“以無為本”的出發點,將老子的“自然”上升到“合理”的層面,認為圣人“與天地合德”,而不可能不應物而動。王弼言理主其和,認為圣人要做到“達自然之性,暢萬物之情”[30]。“天地萬物之情,見于所感也”[31]即是他儒道匯通思想的體現。王弼心中的理想君主,要“與道同體”,“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欲道者以無為為君”[32]乃是他心目中的“內圣”,即所謂“體無”。“體”有直接經驗的意思,“體無”有以人的直接經驗的方式來領會“無”的蘊意,但一般人怎能做到“體無”,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33]圣人真正做到無身無私,應物之性,順應自然,超越自身的局限,而包容天地,達“體無”的境界,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
王弼不同于老莊神秘、直觀、樸素的自然觀,而是將其建立在純粹哲學本體論上,并向社會制度和倫理秩序中延伸,將“自然”發展到“合理”的層面,這與儒家有了相承之處。以“理”作為衡量自然的標準,思辨理性則是人認識自然的方法與原則。他稱宇宙萬物中一種智慧或規律為“理”,“物無妄然,必由其理”[34]“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35王弼對人的自然本性的強調,給人以對自然情感存在的合理的認識,認為“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36]。即為合理的體現。“萬物以自然為性”[37],自然之性即作為一切活動的前提,包括情感在內,“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宗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38]他為“名教”的存在找到“自然”的根據,一個合理的理由。
三、以“用”見“體”:對儒家音樂美學的詮釋
王弼從本體論上將無與有相聯。由于本體論思維方式是由用見體,又由體及用,通過二者間的循環往復來結合本體與現象的,而這種結合的目的不是為了建構理論邏輯結構,而是靠這種結合去抓住、把握一種無限整體,而且王弼的“無”在道家與儒家的發展中屬于兩個不同的層面。
“以無為用,不能舍無以為體。”[39]萬物莫不以無為體,必以無為用。道家之“無”,即以境界上的“無”為本體,即為自然,不作為內容的實際特性。對《老子》的解釋需要由體及用的方式,因為它屬于現象層面,需要把抽象的無與具體的有相聯。但孔子已經達到了圣人“體無”,可是“圣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40]。“無”不可解釋,所以要涉及“有”,所以要從以用見體的思路來解釋,而且孔子的道體本就是“天何言哉?”不可言傳的。中國哲學里對于體、用之間的關系是有體必有用,體不同,用必會跟著改變,但用不同,體卻未必會變。因而王弼通過“舉本統末”的方式對《論語》進行解釋。
自然是本,名教是末。“舉本”按王弼的意思是回歸樸素,老子說:“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41]王弼就通過這“不尚、不貴”來證明如何回歸樸素。在他看來,善、惡是同時形成的,善、惡都屬于“末”。只有“不尚”不提倡,“不貴”不追求,任其自然,才能回歸真正的素樸,才能發揮出舉本統末的具體作用。善與惡各自有各自存在的價值,就讓它們各自獨立存在,不要去分辨,不要去判定,所以他從根本上否定君主自身有教化的作用。
《論語·陽貨》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他解釋“禮以敬為主”“樂主于和”“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所簡于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42]。王弼肯定敬為禮之本,和為樂之本,沒有改變孔子的初衷與意愿,贊成“禮以敬為主”“樂主于和”,要按敬、和的原則,不要把禮樂只用作形式。并從孔子的思想中提煉、轉化出新的含義,認為“禮以敬為主”的作用是糾正社會風氣,可以以“民之自然”來建立。因“樂主于和”能化解人心,利于調節名教和自然的融合,任自然即可。由于王弼認為君主自身是沒有教化的功能與作用的,教化需在“尚”和“貴”中來完成,所以這里明顯可見他在贊成孔子的同時,本質根源上還是屬于老子。
[25]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
[26]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
[27]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8.
[28]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28.
[29]《何劭王弼傳》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40.
[30]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77.
[31]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周易注》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374.
[32]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58.
[33]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81.
[34]王弼著,樓宇烈校釋.《周易略例·明彖》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591.
[35]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137.
[36]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論語釋疑》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33.
[37]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77.
[38]王弼著,樓宇烈校釋.《周易·乾卦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217.
[39]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94.
[40](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
[41]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見《王弼集校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8.
[42]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論語釋疑》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33.
[43]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論語釋疑》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24.
[44]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論語釋疑》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26.
[45]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論語釋疑》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25.
[46]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論語釋疑》見《王弼集校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622.
參考文獻:
[1]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
[2]余敦康.魏晉玄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4]林光華.魏晉玄學‘言意之辨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5]牟宗三.玄學與才性[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6]陳來.魏晉玄學的“有”“無”范疇[J].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6(9).
作者簡介:郭思言(1994-),女,漢族,江蘇省淮安市人,云南師范大學19級研究生在讀,音樂學專業。研究方向:音樂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