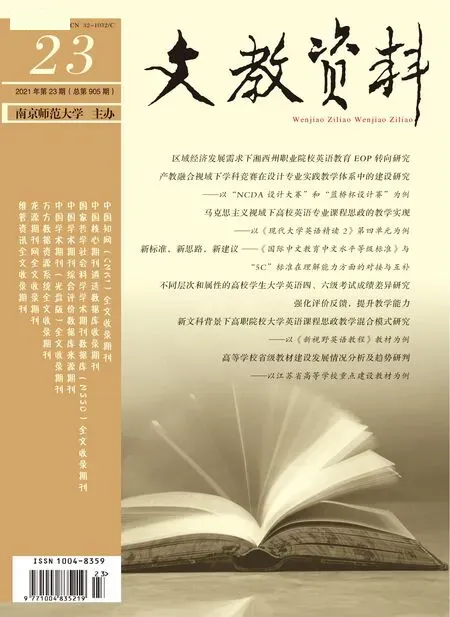“大學語文”課程身份確認下的目標獲得
劉茂田
(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文學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6)
新時期“大學語文”課程,從研究界公認的起點——1981年徐中玉先生主編的《大學語文》出版,至今已有40個年頭了。40年來,針對大學語文的學科定位、功能特性之爭,存廢之辨,歧義紛出,值得欣慰的是,由教育部委托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制定,歷時四年多完成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在2018年1月正式發布,很多專業的通識課程都設有“大學語文”,大學語文通識課程的身份得以確認,課程身份的獲得并不等于教學同仁的認知一致,本文就此談點想法。
一、歷史回應下的身份追尋
爭辯的四十年,已證明了大學語文在學生“素質教育”“傳統文化教育”中的重要性,2007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頒布的《關于轉發〈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紀要〉的通知》明確指出:在高等教育課程體系中,大學語文應當成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校學生開設的公共必修課。新時期“大學語文”重在學生語文素養和人文素養的養成教育,“大學語文”擁有大量傳統文化、西方文化、主流意識形態的諸多文化資源,是文化資源的統一和精選,直接影響學生的審美情操和人文素養,特別是傳統文化與人的倫理、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心靈,并賦之于形,是“自然人”向“文化人”“社會人”自然過渡的文化內隱。大學教育培養具有“社會良心”的社會人,“大學語文”課程是非中文專業學生語文素養和人文素養教育少有的文化資源和精神 底色。
四十年來,身份多變的“大學語文”課程教育結果不太令人滿意。一百年前,蔡元培先生重人格養成、美育陶冶的教育思想,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提倡“通識為本,專業為末”的通識教育理念,設置“大學國文”,但其通識課程身份在歷史發展中余音漸稀。1952年國家采用蘇聯院系教育模式的頂層設計,建立了文理分開的教育框架,“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了社會的主旋律,“大學語文”被弱化;到改革開放時期,教育現代化指向的新時期“大學語文”,服務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身份痕跡依然清晰。正如趙江榮、王大橋所說:“新時期大學語文大致經歷了工具化階段、審美化階段和倫理化階段,語文,文學,人文三維度雖有共識交錯,但歷史發展已成為主要線索,這個過程雖然緩慢艱難,但其方向不可逆轉,共同勾勒了大學語文課程整體功能轉變的方 向。”[1]形成了新時期大學語文自己的問題域:工具性和人文性失統。
“大學語文”通識課程的身份得到全面確認,為百年來的大學語文找到了一張完整的精神拼圖和目標方向。2019年,陳國恩在《通識教學是大學語文課的發展方向》一文中提到身份確認后依然存在的兩種偏向:把“大學語文”講成中學語文技能課;講成中文專業文學史課程的縮寫版或者語言學課程的簡化版。[2]當代社會發展要求“思政教育進課堂”“高職教育升級和擴大招生”“社會自考普及”,社會需求多元化、專業過度化教育框架培養出來的現有大學語文教師,面對這樣“如火如荼”的主流語境場,“大學語文”的人文素質教育又顯得模糊空洞,課程教學實踐會不會再出現朱桓先生《不能承受之輕與不能承受之重——淺談大學語文的學科定位》[3]的擔心,擔心糾偏下的以文學審美主唱的“大學文學”替代“大學語文”,或停留在教材建設、教學方法、教學評價角度談《大學語文課程的反思與優化》,[4]進入新一輪的循環。
二、理念指引下的身份確認
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在《大學一解》一文中這樣表達:“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業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5]梅貽琦通才教育理念引申出通識課程理念教學的人才觀:具備基礎知識的寬度,健全人格的養成,終身學習的思維和深耕細作的專業,簡言之,為當代版的“又紅又專”。通識課程老師提升認知、轉換角度理解課程理念,就能明確通識課程和專業課程具有不同的培養方向:注重專業能力培養的專業課程,側重職業規劃的層面解決學生的專業問題;注重人文能力,健全人格養成的通識類課程,側重人生規劃的層面,解決學生人生的問題。通識課程的能力訓練,側重獨立思考能力和邏輯分析能力,良好的表達和溝通能力和對自己、他人、社會的認知力。認識到通識課程和專業課程的獨特性和相輔相成的關聯性,就能避免課堂教學的一些誤區,如一味地迎合學生的興趣,導致課堂教學“娛樂化”,難以發現課程價值和創造課程價值;對語文功底低下,審美偏向虛擬化的學生進行代償式加餐、補餐;教學思路設計是專業課程知識的淺顯化、簡單化、粗線條化,不講重點難點,忽略通識課程理念下的人才培養目標。
教學考核、評估與教師的教學理念、學生的學習興趣關系密切。秉承通才教學的理念,自然可尋到開放靈活的課程考核和評估方式:注重學習過程,淡化終結考試,考試可以開卷,題目可擬思考型的,也可閱讀范文寫讀后感;平時作業,可以是課堂教學后的拓展閱讀,也可以是生活命題的寫作表達,作業評定注重客觀總結鼓勵。神聚形變,不離其魄。
三、課程目標獲得路徑
課程理念不僅力量巨大,而且有溫度,離我們并不遙遠,因為課程理念下課堂教學實踐有可操作的路徑。培養“社會良心”的社會人,前提是人文素養的獲得,學生單憑自己的經驗和認知難以產生自覺。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論大學國文選目》一文里所說,大學國文不但是一種語文訓練,而且是一種文化訓練,強調文本與示范結合訓練。再如張福貴所說,“大學語文與其他中文專業的教學活動方式有所不同,它更注重教學過程中實踐性活動,即在知識把握的基礎上,更加增加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6]。以往的課堂教學的模式,通常以對時代背景、作家背景、作品梗概的介紹入手,再對思想內容,藝術特征的分析,知識量大,一般運用于專業課程。通識課程教學應創造性地立足教材,進行篇目分類,注重文本和人本統一;緊扣人性,提煉出學生共鳴的人生、社會、生命、生活的話題,進行教學設計;拓展形式和內容相統一的課堂教學思路,教學設計從形式角度切入,詮釋文本,引導學生閱讀、思考、表達,以實現教學目標。下面以三種方式加以說明。
(一)話題交流中陶冶情操
1974年第4期《詩刊》發表了舒婷的《致橡樹》,無論是現代意識的主題表達,還是抒情說理的精致構思,都引起了青年讀者的廣泛興趣。話題討論:A男性眼睛中的女性,B女性視角下的愛情模式,由A引出創作背景,源于舒婷偶然一次和一位老詩人的散步和交談,給善于留意生活、關注生活的舒婷內心蕩起了微妙的波紋。“我如果愛你——/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愛你——/絕不學癡情的鳥兒,/為綠蔭重復單調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長年送來清涼的慰藉;/也不止像險峰,/增加你的高度,襯托你的威儀。/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這些都還不夠!/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由此生成不同的“愛情模式”:[7]“攀高枝型”“小鳥依人型”“賢妻良母型”“比翼雙飛型”“女漢子型”和“相依獨立型”,對應的意象為:攀援的凌霄花,癡情的鳥兒,源泉,險峰,日光春雨,木棉、橡樹。朗讀全文后討論交流,延伸多重意象的獨特魅力,感受密集多變的意象,長短不一句式的意象組合帶來詩歌內在多變的節奏感,明快有力的音樂美,具有擬人象征的意象,表現詩歌舒展和諧的抒情說理融合的新高度。朗讀后體會并交流“絕不”“也不止”“甚至”“不”“必須”等虛詞的價值,體會這些虛詞在作品中的起承轉合,感受虛中有實,由松到緊,由弱到強,否定中肯定的語言魅力,感受作家抒發個性愛情宣言的遞進力量。朗讀中討論“分離”和“相依”,領悟對立統一的木棉、橡樹意象,體悟詩歌表現的愛情藝術和生命哲學的價值。
(二)領跑式追問,感知思想
對魯迅的作品《傷逝》的解讀歷來是一種社會性的認識:對青年個性解放和婦女問題的反思和批判。如何解讀出涓生無序甚至錯亂的情感行為和反抗行為以及體現的復雜人性,感知個人自由追逐與社會正義責任承擔的命題?閱讀文本看到涓生、子君兩條不同的情感邏輯線索。涓生的情感邏輯:①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②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須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的。③人的生活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生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于戰斗的,只有一同滅亡。子君的情感邏輯:為愛而生,義無反顧地走向愛和回歸毀滅地走出愛,即使失業,也依然承擔相應的愛情責任。帶著兩條不同的情感邏輯線索去閱讀分析涓生的懺悔,懺悔是一種個人認清后的自責,以自我良知譴責來承擔罪過,或乞求寬恕。從涓生懺悔的內容和行為看,本質與行為相悖,涓生為什么要懺悔?是因為子君的離去還是自己道德良心的不安?但文體中間的懺悔內容又顯出其對子君的厭棄和有理由的自我辯解,隱藏對子君直面真實生活勇氣的認同和自己無力面對生活真實的困惑和矛盾,這樣懺悔式的反抗自然是無助的、無望的,是一種困惑的掙扎,是一種無能力愛的偏執反抗。懺悔后的涓生為什么會出現批判反抗的面目?在他的情感邏輯中生存是第一要義的,帶著西方式個人自由奮斗思想的生存是涓生的全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份的涓生在追求中迷失了自我、看不清自己、看不清子君、更看不清社會繁雜。魯迅先生為什么要以懺悔的形式來表達?為什么寫涓生絕望的反抗?引導出作品的創作背景,寫于1925年10月的《傷逝》,正是魯迅和許廣平確定關系之后,此時的魯迅深陷矛盾的情感世界,該如何處理徐廣平和母親“送給的禮物”——朱安的關系?朱安是無辜的,也是不幸的,魯迅受良心的譴責,又帶著強烈的內疚和巨大的悲哀。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文藝匯演中的演講《娜拉走后怎樣》中自信地指出:婦女個性解放必須與社會解放相結合。魯迅對啟蒙思想本身抱有清醒的懷疑,清楚看到迷失的涓生懺悔結果:“我活著,我總得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卻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我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三)以點帶面,引導價值取向
《論語·學而篇第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楊伯峻《論語譯注》譯文是:孔子說:“學了,然后按一定的時間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處來,不也快樂嗎?人家不了解我,我卻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8]課堂教學,是從倫理文化的角度去詮釋,學習的終極價值:為“人”,為“有德者”[8]的自覺。“有德者”的自覺并不是他人能了解的,學、習、說、樂并不是一種炫耀,而是一種內省,面對別人的不理解,怎么會有怨氣呢?因為“古之學者為己”“君子之學美其身”。教學設計可以從有趣味的漢字知識——字形構造來理解“悅——樂——平”和君子的層層遞進關系,傳遞出漢字本身承載的強大歷史文化的訊息,感悟學而為仁,學在人間,學無止境,啟發學生樹立終身學習的意義和對朋友的理解。
學,覺也。知道為什么學,如何看待自己、別人和社會。習是溫習、練習,學以致用,像陽光里的小鳥不斷地去踐習。“有朋”這里當“友朋”,[8]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互切互磋,不也是高興的事情嗎?朋,同門曰朋,[8]因為朋是一串貝殼、美玉或貨幣,可用來交換,引申出人與人的幫助是相互的。友,雙方右手相握,取志同道合義,志同道合的人重在精神交流,可致君子的境界。
“大學語文”課堂教學應選取經典文本教材,分類選文,課堂教學中話題分類,提煉與學生人生、社會、生活、命運密切相關的話題,以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和學習熱情,避免苦口婆心的講解和強力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