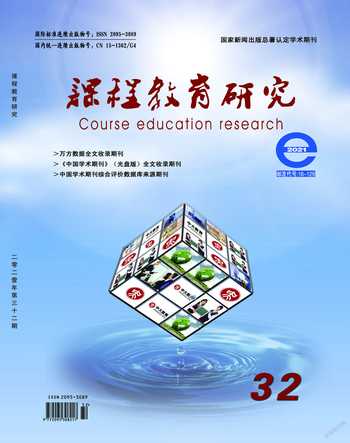貫通融合課程設置模式在口腔醫學本科教學中的應用
謝蘭竹 李江 江千舟 葛林虎 易曉敏





【摘要】我國的口腔本科學生畢業一年后參加國家執業醫師考試通過方能獨立執業[1],荷蘭、美國、香港等地牙醫學生在畢業前即參加相關執業考試通過后畢業即可執業[2]。兩種教育體系培養的學生畢業后在執業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這與我國口腔人才培養的體制、體系、學生背景、教學方法等方面息息相關[3]。其中,人才培養體系中課程的設置是影響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一環,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關鍵所在[4]。我校基于扎實口腔本科學生專業知識,對傳統課程相對獨立,專業主干課程通常集中在后兩學年,即專業課程“集中獨立式”課程設置進行了改革,通過與荷蘭奈梅亨大學牙學院(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建立教學合作,借鑒其對專業的教育從入學至畢業貫通始終的課程設置模式[5],結合我校實際對專業課程采取了“貫通融合式”課程設置模式,課程間打破壁壘形成“以疾病為中心”知識體系,合理貫通安排于1~4學年。以該模式已完成一屆學生的培養,通過對比和統計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貫通融合式”課程設置模式在扎實口腔學生的專業知識方面相比專業課程“集中獨立式”課程設置模式具有更優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口腔醫學? 課程設置? 貫通融合? 本科教學? 應用
【中圖分類號】G42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21)32-0173-03
一、傳統“集中獨立式”課程設置模式的不足
1.傳統專業課程集中設置存在的問題。傳統的口腔五年制教育體系為3+2模式,前三年為通識課程和醫學基礎課程,后兩年為專業課程[6]。這種前三年基本不接觸專業課程,直到第三年才切入專業課程集中于后兩學年,這種拐彎過快的專業課程設置帶來學生早期的專業認同感和興趣不強,導致了學習專業的動力相對不足,影響教學效果的問題。
2.傳統專業課程獨立教學存在的問題。傳統本科主干課程相對獨立,課程之間各自為政,缺乏橫向的聯系,往往存在知識點重復教學。如齲病的內容涉及口腔解剖生理學、口腔影像學、牙體牙髓病學、口腔材料學、口腔修復學、口腔預防醫學等課程,分散在各課程中獨立講造成知識點的分散零碎化,不利于學生對知識的記憶和掌握。專業主干課程獨立式的教學,也帶來學生在某學期完成該課程考核后往往不再重拾課本,在第5學年臨床實習時對理論知識的掌握出現捉襟見肘,各實習基地也常反饋學生專業理論知識不夠扎實。
二、貫通融合課程設置模式具體內容
1.專業課程前伸,延長專業教學學年,將專業課程的設置貫通1~4學年。修訂2015級五年制口腔醫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將專業導論課程前伸至第1學期,牙體牙髓病學、口腔修復學、口腔頜面外科學、牙周病學、口腔專業英語等多門課程重新適當增加調整學時,并按理論知識由淺入深、實踐內容由簡入繁拆分為3~4部分,貫通設置在3~8學期中,保持專業教學的不間斷[4]。
2.專業課程進行融合,形成“以疾病為中心”的教學大綱。即所有專業課程打破壁壘,實現基礎、臨床和口腔專業知識體系的融合。如齲病,將與該病有關的各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中知識點拎出重新梳理,形成齲病知識體系來進行教學(圖2說明以齲病為中心的課程融合)。
三、教學效果分析
1.改革前年級和改革后年級的執醫考試理論成績的對比分析。2014級采用課程集中獨立式教學學生的執業醫師考試理論通過率為82%,專業平均分253.46分,2015級采用采用課程貫通融合式教學的學生執醫考試理論通過率為100%,參考人數專業平均分為271.06分(對比情況詳見表2)。雖然影響通過率和分數還與生源、教學過程、師資等諸因素相關,但課程體系作為傳授知識的載體,其設置模式是關鍵而重要的一環。我們將課程進行優化的“貫通融合”課程設置模式對提升學生專業理論成績在一定程度起到較好作用。
2.為了進一步說明兩種專業課程設置模式的教學效果,我們同時從報讀我院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2020屆其他國內口腔院校接受傳統集中獨立式畢業生隨機抽取30人(A組)作為對照組,從我校接受貫通融合式課程教學的2015級畢業生隨機抽取30人(B組)作為實驗組,對兩組的住培醫師理論測試成績進行了統計分析。
結果顯示,B組的成績高于國內同等水平大學本科生成績,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如表3所示。
四、總結及反思
將專業課程貫穿融合的課程設置模式突破傳統集中獨立的課程設置模式,是國內首家在口腔醫學本科教育中課程設置模式大刀闊斧式邁出的改革舉措,歷經近6年的實踐檢驗,極大推動了我校僅十幾年辦學歷程的口腔專業建設整體水平的高質量發展和提升。在2021年獲廣州市教學成果獎,同年獲學校教學成果一等獎。本專業在2020年獲批國家一流本科口腔醫學專業建設點。實踐及相關的數據分析證明,相對合理的課程設置模式是提升專業教學質量的關鍵因素之一[4],而以扎實學生專業理論知識為目標的貫通融合課程設置模式優于傳統集中獨立的課程設置模式。
在實施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教研室的教學任務變得更繁重了,從之前一個學年只承擔一門課程相對輕松的教學格局轉為每學期疊加了多個年級同一門課程不同階段,繁重得多的教學格局,另跨學科“以疾病為中心”的課程融合模式教學對教師跨學科教學能力要求提高了,這是在師資數量及教學能力帶來的較大挑戰,在后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結合我們在教學模式上采用了一定比例的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7],我們利用粵港澳灣區地理優勢及相關教育聯盟等聘請了香港大學13名兼職老師參與我院教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決了師資不足問題,另及時成立了教師發展中心,有計劃和有目的地培訓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教師的跨學科教學能力,確保了教學質量。貫穿融合的課程設置模式同時帶來的另一巨大挑戰是實踐平臺,當有3個年級均進入教改體系后,實驗教學中心一個學期需同時承擔多個年級的實驗課程,原實踐資源無法滿足教學需求,我們在取得多方支持后對實驗教學中心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擴建,目前口腔仿頭模數量已增加至145臺(每年招生人數為60人左右),另購進數字化仿真培訓系統多臺,在排課方面也進行了較為合理精準的排布,但實驗教學中心在學期的中后期仍基本處于滿負荷運作狀態,還需進一步優化和改擴建。
國家提出需推進高等教育提質創新,改革創新是發展的動力[8]。貫通融合課程設置模式是國內口腔本科教育專業課程設置模式的大膽嘗試,雖面臨諸多挑戰,但為口腔本科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路和借鑒。
參考文獻:
[1]劉雪楠,高學軍,郭傳瑸,等.關注新時期我國的口腔衛生政策[J].中華口腔醫學雜志,2017,52(6):331-335.
[2]王莉,張倩,等.中荷兩所院校口腔醫學教育的比較與啟示[J].醫學教育研究與實踐,2021,29(1):23-26.
[3]趙信義,等.軍醫大學口腔醫學本科教育[J].基礎醫學教育,2018,20(10):880-882.
[4]程藝,等.學校課程融合建設的探索研究[J].教師,2021(1):96-97.
[5]江千舟,樊明文,葛林虎,等.荷蘭口腔醫學教育及口腔醫學人才的培養模式[J].口腔醫學研究,2015,31(6):568-570.
[6]魏裕,等.本科口腔專業“3+2”教學改革模式探討 [J].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17(8):66-68.
[7]李福軍,等.國內口腔醫學專業PBL教學現狀及改革設想[J].科教導刊,2014,8(上):239-240.
[8]萬陳芳.高等教育國際化視閾下創新人才培養質量提升路徑研究[J].世界教育信息,2021,34(3):37-41.
作者簡介:
謝蘭竹(1976年8月-),女,廣東省河源市人,漢族,本科學歷,醫師/助教,長期從事口腔醫學教育管理工作。
李江(1969年6月-),男,吉林省長春市人,漢族,博士,教授/主任醫師,長期從事醫院管理、口腔修復臨床、科研及教學工作。
江千舟(1975年6月-),女,浙江平陽人,漢族,博士,教授/主任醫師,長期從事口腔醫學教育、科研、臨床醫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