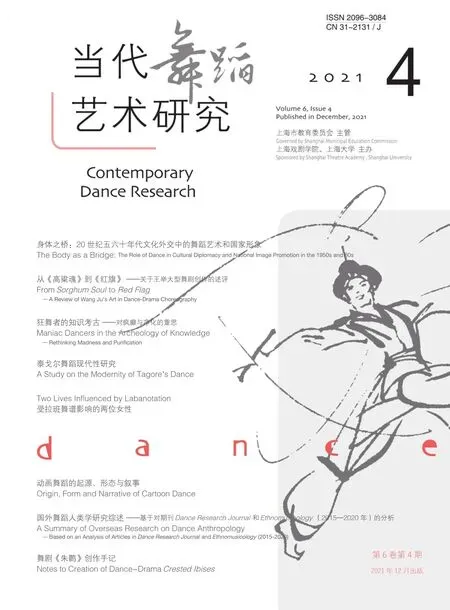“啟蒙”“立人”“民族性”
——以20世紀80年代魯迅文學遺產的舞蹈改編為考察中心
任文惠
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雨果、普希金等文學巨匠的經典作品都曾以多種藝術形式進行演繹與傳承,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魯迅的文學作品也是如此。魯迅為世界留下了豐富的文學遺產,美術、戲劇、戲曲、影視、舞蹈等藝術形式成為魯迅文學遺產繼承和傳播的重要途徑。對魯迅文學遺產的藝術傳承進行闡釋是個重要的課題,它不僅是文學與藝術之間的對話,更是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思想源泉不竭的生命力的體現。在這種闡釋中,舞蹈藝術曾經和魯迅的結緣再次浮出水面,這次結緣發生在剛剛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之初。①1981年,為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中國舞蹈界掀起了一股魯迅作品的改編熱潮,《祝福》《阿Q正傳》《傷逝》等先后被改編成舞劇,分別為中央芭蕾舞團的四幕舞劇《祝福》,中國歌劇舞劇院的獨幕舞劇《祝福》,上海芭蕾舞團的獨幕舞劇《魂》《傷逝》以及交響舞劇《阿Q》,重慶市歌舞團的舞劇《阿Q正傳》,空政歌舞團的舞劇《傷逝》。②其中中央芭蕾舞團改編的《祝福》已成為其代表性劇目,其第二幕曾在世界各地連續上演。《人民日報》《文匯報》《舞蹈》《舞蹈論叢》《上海舞蹈藝術》《上海戲劇》等報紙和雜志紛紛發表文章,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改編熱潮進行書寫與評論③,這一改編事件在當時無論是在創作實踐上還是在文字書寫上都頗具規模,盡管已經過去了40年,但它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舞劇發展史中卻是一段繞不開的文化記憶,[1]162—166并持續引發了中國舞蹈改編文學名著的熱潮。事實上,舞蹈作為身體語言的藝術和文學完全是兩套媒介系統,魯迅作為以思想深邃而著稱的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其作品的思想性與注重身體表現的舞蹈藝術之間似乎天然存在鴻溝,那么,舞蹈為什么要改編魯迅的作品?僅僅因為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這一契機?二者的邏輯契合點在哪里?相比較學術界對魯迅作品的其他藝術改編而言,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研究較為匱乏,本文以20世紀80年代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為考察中心,深窺其結緣的深層原因,透視舞蹈在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際遇,開啟魯迅文學遺產與舞蹈藝術傳承的互動研究,探尋舞蹈與文學在跨媒介的對話中背后的深層邏輯,從而挖掘魯迅文學遺產在不同藝術門類傳承中的深遠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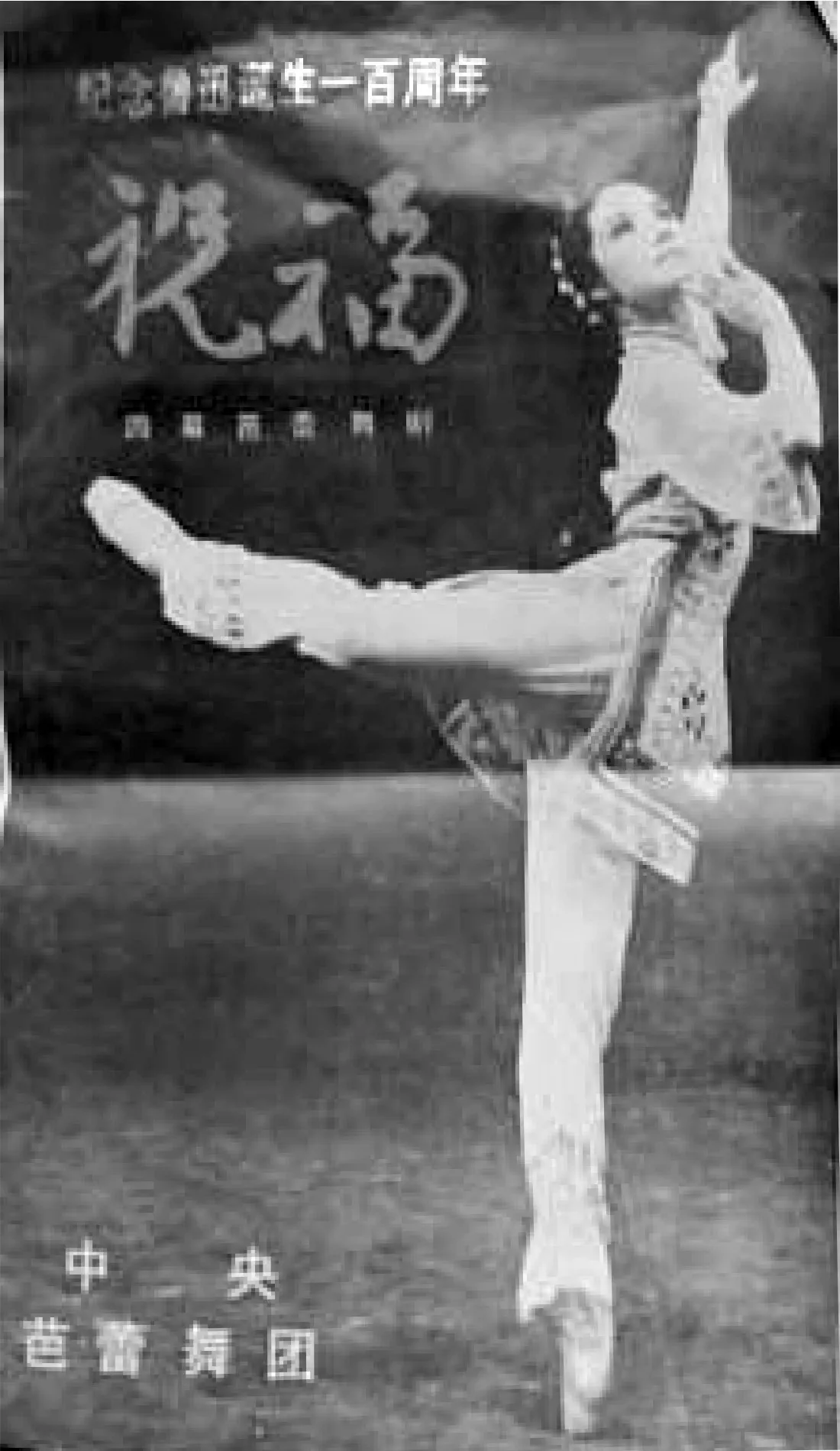
圖1 中央芭蕾舞團四幕芭蕾舞劇《祝福》節目單封面
一、啟蒙的隱喻:20世紀80年代魯迅作品舞蹈改編的邏輯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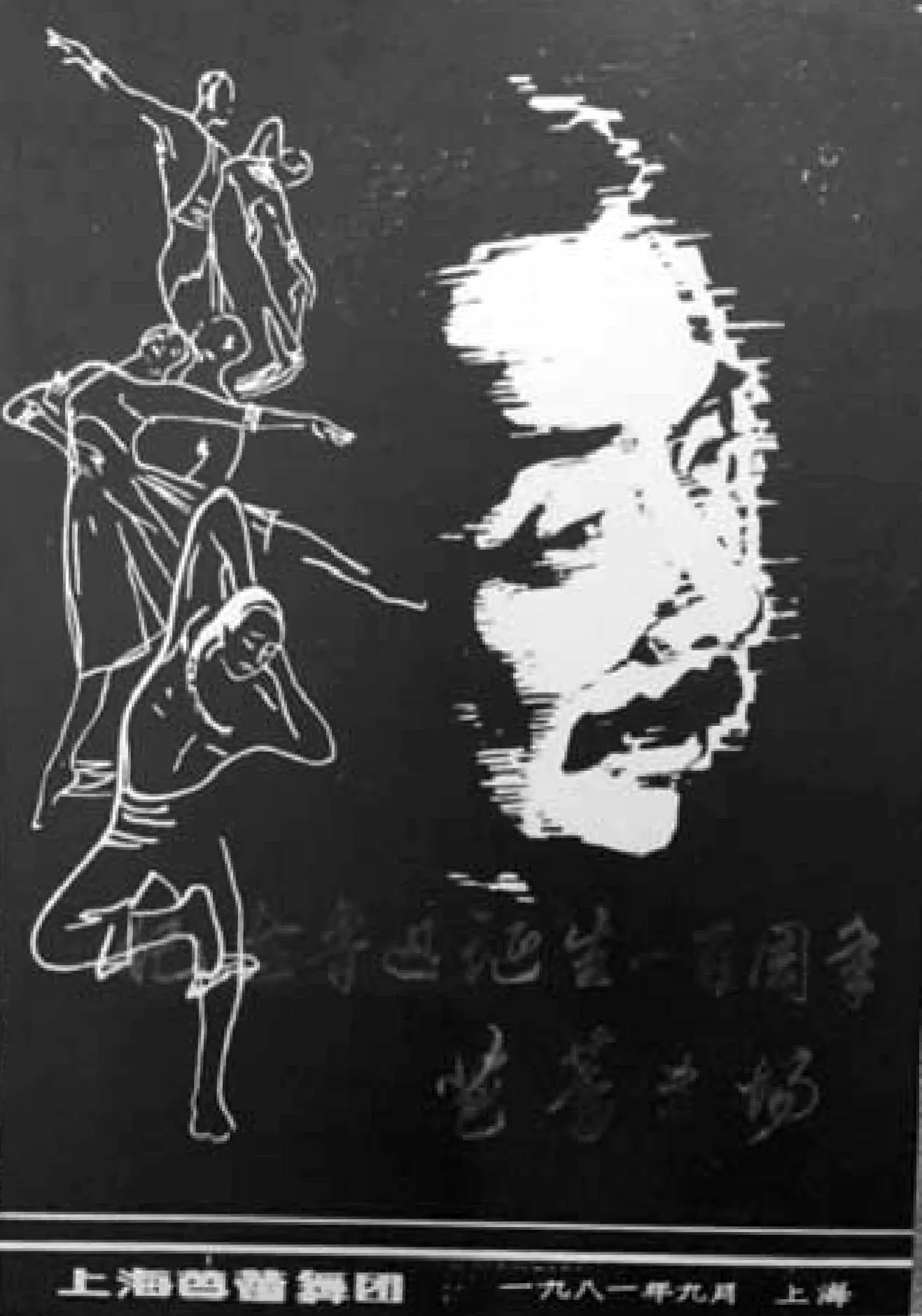
圖2 上海芭蕾舞團《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芭蕾舞專場》節目單封面
隨著“文革”的結束,20世紀80年代接續“五四”時期未完成的現代啟蒙,重新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征程,“對‘五四傳統’的重新啟用,幾乎可以說構成了80年代一個持續的文化展開過程”[2]。在這一過程中,為重返現代化的社會秩序尋求歷史的依據,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啟蒙精神再次出場,拉開了新時期啟蒙的序幕。作為20世紀舞臺藝術形象的舞蹈藝術,其本身就是現代國家身份形象建構的產物,吳曉邦的新舞蹈藝術、戴愛蓮的邊疆音樂舞蹈大會都曾在思想啟蒙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作為“民族魂”的魯迅及其作品鮮明的所指,更是將二者緊密地聯系了起來,魯迅作品的舞蹈形象改編從某種程度上也就成了新時期以啟蒙為中心的國家形象的重新登場。正如有的學者所言:“當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舞蹈改編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它們就和同一時代的文學共同構成了一次啟蒙主義的出場,一次關于人性、人道主義和人的主體性的敞開,一次對左翼歷史過程的共同反思,文學與舞蹈因此以共生的方式構成了關于歷史、生命、世界等方面的共同的言說和敞開。”[3]此時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在傳遞新時期的國家民族形象上保持了與國家話語的高度契合與統一,成為新啟蒙話語的重要象征和國家意志的體現,這一潛在的隱喻構成了其改編的內在邏輯向度,成為魯迅作品舞蹈改編的邏輯起點。
“文革”結束之后,隨著文藝“革命范式”一統天下的格局漸趨沒落,“現代化范式”逐漸確立。這一話語轉型帶來文化形態的重要變化,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知識群體主體性的迅速凸顯,他們從極端時期的被啟蒙者轉而獲取了主導權,成為新時期的啟蒙者并重新開啟了對社會和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在舞蹈領域,啟蒙的序幕首先由舞蹈編導拉開,唯“革命話語”的創作模式被打破,創作的主體性地位重新確立,首要體現就是“傷痕舞蹈”創作的出現。和“傷痕文學”“傷痕美術”“傷痕電影”等其他“傷痕藝術”一樣,《割不斷的琴弦》《無聲的歌》《啊,明天》等“傷痕舞蹈”的登場,同樣以主體性的“創傷記憶”開啟了新時期的舞蹈反思歷程。經受創傷的舞蹈創作主體帶著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思索重新反思舞蹈的創作,著力改變人們對于樣板戲時期的舞蹈印象,在創傷與反思的雙重驅動之下,魯迅走進了舞蹈創作者的視野:“粉碎‘四人幫’之后,許多正直的人們,特別是受到迫害的文藝工作者們,開始對我們社會的現實進行新的認識和探討,希望運用各種藝術手段,對它存在的矛盾進行揭示與剖析,以干預生活的姿態用作品參加撥亂反正的斗爭。于是一股文藝創新的潮流開始萌動……有著不幸遭遇和切身感受的祖慧④和我,以及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們,選擇了魯迅名著《祝福》作為舞劇的題材,并以極大的熱忱與勇氣,幾乎是不顧重重阻力要把它搬上芭蕾舞臺。我們是懷著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悲憤,對成千上萬受害者的同情,和力求使芭蕾藝術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這種思想感情作為動力的,可以說,它是痛定思痛的內心愿望。”[4]當舞劇的編導們在“文革”結束后由于切身的痛苦經歷再次不自覺地走近、回憶、紀念魯迅的時候,其喚起的是整個舞蹈界對于樣板戲時期中國舞蹈畸形發展的強烈反思,他們在精神實質上開啟了一段新時期舞蹈反思、批判的歷程,封建主義對祥林嫂的戕害觸發了編導對于“文革”帶給中國的創傷記憶,魯迅作品的改編因而成為舞蹈走出“文革”陰影、重新開始啟蒙的象征。在思想激蕩的20世紀80年代,舞蹈藝術家由創傷記憶而引發的主體性的復蘇與覺醒要借由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完成其主體性的言說,經由魯迅啟蒙者的形象建構舞蹈藝術的啟蒙姿態,開啟其在新時期的出場與轉型。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舞蹈為何要迫切進行重新的啟蒙?這也和中國舞蹈在這一時期的現實際遇與創作訴求有密切的關系。在中國舞蹈的創作表演中,“花鳥魚蟲”“神話傳說”是舞蹈表現的一些重要題材,“文革”時期,這些題材的作品被視為“毒草”,大受打擊;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思想的解放,舞蹈創作從單一的樣板戲中解脫出來,這一部分表現內容的作品又重新活躍起來,“花鳥魚蟲”重又回到人們的視野,但是這種繁榮的背后又使舞蹈界出現了一種單一的創作傾向,“仿佛舞蹈要表現美,就只有通過花鳥魚蟲和神話傳說之類”[5]。人們繼而反思舞蹈不再只是生活的再現,不應該僅僅只是外部肢體動作的技巧與美觀,單純給人以美的享受;也不應該只是某種風格的展示,而更應該是對文化的追問與探索,對社會現實生活的介入與批判。魯迅的作品為這種介入提供了絕佳的契機,其思想的批判性使中國舞蹈的題材和表現空間得到了延展,由生活的再現變為對生活的表現,并嘗試向思想的深度開掘發出挑戰。在這一轉型的內在力量驅使之下,由魯迅小說《祝福》改編的獨幕舞劇《魂》的創作組發出這樣的疑問:“藝術除了給人們以美的享受之外,與此同時是否也應該給予人們思想上的啟迪?!我們談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先驅——魯迅先生和他的作品,一種崇高的責任感給了我們勇氣,終于選定了《祝福》作為改編成劇本的題材。”[6]24魯迅作品的改編對中國舞蹈在新時期的轉型可謂是意義非凡,吳曉邦這樣評價道:“我看了他們的芭蕾《魂》,不由地感到這些年輕舞蹈家們已經離開了50年代芭蕾表現王子、公主神話傳說的陳規老套而進入大膽面向現實生活的新探索。”[7]這一轉變對芭蕾藝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芭蕾在中國的發展一開始主要移植了西方王子公主、神話傳說的模式,盡管也曾有過《紅色娘子軍》《白毛女》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品,但其革命范式和新時期的話語訴求明顯產生了疏離,對樣板戲極端排他性經驗創作者對這一模式從潛意識中開始揚棄,并尋求更具文化主體意識的表達:“芭蕾藝術不僅可以表現神話、民間傳說等古典或浪漫主義作品,也應該走向表現人,表現人的命運,表現整個社會和時代的現實生活的道路。”[6]24經由魯迅作品的改編,中國舞蹈完成了其時代訴求——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和介入,使中國芭蕾舞蹈藝術從神話走向現實,正是這種對舞蹈藝術主體性的反思,由再現向表現的文化主體意識的內在訴求,對舞蹈深層文化功能的開掘成為新時期舞蹈啟蒙的另一邏輯向度和內在驅動力。
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美學熱、文學熱成了最炙手可熱的名詞,“文學在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成為政治表達和情緒釋放的重要載體”[8]。舞蹈掀起文學改編的熱潮也是在這種時代氛圍與癥候之下的必然反應,它和其他文學藝術一樣,從反思與批判開始,重提創作者的主體意識和文化意識,完成80年代中國舞蹈藝術觀念的革新與舞蹈思想的新啟蒙,而在歷史的契機之下,先由魯迅完成了這一主體性的啟迪與導引,不得不說既是巧合,也帶有某種必然。
二、“立人”的賡續:魯迅作品舞蹈改編的立場與策略
中國舞蹈以現代舞臺藝術為主的呈現方式是進入20世紀以后的事情。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發展迅速,其舞臺化的建構主要與參與國家形象的建立直接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段時期舞蹈發展以風格形式的確立為中心的模式,革命樣板戲更是以“三突出”的形象塑造為主要的舞臺訴求,人自身情感的表達處于失語的狀態。“文革”之后,經過反思,“人”的重新發現和再次回歸,成為20世紀80年代文學和藝術的共同主題。在舞蹈藝術中,“人”的探索構成了80年代最恒定的主題。《再見吧,媽媽》《希望》等作品都從不同角度探索人的情感向度。“五四文學”確立了人的文學,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以“人”為最根本的指向,“立人”是魯迅作品與思想中的核心觀念,對人的思考一直是魯迅思想中的重要命題。中國舞蹈回歸到人自身,這與“五四”以來魯迅“立人”思想一脈相承,二者在80年代的相遇是整個20世紀的對人這一重要主題的現代探尋下必然的重逢。正是這種從人自身出發的創作訴求,使得這一時期中國舞蹈在“人”的重新出場與人性的覺醒中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也是80年代中國舞蹈對“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立人”話語的重新征用與賡續。
首先以中央芭蕾舞團的四幕舞劇《祝福》為例,在“立人”的改編立場和主體結構召喚之下,舞劇的改編緊緊抓住“人”這一核心展開,圍繞著表達人、塑造人這個中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祥林嫂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祝福》中的女性形象通過和《紅色娘子軍》中革命女戰士瓊花的英武形象相對比,塑造以祥林嫂為代表的江南女子柔美的形象。第一幕《魯鎮河畔》大約6分半鐘的水鄉女子浣紗群舞伴隨著江南《茉莉花》曲調,將芭蕾舞的優美充分展現出來,這一鮮明的對比昭示著新時期的芭蕾舞劇對革命范式的告別,回歸舞蹈的審美范式。在“立人”的創作原則之下,和原作相比,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在舞劇結構上進行了創造與轉換,芭蕾舞劇《祝福》分為序幕《荒野陵園》、第一幕《魯鎮河畔》、第二幕《賀老六家》、第三幕《賀老六家》、第四幕《觀音廟堂》。結合芭蕾舞劇表現的特點,舞劇《祝福》去掉了原著中的敘述者,以祥林嫂為主要人物的心理情感發展建構整個舞劇結構,最大的改動是在小說中以背景人物出現的賀老六在舞劇中作為主要人物而出現,因而賀老六家兩次出現成為舞劇發生的主要場景。將小說中的隱性人物變為舞劇中的主要人物,這是從芭蕾舞雙人舞的表現特點出發的,改編不是照搬原著,而是結合改編藝術自身的藝術特點進行的二度創作,所以全劇根據舞蹈的表現特點進行了從文學到舞蹈的跨媒介轉換,第二幕和第三幕都是圍繞祥林嫂和賀老六的情感以及悲劇故事展開,其第二幕《賀老六家》中祥林嫂和賀老六的苦結良緣成為《祝福》全劇的經典片段⑤。在這一幕的雙人舞中,圍繞祥林嫂和賀老六的人物關系,編導分三個段落來表現祥林嫂對賀老六情感的轉變,第一段用中段舉扶和地上扶的動作,用急轉、急舉等技巧,突出祥林嫂要出走而賀老六極力挽留的情感狀態。第二段用靜場和矛盾掙扎的動作組合,表現祥林嫂從執意要走到內心充滿激烈的思想斗爭的情感變化。第三段用靜場和連續托舉組合,表現祥林嫂被賀老六感動最終決定留下來的情感轉折。這三個舞段一氣呵成,配合音樂的主題變化對祥林嫂和賀老六的情感發展過程進行了很好的詮釋,這是舞劇的祥林嫂所獨有的。這種轉換在新時期的中國舞蹈的創作觀念上是一種巨大的變化,它借由芭蕾藝術男女雙人舞的形式特點拆解了“十七年”和樣板戲時期舞蹈藝術對男女情感表達的壓制和隱匿,以祥林嫂心理情感的發展變化建構舞劇的主體結構。通過祥林嫂情感、精神幻滅這一角度,將以人物為中心,著力開掘人的心理與情感的新時期舞劇創作模式與“十七年”、樣板戲時期的舞蹈拉開了距離,用“人性”表達取代了“神性”塑造。
同樣根據《祝福》改編的上海芭蕾舞團的獨幕舞劇《魂》劇也是如此,“《魂》劇的創作,我們力求從人物出發,從人物內心世界出發,打破程式,摒棄唯美主義的傾向”[6]25。但相比較于中央芭蕾舞團的《祝福》,上海芭蕾舞團的《魂》在結構的改編上更為大膽、更具突破性,作為獨幕舞劇,同樣去掉了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緊緊圍繞小說中祥林嫂提出的“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那么,也就有地獄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三個問題展開,圍繞這三個問題,祥林嫂發問的動作設計改變了芭蕾優美的外形動作,改為雙腿關閉半蹲,雙手在胸前彎曲攤掌的形態,從人物出發而不是從動作的風格性出發,體現出創作者以人物為核心的創作理念。

圖3 中央芭蕾舞團《祝福》劇照
舞劇從祥林嫂被趕出魯家大門,在痛苦、悲憤和絕望中產生幻覺開始,以祥林嫂的心理意識為敘事的邏輯,首先是祥林嫂被趕出魯家的大門,伴隨激昂悲傷的音樂,她不斷敲門叩問。幻覺中象征兒子阿毛的虎頭鞋出現,音樂隨之轉而歡快,之后是祥林嫂和賀老六抒情的雙人舞,群鬼和閻王出現分開二人,推出祥林,制造更多的矛盾與痛苦,之后是祥林嫂、賀老六、祥林之間矛盾掙扎的三人舞,將祥林嫂在祥林和賀老六之間的拉扯與痛苦用人體的動作與造型加以呈現,最終群鬼向上拋起祥林嫂,將近2分鐘的空白為觀眾留下了思考的空間……最后祥林嫂再次出現在魯四老爺家的大門口,通過八個舞姿造型將祥林嫂的發問與控訴推向高潮。這種舞蹈的獨有處理方式,突出了祥林嫂的心理和精神創傷,增強了作品的控訴力量,形成了更深刻的悲劇力量。獨幕舞劇《魂》不以情節的敘述為中心,而是從人物的心理感受與變化出發,將祥林嫂的心理幻覺與現實際遇交替結合起來,從舞劇創作的“戲劇結構”轉向“心理結構”,體現出鮮明的結構變化,使舞劇不再受制于戲劇的敘事邏輯限制,專注于人物情感、心理變化的深度挖掘,打破時空的限制,充分發揮舞蹈藝術長于抒情的特質,強化了舞蹈本體意識,帶來視覺藝術更突出的震撼效果。這種“心理結構”的表現方法也預示著20世紀80年代舞劇發生的創作轉向,它“揭開了中國芭蕾歷史新的一頁。祥林嫂的人生轉折也為中國芭蕾的歷史轉折提供了一個起點”[9]24。

圖4 獨幕芭蕾舞劇《魂》劇照
這樣的轉向,在交響舞劇《阿Q》的改編中進一步得到了深化,《阿Q》的創作極其重視音樂和舞蹈的關系,作曲家全程參與了舞劇結構的創作,力求使舞蹈和音樂互為表里、水乳交融。《阿Q》突破了舞劇結構的慣常概念,不以故事情節取勝,而是人物的精神狀態為貫穿線,多層次地刻畫出人物的幾個側面。用創作者的話來說,就是“采用了交響樂曲中四個樂章但不間斷的結構”,擇取阿Q遭遇中的四個片段:“賭博”“戀愛”“幻想革命”和“大團圓”,而給阿Q勾勒了四幅畫像。這個結構法也可以說是四個“舞章”,它們既相對獨立,又都以阿Q的“精神勝利法”貫穿其中[10]。第一樂章“戲謔曲”用賭博的舞蹈體現阿Q的“精神勝利法”,第二樂章“圓舞曲”以不正規節拍的圓舞曲節奏和旋律來體現阿Q的“戀愛悲劇”,第三樂章“進行曲”表現阿Q“幻想革命”,第四樂章“送葬進行曲”表現阿Q被槍決[11]。舞劇《阿Q》中這種帶有探索意味的“樂章結構”,使舞蹈在與音樂的融合中產生戲劇的張力,避免了阿Q這一人物形象在舞臺上被圖解的尷尬,很好地將文學中的人物轉化為舞臺上的人物,在舞蹈和音樂自身的藝術屬性中探尋阿Q在不同媒介轉化中的出場方式,同樣也在舞劇的結構形式方面具有很大的創新。交響舞劇《阿Q》的創作可稱為后來舞蹈界出現的“交響編舞法”的前奏,它帶給舞劇創作者更多結構形式的嘗試和多種可能的空間,這對于習慣了戲劇芭蕾的中國芭蕾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突破,而這種嘗試正是從深入挖掘阿Q這一人物的精神狀態開始的。在改編中“立人”的立場直接導致了舞劇結構思維的創造與轉換,使以追求戲劇性為主的舞劇創作向舞蹈本體的創作方式進行探尋與嘗試,這種結構的創新“標志著80年代初期中國芭蕾對60年代中期中國芭蕾的一個超越”[1]166。

圖5 獨幕芭蕾舞劇《阿Q》劇照
繼魯迅之后,舞蹈界又陸續出現了對曹禺、巴金等現代文學大家作品的改編,文學名著沉郁著的“人文氣息、思辨精神、哲理性以及歷史穿透力,為創作心象的構成提供了厚度”[9]24。《繁漪》《鳴鳳之死》等作品在創作手法及結構上進一步以人物為核心,向人物心理進行深度開掘,嘗試意識流表現手法,在舞劇結構的轉換與創造上取得了更大的突破,成為中國舞劇探索人、塑造人、立人的重要創作轉向,同時也開啟了中國舞劇在這一時期以人為核心的重要創作模式的轉變,為中國舞劇從風格形式向情感表現的現代轉換打下了基礎,這種創作模式和魯迅“立人”的感召是密不可分的。
三、民族性與世界性:芭蕾“民族化”與魯迅文化觀的當代意義
在20世紀80年代舞劇的文學改編中,芭蕾舞首開先河并對中國芭蕾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芭蕾作為一種外來的舞蹈藝術,在其進入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是中國芭蕾幾十年來面臨的一個重要命題。“民族化”曾是中國芭蕾發展的一個重要路徑,而如何民族化,如何處理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的關系,在中國芭蕾的發展中就顯得尤為重要。魯迅的文化觀對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參照視角,他在《文化偏至論》中所說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12],對中國文化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關系進行了很好的詮釋。在《看鏡有感》中魯迅談到了對漢唐文化開放態度的認同:“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13]再到《拿來主義》中在對待西方文化時,魯迅贊同“拿來主義”的態度,“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14]。魯迅的上述文化觀對中國芭蕾的發展頗具啟發意義,以世界人的視野,開放的姿態,兼收并蓄,將世界優秀的文化遺產拿來為我所用,同時保存自身的文化血脈,在文化發展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達到共融。中國芭蕾民族化的追求和魯迅的文化立場也在某種層面上達成契合。
芭蕾民族化一直是中國芭蕾發展的一個重要藝術追求,改編中國文學大家的文學名著,同時也是中國芭蕾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部分:“中國芭蕾舞劇的名著改編之潮,始于70年代末,盛于80年代中期。它們也是80年代以后中國芭蕾舞劇創作的真正體現者,是新時期芭蕾民族化探索的最重要的成就。”[15]從《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的芭蕾民族化探索肇始,到20世紀80年代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都是芭蕾在民族化道路上不斷的深入。因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的芭蕾,應該始終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16]539。在“創造出中國人自己的芭蕾”的目標的引領之下,“我們一方面要把中國傳統的民間文學、神話故事編成舞蹈(劇),還要努力創作出反映近代中國人‘靈魂’的舞劇,這將更有現實意義。為此,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師的名著都可以成為我們創作的題材。即使失敗了,我們也愿做一塊鋪路的石子。”[16]539芭蕾為什么要民族化,這是中國舞蹈參與現代化國家形象建構的一個重要使命:在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確立新時期的國族形象,與作為民族魂的象征的魯迅的“聯姻”在一定程度上穩固并深化了這一重要使命。
芭蕾民族化的話語實踐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50年代的芭蕾舞劇《和平鴿》,因其西方化與民族的接受上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受到質疑。如何將古典芭蕾的貴族化氣質轉化為人民大眾的文藝形象,是中國芭蕾在發展之初就面臨的生存與發展的大問題。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顯然行不通,在文藝“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方向的指引下,60年代,芭蕾民族化的創作意識占據了主導地位,民族化的實踐在《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這兩部舞劇在毛澤東“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和“文藝為廣大群眾服務”文藝方針的指導下,在把握芭蕾基本形態特征的基礎上,融合中國民族民間的舞蹈語匯,塑造出了當代中國人民的革命形象,突破了西方芭蕾的人物模式,創造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芭蕾形象。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時代,當中國以完全開放的姿態重新融入世界之時,重新回顧魯迅的文化觀的時代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對于中國芭蕾而言,在新的歷史機遇面前,如何將世界優秀的舞蹈文化拿來為我所用,對世界傳遞中國形象,真正建構中國芭蕾在世界芭蕾之林的一席之地,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這一時期的民族化和前一時期相比,在內涵和指向上都在發生變化。有學者將新中國成立后三個時期的中國芭蕾的民族化用三個形式來總結[17]28—29,《和平鴿》時期是“套用型”,將西方芭蕾的天鵝置換成中國的和平鴿,更多的是直接移植與套用;《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是“糅合型”,將中國舞蹈語匯與中國的舞蹈形象和西方芭蕾糅合起來,在創作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而到了80年代,以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為代表的《祝福》《魂》《阿Q》等則已經成為“滲入型”,不再是簡單的拼接,而是將“民族風格、民族氣質、民族文化內涵與芭蕾固有的規范美結合在一起”[18]。以中央芭蕾舞團的《祝福》為例,為了更好地體現該舞劇中人物的民族氣質,創作者在舞蹈語言的選擇上除了芭蕾舞固有的動作之外,還結合民族舞蹈進行了舞蹈人物形象的塑造。祥林嫂身上除了芭蕾語匯之外,還融入了戲曲青衣和朝鮮族舞蹈的元素,表現其矜持謙恭的人物性格;賀老六身上則融合了戲曲武生的沉穩堅毅和山東鼓子秧歌的樸實粗獷。這種融合不僅沒有違和之感,反而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編導沒有把民族舞蹈當作民族化的裝飾,而是“從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出發,在我們多種的民族藝術里,集中提煉具有體現這種特征的因素,在提煉的過程中,又始終著力和芭蕾語言的融合……構成了既有芭蕾特點、又有民族氣質的完整的舞蹈形象”[19]。《祝福》的音樂的創作上也清晰地體現了濃郁的民族特點,江南《茉莉花》曲調、紹興戲的曲牌用現代音樂的技法予以創作,結合符合人物形象特點的主題音樂,將民族音樂和舞蹈很好地統一起來,也在芭蕾舞詮釋民族精神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芭蕾舞劇《阿Q》也在民族化的探索上進行了諸多嘗試,在創作之初,創作者面臨著如何“既能用芭蕾的語匯來為阿Q設計舞蹈,又能避免舞臺上阿Q的洋化”[20]543的難題,最終創作組決定必須服從“必須像阿Q”這一原則,并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打破了古典芭蕾追求挺拔瀟灑的男子形象的傳統,用“反背雙手,雙腳輪流拖收五位,身體左右搖擺,以帶動頭上的小辮一晃一晃”的動作作為阿Q的主題動作[20]544,力求既要符合芭蕾的特征,又要突破傳統芭蕾的限定而具有民族的特色。最終舞臺上的阿Q得到了認可,因為“它既是芭蕾,確又是中國民族氣派的芭蕾,……是芭蕾民族化道路上邁進的一大步”[21]。
中國芭蕾從“套用型”到“糅合型”再到“滲入型”,轉變可謂是意義非凡:“40 多年的實踐摸索,中國的芭蕾藝術正一步步踏入意識與操作的成熟期,使得“以中國人的意識,利用芭蕾的手段,表現新的內容成為“中國芭蕾的某種共識,建立中國芭蕾學派的朦朧目標似乎也明確起來。”[17]29與芭蕾紅色經典的民族化相對照,20世紀80年代魯迅作品舞蹈改編中《阿Q》的交響芭蕾編創,《魂》的心理結構等的嘗試,見證著中國芭蕾經過特定歷史環境下的民族化的發展再次向世界性靠攏,在民族性的探索上更具精神性的內涵,逐漸從革命范式向現代范式轉變。樣板戲時期的《紅色娘子軍》《白毛女》芭蕾的民族化是為了革命化與群眾化,沒有了革命化與群眾化,民族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中國芭蕾的民族化探索,更多的是以中國芭蕾現代化為目標,是中國芭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的現代訴求,從革命樣板戲到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民族化歷經革命文藝的實踐到新時期世界視野下的文化訴求,又回到了魯迅在五四時期自覺以世界人為視野的自我反思與探索,尤其是中央芭蕾舞團的芭蕾舞劇《祝福》第二幕廣泛在世界各國巡回上演,不僅傳播了魯迅的國際聲譽,而且促進了芭蕾“中國形象”的建立,對西方優秀舞蹈文化遺產的借鑒與征用,出于中國芭蕾自發的創造性轉化的內在動機,是開放的中國一步步走向世界的明證。魯迅關于文藝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論述再次對舞蹈藝術在新時期的歷史使命給予了確認與回答。
結 語
今年是魯迅誕生140周年,距離紀念魯迅誕生100周年的舞蹈改編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但40年前中國舞蹈界這一具有重大影響的文化事件,伴隨著中國舞蹈40年發展的步伐從未被遺忘,其意義隨時代發展而愈加凸顯,直接掀起了新時期中國舞蹈創作改編文學名著的高潮,使中國舞蹈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改編雖是為了紀念,但這次舞蹈改編并不是簡單的在舞蹈的園地中出現魯迅的身影,借以和其他藝術形式形成平等的地位,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如何將魯迅的精神資源注入中國舞蹈藝術的社會價值與文化價值中去,使其更好地傳承與發揚,從而從多角度詮釋魯迅與20世紀中國文藝的血肉聯系。20世紀80年代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不僅是作為舞臺藝術的舞蹈在構建新時期國家形象上借用魯迅的文學作品完成的啟蒙隱喻,更是從文化的層面出發對舞蹈創作本體語言的革新與創造,并為重新審視舞蹈藝術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問題,為中國舞蹈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提供生動的案例,也為魯迅文學遺產與舞蹈藝術的傳承與對話開啟一個新的研究視閾。
【注釋】
① 據文獻記載,早在1977年舞蹈界就有人提出把魯迅的《祝福》改編成芭蕾舞劇的建議,見蔡國英,等.路是人走出來的[J].上海舞蹈藝術,1981(3):19.
② 這些作品中影響較大的是中央芭蕾舞團的四幕舞劇《祝福》,上海芭蕾舞團的獨幕舞劇《魂》《傷逝》以及交響舞劇《阿Q》。
③ 圍繞魯迅作品的舞蹈改編,據不完全統計,各類報紙和雜志先后刊登了近30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對改編進行書寫。其中包括舞劇的文學臺本3篇,分別為宋國良等的《〈魂〉舞劇文學本》、錢世錦的《〈傷逝〉舞劇文學本》《〈阿Q〉舞劇文學本》(均刊載于《上海舞蹈藝術》1981年第3期;另外還有新聞報道、創演談、評論若干篇,分別為《魂》劇創作組的《〈魂〉劇創作的幾點體會》(刊載于《舞蹈》1980年第4期);孔小石的《為芭蕾舞探索新的道路——看獨幕芭蕾舞劇〈魂〉有感》(刊載于《上海戲劇》1980年第4期);舒巧的《舞劇要創新——看芭蕾舞劇〈魂〉的感想》(發表于《文匯報》1980年6月16日第4版);《祝賀魯迅三篇著作搬上芭蕾舞臺》(發表于《舞臺與觀眾》1981年9月26日);荒雄的《努力開拓芭蕾民族化的道路——評獨幕舞劇〈魂〉、〈傷逝〉、〈阿Q〉》,陳沂的《一次成功的嘗試——祝賀魯迅三篇著作搬上芭蕾舞臺》,杜宣的《祝魯迅作品改編舞劇成功》,拾風的《最好的紀念》,蔡國英等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奚其明的《舞劇音樂要著力抒發“情”》,施雄的《努力開拓芭蕾民族化的道路——評獨幕舞劇〈魂〉〈傷逝〉〈阿Q〉》,歐陽云鵬的《演涓生的一些體會》(均刊載于《上海舞蹈藝術》1981年第3期);陳敏凡的《紀念魯迅和舞劇〈祝福〉的構思》(刊載于《舞蹈論叢》1981年第3輯);吳曉邦的《舞蹈要和人民的生活相結合——看〈魂〉〈傷逝〉〈阿Q〉后的感想》(刊載于《舞蹈論叢》1981年第4輯);周威侖的《“這是我們自己的芭蕾”——〈祝福〉民族化斷想》,胡爾巖的《壓力與追求——寫在〈祝福〉上演之后》,呂兆康、計文蔚的《大膽嘗試 別開生面——評芭蕾舞劇〈魂〉的藝術構思》(均刊載于《舞蹈》1981年第4期);劍兵的《篇章明 含意深 舞姿美 手法新——評舞劇〈傷逝〉》,嘎倫的《一首深沉凝煉的舞蹈詩——看歌劇〈傷逝〉中的雙人舞》,錢世錦等的《阿Q站立在芭蕾舞臺上》,方雄的《敢出難題 勇創新意——評獨幕舞劇〈阿Q〉》,萬戈等的《金菊一枝入苑來——小型民族舞劇〈祝福〉觀后》(均刊載于《舞蹈》1981年第6期);歐陽云鵬的《外部動作要與內心體驗相統一——演涓生》(刊載于《上海戲劇》1981年第6期);周威侖的《〈祝福〉上了芭蕾舞臺》(發表于《人民日報》1981年8月29日第8版)等。
④ 即蔣祖慧,芭蕾舞劇《祝福》的編導,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編導之一,作家丁玲之女。
⑤ 在1980年北京舉行的文化部直屬院團觀摩評比中,該劇獲演出、編導、表演一等獎,作曲、舞美二等獎。在1994—1995年舉行的“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評比展演中,第二幕獲經典作品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