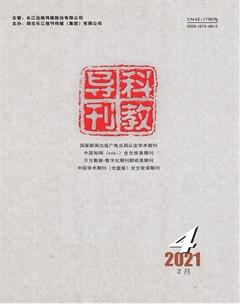認知語言學啟示的英語動詞短語課堂教學設計
摘 要 認知語言學系統地解釋了語言的構成、使用和學習,為這一學派啟發和運用于外語教學提供了充分理論依據。本文在國內外相關研究基礎上,以英語動詞短語take up為例,從微觀層面具體呈現一項基于認知語言學原則性多義模型的課堂教學設計。
關鍵詞 認知語言學 動詞短語 教學設計
中圖分類號:G424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s.2021.02.061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of English Verb Phrases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QIN Ji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Abstract Cognitive linguistics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formation, use and learning of language, which provides a sufficie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is school to inspire and appl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lish verb phrase take up as an example to present a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the principled polysemy model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from the micro level.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verb phrases; teaching design
0 引言
在過去的30余年,認知語言學和基于使用的語言觀已經成為二語習得研究的主流學派之一(Tyler, Ortega, Uno, & Park, 2018)。作為一種語言學學派,認知語言學認為小至詞語,大至句子和語篇層面,對任何層面的語言結構的理解都不能脫離關于語言是如何創造意義的研究;換句話說,所有的語言單位都有意義。意義構建的本質是概念化,意義指頭腦中的概念結構而非客觀的獨立于頭腦之外的外部世界,其特點是具有高度主觀性。因此,對語言單位的意義的討論等同于探討概念化的本質。而且,這種具有高度主觀性的概念化并非空穴來風,而是來源于外部世界的空間物質屬性以及人類感知世界的經驗和與物質世界的互動,即意義是在與世界的體驗互動中構建的。認知語言學的這些核心思想,包括意義構建、概念化本質和體驗意義,系統地解釋了語言是如何構成、使用和學習的,也為這一學派啟發和運用于外語教學提供了充分理論依據(Masuda, Arnett, & Labarca, 2015; Tyler, 2012)。
近十年來,國際上已有一些學者先后開展了認知語言學運用于課堂環境下二語教學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的目標語言形式涵蓋單詞(如介詞、小品詞、情態動詞)、短語(如搭配)和句子層面(如條件句、致使-接受構式),研究結果大致表明與無教學干預相比,認知語言學啟示的二語教學有一定效果。國內亦有一些學者探討過認知語言學與外語教學的結合,他們的研究以理論評介和啟示為主,從宏觀層面為認知語言學在外語教學中的運用拓展思路和奠定基石(劉正光、艾朝陽, 2016;秦潔,2020;文秋芳,2013; 文旭, 2014)。然而,國內很少有學者從微觀層面深入探究認知語言學理論如何運用于二語教學研究及效果如何,朱京和賈冠杰(2018)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但其構建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仍過于寬泛,僅依照此教學模式實施課堂教學的可操作性不強。因此,本文旨在在國內外研究基礎上,以一項具體的語言構式——英語動詞短語為例,從微觀層面具體呈現基于認知語言學理念設計的課堂教學模式。
1 認知語言學的主要理念
與傳統學派不同的是,認知語言學將短語視為可分解和可分析的,認為它們的意義并非隨機的而是具有理據性,即形式和意義之間是有理可循、有據可查的。一個短語的各個單元的意義系統地構成這個短語整體的基本義和比喻引申義(Yasuda, 2010)。而且,對短語的解釋不僅僅基于詞匯單元的意義組合,而且有賴于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交際情境和認知機制,后者如比喻、轉喻、思維空間等(Mahpeykar & Tyler, 2015)。例如,動詞短語get up由get和up組成。Get描繪隨時間推移的一種動態關系,up則展現動體(trajectory,即聚集的元素)相對于界標(landmark,即背景)的一種空間關系,兩者的結合是構成get過程的動態關系和up表示的空間格局的融合,代表動體從一個較低的位置向更高的位置移動(或被移動)。以此為基礎,我們還可以借由比喻、轉喻、思維空間等認知機制,從get up基本義進一步延伸至不同交際情境下的引申義,如在“get up a game for Christmas”表達中get up取組織活動義。
在認知語言學框架內,Tyler和Evans (2003)針對介詞的多義性研究開發出一個專門分析詞語多義性的理論框架——原則性多義模型,其核心觀點是一個詞語的多個意義之間既獨立又相互關聯。在介詞多義性研究基礎上,Mahpeykar和Tyler (2015)將這一模型延展至動詞短語的多義性分析。與其它基于認知語言學的分析模型相比,原則性多義模型的獨特優勢在于:(i) 多義性分析的基礎是一些廣泛認可的認知機制,比如體驗意義、語用推斷和經驗關聯等;(ii) 它基于對詞源的深度分析和多義性網絡確定詞匯單元的基本義;(iii)它由基本義出發系統地推導出比喻引申義,并有一套標準評判某個具體使用是否構成一個單獨的意義,或只是同一個意義在不同語境下的使用。
2 英語動詞短語課堂教學設計
基于Tyler等提出的原則性多義模型(Mahpeykar & Tyler, 2015; Tyler & Evans, 2003),本文嘗試以take up為例設計課堂教學,旨在從微觀層面啟示認知語言學在外語教學中的運用,并為此研究方向的實證研究打好鋪墊。
步驟一:認知語言學基本理念講解
認知語言學的諸多概念與傳統語言學大相徑庭,因此有必要在課堂教學的開始階段先系統講解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念和術語,為后續教學步驟打好基礎。
可分解性:動詞短語是可分解和可分析的,每個動詞短語的單個部分意義系統地構成對整體意義的解讀。
動體與界標:在“the bike lays besides the river”表達中,動體為the bike,通常是一個運動的、活躍的、相對較小的物體;界標為the river,往往是一個靜態的、穩定的、相對較大的物體。若反過來,“the river lays besides the bike”表達則不合乎常理。
概念隱喻:人們借助對外部物理世界的理解來表達情感、體驗、感受等內在抽象概念。這是因為在人類對世界的體驗中,如果兩個原本獨立的現象反復地共同出現,人們會逐步建立起它們之間的關聯,一旦建立了這種緊密關聯,人們傾向于用外部現象來表達內在感受。
意義引申:由于概念隱喻的普遍存在,一個單詞或詞組兼有基本義和比喻引申義。基本義指基于詞語的詞源詞根分析和在當代語料庫中詞語使用確立的最基本的意義,比喻引申義為根據語料庫中詞語使用歸納的與基本義涵義不同但又系統關聯的其它意義。
步驟二至四:Take up概念知識講解
先單獨分析take和up各自的基本義和引申義,再分析兩個詞的組合如何構成take up的整體基本義及引申義(Mahpeykar & Tyler, 2015)。講解的重點放在結合動體、界標概念闡述整體義如何由單個詞組合而成,并在基本義基礎上結合概念隱喻和意義引申推導出引申義。
步驟五:討論和內化
教師從語料庫中搜索一些蘊含take up基本義和引申義的例句,組織學生分組討論每個句子中take up的意義,并要求他們繪制意義圖或向同伴口頭描述關于短語意義的概念知識。分組討論結束后進行教師引領的全班討論,目的是內化學生對意義的分解和組合、基本義與引申義的關聯的概念化知識。
3 小結
本文以英語動詞短語take up為例設計了基于認知語言學原則性多義模型的課堂教學具體步驟。在課堂上,教師首先細致剖析take和up各自的基本義和引申義,之后解析兩者的組合如何構成整個詞組take up的整體基本義及引申義。由于這種語義分析涉及認知語言學一些基本理念,如意義構建、概念化本質、概念隱喻等,學生在語義分析和討論過程中必然需要深刻體會和理解這些核心理念,甚至需要更新他們已有的關于形式與意義的關系的認知模式。當然,本文由于篇幅有限,未能檢驗認知語言學運用于課堂外語教學的成效如何,也無法驗證認知語言學關于形式和意義的關系是否可以延展到新的詞組中。未來研究還需在理論層面融合多種學派和視角,并采用多樣化的測量工具和數據分析方法在不同情境下反復取樣驗證(秦潔, 202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碩士生譯者認知過程的實驗語用學研究”(編號:18BYY028)
參考文獻
[1] Mahpeykar, N., & Tyler, A.(2015).A principl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ccount of English phrasal verbs with up and out. Language and Cognition, 7, 1-35.
[2] Masuda, K., Arnett, C., & Labarca, A. (Eds.).(2015).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Application for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Germany: De Gruyter Mouton.
[3] Tyler,A.(2012).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etical Basics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4] Tyler, A., & Evans, V. (2003).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Spatial scenes, embodied meaning,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Tyler, A., Ortega, L., Uno, M., & Park, H. (Eds.).(2018). Usage-inspired L2 instruction: Researched pedagog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6] Yasuda,S.(2010).Learning Phrasal Verbs Through Conceptual Metaphors: A Case of Japanese EFL Learners. Tesol Quarterly,44(2),250-273.
[7] 劉正光,艾朝陽.從認知語言學看外語教學的三個基本問題.現代外語,2016.39(2):257-266.
[8] 秦潔.《語言使用觀啟發的二語教學:實證依據》評介.現代外語,2020.43(1):143-147.
[9] 文秋芳.認知語言學對二語教學的貢獻及其局限性.中國外語教育,2013.6(2):23-31.
[10] 文旭.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特征及其對外語教學的啟示——應用認知語言學探索之二.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4(3):16-22.
[11] 朱京,賈冠杰.基于認知語言學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研究.外語界,2018(3):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