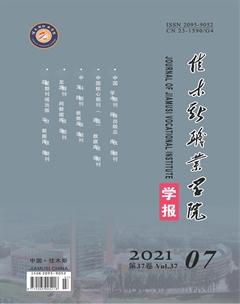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困境與發展研究
邢夢霄
摘 ?要:自20世紀初,比較教育學便在我國進入萌芽期,并先后經歷了創立、初步發展、停滯、復蘇、重建與成型等諸多階段[1]。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革,比較教育學的討論已經由初期的學科問題演變為具體問題的探討,預示著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將面臨諸多困境,包括身份危機、生態缺失及方法失當等。因此,為突破比較教育學面臨的發展困境,提升其實踐定位,更好地探索未來發展方向,本文從學科定位、學科功能等方面提出了未來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的策略。
關鍵詞: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困境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G40-059.3;G6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1)07-0-02
一、比較教育學的內涵
“比較教育學”的概念最早產生于法國教育家朱利安的研究,他在《比較教育的研究計劃與初步意見》中對比較教育學進行了初步闡釋。迄今為止,比較教育學自19世紀發展至今,已經有二百年余年的發展歷程。比較教育學依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并適度融合現代新的科技手段,針對不同國家或者民族的教育問題,探索各國教育的共同特征及未來發展趨勢,使教育價值最大化,對國民整體素質提升意義重大。盡管我國關于比較教育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并且在概念的闡述上缺乏統一性,但經歷不懈的研究和實踐,已經對比較教育學有了更深度的理解。一是比較教育學的基本特征為“比較”或“比較分析”;二是比較教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為比較法;三是研究對象覆蓋教育的全領域;四是比較教育學研究空間緯度更大,具有跨國性;五是現代或者當代教育問題是研究的目標;六是比較教育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借鑒。基于人類知識的發展歷程看,一般都是通過從無到有、由少到多、不斷分化與重組的過程,因此對于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而言,同樣需要通過探索、分析、改進與發展,使其在我國的發展枝繁葉茂。
二、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困境
(一)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面臨“身份危機”
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便開始了關于比較教育學“身份危機”的討論,尤其是任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先生,專門發表了《中國比較教育的名和實》以闡述比較教育學的學術觀點,在文中提出:“中國比較教育工作者肩負著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教育體系的重任[2]。”通過該段論述可以明顯感受到,顧明遠先生對比較教育學發展成果的關切,以及對比較教育學未來發展的擔憂。在1993年,曾任比較教育分會會長王英杰先生也在其發表的《比較教育學定義問題淺議》中提出:“由于當前比較教育學界尚未對比較教育的定義取得一致的意見,比較教育學科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礙,出現了所謂身份危機[3]。”通過教育學術界之間的大量討論,將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推向風口浪尖。2010年,陳時見教授也依據多年研究成果,發表了《比較教育學的現實境遇與發展前景》,再次對我國比較教育學進行了闡述。在二十余年間,教育界關于“身份危機”的研究與探索從未間斷。
(二)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存在生態阻隔
若將教育學比作一棵參天大樹,則比較教育學則是其中的重要分支,如何使之在教育滋養下獲得成長,應成為教育界重點思考的問題。但從現階段的發展形態上看,其在公信力方面依然存在較大爭議。尤其是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必然需要在前瞻性中具備一定的要求,同時這也是教育學發展的重要功能之一。特別是比較教育學作為一種研究當代教育現象與規律的方法,應具備更高的前瞻性,以適應當前世界教育格局與動態,展現更加突出的研究性。但我國在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上發展遲緩,往往是針對教育實踐之后的問題進行經驗借鑒,用以彌補已經存在的事實性問題,并且實質方法也是以“翻譯介紹”替代“深入研究”,使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過于趨向于“拿來主義”。試想,若過于依賴這種“拿來”上的滿足,將使比較教育學學科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三)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方法失當
長期以來,在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方法中更加側重于“比附”而非“比較”,導致其難以有實質性的進步。比如,張東蓀在中西思想史的比較研究中提到“比附”與“比較”的方法差異,其中明顯闡述了“比較以見其相異更為重要”的觀點,好比觀察一個人的面部特征,分而觀之可感覺與他人十分相似,若以整合的方法觀察,將出現完全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利用“比附”作為著眼點時,顯然不會從整個體系進行理解,而是顯著脫離整個語境或者情境,只一味地尋求共同點,盲目依賴于國外教育改革與發展成果,未充分結合我國具體的教育實際,會導致所獲得的成果空洞無意義。本質而言,在比較教育學的學科建設上,一方面應注重經驗的吸收與借鑒,實現成就上的認同,另一方面要科學鑒別、客觀實際地尋求差異,注重深度的求異。目前我國更趨向于前者的深化,而削弱了后者的價值與意義。
三、關于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的發展路徑思考
(一)明確學科定位,夯實建設之基
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要想突破“身份危機”,必須優先厘清教育中所涉及的要素,即包括教師與學生在內的基礎要素。特別是完成整個教育過程的貫穿,應依賴一定的載體或者介質,這便是課程與教學路徑,同時也是教育發展難以分割和回避的領域。比較教育學作為一種全新的嘗試,應當遵循比較研究法的方法論原則,通過對各國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分析、借鑒與拓展,以尋求一致性的教育規律。如今,隨著比較教育學研究的日趨深入,其已然成為教育研究中的活躍內容。那么,要想全面落實比較課程與教學論之間的有效“嫁接”,首先應重點闡述該理論是否具備了獨立學科的基本特征,如愛潑斯坦(Erwin H. Epstein)認為,學科理論的構建要從三個方面加以體現,即內在一致性、互不相容性及包攝性。另外,對于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而言,在比較課程與教學論體系中保持一致性的同時,也不能妨礙對不同領域的理解。同時,避免出現互不包容性的思想,相互補充和相互啟迪,徹底實現比較教育學“身份”的融通。
(二)整合教育生態,發好教育先聲
“比較之道,必本于思。”比較教育學之所以能夠受到廣泛關切與研究,其具備的拓展與創新價值不言而喻。比較教育學尤為注重對深層次問題的研究,而非是簡單地借鑒或者介紹別國教育現象。因此,比較教育學所承載的使命,理應處于教育研究的世界前沿,掌握更豐富、更全面的教育學科發展動態,將研究成果逐步轉化為教育實踐,引導國家教育宏觀層面上的發展。首先,強化比較教育研究的科學性。注重比較教育學研究方法的創新,針對當前多元文化特征進行比較,運用比較思維及定性、定量研究的結合,注重歷史與因果、宏觀與微觀上的探索,盡可能全面地呈現比較教育學學科的科學性。其次,注重比較教育研究的創新性。挖掘和發揮獨立學科的意義與價值,摒棄一味借鑒西方研究成果的弊病,注重自身的學術創新,通過思維、創造能力與科學精神的協同,保證比較教育學學科發展的科學性與前瞻性,促進我國比較教育學快速形成研究體系,構筑全新的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陣地,甚至是引領世界教育方向。最后,增強比較教育研究的實踐性。從國內的教育實際出發,堅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通過探索、實踐獲得發展真理,不斷實現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
(三)厘清學科功能,創新學科方法
比較教育學實踐中的比較課程與教學論,并非教育學科體系中的宏觀內容,而更傾向于實踐層面的方法,致力于對基礎實踐問題的解決。因此,從比較教育學科建設的功能上看,具備顯著的實踐性特征,需以比較課程與教學論的教育服務作為起點,為夯實我國教育基石提供助力。首先,比較課程與教學論屬于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的具象化,其內在也同樣蘊含著比較研究的“血統”,不然便與一般課程與教學論無異。因而在比較課程與教學論的實踐中,應以“比較—借鑒”作為根本,利用國際視野進行理論分析與實踐比較,從而為國內教育發展提供有效借鑒。其次,比較課程與教學論將提示教育基本規律,為教育問題提供豐富解釋與解決路徑。具體而言,雖然該功能并非比較課程與教學論獨有,但其最核心的差異在于比較課程與教學論突出“比較研究法”,將更國際化的研究視野作為根本取向,使之所研究的內容有別于一般的研究風格,以發揮最大的學科效能。最后,比較課程與教學論中具備創新實踐功能,即利用其與國際間教育研究對接的特征,吸取更具有前瞻性、先進性、創新性的理論,通過與國內實際國情的融合調整,指導教育改革發展。
四、結語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云萬里天”。若一個學科擁有了博大的胸懷和眼界,就能從根本上具備無限發展的潛力。比較教育學學科之所以能夠長久屹立,且保持著獨樹一幟,根源便在于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力量。對于當代我國的教育發展而言,必須要注重審時度勢,不斷適應教育研究領域的全新范式,嘗試深度轉型與創新,通過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的發展,為母體學科的研究范式轉型帶來積極啟發。
參考文獻:
[1]侯懷銀,李旭.20世紀比較教育學學科建設的本土探索[J].高等教育研究,2010(2):53-60.
[2]顧明遠.中國比較教育的名和實[J].外國教育資料,1991(1):1-4.
[3]王英杰.我國比較教育研究的成績、挑戰與對策[J].比較教育研究,2011(2):1-4.
(責任編輯:董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