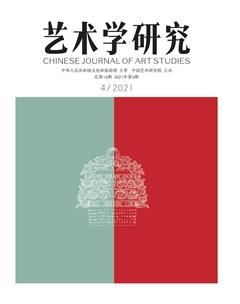藝術史學理論的基本構成
夏燕靖
【摘 要】 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以來,藝術史學科建設和藝術史學理論研究受到整個人文學科的影響并由此獲得極大推進,其研究成果的呈現(xiàn)值得關注。尤其對藝術史及藝術史學多視角的認知形成了多種可能,對藝術史學理論的建構也釋放出許多新的認識觀念。由此,探討藝術史學理論的基本構成,應從以下三方面加以思考:依據(jù)門類藝術史學及相關學科建構跨門類、跨學科史學理論的必要性;藝術史學理論建構離不開史學范式的相互作用;從治史經驗到藝術史學理論系統(tǒng)建構的學術進程。
【關鍵詞】 藝術史學理論;跨門類與跨學科;史學范式;多元互動
夯實藝術史研究的基礎,需要有堅實的史學理論作支撐,進而確立史觀地位,明晰史述方向。因此,就藝術史學理論而言,凸顯出來的問題必定是對“理論思維”的深入認識。這里所說的“理論思維”,包括史學理論思維及其史學理論構成。藝術史學理論在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中始終起著棟梁性的作用,是藝術史研究生成、生產與傳播,乃至學術創(chuàng)新必須借助的思想源泉和認知理路,更是讓藝術史觀成為一種思想潮流的根本指向。自2011年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以來,藝術史學科建設和藝術史學理論研究就受到整個人文學科的影響并由此獲得極大的推進,其研究成果的呈現(xiàn)值得關注。尤其是對藝術史及藝術史學多視角的認知形成多種可能,對藝術史學理論的建構也釋放出許多新的認識觀念。本文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探討藝術史學理論的基本構成。
一、依據(jù)門類藝術史學及相關學科建構跨門類、跨學科史學理論的必要性
藝術史學理論從淵源到構成,與所依托或涉及的學科關系密切,藝術史學觀念更是眾多理論融會貫通的結果。隨著各類交叉學科的興起與運用,除歷史學、文學、文藝學和美學外,圖像學、考古學、分析學及“科學范式”研究等一批藝術史學知識,被不斷地挖掘出來,并且豐富著藝術史學理論體系。探究藝術何以成為藝術的歷史,抑或藝術史的架構,不僅成為藝術史的書寫問題,而且成為藝術史學的核心問題。正像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新的宇宙觀推倒了所有的隔離墻,理性和信仰、藝術和科學、理論和實踐等之間的壁壘被漸次移除。……藝術和科學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和科學不再像中世紀那樣涇渭分明,而是兩者相輔相成,在一個彼此交融的前沿共同發(fā)展”[1]。文藝復興之所以繁榮,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學科之間的“隔離墻”被拆除,從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學科大融合,并真正實現(xiàn)學科間相互滲透的局面,這是各個學科完滿融合的基礎,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和諧共處。以史為鑒,可以說藝術史學理論是相關學科乃至多學科的融合,是融通跨門類藝術史學、跨學科史學理論的滲透與凝練。跨門類與跨學科的根本,不只是知識跨界,更為重要的是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實現(xiàn)跨界,這是藝術史學理論建構的核心內涵。
例如,關于藝術觀念史的史學理論,主要關注的是史學研究中的思想演變與發(fā)展。要闡明觀念史特征比較困難,這里借助劍橋大學西方政治史學派代表約翰 · 鄧恩(John Dunn)關于觀念史特性的解釋來做比附援引,即“對過去某個人的觀念做充分的哲學論述與對這些觀念做準確的歷史敘述,二者之間的關聯(lián)非常緊密;如果我們把歷史的精確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與哲學的精微(philosophical delicacy)共同奉為追求的目標 ,那么這要比在研究初期就在兩者之間分出軒輊更容易達到理想的效果”。鄧恩據(jù)此進一步揭示出“歷史事件與解釋(explaining)歷史事件的觀念近來受到了相當多的哲學關注。認識論和解釋的邏輯形式中的復雜問題得到了廣泛的探索,史學家的實踐也多少得到些澄清”[2]。如是說來,什么是“觀念史”?“什么是觀念史的主題”?說到底這是一組關涉哲學思考的史述,而支撐其史述的則是囊括個案的“涵蓋性法則”,還有對特定歷史建構的哲學思考。簡言之,任何一種史學觀念都不可避免地受其產生時的歷史境況所影響,“歷史上任何時刻任何個人做出的任何陳述,只有了解了其情狀歷史(the conditioning-history)和引發(fā)了它的那組當時的誘因狀況(present stimulus condition)之后,才可以說獲得了充分的理解”[3]。言下之意,觀念史是對其具有的“歷時性”(diachrony)和“共時性”(synchronicity)史學觀形成的認知。所謂“歷時性”,是按照歷史進程來結構史學研究的脈絡,探究藝術在歷史進程中逐步演變的進化觀念。“共時性”則不以歷史線索為主要根據(jù),最明顯的特征體現(xiàn)在結構主義歷史觀上,諸如,藝術觀念史的敘事結構,遵循以“神話”“宗教”和“圖像”等為母題,從古至今依其所共有結構進行排列的原則,形成一條有關“共時性”探討的史學線索。可以說,“歷時性”與“共時性”是構成史學研究的一般規(guī)律和原則,“共時性”則較為突出。依“共時性”來闡明時代與社會,以及形成的相應史學觀,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新穎的視角和堅實的史學理論基礎。進言之,這是對觀念在不同歷史階段或區(qū)域之間所隱含“共時”聯(lián)系性問題進行闡釋的體現(xiàn),進而尋找觀念上的共通性。任何觀念史都是一定歷史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下的產物,觀念隨時代和社會環(huán)境的改變發(fā)生相應轉變,新的觀念認識隨之產生。不僅如此,觀念還因闡釋角度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質言之,藝術觀念史的突出特點,還在于能夠拆解藝術史認識視角上的界域藩籬,盡可能涵蓋更廣泛的藝術跨門類史學研究,甚至是與相關學科史學觀念發(fā)生“共時性”的闡釋。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后,藝術學理論學科中的藝術史二級學科特性便被凸顯出來,從藝術觀念史角度來認識其史學理論的構成,使之成為史學理論一種共識視角是非常必要的。如劉成紀的《先秦兩漢藝術觀念史》[4],便是以觀念史這一全新視角重新審視中國藝術史及中國傳統(tǒng)美學思想史的發(fā)展脈絡,其史學理論建構是“基于對藝術概念的本土轉化、對藝術史觀的反思和對‘三重證據(jù)法的運用所形成的藝術觀念史范式”[5]。誠如作者所認為的,“甲骨文對構建中國藝術觀念‘信史的起點極為重要。正是通過對甲骨文字和史前器物的分析,作者重申了摹仿作為中國上古圖繪藝術的基本理念的價值,并認為自傳說中的夏禹‘鑄鼎象物始,逼真地摹寫現(xiàn)實就是中國繪畫藝術不可動搖的基礎,認知功能對于中國繪畫永遠具有奠基性。這可以說是對學界長期流行的中國藝術重表現(xiàn)而輕摹仿觀念的有力糾正”[1]。該書的這些史述例證,可以佐證藝術觀念史是支撐藝術史學理論的重要基礎之一。
又如類型化藝術史學理論的形成,即以藝術史類型劃分與建構藝術史研究特質為主旨,強調藝術史學研究具有的特殊性—視角與觀念上的特殊性,以此形成對藝術史學認識的兩點核心:一是藝術史學必須有自身敘事的特點,從而使其史料具有不一般的真實性;二是必須將史學研究的因果規(guī)律運用于對藝術家、藝術作品及藝術創(chuàng)作的歷史認識之中,從而揭示藝術史的演變過程。一言以蔽之,類型化藝術史學理論突出體現(xiàn)藝術史學研究的個性化特征,重點關注藝術家、藝術作品、藝術創(chuàng)作及藝術思潮對藝術史產生的影響作用。與此同時,聯(lián)系藝術史形狀問題的研究,無論是從立意、構思,抑或是敘事諸方面,類型化藝術史學的方式方法都有別于一般史學研究,凸顯藝術史學研究對范疇與方法特殊定位的要求,有助于跳出一般史學研究的藩籬而獲得更多的啟發(fā)。這也是當代藝術史書寫離不開的“新概念”和“新思維”,這些“新”的表達方式,能夠適應或揭示藝術史學研究的新動向,這是“支撐著當代藝術史及其理論的基本語碼或框架,折射出當代藝術史與以往文體不相同的某種先鋒性”[2]。由此可見,類型化藝術史學理論值得關注。正如喬爾喬 · 瓦薩里(Giorgio Vasari)對后世西方藝術史的知識生成影響深遠,以至于20世紀兩大主導的藝術史論研究范式—審美論和文化政治論都關注藝術風格。誠如阿諾德 · 豪澤爾(Arnold Hauser)所言:“對于藝術史來說,‘風格概念是中心的和基本的概念。”[3]此外,后世藝術史論家以風格為核心展開藝術史敘事時往往對肇始于瓦薩里的線性藝術史敘事亦步亦趨。如溫克爾曼在《古代藝術史》一書中“將希臘藝術概括為遠古、崇高、典雅和模仿四個階段;在黑格爾(Hegel)關于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的論述中、在李格爾(Riegl)對于西方藝術史從觸覺到視覺發(fā)展的闡釋中,我們都可以從中尋覓到瓦薩里所開啟的線性藝術史敘事的蹤跡”[4]。的確,在藝術風格史定位上的表達方式尤為突出,這是對藝術現(xiàn)象進行概括與定性描述的必然結果。故而,可以將藝術風格史看作對藝術史形狀多面性且更具個性化的書寫。
由之派生而來的藝術風格史、藝術流派史以及藝術思潮史之類的類型化藝術史學研究[5],必然具有自身特點。歸納來說,有三方面理論意義值得關注:一是藝術風格以藝術史發(fā)生、發(fā)展和演化歷程中出現(xiàn)的典型性藝術現(xiàn)象(形式)為依據(jù),側重于從特殊視角或特殊規(guī)律來考察藝術作品與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個性”問題。諸如,依循藝術家、藝術作品和藝術活動(抑或“藝術運動”)的視角來闡釋藝術史特有的狀貌,尤其側重揭示藝術史發(fā)展進程中產生重要影響力的歷史階段。二是藝術流派的形成往往是以群體化形態(tài)展現(xiàn)出來的,即藝術家群體及相似藝術狀貌和審美特征的創(chuàng)作,其影響波及廣泛而持久。嚴格意義上講,藝術流派應該是一系列藝術事象按因果序列構成的結果,具有延續(xù)性的演變狀態(tài)。類型化藝術史學研究,就是要從歷史現(xiàn)象的因果關系中,認識其變化的延續(xù)性,從而把握藝術的發(fā)展歷程。三是藝術思潮的呈現(xiàn)側重于從社會性、審美性乃至思想性的角度考察藝術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如西方藝術思想史通常是從蘇格拉底前的古希臘到現(xiàn)代社會對藝術認知的探求,并將這種探求融入藝術哲學中,啟迪從精神領域來領略藝術的根本特性。可以說,這是從更為廣闊的歷史語境中揭示藝術思想的淵源及歷史狀貌的審美特征。相對來說,藝術思潮史較之藝術流派史,其波及范圍更加廣闊,具有社會化、歷史化和時代化的諸多特征。
具體而言,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發(fā)展,始終是藝術史自律語境中的演進主題,更是藝術史獨特的研究領域。就中國藝術史總體面貌而言,藝術風格與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其突出標志是儒釋道精髓的融入。如在考察藝術家時,通常聯(lián)系其藝術風格,并結合儒釋道精神融入其藝術表現(xiàn)上的體現(xiàn)來加以分析。于是,在核心思想觀念上,將修身齊家這一治世之道融入藝術史學研究中,揭示其藝術價值觀對藝術史風格成因產生的影響作用。事實上,我國古代各門類藝術在數(shù)千年發(fā)展歷程中,不僅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而且在理論闡述上,都積累了關于“風格”概念與范疇的知識生成。諸如今人在古人的文字中總結而來的“中和”“麗”“清”“雄渾”“勁健”“含蓄”“逸”“淡”“婉約”“豪放”“陰柔”“陽剛”等,可謂是“風格”范疇術語對藝術表現(xiàn)的高度理論概括,反映出不同時代人們對藝術風格的認識與思維認知,同時也集中體現(xiàn)了我國古代藝術風格的民族特色。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1]中以鳥瞰式角度對我國數(shù)千年藝術美學做出的概括性描述以及審美把握,有其整體性認識的價值。一個又一個歷史的審美空間被縱深宏闊地描述出來,呈現(xiàn)的是復雜多變的藝術景象,讓人們感受到的是唯美的、入世的、理智的、可望可游的藝術史長廊。尤其是該書提出的觀點,諸如,遠古藝術的“龍飛鳳舞”,殷周青銅藝術“獰厲的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補”,楚辭、漢賦、漢畫像石之“浪漫主義”,“人的覺醒”的魏晉風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元山水繪畫以及詩、詞、曲各具審美三品類,明清時期小說、戲曲由浪漫感傷而現(xiàn)實之變遷,等等,可謂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2]這便是我國藝術風格史應當記載的關于“風格”形成及價值觀構成的關鍵,既是藝術家與文人之間既有的入世精神的寫照,又包含對儒釋道精髓的自省和修身意義。
自18世紀以來,西方藝術史家和考古學家特別重視風格史問題的研究,其研究路徑主要是根據(jù)藝術呈現(xiàn)的某種特定組合方式,來對藝術作品的構成形式及內、外在因素作綜合性探究,如對某一時期代表性藝術家作品表現(xiàn)的成熟度給予解析,這與傳統(tǒng)藝術史注重藝術家、藝術作品和藝術形式的單向性研究有著明顯區(qū)別。舉例來證,“巴洛克”(Baroque)在西方藝術史上一直是藝術史家關注的話題,其慣指17世紀以及18世紀上半葉(約1600—1750)的藝術風格。當然,年份并不代表絕對的藝術風格,其繪畫、建筑、音樂與設計等表明這一時期是上接文藝復興、后續(xù)古典與浪漫主義的重要發(fā)展階段。究竟是依據(jù)18世紀古典主義者追奉的觀念,用巴洛克來概括17至18世紀整個歐洲藝術的主流風格;抑或是追蹤巴洛克成為獨特風格的歷史軌跡,如在藝術精神和藝術手法區(qū)分盛期文藝復興,即將西方藝術史學界劃分的文藝復興歸為“古典主義”,而將巴洛克歸為“浪漫主義”,這種種認知上的差異,導致西方藝術史在涉及巴洛克時期藝術風格問題上的判斷產生了諸多不同的史學觀。而事實上,巴洛克風格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風格體現(xiàn),強調各種藝術類型的融合。從建筑來看,巴洛克風格看重的是建筑與雕刻以及繪畫間的融合;巴洛克時期的音樂也是對文學、戲劇等領域的廣泛吸收和融合。
如上可證,類型化藝術史學的“特殊性”非常明晰,且知識譜系也十分豐富。類型化藝術史學理論,即作為敘史脈絡的理論支撐,包括思想、審美與歷史多個維度的認識。這也是對藝術史學理論領域中一個長期被混淆問題的重新厘清,該問題就在于混淆了作為客體的歷史與主體對客體認識的史學區(qū)別。在藝術史及藝術史學研究中,主體對客體的認識非常重要,而且這種認識需要將學科或門類藩籬拆除并使之貫通。無論如何,“歷史學,是史學家透過時空的間隔對歷史的反求構筑,忽略史學家這個主體因素是無法科學地談論歷史學的。以往我們的史學分類都是著眼于作為研究客體的歷史”[1]。歷史學研究如此,藝術史學研究自然也應如此。
二、藝術史學理論建構離不開史學范式的相互作用
所謂“史學范式”,可以理解為兼具史學視角與理論建構的一種交叉模式,并且與史學方法之間構成一種“權衡”,對其如何取舍一直以來都是史學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問題。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 · 庫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書中提出“范式”概念,這是依據(jù)科學發(fā)展階段論[2]提出的。他認為每一個科學發(fā)展階段都有特殊的內在結構,而體現(xiàn)這種結構的模型即為“范式”(paradigm),這是以具體的科學理論為范例來表示科學發(fā)展階段的模式。庫恩的史學理論為當代科學思想史研究建立起一個廣為人知的討論基礎,不論是贊成者抑或是批評者,都大量引用他的觀點,表明“其影響不僅在于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而且延伸到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學史、藝術史、政治史、宗教史等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甚至在社會公眾領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書中提出的‘范式轉換一語,如今已成為我們耳熟能詳?shù)囊粋€重要詞匯”[3]。
庫恩的“范式”理論,經過發(fā)展和完善,尤其是借助科學歷史主義的認識論,以嶄新的研究視角,提出了一整套科學有效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將研究視角的具體性作為哲學思考的核心,所建構的研究“范式”,如將“圖像”“模型”和“哲學”建立起相應的聯(lián)系,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認知的契機與手段。庫恩在“范式”理論中揭示了理論建構的經驗、理論和哲學三個層次,形成相互作用的結構,給予理論形態(tài)特有的層級劃分,進而闡明“范式”是由科學和哲學相互結合的產物。“‘范式或者說理論體系具有系統(tǒng)完整性和結構層次性。一般說來,經驗對象、語言、邏輯形式、定理公理體系的總和、基本原理、基本觀念是‘范式由經驗表象層次到抽象理論層次的主要系統(tǒng)要素,而這些要素的相互關聯(lián)則構成‘范式的結構。在此結構中,經驗對象屬第一層次,各種定理公理體系的總和屬中間層次;基本觀念、基本原理、邏輯形式是最高層次。任何一個‘范式的完善程度可以從其系統(tǒng)要素的齊備和結構層次的完整這兩方面進行評價。”[4]庫恩的“范式”理論借助科學史和哲學史的認知規(guī)律,從不同方面、層次和角度對“范式”概念所做的多重界定和闡釋,揭示其鮮明特征,使史學研究避免出現(xiàn)某些偏差。將其遷移到藝術史學理論與方法建構上來比照論證,足以證明庫恩的說法,“有無‘范式,是判別一門學科是否真正處于‘科學階段的重要標志之一。‘范式在規(guī)范科學知識的形態(tài)特征、引領科學研究的導向、促進科學沿著邏輯的次序的方向發(fā)展諸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功能”[5]。
以庫恩“范式”理論為參照,由經驗到理論抽象,建立起一個系統(tǒng)的認知結構,并由此確立“范式”結構的層次,其中的“中間層次”理論非常關鍵。“中間層次”理論,即“中層理論”或“中觀理論”,多為理論闡釋的轉換,有許多具有平行認識的理論可供選擇,進而發(fā)揮理論承上啟下的、溝通宏觀與微觀的作用。從史學觀理論到“中層理論”的轉換,有著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經驗表象之間的互通性,本質上,這是對藝術史學“中層歷史對象”的概括性理論,是結合史學“范式”的結構功能用以分析,并通過具體的史學研究案例的融合、派生而成的。誠如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 · K.默頓(Robert King Merton)在《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Th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1949)一書中所指出的,完整的理論體系正在遇到越來越大的挑戰(zhàn),將被逐漸成熟起來的經驗科學所取代。為此,他提出過往將注意力集中到構建龐大理論體系上的做法應有轉變,要努力研究中層理論的范例。強調中層理論的作用,即介于宏觀理論與微觀理論之間。中層理論既關注一般性問題,又能提出切實可行的理論假設;既有價值取向的指導,又有事實證據(jù)的支持。[1]由之,默頓的“中層理論”是可以用來參證并幫助建構藝術史學的,該理論也為藝術史學研究奠定了一個較高的起點,即貫穿宏觀與中層,乃至構成微觀聯(lián)系認知的藝術史學認識論。當然,對藝術史學“中層理論”的解讀仍然應該是多樣性的。“傳統(tǒng)觀點認為,歷史學需要嚴格依據(jù)歷史事實寫作,歷史事實是歷史敘述追求真實性和客觀性的基本保證。但海德格爾卻認為歷史學的中心課題是‘曾在此的此在(Dasein)的生存可能性,主張以可能之事作為歷史學課題,這在傳統(tǒng)觀點看來,多少有些不合時宜。通過仔細考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兩種研究,其重點不在于探究歷史上的可能之事,而是借可能性觀點重新規(guī)定歷史學的題材、性質和寫作方式。”[2]這里關于探究歷史的“真實性”“客觀性”和“可能性”就屬于史學研究的“中層理論”,此后,由史學“中層理論”產生的各種理論觀點的融合,派生出特定的史學專門化研究領域,可謂是建構起史學“中層理論”體系的重要依據(jù),而史學“中層理論”絕不僅僅是單純的理論演繹過程,更為關鍵的是其能夠解決理論研究的許多切實問題。質言之,建構史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具體的史學“中層理論”的積累與應用,更取決于史學研究者依據(jù)各種“中層理論”的闡釋與建構,形成藝術史學理論的基本脈絡。
的確,在當今藝術史學研究中,種種理論層出不窮,在此情形下探究其史學研究的“范式”理論顯得尤為重要。那么,重溫過往藝術史學研究中作為討論焦點的“范式”理論,究竟有何意義呢?答案是明確的,即通過重溫和闡釋,將其作為一門科學并確立起理論與方法論,進而加深對藝術史學研究的科學性理解,深化認知藝術史學的本質內涵及史學知識的生成:一方面強調其研究內容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之間所存在的區(qū)別;另一方面又強調其研究目標是發(fā)現(xiàn)歷史的規(guī)律及其構成的因果關系。有關這兩方面的研究課題,近年來層出不窮,并且有著較為集中的呈現(xiàn)。
舉例來說,張旭在《福柯與中國藝術史研究范式》中指出,中國藝術史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全面推進之時,曾遭遇了“福柯效應”,尤其是在各個學術領域引發(fā)沖擊和挑戰(zhàn)。諸如,福柯提出的學術探究理論應從哲學走向更為實際的社會學,由此對哲學、社會學、史學、文學、政治學、法學和藝術史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改變了這些學科的既定面貌。文章進而論述福柯的史學思想對中國藝術史學派“藝術史知識生成”所給予的有效支持,福柯對中國藝術史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其建立起一個闡釋系統(tǒng),如“福柯知識考古分析的旨趣實際上有別于一般思想史或藝術史的文獻考據(jù)、文物考證、史實索隱的實證研究,就其對人文科學知識的話語構成中未被思考的歷史先驗性或實證性進行批判性反思而言,它倒是可以被稱為‘元史學或‘元文獻批判”[3]。文章以較大篇幅就藝術史研究專題的“范式轉變”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如何將“范式”問題轉借到藝術史學領域,需要明確一個前提,即認識“范式”理論在藝術史學研究中的價值,并理性厘清“范式”這一概念下的藝術史形態(tài)。這一點在文章中有所闡明:“過去三十年藝術史研究領域中基本學術范式的轉變,……可以說是與福柯的思想效應、尤其是其知識考古與權力譜系分析背后的激進歷史主義與激進解釋學的思想效應相同步的。……福柯晚期對主體化的實踐、自我關切的倫理以及相關真理經驗的全新思考,……為藝術史研究打開一個全新的問題域。中國藝術史的譜系研究如果采用福柯晚期的思想方法,可以更加深入地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認知類型、視覺認知主體的建構及其在繪畫中的真理體驗三者之間的獨特關系。這不僅能揭示種種迥異于西方現(xiàn)代繪畫以及現(xiàn)代藝術的自我技術、真理游戲和文化經驗,而且也將為中國藝術史研究找到立足于自身的解釋學方法。”[1]可見,福柯的藝術史研究思想一方面為藝術史學研究拓展了“范式”理論的闡釋基礎;另一方面為尋求中國藝術史學研究路徑建構起具有“范式”理論支撐的認知類型。
與此同時,對福柯藝術史研究視角的探討,近年來也引起相關學者的極大關注。福柯關于委拉斯開茲、馬奈和馬格利特代表性繪畫的三次討論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魯明軍在《福柯的繪畫研究與20世紀藝術史學范式的轉變》中認為:福柯從“對于繪畫本身的認識”“歷史的觀念”以及“‘知識考古學作為一種新的思考方式”三個層面進行探討。[2]的確,在福柯看來,繪畫不只是一種“話語實踐”,借此提升認識必然關涉藝術史及藝術批評理論的建構。對此,福柯的“范式”理論帶給藝術史的思考,便是通過講述每一幅作品背后的關聯(lián)性秘密,揭示其藝術創(chuàng)作的本質特征,從而更加接近繪畫創(chuàng)作的真諦。如在《福柯文選》中有對上述文藝復興時期三位杰出藝術家作品給予的細致而深入的評述,就是極富藝術史哲學理念的思考。[3]其實,在西方出版的多部繪畫史學著述中,都體現(xiàn)出福柯對自由空間的構想和追求的認識啟迪,可以說福柯追求的是一種新的藝術體驗—在語言、意象中“看”或“說”的斷裂問題上尋求藝術史學認識論的新思路。諸如,福柯在評論馬格利特的作品《這不是一只煙斗》時指出:“在現(xiàn)代,‘與其說繪畫擺脫形象,毋寧說它已著手摧毀形象(《福柯集》)。這也是他一直在癡迷的主張—語言、圖像和事物三者斷裂的理論。福柯不僅從《宮娥》和《這不是一只煙斗》中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也從馬奈的繪畫中深刻印證了這一事實。”[4]這是福柯對藝術史考察的特殊之處,他所提出的“語言、圖像和事物三者斷裂的理論”表明,從認識具體藝術現(xiàn)象(繪畫本體)入手,重新關注藝術表現(xiàn)(繪畫表現(xiàn))語言的寓意,使藝術史家探討問題的指向性越來越接近真實,把藝術行為與藝術史的記載選擇融合到一起,使得藝術史學觀念的建構更富有藝術特性的價值體現(xiàn),也更接近對藝術史學核心問題的探討。
就福柯理論對藝術史學的影響而論,在魯明軍看來:“由于深受福柯思想的影響,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藝術史研究既不同于形式主義和圖像學,也有別于激進思潮和文化研究支配下的新藝術史,而是在認知機制這個維度上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藝術史知識范式。”[5]福柯理論影響深遠,甚至顛覆了19世紀以來所形成的人文學科邏輯和基本敘述框架。如是而言,引進福柯理論并將其“嫁接”到對中國藝術史學理論的探討中是必要的:一是中國古代藝術史有其突出的歷史地位,梳理其藝術發(fā)展脈絡,揭示其藝術發(fā)展規(guī)律非常重要。例如,顧愷之提出“以形傳神”“形神兼?zhèn)洹钡乃囆g主張,倡導的是藝術“精神”“氣質”的內在性,這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始終是藝術家、藝術評論家依循的認識原則。借鑒福柯理論架構,可以拋開一大堆概念,以差別認知方式將“連貫性”主題加以推展繁衍。雖然在理論上還沒有一個緊密的結構去聯(lián)系或貫穿起這些概念,但是它們顯示出的有關史學的認知功能卻是明確且有指導性的。可以說,借助這樣的理論厘清中國藝術史及其史學理論的基本構架是有積極作用的。二是藝術史和藝術史學在近現(xiàn)代學科體系建構下,具有日益顯著的人文學科核心地位。當然,有關藝術史學理論與方法論之間的博弈是一直存在的。
就藝術史學視域、視角及闡釋域而言,本篇論題所指稱的史學理論建構離不開史學范式的相互作用,即是說,藝術史與藝術史學理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任何史述之前都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治史思想或方略,這便是史學理論應當發(fā)揮的作用。藝術史學理論必須明確一點,即真正建立起多元互動,以及跨學科、跨門類的藝術史研究的理論預設。這里的“跨”,是指建立在一般藝術學意義上承認藝術史存在為前提的認識,是建立在打通門類藝術基礎上的藝術史學研究,尤其包含造型藝術之外的其他門類藝術,如視聽藝術、綜合藝術等。以視覺文化為例,可以說它是當今藝術史研究的一大主題,其對象、內容、方法與藝術史之間關系密切。有研究者認為:“視覺文化研究,是視覺研究與文化學研究的結合……文化學研究在歷史寫作中融合了社會關注,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1]通過視覺文化研究來解析藝術史研究有極大的對應性,尤其是符合將藝術事實(史實),置入普遍的規(guī)律(或“定律”或“一般論”)進行組合研究得出結論,進而探尋一般藝術史的“治史原則”與方法。
質言之,當我們探討以庫恩的“范式”理論為參照構成藝術史學“中層理論”的問題,以及從“福柯效應”引發(fā)對藝術史鋪展開來的獨特性問題時,這些看似以西方史學為中心論的有關討論,其實“中心”已經發(fā)生轉移,即討論問題的意識和目標,是借助庫恩、默頓、福柯等西方史學視角、視域及闡釋域進行的遷移性問題探討,不是局限于西方中心地域內的認識,而是將研究思路投射到整個藝術史中來認識,這是藝術史學多元形態(tài)構成的出發(fā)點,更是藝術史學理論構成的重要支點。拓展而論,對于中國藝術史學理論而言,關鍵點同樣是形成對綜合藝術史及史學理論的認識。這樣的藝術史學理論范式建構,應當考慮在我國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吸納西方史學理論資源,走出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史學理論建構之路,并且形成范疇、命題、方法、視域、闡釋域、問題域等各具風格的理論范式。而且,這一理論范式又可以區(qū)分為認識論范式、實踐論范式和藝術論范式等。在一個重大的藝術史學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這些史學理論問題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三、從治史經驗到藝術史學理論系統(tǒng)建構的學術進程
回溯過往藝術史學理論的基本形態(tài),無外乎兩類,即一般藝術史學理論和特殊藝術史學理論。且這兩類史學理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處在相對獨立的發(fā)展領域中,前者主要存在于文史研究領域,乃是觸及藝術問題的史學探討,并非作為專門史學研究來被對待,而是被一般史學理論所覆蓋;后者則主要存在于門類藝術史學研究領域,屬于門類藝術史論研究范疇。故而,探究治史經驗是尋源與積累;更為重要的則是尋求建構起一種理論體系—適應當今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與發(fā)展需要,以跨門類疏通與整合為導向,將門類藝術問題上升至一般藝術史及藝術史學的共識問題進行探討,并強調融西匯中,突出以中國史學“話語場”為其闡釋條件與基礎,且以貫穿的、比較的、典型的和聯(lián)系的藝術史眼光認識跨門類藝術史學,其中重點是藝術史學理論體系如何建構的問題。此謂之中國史學“話語場”,其特點有三:一是基于史學研究中國立場實踐意識的“話語”表達;二是在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基礎上提煉出的史學理論“話語”;三是支撐史學研究的條件有著豐富性,即有實踐支撐,文化價值支撐、話語范式支撐和學理支撐。所謂“理論體系”,指的是通過理論視角對藝術史進行多元闡釋的整合,包括理論思維與理論知識的生成。進言之,藝術史學闡釋理論,應該是涵蓋藝術諸多門類領域,并涉及哲學、歷史學、社會學,乃至考古學和人類學等各種學科互通闡釋的理論。
舉例來說,《黑格爾美學講演錄》(朱光潛中譯本為《美學》)[2]為藍本的藝術哲學,就是“全面而系統(tǒng)地考察整個世界藝術的歷史,甚至可以說一切藝術的方方面面的歷史”[3]。這關系到對藝術史敘事模式理論的探討,藝術史既涉及藝術家、藝術作品、藝術系統(tǒng)、藝術鑒賞、藝術批評和藝術發(fā)展的相關事件事象等;也涉及對藝術哲學諸多問題的思考,這是藝術史特征得以表現(xiàn)的重要因素,也是藝術史對歷史上藝術事件事象給予判斷的重要依據(jù)。可以說,黑格爾對藝術哲學所做的分析,對藝術史的書寫有著突出的貢獻。在這部著作中,首先提出“藝術終結論”[1],這是從“哲學、美學邏輯架構的角度解讀其關于藝術‘終結或‘解體的內在邏輯含義;進而揭示黑格爾對藝術美本質的規(guī)定是其藝術‘解體或‘終結論背后的邏輯根據(jù)”[2]。由此,依照藝術歷史類型構成演進邏輯思路,即是對黑格爾闡述的三種藝術類型(象征型藝術、古典型藝術、浪漫型藝術)各自特殊性所形成的演進邏輯關系的認知。但這三種藝術類型演進到各自發(fā)展階段的后期,都會產生分裂(或曰“裂變”,象征型藝術強調形象特色的塑造,古典型藝術則是形式裂變注重個性表現(xiàn),浪漫型藝術則是內容超越形式等)。于是,應按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的演進歷程來認識不同階段的藝術“解體”及共通藝術形式與內容的裂變。這三種類型,其實是有著相互支撐的邏輯聯(lián)系的,就是說“它們與哲學體系的邏輯推演不同,確實有歷史、時間方面的內涵。在特定意義上,它們的演進正是黑格爾對一部世界藝術發(fā)展史的概括勾勒和描述。但同時,這三個歷史類型又體現(xiàn)著藝術發(fā)展的內在脈絡、規(guī)律和邏輯進程,將一部人類藝術史概括成絕對理念(精神)在不斷外化自己,顯現(xiàn)自己的運動中,從摸索感性形象(象征型);到形象吻合(古典型);再到返歸精神(浪漫型)的邏輯歷程”[3]。至此,我們能夠清晰地理解黑格爾所引出的針對藝術三種類型的劃分意義[4],以及藝術在哲學體系中地位問題的討論。[5]質言之,在黑格爾美學中討論的藝術問題,都是基于其藝術哲學關注的藝術史學問題,這些問題討論的理性認知自然也就是藝術史學理論的構成基礎。
黑格爾這部著作在國內有多種譯本,引起學界的特別關注。如朱光潛在黑格爾《美學》譯后記中說,這本美學著述也是一部藝術史大綱,具有較高的文獻挖掘意義。按照上海譯文出版社對該書2020年新譯版本的推薦提要所示,黑格爾的講演文稿,主要是根據(jù)他在海德堡大學和柏林大學任教期間所做的“美學講演錄”經典內容及學生的聽課筆記匯集而成,代表了黑格爾晚年成熟的美學思想。該講稿由T.M.諾克斯爵士譯成英文并出版,看來在不同語境下,對黑格爾美學的認識尚有語言差異與學者解讀、認知理解的再創(chuàng)作,正如這部新譯本的推薦語所言:黑格爾首先指出了“理念就是概念與客觀存在的統(tǒng)一”;進而稱藝術為“絕對精神的體現(xiàn)”;繼而闡述了“理念最淺近的客觀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種美就是自然美”;跟進論述了“理想的特點和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一般規(guī)律”。[6]由此,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部著作,在西方國家語言體系中發(fā)揮了與皆屬于西日耳曼語支的德語語言、思維的“近親”相似的邏輯作用,即為解讀黑格爾美學提供了一個理解藝術與哲學和美學相關性命題的切入點,其認識問題的背景反映出在西方文藝史上存在著的“工具論”與“自主論”的爭論[7],且有著悠久的歷史。這里提及的“工具論”,向來以是否揭示真理作為文藝作品的評判標準,其倡導者是古希臘的柏拉圖;“自主論”是亞里士多德的主張,認為文藝作品應當符合美的自身規(guī)律。黑格爾的哲學觀念更接近柏拉圖的“工具論”,其淵源便是他對“理念”的認識和思考。黑格爾的理念視角應該是種種特定的形式:藝術的、宗教的,再就是哲學的,其中藝術的則尤為重要。正因如此,黑格爾才會提出“藝術終結”論的核心命題。由之可言,《黑格爾美學講演錄》中所包含的藝術論,實際上是通過對藝術問題的討論觸及藝術史問題的構成。這表明“藝術史離不開歷史觀的指導,藝術史教學是透過史學進入藝術的內核,呈現(xiàn)藝術發(fā)展脈絡和規(guī)律,解答藝術本身不能回應的問題,闡釋藝術現(xiàn)象或藝術活動的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評判藝術作品的形式、內容,從而界定藝術史的貢獻”[1]。與此相關,“黑格爾體系”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2],它是由黑格爾引出,自受其影響的布克哈特、沃爾夫林、李格爾等人研究之后形成的歷史思想學派,后來被稱為藝術科學學派。稱之為“黑格爾體系”,是將其作為藝術史學方法論研究體系的傳統(tǒng)說法。[3]
《貢布里希文集:敬獻集—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解釋者》[4]也是一部關于西方藝術哲學和藝術史的重要佐證著述。該書收入了貢布里希在慶祝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成立200周年系列講座上的主旨發(fā)言,以及他對黑格爾等11位世界著名文化學者的藝術思想的評述,這些文化學者都接受過古典傳統(tǒng)教育,代表著傳統(tǒng)文化的延續(xù),貢布里希對他們的致敬其實也表達了他對古典傳統(tǒng)價值的贊揚。如同貢布里希在書中所強調的,人文學科是人類記憶的里程碑,人文科學者必須有把握史料的藝術訣竅,培養(yǎng)感受力和理解力,并且尊重價值。[5]其中代表性篇目:兩篇導言《藝術與人文科學的交匯》《藝術的多樣性—〈拉奧孔〉在G.E.萊辛(1729—1781)生平和創(chuàng)作中的位置》,分論篇《“藝術史之父”—讀G.W.F.黑格爾(1770—1831)的〈美學講演錄〉》《古典傳統(tǒng)的雙重性—阿比 · 瓦爾堡(1866—1929)的文化心理學》,是對藝術史學理論的透徹闡釋。這也表明史學理論的產生,有著借鑒與互融的漫長研究與反思過程。這一過程在西方藝術史學領域有哲學、美學與藝術史互證發(fā)展的見證,是一種回歸史學探究軌道、重視學術闡釋的嘗試,進而提出一套符合解釋藝術史實際問題和概念的理論,拓展了哲學、美學與藝術史學融合而成的廣義史學理論的提升空間。如前所述,明確的藝術史及藝術史學的“整體性”邏輯思維,具有“公共闡釋”與“公共史學”價值,這便是重新確立藝術史學理論的學術意義。
不僅西方藝術史學的發(fā)展路徑,有著將藝術史問題上升至史學共識問題的認知探討,在我國傳統(tǒng)藝術史學中也有相似的認知形態(tài)。如“通史家風”的說法,始自清代史家章學誠提出的史學研究應重視貫通古今的倡導,是對治史通識觀念的傳統(tǒng)概括,既表現(xiàn)為“通古今之變”的縱通,又表現(xiàn)為“會天下之書于一手”的橫通,縱橫交織,構成了“通史家風”的整體性特征。[6]依照藝術史學“融西匯中”觀念而論,中國藝術史學不應只是簡單移植西方藝術史學觀的延續(xù)或變種,而應與西方藝術史學同處于一個史學知識譜系與理論體系建構中,具有突出的自我主體性。這正如前所述,突出以中國史學“話語場”為其闡釋條件與基礎,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史眼光來認識跨門類藝術史學理論的發(fā)展。
我國傳統(tǒng)藝術史學理論是伴隨中華文化與文明的延續(xù)而發(fā)展的,內涵豐富,為傳統(tǒng)史學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撐。我國傳統(tǒng)藝術史學的記載與整理,主要以文獻典籍以及考古史料為據(jù),在近代以來新史學的推動下,其史學理論的脈絡經過梳理與建構已經逐漸明晰。比如,《呂氏春秋》中的《適音》篇,可作為我國傳統(tǒng)藝術史學的重要史料,其對“適”從“行適”“心適”“音適”三方面所做的概念界定,將一種認識音樂存在的思維認知模式(甚至是文化模式)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如若按照新史學思想來分析,對其概念的界定和區(qū)分,已經具備一種對我國古代音樂發(fā)展史的認知,即從“行為、形態(tài)、觀念”三要素來認識音樂理論,這正是“樂本體”思維模式在2000多年前的呈現(xiàn)。在《呂氏春秋》的天道自然觀中,音樂的產生具有數(shù)理基礎和物質基礎,《大樂》《適音》諸篇中使用的“和”與“適”這兩個概念,都是為認識和把握事物存在的內在規(guī)律和法則而設定的,具有不同以往的音樂哲學思維的認識高度。進言之,提升至藝術形而上觀念來認識,這便是藝術作為“載道”的一種文化形態(tài)的顯現(xiàn),勢必受到古代詩文及傳統(tǒng)文化審美觀念的諸多規(guī)約,而這正是我國古代藝術與詩文(或者說文化)建構起來的藝術審美的“聯(lián)姻”。質言之,這種審美“聯(lián)姻”早在先秦時期已作為禮樂制度的一種形式被踐行,即借助詩文來明辨音樂“文以載道”的意義,以致世代相傳。如今,當我們以新史學思維重新識讀這些古代文獻時,但凡涉及對音樂的評述,通常都會與詩文發(fā)生密切的聯(lián)系[1],這可以理解為以傳統(tǒng)藝術史學觀來認識史家向來注重的“通”的觀念,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貫通古今各個領域來審視藝術發(fā)展歷程的理論思維,這樣卓有成效的史學研究方法,可以被認為是“通史家風”的集中表達。因此,“通”的史學觀念是我國傳統(tǒng)史學到新史研究必然貫通的方法和方向,藝術史學理論亦是如此。
無獨有偶,“意象”與“意境”也是我國傳統(tǒng)藝術史學理論的重要命題。考據(jù)“意象”概念的源頭,其是從《周易》和《莊子》演化而來的。《周易》謂之的“觀物取象”[2],成為象征表意文化的經典。當然,《易》“象”的形成、確立與藝術形象塑造之間有著典型的相通性。比較“意象”與“意境”可知,“意境”審美觀的提出要晚許多。具體來說,“意境”是魏晉玄學與禪宗思想相結合的成果,尤其是古代玄學家對該領域的闡述,如《周易》《老子》《莊子》等給出的相關解讀,在思想根源上對“意境”的產生起到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而這些思想包含“有無體用”“虛靜逍遙”“得意忘象”等。其中,王弼在闡釋《周易》“意象”理論時提出來的“得意忘象”,成為我國古代文藝美學中一個重要理論命題。該理論強調的是在審美的至高境界中的一種獨特體驗,這份體驗便是逍遙之境,將景物化入純然的觀看之中,可洞見萬物視如洞見己心,“心物”“虛靜”“澄明之象”,以至“大巧若拙”等審美思想,借以吐露藝術審美追求的中和之性、質樸之情。由此來看,“意境”是“意象”與“氣韻”這兩大傳統(tǒng)美學觀所觸及的審美范疇的融合,在鐘嶸的《詩品》與宗炳的《畫山水序》關于詩畫融通的審美理論中,可以剝離出“意境說”的論理。唐代是“意境說”的真正成熟期,這與唐代出現(xiàn)的儒釋道文化相融合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更表現(xiàn)在藝術審美的實踐中,如詩與畫之間的互相促進和相互結合。依此而言,中國古代藝術史的構成沒有門類概念的壁壘,相互貫通、相互借助是闡釋藝術史及藝術史學認識的基礎。
事實上,有關“意象”“意境”之說,不僅成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美學、古典文藝學乃至古典藝術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而且自先秦伊始,“境”之觀念還包括樂曲舞賦的一部分,并引申到藝術精神的認知范疇。故此,關于“境”的闡述,以及“境”之審美,為后世藝術史學理論的產生奠定了重要基礎。諸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 · 隱秀》篇中用“境玄思淡”來評論嵇康、阮籍的詩,謝赫“六法論”提出的“氣韻生動”,都最為接近“意境”之說。對于中國畫的意境塑造而言,藝術家通過將情感寄于所描繪的景物之中,進而營造出藝術意境,觀者在藝術接受過程中通過聯(lián)想產生共鳴。評價繪畫是否具有意境,也是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歸納來說,在中國畫意境塑造上,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畫中有詩”,蘇軾評王維畫作曰:“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東坡題跋 · 書摩詰〈藍關煙雨圖〉》),既是傳統(tǒng)審美觀念的體認,更是對王維創(chuàng)作方法的稱贊,終歸于傳達意境中的感情抒發(fā)和想象力的發(fā)揮;第二類是“意境美”,這是在“不似之似”之間的境界顯現(xiàn),石濤曰:“明暗高低遠近,不似之似似之”(《大滌子題畫詩跋》),這“不似之似”便是古代形神論在審美上的提升,從而成為傳統(tǒng)繪畫創(chuàng)作遵循的法則;第三類是“意境美”,在于滲透令人神往勝景而達至情與景、心與物的相互交融,如劉勰在《文心雕龍 · 論說》中提到的“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這可說是為“意境”概念奠定了學理基礎。而鐘嶸提出的“滋味說”,與“意境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算是“意境說”的先聲。又有“是以《詩》人感物,聯(lián)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qū)。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文心雕龍 · 物色》),無論是傳統(tǒng)繪畫的意境營造,還是藝術家借助豐富想象力來實現(xiàn)描繪對象的升華境界,既有感悟,更有認知。應該說,這三類意境若以禪宗修行終極目標來比喻,則是“體認天人,物我同一”的境界寫照。將其提升至學理闡釋層面,便是將“美”從現(xiàn)實轉化至藝術理論的解讀視域,是關乎生命美學的命題。猶如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表達,借景言志,借物抒情,進而闡明藝術追求的理想,為傳統(tǒng)藝術精神擬定一個接受美學的模式,這便是最透徹的解釋。也正因品格的差異,才體現(xiàn)出不同藝術家的不同審美趣味。如是,就畫學理論而言,有著歷史積淀的畫論、畫學在針對藝術表達細節(jié)上的解析有其獨到之處,這正與西方藝術理論宏大結構相得益彰。事實上,無論是從中國藝術特質來講,抑或是從中國藝術理論構成與發(fā)展來看,將畫學理論融入整個古典藝術理論開展相應的理論系統(tǒng)研究與建構,都是具有深刻啟示意義的。
由此,從本質上來說,雖然“意象”與“意境”都是主客觀統(tǒng)一的產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區(qū)別:意象與表現(xiàn)相關,意境與再現(xiàn)對應。當然,這里指的是傳統(tǒng)藝術的表現(xiàn)與再現(xiàn)。其實,在古代繪畫品評中,“意境”之說比比皆是。[1]如同郭煕所述,所做之畫意境極妙境界當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林泉高致 · 山水訓》)。如此,觀者神游畫中,流連忘返,樂莫大焉,把握山水的意境之妙。由之,“意象”與“意境”成為傳統(tǒng)畫學思想的化境符號,也成為整個傳統(tǒng)藝術表達之境的追求。可見,中國傳統(tǒng)文藝理論或美學思想,抑或是畫學理論在學術立意上已經融合為傳統(tǒng)藝術理論核心思想的源泉,豐富了傳統(tǒng)史學理論的內涵與外延。
結語
不可否認,在我國藝術學升格為門類學科之前的較長時間里,藝術史學研究大多被置于藝術門類領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狹義”藝術史及藝術史學中。而且,流行于英語世界的藝術史研究在被引入國內后的情形亦是如此。這有可能是受到一種習慣性認識的影響,即如澳大利亞藝術史家保羅 · 杜羅(Paul Duro)和邁克爾 · 格林哈爾希(Michael Greenhalgh)所言:“藝術史(Art History)是研究人類歷史長河中視覺文化的發(fā)展和演變,并尋求理解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中視覺文化的應用功能和意義的一門人文學科。”[2]這種用藝術史這一稱謂來指稱視覺文化,即以繪畫、雕塑和建筑等造型藝術為主體的史論研究,或許就是某一時期內西方相關學術界的共同看法。
如今,這樣的史學觀念確實需要修正與更新,目的就在于突出跨門類藝術史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關鍵,即“跨”字。藝術史學理論建構的立足點,即在于將門類與跨門類藝術史學進行有機整合,而這又體現(xiàn)出四個基本特質:其一,以門類藝術史研究為基點,衍生出具有公共史學意義的藝術史學理論;其二,展開跨門類藝術史的融合研究,構成彼此間共同關注的史學理論探討的問題;其三,藝術史的微觀與宏觀敘事,需要跨門類乃至參證多學科史學視角探究,從中凝練出具有公共藝術史學闡釋意義的理論;其四,多學科、多領域的交叉與融合,是推進藝術史及藝術史學研究與理論建構的新進程。依此去尋求藝術史及藝術史學研究的整體性原則,從而推動藝術史學研究在哲學意義上的認識提升,尤其是通過揭示其史學研究內在的連貫性、有機性和系統(tǒng)性,形成對藝術史及藝術史學“整體性”邏輯思維的認識,進而在各門類藝術史具體史實研究之上建立起探索藝術總體規(guī)律,或者說具有共性特征的史觀,其研究深度是微觀與宏觀的統(tǒng)一,充分體現(xiàn)藝術史學理論構成的融合性與廣博性。這不僅規(guī)范了藝術史學研究路徑,而且闡明了治史條件和特性,更豐富了藝術史學理論以理性解構與建構的學術思想,形成由“狹義史觀”向“公共史觀”的轉變,為根基多樣性的藝術史學理論奠基。
此外,我國藝術史學研究領域還有其特殊性,這便是文獻及文獻研究的支撐。尤其是近現(xiàn)代以來,我國學界重新反思文化歷史的形成,在文獻方面推重“文獻之邦”的學術聲譽。例如,20世紀30年代,鄭鶴聲、鄭鶴春編撰《中國文獻學概要》時強調:“中國文化之完備,世界各國,殆莫之京,此為中國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1]此后類似論述,可謂層出不窮。自然,解讀文獻與理論建構有所不同,文獻需要對“他者”意義的解讀,更為重要的是“自我”反觀合理性的認識,因此,對文獻傳統(tǒng)構成的史學認知,通常是“自我”解釋為主。而理論建構是對有內在聯(lián)系的命題進行等級系統(tǒng)邏輯推理,即從層層命題中推演得出。而且又用“理論”命名的概念題域來表示不同觀念的整合,如學說、流派、學科及思想等,實現(xiàn)西學倡導的科學意義上的理論建構,做出系統(tǒng)性的闡述與闡釋。所以說,治史學問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基礎建構,便會缺乏依據(jù)。故而,厘清我國古代藝術文獻具有的理論價值,其闡釋極為復雜,特別是對文獻內涵的解讀,遠比單純的文獻文本解讀難度要大得多。作為“文獻之邦”的立論,確實需要新的思維,以融西匯中的方法從文獻傳統(tǒng)與理論建構的多重角度探知藝術史學觀。
當然,真正史學問題的探究,還需從源頭入手,這便關涉藝術史學理論形成的歷史淵源。我們所說的藝術史學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與整個史學傳統(tǒng)不可分離的。在中外史學傳統(tǒng)中直接或間接關涉藝術史學理論的選題比比皆是,藝術史學不可能僅以一般史學理論與方法論作為其參照,特別是有關藝術風格與藝術形式、藝術觀念與藝術語言,以及視覺認知和聽覺感悟等關涉藝術現(xiàn)象的史學問題的思考,還有藝術鑒賞、藝術審美、藝術史類別的特殊性等問題的揭示,都具有自身史學規(guī)律的語境,并有著相對專業(yè)性的知識譜系。其理論建構,首先是對現(xiàn)代性史學問題的探討,需要藝術史學研究者超越新與舊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從現(xiàn)代性發(fā)生、發(fā)展的角度來思考藝術史學的性質與特點等問題,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較為突出的是從“現(xiàn)代性”拓展而出的“現(xiàn)代派”,在藝術史學的共識中引入政治現(xiàn)代性、文化現(xiàn)代性、審美現(xiàn)代性等概念,極大地豐富了藝術史學理論相關主題的闡釋,也深化了人們對現(xiàn)代藝術史學研究價值和意義的認知。其次,現(xiàn)代性視角極大地改變了藝術史學的研究格局,特別是世界性問題,這是現(xiàn)代藝術史學研究發(fā)展到全球化時代必然要出現(xiàn)和面對的新話題。自然,經過史學研究而形成的再生“世界性”,如若再被還原到世界性的知識譜系中去,將對豐富藝術史學的內涵以及知識譜系做出新的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跨門類藝術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項目批準號:20ZD2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