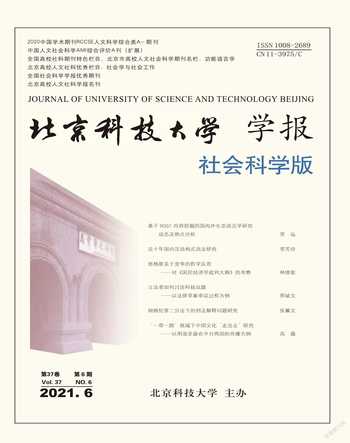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展模式探微
張瑞軍 蘇禹名
〔摘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我們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武器。隨著革命事業(yè)的變化發(fā)展,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及其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發(fā)展模式應(yīng)時(shí)而變,取得了巨大的進(jìn)步。遵循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的斗爭(zhēng)脈絡(luò),追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發(fā)展模式的變遷,不斷走向成熟與穩(wěn)定,對(duì)于進(jìn)一步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探尋其規(guī)律具有重要價(jià)值,對(duì)于新時(shí)代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與加強(qiáng)黨的政治建設(shè)具有重要啟示。
〔關(guān)鍵詞〕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民主主義革命;發(fā)展模式
〔中圖分類號(hào)〕 B258〔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 A〔文章編號(hào)〕1008?2689(2021)06?0696?06
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我們黨特有的政治優(yōu)勢(shì),它具有團(tuán)結(jié)一切可以團(tuán)結(jié)的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是保障我黨革命、建設(shè)、改革與他各項(xiàng)事業(yè)順利進(jìn)行的重要法寶。所謂政權(quán)組織結(jié)構(gòu)形式是指統(tǒng)治階級(jí)采用特定的原則和方式組織自己的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以反對(duì)敵人,保護(hù)自己,是一個(gè)國(guó)家政治制度的最基本表現(xiàn)。回顧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發(fā)展模式,從農(nóng)村土地革命到反帝抗日戰(zhàn)爭(zhēng)再到三年內(nèi)戰(zhàn),革命形勢(shì)有變,革命任務(wù)不同,不同階段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各有側(cè)重,與其相應(yīng)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也有所不同。回顧這三個(gè)階段的歷史,揭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的變化發(fā)展,探尋規(guī)律,以史鑒今,對(duì)新時(shí)代鞏固黨的執(zhí)政基礎(chǔ)和加強(qiáng)黨的政治建設(shè)有重要意義。
一、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的工農(nóng)兵代表發(fā)展模式
1927年,由蔣介石、汪精衛(wèi)所帶領(lǐng)的非左派國(guó)民黨勢(shì)力先后與革命背道而馳,相繼策劃并發(fā)動(dòng)了“四一二”清黨和“七一五”分共等一系列活動(dòng),對(duì)共產(chǎn)黨人進(jìn)行大肆抓捕和屠殺,導(dǎo)致國(guó)共合作破裂,革命力量急劇減弱。中國(guó)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jí)和上層小資產(chǎn)階級(jí)紛紛動(dòng)搖,加入了大資產(chǎn)階級(jí)的反革命行列,革命陣營(yíng)嚴(yán)重削弱,革命活動(dòng)嚴(yán)重受挫,中國(guó)革命處在十分緊急的關(guān)頭。針對(duì)革命環(huán)境和條件發(fā)生的變化,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huì)召開了一次黨歷史上的重大轉(zhuǎn)折會(huì)議?“八七”會(huì)議。這次會(huì)議為黨指明了新的方向,制訂了革命發(fā)展的總方針:實(shí)行農(nóng)村的土地革命和以武裝斗爭(zhēng)的形式反抗國(guó)民黨,從而解決黨成立以來(lái)就一直沒有解決的思想問(wèn)題。同時(shí),為了擴(kuò)大黨的組織基礎(chǔ),提出了建立工農(nóng)民主主義性質(zhì)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設(shè)想。會(huì)議通過(guò)的《告全黨黨員書》一文提出:“應(yīng)當(dāng)促進(jìn)并擴(kuò)大激勵(lì)工人反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農(nóng)民反對(duì)地主的階級(jí)斗爭(zhēng)”[1]258,“必須迅速勇敢堅(jiān)決的實(shí)行武裝工人和農(nóng)民”[1]262。“八七”會(huì)議后,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通過(guò)對(duì)大革命的失敗進(jìn)行全面深刻總結(jié),對(duì)廣大工人和農(nóng)民群眾的巨大力量予以肯定,對(duì)忽視工農(nóng)群眾的力量而一味依賴國(guó)民黨的路線進(jìn)行了深入批判,從而開啟了動(dòng)員廣大工農(nóng)群眾投身革命與主要依靠工農(nóng)群眾武裝革命的道路。就此,工農(nóng)民主主義性質(zhì)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雛形初步形成。1927年8月20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應(yīng)在粵、湘、鄂以及贛四個(gè)省中建立“工農(nóng)兵蘇維埃”。1927年9月初,在秋收起義前夕,毛澤東提出要以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掌握一切權(quán)力的形式建立蘇維埃。9月10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政治局在《關(guān)于國(guó)民黨及蘇維埃口號(hào)的決議》中提出了建立“工農(nóng)蘇維埃”即工農(nóng)民主專政的主張,并于11月初召開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臨時(shí)政治局的擴(kuò)大工作會(huì)議上確定了武裝暴動(dòng)的總口號(hào),即“由工人、士兵和貧苦人民的代表會(huì)議掌握一切權(quán)力”[2]。根據(jù)地政權(quán)的組織形式也根據(jù)這個(gè)口號(hào)開始變化,就是以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替代農(nóng)民協(xié)會(huì)。在此之后,我黨在的各個(gè)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分別召開了各級(jí)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并建立了相應(yīng)的民主政權(quán)。
在工農(nóng)民主主義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的指引下,工農(nóng)兵大表大會(huì)制度開始逐步形成。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于莫斯科召開,制定了工農(nóng)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策略。六大的決議指出,建立蘇維埃政權(quán)的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是當(dāng)前我國(guó)革命最主要的任務(wù)。大會(huì)通過(guò)確定了工農(nóng)兵代表會(huì)議(蘇維埃)政府為蘇維埃國(guó)家政權(quán)的正式名稱,進(jìn)一步明確了蘇維埃國(guó)家政權(quán)的指導(dǎo)思想和策略。1930年9月,六屆三中全會(huì)順利召開,全會(huì)制定了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提出要實(shí)行下層范圍內(nèi)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gè)統(tǒng)一戰(zhàn)線應(yīng)由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去領(lǐng)導(dǎo)底層的黨員和非黨員聚在一起進(jìn)行斗爭(zhēng)。要在維埃政權(quán)的口號(hào)之下,日常斗爭(zhēng)也要體現(xiàn)出“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gè)方針。這一方針確定了這一時(shí)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即反對(duì)封建地主階級(jí)和反對(duì)國(guó)民黨的工農(nóng)民主主義性質(zhì)的、民族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十月革命過(guò)去14年之后,在這種性質(zhì)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引領(lǐng)下,首次全國(guó)范圍的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在1931年成功召開。會(huì)議通過(guò)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憲法大綱》《蘇維埃地方政府暫行組織條例》,選舉成立了全國(guó)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huì)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臨時(shí)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員會(huì)[2]。它明確了這一時(shí)期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也標(biāo)志著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的正式確立。這次大會(huì)與1934年1月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huì),系統(tǒng)地規(guī)定了工農(nóng)共和國(guó)的階級(jí)性質(zhì)和組織形式。根據(jù)這兩次大會(huì)出臺(tái)的有關(guān)大綱和文件,規(guī)定“中華蘇維埃所建立的是工、農(nóng)兩個(gè)階級(jí)民主專政的國(guó)家,工人、農(nóng)民和紅軍戰(zhàn)士以及所有勞動(dòng)并且困苦的大眾是掌握蘇維埃一切權(quán)力的”[2]。這更加系統(tǒng)明確地說(shuō)明了這時(shí)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也揭示了這一階段我黨領(lǐng)導(dǎo)并建立的共和國(guó)是工農(nóng)民主主義專政性質(zhì)的政權(quán)。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充分體現(xiàn)了工農(nóng)民主主義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性質(zhì),充分發(fā)揮了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民主制度建設(shè)中的重要作用。
根據(jù)上述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從1927年9月初毛澤東領(lǐng)導(dǎo)秋收起義時(shí)提出的“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到1931年11月第一次工農(nóng)兵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的召開,與1927年“八七”會(huì)議首次提出建立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思想到1930年六屆三中全會(huì)制定的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這兩個(gè)過(guò)程是同時(shí)并進(jìn)且相互交織,前者一直處于后者的影響與指導(dǎo)之下。此外,這一時(shí)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在逐步指導(dǎo)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建立的同時(shí),也因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的建立與完善而逐漸明晰其概念和性質(zhì)。由此可見,二者形成和建立的過(guò)程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的建立,令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作用在政權(quán)組織形式的建設(shè)中得到充分發(fā)揮。從此,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有了正式的、規(guī)范的現(xiàn)實(shí)理論的基礎(chǔ)。
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的參議會(huì)發(fā)展模式
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后逐步形成和發(fā)展。“九一八”事變發(fā)生之后,由于國(guó)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攘外必先安內(nèi)”策略,導(dǎo)致東北三省及內(nèi)蒙古東部區(qū)淪陷,日本關(guān)東軍在中國(guó)東北建立了傀儡政權(quán)?“偽滿洲國(guó)”。在東北軍民進(jìn)行抗日斗爭(zhēng)的影響下,全國(guó)人民反帝抗日的呼聲愈加強(qiáng)烈,掀起了全國(guó)范圍內(nèi)抗日的浪潮。黨在調(diào)整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政策時(shí),已經(jīng)將革命重點(diǎn)置于反帝抗日的旗幟之下。
1933年1月,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huì)在致中共滿洲黨組織的信中首次提出“反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張,表明中共中央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wèn)題上有了重要的變化和發(fā)展。當(dāng)時(shí),國(guó)際上法西斯聯(lián)盟氣焰囂張,嚴(yán)重威脅著世界和平;在中國(guó),日本侵略者實(shí)施所謂“防共自治運(yùn)動(dòng)”,大肆收買漢奸,鼓動(dòng)華北五省脫離中國(guó)而獨(dú)立。而此時(shí)的國(guó)民黨政府卻依舊妥協(xié)退讓,嚴(yán)重影響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1935年10月1日,我黨以中國(guó)蘇維埃政府、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huì)的名義在巴黎出版的《救國(guó)報(bào)》上發(fā)表了《八一宣言》。根據(jù)當(dāng)時(shí)因時(shí)局變化而造成的緊迫形勢(shì),《八一宣言》強(qiáng)調(diào)要改變“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拓寬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陣營(yíng),建立涵蓋中高層在內(nèi)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宣言》號(hào)召全國(guó)人民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共同抗日,停止不必要的內(nèi)戰(zhàn),組織抗日聯(lián)軍,建立國(guó)防政府。而且根據(jù)新的斗爭(zhēng)形勢(shì)和任務(wù),我們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也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1935年,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huì)召開了瓦窯堡會(huì)議。會(huì)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策略,并且調(diào)整了一些有關(guān)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具體細(xì)節(jié)政策。在會(huì)議的主題發(fā)言中,毛澤東著重分析了各階級(jí)對(duì)抗日的態(tài)度,明確提出民族資產(chǎn)階級(jí)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guān)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性,甚至連大資產(chǎn)階級(jí)也可能營(yíng)壘分化、參加抗日。他主張要將我們從關(guān)門主義中解放出來(lái),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了適應(yīng)世界反法西斯的革命浪潮、適應(yīng)國(guó)內(nèi)革命形勢(shì)的變化和革命階級(jí)的變化,團(tuán)結(jié)所有可能抗日的進(jìn)步力量,組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挽救中華民族。1935年12月, 中共中央通過(guò)《關(guān)于目前政治形勢(shì)與黨的任務(wù)決議》,提出要更改第二次國(guó)內(nèi)革命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建立的“工農(nóng)共和國(guó)”為“人民共和國(guó)”,后又改“人民共和國(guó)”為“民主共和國(guó)”[3]。說(shuō)明這時(shí)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開始根據(jù)即將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來(lái)調(diào)整根據(jù)地的政權(quán)建設(shè)。
1936年12月12日,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張學(xué)良、楊虎城毅然決然實(shí)行了“兵諫”,扣留來(lái)陜西督戰(zhàn)的蔣介石,發(fā)動(dòng)了著名的“西安事變”。此時(shí),我黨為了盡可能地團(tuán)結(jié)全部可能與日本侵略者進(jìn)行斗爭(zhēng)的勢(shì)力,建立更大范圍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決定和平解決此事變。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lái)等人的努力下,蔣介石作出妥協(xié),摒棄了“攘外必先安內(nèi)”并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六項(xiàng)主張,成就了國(guó)內(nèi)斗爭(zhēng)轉(zhuǎn)向抗日斗爭(zhēng)的轉(zhuǎn)折點(diǎn),也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準(zhǔn)備了必要的前提。聯(lián)蔣抗日不僅體現(xiàn)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不計(jì)前嫌的胸懷格局,也展示了民族危亡之際我黨排除一切紛擾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民族大義。在此背景下,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huì)于1937年9月正式宣布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的稱號(hào),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臨時(shí)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為中華民國(guó)特區(qū)政府即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將邊區(qū)工農(nóng)民主專政性質(zhì)的政權(quán)轉(zhuǎn)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的政權(quán)[2]。為了適應(yīng)政權(quán)性質(zhì)的轉(zhuǎn)變,陜甘寧邊區(qū)政府開始參考、對(duì)照國(guó)民黨的咨詢機(jī)構(gòu)召開各層級(jí)參議會(huì)。在此基礎(chǔ)上,1939年1月召開了陜甘寧邊區(qū)第一屆第一次參議員大會(huì),討論并審查了邊區(qū)政府的工作報(bào)告,通過(guò)了《陜甘寧邊區(qū)抗戰(zhàn)時(shí)期施政綱領(lǐng)》《陜甘寧邊區(qū)各級(jí)參議會(huì)組織條例》《陜甘寧邊區(qū)組織條例》和《陜甘寧邊區(qū)選舉條例》,選舉產(chǎn)生了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huì)常駐會(huì)和政府、法院,逐步建立了與國(guó)民黨地方政權(quán)相同名稱和形式的基層政權(quán)[4]。陜甘寧邊區(qū)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全國(guó)各根據(jù)地中率先建立了參議會(huì),實(shí)現(xiàn)了政權(quán)組織形式的轉(zhuǎn)變,不僅為廣泛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起到了示范作用,還為其他根據(jù)地參議會(huì)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引領(lǐng)作用。陜甘寧邊區(qū)建立起參議會(huì)制度政權(quán)以后,各根據(jù)地按照中央委員會(huì)的要求遵循“三三制”原則先后選舉參議員并召開參議會(huì),新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逐漸成型。
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論指導(dǎo)下,參議會(huì)制度成為這一時(shí)期我黨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據(jù)此規(guī)定和當(dāng)時(shí)的實(shí)際做法,參議會(huì)制度與國(guó)民黨地方政權(quán)咨詢機(jī)構(gòu)的形式相同,是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需求之下,在前期的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基礎(chǔ)上形成的。但這種制度不同于國(guó)民黨地方政權(quán)的咨詢機(jī)構(gòu),而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全權(quán)機(jī)關(guān)。從規(guī)模上而言,參議會(huì)制度比不上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但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的基本原則得到了保持和繼承,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發(fā)展。
各級(jí)參議會(huì)是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各大根據(jù)地的人民代表機(jī)關(guān),也是政權(quán)機(jī)關(guān)。參議會(huì)制度是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號(hào)召下形成的,是一個(gè)聯(lián)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日的實(shí)踐活動(dòng)載體。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革命根據(jù)地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才由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轉(zhuǎn)變?yōu)閰⒆h會(huì)制度。參議會(huì)制度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中國(guó)大地全面開花的結(jié)果,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為挽救中華民族而不懈奮斗的結(jié)果,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抗日決心和團(tuán)結(jié)其他抗日勢(shì)力的誠(chéng)意。但這種政權(quán)組織形式并非是對(duì)國(guó)民黨參議會(huì)制度的生搬硬套,也不是歐美相關(guān)制度的沿襲仿照。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guó)是各革命階級(jí)聯(lián)合專政的共和國(guó),而非資產(chǎn)階級(jí)專政的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國(guó)家,也非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專政的蘇聯(lián),這在實(shí)際上也指明了我們黨政權(quán)組織的獨(dú)特性。
三、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的人民代表大會(huì)的發(fā)展模式
“人民代表大會(huì)”的概念最初是由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中國(guó)此時(shí)可以采取全國(guó)直至鄉(xiāng)一級(jí)的人民代表大會(huì)系統(tǒng),并且通過(guò)這個(gè)系統(tǒng)組建各級(jí)政府。但由于當(dāng)時(shí)正處于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在當(dāng)時(shí)的政治環(huán)境里建立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度是無(wú)法實(shí)現(xiàn)的。只有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之后的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人民代表大會(huì)才有了可以逐步建立和發(fā)展的政治條件。
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以后,國(guó)際上美、蘇就中國(guó)問(wèn)題達(dá)成某種妥協(xié)。而國(guó)內(nèi),在蔣介石統(tǒng)治集團(tuán)無(wú)法立即發(fā)動(dòng)大規(guī)模內(nèi)戰(zhàn)以及人民渴望和平、停止內(nèi)戰(zhàn)的環(huán)境下,蔣介石為發(fā)動(dòng)內(nèi)戰(zhàn)贏取時(shí)間,連續(xù)三次發(fā)送電報(bào)邀請(qǐng)毛澤東到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guó)共雙方簽訂《雙十協(xié)定》并公開發(fā)表,確定了以和平而非內(nèi)戰(zhàn)的方式建國(guó)的大體方針。雙方?jīng)Q定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邀請(qǐng)各黨派、無(wú)黨派人士共商和平建國(guó)大計(jì)。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在重慶召開,會(huì)議期間,包括我黨在內(nèi)的國(guó)民黨以外的一些黨派提議改組國(guó)民黨,避免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gè)人獨(dú)裁,切實(shí)保障人民的各項(xiàng)民主權(quán)利。同年4月,《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在第三屆參議會(huì)第一次大會(huì)通過(guò),其中明確提出“人民管理政權(quán)的機(jī)關(guān)是各邊區(qū)、縣以及鄉(xiāng)的人民代表會(huì)議”[2],這就使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通過(guò)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lái),以此取代參議會(huì)制度。這實(shí)際上就是人民代表大會(huì)的雛形。
1946年6月,蔣介石不顧國(guó)際輿論的反對(duì)和國(guó)內(nèi)人民的和平意愿,悍然發(fā)動(dòng)內(nèi)戰(zhàn),假和平真內(nèi)戰(zhàn)的真實(shí)面目暴露無(wú)疑。為此,1946年10月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huì)確定了建立盡可能大范圍的民族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原則,即廣泛地動(dòng)員群眾,聯(lián)合所有可以聯(lián)合的勢(shì)力,使國(guó)民黨統(tǒng)治集團(tuán)完全被孤立。人民的民主主義性質(zhì)統(tǒng)一戰(zhàn)線開始初步形成。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huì)議上通過(guò)了《迎接中國(guó)革命的新高潮》[5]728的黨內(nèi)指示,提出“這里包括工人、農(nóng)民、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jí)、民族資產(chǎn)階級(jí)、開明紳士、其他愛國(guó)分子、少數(shù)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nèi)。這是一個(gè)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gè)指示明確規(guī)定了這一時(shí)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在具有人民民主性質(zhì)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指導(dǎo)下,解放區(qū)的政權(quán)先后發(fā)生改變,即建立新的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并且撤銷原來(lái)的參議會(huì)制度。
1947年11月,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huì)批轉(zhuǎn)了一個(gè)重要指示,要求解放區(qū)政權(quán)自下而上轉(zhuǎn)變,實(shí)施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次年的晉綏干部會(huì)議上,毛澤東指出,解放區(qū)人民參與管理的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要逐步以各級(jí)人民代表會(huì)議替代參議會(huì)。此后,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在各解放區(qū)先后建立。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對(duì)“人民”的概念進(jìn)行了詳細(xì)闡釋,指出“在現(xiàn)階段的中國(guó),人民是由工人階級(jí)及其先鋒隊(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工人階級(jí)、農(nóng)民階級(jí)、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jí)以及民族資產(chǎn)階級(jí)組成的,并且這些階級(jí)聯(lián)合起來(lái)建立自己的國(guó)家并選舉自己的政府”[6]1475。毛澤東對(duì)“人民”概念的解釋更加凸顯了這一時(shí)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之初,由于各解放區(qū)的政治秩序還不穩(wěn)定,還不具備召開地方和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的條件,于是決定以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代以行使職權(quán)。其實(shí),早在1948年我黨就已經(jīng)開始號(hào)召各民主黨派、非黨派進(jìn)步人士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共同商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huì)和建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事宜,并隨后在1949年6月至9月間舉行了新政協(xié)會(huì)議的籌備會(huì)。
1949年9月,中國(guó)第一次政協(xié)會(huì)議召開,選舉產(chǎn)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huì),會(huì)上一致通過(guò)的《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共同綱領(lǐng)》,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為新民主主義, 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guó)家, 實(shí)行工人階級(jí)領(lǐng)導(dǎo)的, 以工農(nóng)聯(lián)盟為基礎(chǔ)、團(tuán)結(jié)各民主階級(jí)和全國(guó)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7]。正式提出了“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概念,并明確規(guī)定“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為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形式”[8]587。在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政協(xié)會(huì)議就相當(dāng)于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huì)代行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的職權(quán)。后來(lái)在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指示下,在人民代表會(huì)議基礎(chǔ)上,經(jīng)過(guò)發(fā)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度于1954年正式誕生,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應(yīng)該說(shuō),“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探索和推進(jìn)中國(guó)現(xiàn)代化國(guó)家建設(shè)的實(shí)踐中,具有獨(dú)特的政治優(yōu)勢(shì)”[9]。
可見,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過(guò)程是交織在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逐步形成和發(fā)展的過(guò)程之中,前者為后者的表現(xiàn)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內(nèi)容指引。但是這一時(shí)期與上述兩個(gè)時(shí)期的差異在于:1946年陜甘寧邊區(qū)第三屆參議會(huì)第一次會(huì)議以立法形式確定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時(shí),我們黨并沒有正式提出“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思想和政策,而只是初具萌芽;直到1949年的《共同綱領(lǐng)》才正式了提出“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概念,而在此之前,各級(jí)人民代表會(huì)議已經(jīng)普遍替代了參議會(huì)。由此可以看到,沒有前兩個(gè)時(shí)期黨在政權(quán)建設(shè)方面上的實(shí)踐探索,就不會(huì)有這一時(shí)期政權(quán)組織形式上的完善與健全。而隨著政權(quán)組織建設(shè)的日益成熟,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政權(quán)組織形式之間的聯(lián)系也更為緊密,已經(jīng)在潛移默化地發(fā)揮作用,指導(dǎo)政權(quán)組織形式的變化和發(fā)展。
四、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發(fā)展模式的基本經(jīng)驗(yàn)
(一) 組織形式的發(fā)展得益于黨的正確領(lǐng)導(dǎo)
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概念是由恩格斯最早提出的,列寧擴(kuò)大與發(fā)展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概念與內(nèi)涵。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中國(guó)革命斗爭(zhēng)的實(shí)際情況,將統(tǒng)一戰(zhàn)線作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來(lái)指導(dǎo)中國(guó)革命,指導(dǎo)革命根據(jù)地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建設(shè)。使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根據(jù)地能夠團(tuán)結(jié)一切可以團(tuán)結(jié)的力量與敵人斗爭(zhēng),最終取得中國(guó)革命的勝利。還能夠積極協(xié)調(diào)各方面關(guān)系,為“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和改革開放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huì)環(huán)境”[10]。
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是中國(guó)工人階級(jí)的先鋒隊(duì),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負(fù)起民族獨(dú)立、人民解放、國(guó)家富強(qiáng)以及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在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同階段,都運(yùn)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法寶團(tuán)結(jié)被壓迫工人、農(nóng)民等階級(jí)以尋求民族獨(dú)立和人民解放。黨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作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實(shí)踐載體,以每一階段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的變化和調(diào)整為基礎(chǔ),為尋求民族獨(dú)立和人民解放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追根溯源,正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正確領(lǐng)導(dǎo),黨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才能逐漸進(jìn)步和發(fā)展。
(二)組織形式的進(jìn)步得益于正確、科學(xué)的策略方針
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為黨的總路線服務(wù)的,因此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面對(duì)不同的歷史任務(wù),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也應(yīng)適時(shí)調(diào)整才能保證黨的政權(quán)建設(shè)沿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才能分清敵友、保證革命事業(yè)取得一個(gè)又一個(gè)的勝利。
在土地革命時(shí)期,由于蔣介石、汪精衛(wèi)背叛了中國(guó)革命,無(wú)情殺害共產(chǎn)黨人與進(jìn)步人士,所以黨及時(shí)調(diào)整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建立了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了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保存了革命力量,使得革命火種沒有熄滅。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以后,國(guó)內(nèi)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巨大改變,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此時(shí),黨及時(shí)擴(kuò)大了革命陣營(yíng),建立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抗日根據(jù)地普遍建立起了參議會(huì)制度,在所有愛國(guó)階級(jí)和進(jìn)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以后,面對(duì)蔣介石集團(tuán)的倒行逆施的行為,我們黨又一次及時(shí)地調(diào)整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采取團(tuán)結(jié)一切可以團(tuán)結(jié)的力量,徹底孤立蔣介石反動(dòng)集團(tuán)的總方針,并且在解放區(qū)逐漸以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取代了參議會(huì)制度。實(shí)踐證明,正是黨對(duì)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及時(shí)調(diào)整并且制訂了正確的方針策略,“堅(jiān)持用制度來(lái)規(guī)范和保障民生”[11],才使黨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建設(shè)更加科學(xué)、合理,更加符合革命的需要,最終取得革命的完全勝利。
(三)政權(quán)組織形式建設(shè)得益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變化調(diào)整
黨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不是憑空臆想出來(lái)的,而是以黨的基本的策略方針為基礎(chǔ)的,比如土地革命時(shí)期的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制度是在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指導(dǎo)之下建立的。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參議會(huì)制度是出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需要而建立的。“認(rèn)清中國(guó)社會(huì)的性質(zhì),就是說(shuō),認(rèn)清中國(guó)的國(guó)情,乃是認(rèn)清一切革命問(wèn)題的基本的根據(jù)”[12]633,因此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是在尚未成熟的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建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的實(shí)踐證明,在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政權(quán)組織形式是科學(xué)的、是合理的,從而成功地引導(dǎo)中國(guó)革命走向了成功。新時(shí)期以來(lái),我國(guó)的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度不斷完善,保障了所有愛國(guó)人民共同管理國(guó)家的權(quán)利。在所有愛國(gu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國(guó)家已經(jīng)步入了新時(shí)代,已經(jīng)愈發(fā)繁榮昌盛,更加接近于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奮斗目標(biāo)。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和建設(shè)的諸多實(shí)踐證明,只有將黨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建設(shè)始終置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下才會(huì)取得勝利,才能保證革命和建設(shè)事業(yè)順利進(jìn)行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五、結(jié)語(yǔ)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3]399時(shí)提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回首黨的發(fā)展歷程,在黨的百年華誕之際,就是要搞清楚黨的歷史,搞清楚黨在歷史上所走的曲折的道路,之后這樣才能辦好今天的事情。統(tǒng)一戰(zhàn)線作為黨的三大法寶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民主革命時(shí)期,還是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時(shí)期都發(fā)揮著巨大作用。民主革命時(shí)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的變遷發(fā)展,集中反映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作為“主心骨”引領(lǐng)廣大人民群眾的奮斗歷程,也體現(xiàn)了黨因時(shí)而異、與時(shí)俱進(jìn)的革命品質(zhì)和斗爭(zhēng)精神。農(nóng)村土地革命時(shí)期的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huì)在工農(nóng)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指導(dǎo)下,二者相互推動(dòng)形成與發(fā)展;反帝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參議會(huì)制度是在反帝抗日運(yùn)動(dòng)的如火如荼的形勢(shì)下建立的,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的特殊政權(quán)形式;國(guó)內(nèi)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人民代表會(huì)議制度是在尚未成熟的人民民主主義性質(zhì)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由參議會(huì)變革而來(lái)。無(wú)論哪個(gè)時(shí)期的政權(quán)建設(shè)都離不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指導(dǎo),都是根據(jù)其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性質(zhì)建立起相應(yīng)的政權(quán)組織形式。深入了解民主革命時(shí)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政權(quán)組織的發(fā)展變化,對(duì)于我黨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與政權(quán)合法性以和加強(qiáng)黨的政治建設(shè)都有重要的啟示。
〔參考文獻(xiàn)〕
[1 ]中央檔案館, 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cè))[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9.
[2]尹中卿.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度的形成和發(fā)展(上)[J].人大研究,2004(9):4-10.
[3 ]趙宏強(qiáng).從參議會(huì)制度看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度的孕育過(guò)程[J].人大研究,2007(1):4-6.
[4]袁瑞良.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度形成和發(fā)展[J].河北法學(xué),1985(3):34-39.
[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歷史(第1卷下冊(cè))(1921-1949)[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
[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7 ]胡松,饒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與現(xiàn)行國(guó)體、政體的淵源關(guān)系[J].南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5): 121-124.
[8 ]中央檔案館, 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cè))[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2.
[9 ]李俊.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現(xiàn)代化國(guó)家建設(shè)邏輯及其優(yōu)勢(shì)[J].社會(huì)主義研究,2021(5): 142-146.
[10]李平.論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J].毛澤東思想研究,2010(1): 118-124.
[11]張遠(yuǎn)新,吳素霞.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百年來(lái)領(lǐng)導(dǎo)民生建設(shè)的歷史考察及基本經(jīng)驗(yàn)[J].江漢論壇,2021(5): 5-11.
[1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3]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United Fron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ZHANG Rui-jun, SU Yu-ming
(College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United Front was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harvest success. With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 ation, the United Front strate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anged with the times, and tremendous pro- gress had been made. Following the struggle context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racing the changes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under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continuous to maturity and stability is of great value for further summarizing experience and exploring its laws, and had import- ant enlighten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ruling posi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the United Front;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development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