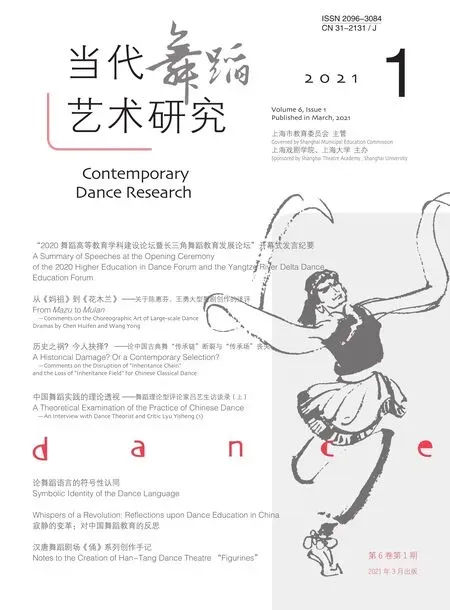從《媽祖》到《花木蘭》
——關于陳惠芬、王勇大型舞劇創作的述評
于 平
一、從尋找失落的“童心”進入舞蹈編創
從1980年到1986年之間的兩屆全國舞蹈比賽似乎都成了原南京軍區政治部前線歌舞團“摘金奪銀”的疆場。在第一屆全國舞蹈比賽中,蘇時進的雙人舞《再見吧,媽媽》榮獲編導一等獎,華超則憑借表、導一體的獨舞《希望》,榮獲編導二等獎和表演一等獎。6年后的第二屆全國舞蹈比賽,蘇時進的群舞《黃河魂》和張振軍、楊曉玲的《踏著硝煙的男兒女兒》雙雙榮獲編導一等獎,而初次亮相的陳惠芬雖然只榮獲表演二等獎,但由她自編自演的兩個獨舞作品《采蘑菇》和《小小水兵》同時榮獲編導二等獎(這兩個作品的編導是她和她的先生王勇)。自那時起步至今,仍在大型舞劇創作中斬關奪隘的編導,一位是在同屆比賽中憑自編自演的獨舞《囚歌》而榮獲編導二等獎和表演一等獎的趙明,另一位就是陳惠芬—那時人們稱她為“采蘑菇的小姑娘”。據陳惠芬、王勇介紹,《采蘑菇》是他們作為舞者嘗試“編舞”的第二個作品(第一個是雙人舞《新婚別》)。他們當時曾想,像這類題材和表現方式的作品還能創作出什么新意呢?另外,同當時舞蹈創作觀念上的更新與發展合拍嗎?起初他們簡單地以為,塑造中國小姑娘形象的最佳表現形式應以民族民間舞為基礎,然而第一稿面世的時候,卻一點也沒有表現出小姑娘活潑靈動、天真可愛的樣子,甚至變化幾個動作,換上另一套服裝,儼然一個回娘家的胖大嫂或是剪窗花的大姑娘。他們陷入了困惑,細細想來,發現是他們沒有從人物質樸的童心出發來進行創作,只是單純強調了外在表現形式,同時意識到民族民間舞的寶貴素材不能只是消極地依賴和照搬,而應積極地對其進行加工、改造和發展,使之與我們的時代和創作相適應。[1]當他們重新編舞時,根據頭腦中那個天真活潑、頑皮可愛的形象,努力尋找人物思維的發展和行為表現的軌跡,捕捉其閃光的童心和細膩的情感表露,從人物體態、童趣的每一個亮點反復推敲和研究,并且大膽、夸張地變形和處理了先前選取的民間舞素材,創造了人物特有的舞蹈語匯。[1]《采蘑菇》的創作和演出使他們對“童心”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感情,接著他們又創作了獨舞《小小水兵》。這個作品也是從“童心”著手的—在創作中他們擺脫了以往只注重展示外在的一些生活再現動作的手法,采用了抒情散文的手法,追求著詩的意境,并通過塑造一只自由自在、快樂飛翔在大海母親懷抱中的海燕,傳遞出小小水兵對祖國媽媽那濃濃的愛 意。[1]雖然與趙明一樣,陳惠芬的舞蹈編創也是從自編自演起步,但趙明的《囚歌》似乎是要掙脫心靈的枷鎖(這與華超的《希望》底蘊相通),而陳惠芬的《采蘑菇》則意圖尋覓失落的“童心”。
二、夸張、變形手法和自然之趣結合的《星星河》
同在原南京軍區政治部前線歌舞團的華超成立了“實驗小隊”,在1988年“全國舞劇觀摩研討會”期間推出了舞劇《曹禺作品印象》—這個“三部曲”由《蘩漪》《日出》和《原野》構成,應該說延續著華超自《希望》以來對“傳統中國”的反思。陳惠芬沒有“小隊”,她與先生王勇“混合雙打”,也在翌年推出了“陳惠芬舞蹈專場晚會”—《星星河》,一看便知仍是表達對“童心”的興趣與情感。對童心童趣的尋覓與表現,還有1986年曲立君創編的舞蹈晚會《記憶的風帆》,《星星河》與之一道沒有走當時“傷痕文藝”的路子,沒有加入“人性的批判”,而是喚醒“未泯的童心”。《星星河》未曾想“挽狂瀾于既倒”,而是向往著“覓清流以濯足”。望著《星星河》中流淌著的一顆顆“星星”,我總是忍不住思索,到底是哪一顆星星會蘊藏著陳惠芬生命的靈性呢?是雙人舞《悍牛與山童》嗎?我想并不是,如若陳惠芬是“山童”的話,我想那“悍牛”可能會失去了“悍性”。那是雙人舞《新婚別》(非沈培藝和李恒達版本)嗎?當然也不是,陳惠芬不擅長舞蹈中的大青衣角色,她更符合小花旦的形象。那是多人舞《山鬼》嗎?那更是不可能了,陳惠芬的確情感豐富,也確實很有毅力,但并不愛憂愁,也不消極抑郁。依我所見,陳惠芬生命的靈性其實蘊藏在《鴨丫頭》《小小水兵》以及《采蘑菇》這三個獨舞作品之中。不知為何,我總是無法進入陳惠芬所表演的《小小水兵》的人物角色之中,我總認為作品中海鷗的“擬象”和手旗的嬉戲,是由于那個鄉村小妞緊隨做輪機長的父親登上甲板而產生的一系列“事象”。不難發現,陳惠芬生命靈性的寄寓其實在于兩個字—自然。這是一種天然形成的形態,它為自然所融化,也就是我們在舞作中見到的忽而戲鷗、忽而攆鴨又忽而采蘑菇的鄉村小妞。馮雙白以《自然天成的童心世界》為題評說《星星河》,其中這樣寫道:觀摩陳惠芬的《星星河》后,他總是不自覺地回味起作品中那富有自然氣息與個性韻味的舞蹈形象,這一形象是變形、夸張手法與自然趣味的融合。[2]在這場作品晚會中,變形與夸張手法的運用極為鮮明。其中,夸張手法的運用多見于采蘑菇小姑娘的體態動作上,歪頭、曲臂、撅臀、塌腰,處處呈現出靈動與俏皮。這些體態動作是由民間舞變形而來的—陳惠芬聚焦先前提煉出的原型動作中的哏勁與俏勁,對之進行趣味性變形,盡管進行了變形與夸張,舞蹈作品仍然保留了民間舞原有的清新與自然的特征。[2]在陳惠芬的舞蹈作品中,你總能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亮色”,例如《悍牛與山童》中倔強而行的“牛步”,《小小水兵》中單腿“坐”的暢想和傾身行軍禮的造型,《采蘑菇》中枕著腳丫入睡等。這些“亮色”既保持著人物的鮮活,又充滿著自然的趣味。[2]當然,陳惠芬遵循自然,卻不盲從自然。她一邊借助舞蹈的魅力觸動觀眾,努力傳遞形象中的神與靈;另一邊又不矯揉造作,她的作品因自然氣質上的變形、夸張,而具有了淡泊之感,看去清淺,實則意深,既辭采華飛,又質樸動人,像一首詩那樣的美,這已接近了成熟的品格。[2]
三、《星星河》源于被主體生命靈性浸透了的生活沃土
與馮雙白就作品本身的動態形象分析不同,張華似乎更看重作品中深藏的“民族性情韻”。張華的舞評名曰《靈化的熱土》,其中寫道:陳惠芬雖然最先創作了《新婚別》,但其真正的起點其實是《采蘑菇》。早年,與一般的舞蹈創作套路相似,借助一個題材來展示民間舞的風格性素材。創造者獨到地發現了“鄉間兒童的形象”與“膠東秧歌動態”二者之間的契合點。但契合畢竟是點上的契合,展開去,困難就當路而橫了—欲風格展覽,就要讓人物削足適履;要人物塑造,人物的生命邏輯就必自行其道。[3]陳惠芬畢竟是聰慧且悟性高的人,她放棄了“風格展覽”,轉而開掘和深化生活經驗,用自己的靈魂呼喚出人物、行動、精神、舞蹈形象及舞蹈意境,掙開既成動作風格規范的拘囿,陳惠芬就徑直走上了創造的道路;跟隨而來的一系列作品中,最具鄉土氣息的莫過于《采蘑菇》與《鴨丫頭》了。[3]原野的純凈、野蘑菇的清香、盛滿小竹籃的孩童夢、河汊湖港里撐出的小舟、爭歡的鴨丫頭、牧鴨伢仔喊出來的似圓似扁的朝暾,這一切同江南的客觀生活固然有深深的聯系,但它們絕不同于客觀的生活景象,甚至也不能說它們僅來源于客觀生活的沃土—它們是陳惠芬的創造,而不單單是發現和概括,它們是構成陳惠芬童真世界的意象群;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我們現實世界中尚未有過的東西,是陳惠芬的生命靈性同她的鄉土生活的純真之戀所孕育的新生命體。[3]張華對陳惠芬《星星河》系列作品的分析,會讓我聯系起房進激分析趙明的《走·跑·跳》,只是張華并不想去分析“創編技法”,他關注的是陳惠芬系列作品“總體情韻中的民族性”,或者叫“民族性情韻”。張華分析道,陳惠芬作為這塊沃土上生長起來的農家女兒,家鄉的客觀生活景象不可能不曾是她的“眼中之竹”,生活景象化為表象在她心中積淀,這些表象往往絕不會僅是眼睛漠然的觀察結果,而總是同切身的生活相糾纏而帶來的身心感受,充滿了情思。[3]一旦投入創作狀態,靈感閃爍,她就進入了高峰值的“當下性”體驗,不過體驗對象不是當下眼前的外部物象,而是童年經驗在當下顯現的記憶表象;由于這類記憶表象來自深處的積淀,又由于它們是在創作激情的沖動下被激活的,因此,它們一開始就充滿了兼容性和可塑性,就已是一種意象、一種“胸中之竹”了,于是從人物出發創造舞蹈形象就有了基本依據。[3]從人物出發,已遠非從生活原型出發,這是從“胸中之竹”進一步化生的人物,從她的性格規定出發,以既有的形象亮點引出更多的形象亮點,組成了人物形象展開的意象系統……要問這里的民族情韻是不是源于生活的沃土?回答是:它并非泛泛地源于生活的沃土,而是源于被主體生命靈性浸透了的生活沃土,源于進入主體范疇內的、在主體能動之下客觀生活內容與主體生命靈性互滲而成的那片沃土—我們稱之為“靈化的熱 土”。[3]是“生命靈性”而非“創編理念”決定了陳惠芬和她的《星星河》的成功流淌。
四、以“個性”豐富“群像”的群舞《天邊的紅云》
推出“陳惠芬舞蹈專場晚會”—《星星河》之后,陳惠芬和王勇沉潛了大約十年。直到1998年首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比賽,在五個金獎作品中,就有他倆創編的女子群舞《天邊的紅云》。這五個作品分別是中國民間舞女子群舞《頂碗舞》和雙人舞《阿惹妞》,中國古典舞女子群舞《踏歌》,陳惠芬、王勇的《天邊的紅云》和趙明的男子群舞《走·跑·跳》是“當代舞”。“當代舞”作為舞蹈賽事的一個類別,在當時其實是指中國古典舞、中國民間舞和芭蕾舞之外的“非類型化”一類。我后來稱其是“表意優先”而非“風格至上”,以至“無類可歸”的一類。其實,就如同張華在分析《星星河》時所說,這是不要讓人物削足適履的“風格展覽”,而要讓人物的生命邏輯呼喚出舞蹈形象和舞蹈意境。在首屆“荷花獎”的金獎桂冠下,陳惠芬與趙明第二次相遇,上一次趙明的《囚歌》是革命歷史題材,陳惠芬的《采蘑菇》和《小小水兵》是現實題材;而這次陳惠芬創編了革命歷史題材的《天邊的紅云》,趙明則從現實題材中創編了《走·跑·跳》。但不論是革命歷史題材還是現實題材,《天邊的紅云》和《走·跑·跳》都屬于“軍旅舞蹈”。除了軍事動作的造型美化和節律韻化外,其動態審美還都有點“芭蕾味”,所以,當后來陳惠芬為遼寧芭蕾舞團創編《八女投江》,而趙明為上海芭蕾舞團創編《閃閃的紅星》之時,我們完全不會感到意外。對于女子群舞《天邊的紅云》,軍旅舞評家趙國政曾評道:《天邊的紅云》以浪漫的情懷、大寫意的手法、抒情詩的筆致,盡寫身著灰軍裝的紅軍女兵們青春之爛漫、歲月之火紅、精神之豐富、心靈之圣潔,以及對偉大時代賦予她們的使命懷有的一腔虔誠、矢志不渝的向往;整部作品很清秀,很超逸,同時也從人物頭上揭去了與觀眾產生隔膜的、人為的神圣和光暈,使人感到她們是一群既普通又超越普通的可愛形象。[4]他還寫道《天邊的紅云》沒有任何血腥的意味,它給人一種猶如薄霧一般縹緲的凄美之感,并且讓人感到那是青春的火焰點燃出的一簇不熄的圣火,是清澈的心靈蕩滌著人間的污穢,是偉大的人性感召著沉睡的良知,是崇高的生命用詩的話語播種著自己的信念和理想……[5]實際上,女子群舞《天邊的紅云》在塑造紅軍女戰士的英雄群像之時,也設計了指揮員、司號員、護理員、炊事員等個性化的人物,這些個性化的人物以其不同的“個性”豐富了“群像”的內涵,也豐富了“群舞”的“織體”。若干年后,當陳惠芬、王勇將其內涵擴展為同名“大型舞蹈詩”之時,我隱約感覺到他倆選擇題材的視角可能受了蘇聯話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影響,那些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因德軍偷襲而犧牲的蘇軍女子話務班成員,都因帶著未來理想的信念之光而不懼赴難,也都有著以個性化的追求獻身于祖國的共同命運!
五、用“紅云”的意象去解讀“媽祖”的神圣
“荷花獎”舞蹈比賽最初兩年一屆,且一屆“小型作品”一屆“大型作品”交錯進行。2000年的第二屆“荷花獎”舞蹈比賽是針對舞蹈詩和舞劇開展的,在此次比賽活動中,趙明的《士兵的旋律》以及王勇和陳惠芬的《媽祖》被評為舞蹈詩金獎,而丁偉的《媽勒訪天邊》以及趙明的《閃閃的紅星》被評為舞劇金獎。趙明和陳惠芬、王勇的獲獎應該視為他們自第二屆全國舞蹈比賽(1986)之后十余年來的“厚積”而“薄發”。在我看來,這屆比賽中的《媽祖》和《媽勒訪天邊》就體裁而言互換指稱可能更為準確,即前者較之后者更具備“舞劇”的形態。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媽祖》是陳惠芬、王勇創編的第一部大型舞劇。舞劇《媽祖》(編導自稱“舞蹈詩劇”)取材于海峽兩岸廣為流傳的一個傳說,還依托了某種史料—史料記載“媽祖”原名林默(劇中稱“默娘”),是一個只活了27歲(960—987)的女子,她在福建莆田湄洲嶼(今福建莆田湄洲島)出生、長大,關愛他人,扶危濟弱,救貧解困;后因解救海難而遇難,被人們尊奉為“海神”并尊稱為“媽祖”。該舞劇共包括四部分內容,即第一幕“天孕”,第二幕“海靈”,第三幕“風泣”,第四幕“云唱”。在觀看完這部舞劇完整的四幕以后,我心中最強烈的感受是,如果由自己來負責對這一舞劇進行創編,絕對不會采取這樣的表演形式。在這部舞劇的第一個部分,媽祖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而到了第四幕的時候,媽祖就化身為象征著吉祥與平安的“紅云”,高高地飄在天空之中,在這中間只經過了第二幕和第三幕這兩個環節,要通過這兩個部分來講述完媽祖從“小妞”成長為“默娘”的整個過程,這顯然是不夠的。由“媽祖”以“紅云”顯靈,讓我聯想起編導表現紅軍女戰士的《天邊的紅云》—這“紅云”不只是血染的霞彩,而更具有神圣的意味。因此,在《媽祖》的創編過程當中,王勇和陳惠芬就采取了一種這樣的方式:四幕都是以舞蹈的方式去講述每一段故事,讓觀眾體會隱含在舞蹈中的情感。不難看出,二人盡量選用了簡單的色調,從而使群舞看起來能夠更加流暢。舞者們有時化身為霞光,有時化身為漁火,有時化身為海浪,有時又化身為星辰,在這樣的背景下漁姑捧著圓笠,漁夫握著長櫓……群舞當中所包含的形象、意韻以及個性與高流暢度共存。但實際上,從更加嚴格的角度來說,這樣一部以舞蹈形式來講述故事的舞蹈詩劇沒能夠完整地塑造出一個飽滿的人物形象。之前還看過《星星河》的觀眾想必會觀察到,講述小默娘在浪花中起舞,與星空交談的第二幕和《采蘑菇》當中描述采蘑菇姑娘的場景極其相似;除此之外,第三幕又和《新婚別》中刻畫新婚娘子神態的表現形式非常相像。當然,之所以會存在這些相似之處,有可能是因為默娘這一人物本身就帶有這些特征,但從筆者的角度來看卻認為這只是為了彌補形象儲備的空缺。就好像在開展論文編寫工作的學者,偶爾也會將過去完成的論文當中的一些想法和內容加入新的論文當中去。但王勇和陳惠芬所編排的舞劇《媽祖》比過去大多數作品的規模都要龐大,能從中感受到過去部分作品的特征是在情理之中的。在該舞劇的編排中有一點讓大家感到非常激動,那就是“紅云”在默娘化身為媽祖的時刻再次出現,讓觀眾們回憶起她從“小妞”開始的成長歷程。
六、緊扣“生態保護”命題創編“全動物”舞劇
數年后,在北京羚祥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的邀請之下,陳惠芬、王勇為該公司特意組建了北京羚祥藝術團,并創編了舞劇《藏羚羊》。編導稱該劇為“現代舞劇”,而就戲劇要素及其構成而言,我以為不如與《媽祖》一樣稱為“舞蹈詩劇”為妥。看舞蹈詩劇《藏羚羊》,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張繼鋼稍早時創編的舞劇《野斑馬》,因為二者都是所謂的“全動物”舞劇。之所以說這部舞劇非常精彩,第一是因為它將抑惡揚善在動物世界的表現方式通過舞蹈呈現給了觀眾,第二是因為該舞劇真正展現出了動物世界所特有的魅力。但王勇和陳惠芬創作的作品更加強調內容和內涵的單純,正如序幕主要呈現的是一片富有靈性的凈土以及有著強大生命力的“藏羚羊”,而尾聲主要呈現的是神圣的生命遭到殘暴的偷獵者的威脅,發出陣陣悲鳴。該舞劇分為四幕:第一幕,羊群當中名為“月亮”的王妃和名為“太陽”的國王首領在感人的溫情和激烈的競爭當中產生;第二幕,在歡樂喜悅的場景下,羊群們展示著天性,該部分同時也對異性之間的親密關系進行了刻畫;第三幕,羊群對天敵進行抵御,不畏困難艱險跨過冰川;第四幕,羊群帶著對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希冀迎接清晨的到來。根據筆者所掌握的信息,該舞劇是國內最先關注“生態保護”命題的,比佟睿睿為上海歌舞團創編的《朱鹮》早了十余年。就該劇的編創理念而言,陳惠芬、王勇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其一,以較高的水平全面且深層次地提煉動態化的主題形象,以確保風格和個性共存的方式來動態化地展現“藏羚羊”這一形象;其二,在對一個形象的發展和成長階段進行描述的過程當中,創造出極富內涵和美感的場景與意境,在關鍵處落下點睛之筆,從作品來看具體體現在基于渲染力和刻畫力的融合來對有著強烈求生意志的“藏羚羊”形象進行刻畫。除此之外,不將沖突直白地呈現于舞臺,而是在強調信念以及主題精神的基礎之上對形象進行刻畫,將一種強大的能量注入這樣單純的演繹中去,這也形成了他倆在日后舞劇創作中的一個特點。在該劇首演后的座談會上,兩位編導在原解放軍藝術學院舞蹈系進修編導時的專業老師肖蘇華指出,《藏羚羊》將“單純”展現得淋漓盡致,拋開了復雜的戲劇任務,把每一段的情節淡化,但這樣的表達方式給舞蹈創造了一個更大的展示空間,該舞劇的凝重和清晰正是最吸引他的地方,舞劇當中專門的舞蹈語言體系在對“藏羚羊”形象的刻畫上達到了非常震撼人心的效果,每一個表演動作都非常精致。軍旅舞評家趙國政指出,在這一部作品當中,實際上是以一種擬人化的方式來處理藏羚羊的動作行為所傳遞的情感,但這樣的擬人化處理并不生硬,而是基于對藏羚羊的習性以及性格特征方面的分析來展現的,因此給人感覺十分自然且生動,面對死亡時的恐懼以及與同伴嬉戲時的快樂都得到了非常形象的刻畫。著名舞蹈家賈作光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提出了三點改進的建議:首先,可以以更加經典化的方式來編排舞蹈,這樣一來,舞劇當中的舞段就能夠在相關的節目當中進行單獨表演;其次,建議采用更加豐富的色彩來設計舞美;此外,在進行舞劇創編的過程中,應當盡可能地實現從細節上打動人心,例如可以以更加擬人化的方式來對“羊”的舞臺形象進行呈現,特別是在舞蹈編排上,盡量避免多次重復“羊”的簡單的肢體動作。[6]應當說,上述專家的點評都是十分準確的。
七、《天邊的紅云》由“女子群舞”升級為“舞蹈詩劇”
在趙明為上海歌舞團創編舞劇《閃閃的紅星》和《霸王別姬》后,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2006),陳惠芬、王勇為上海歌舞團編創了一部已有同名女子群舞的大型舞蹈詩劇,即榮獲第四屆全國歌劇、舞劇、音樂劇優秀劇目展演創作一等獎的作品—《天邊的紅云》。不久后,該劇又榮獲第七屆“荷花獎”舞蹈詩金獎,聯想到趙明創編的舞劇《霸王別姬》也在第四屆中斬獲該獎項,真覺得陳惠芬、王勇和趙明與“荷花獎”緣分不淺。以往表現長征的舞蹈作品中,最成功的應該是雙人舞《艱苦歲月》和群舞《飛奪瀘定橋》,后來的雙人舞《漫漫草地》似是前者的翻版。《天邊的紅云》在以女子群舞的體裁“亮相”時,就體現出與男子群舞《飛奪瀘定橋》截然不同的視角,前者是表現堅韌不拔的信念而后者是浴血奮斗的“戰場”。《天邊的紅云》升級為“舞蹈詩劇”后,我不知該給“舞蹈詩劇”一個怎樣的定義,或許“戲劇要素不完備,但情感色彩很濃烈的舞劇”較為貼切些。
《天邊的紅云》將云、秋、秀、娃和虹這五位主要人物的身份,分別定為某部的護士、教導員、炊事員、司號員和班長。不同于舞劇以“故事”立劇的敘事特性,舞蹈詩劇重在立“人物”,這里的人物不再是故事敘述的符號,而是“故事”本身。如此看來,人物的類型特征及其覆蓋面是“人物”選材的重點。以該劇為例觀察舞蹈詩劇,可見其力避“山重水復”而趨近“柳暗花明”的結構特征,而“長征”則是讓劇得以按“線性”展開的場景,使“柳暗花明”的敘述更加暢達、空靈、富有詩意。我們跟著長征的幸存者“云”的追憶進入了“故事”。只見戰友們群聚著回到了那個槍林彈雨的戰場,突出重圍時,子彈穿透了“虹”的胸膛;翻山越障時,嚴寒冰封了“娃”的青春;跋涉沼澤時,野菜導致了“秀”的沉沒;決勝黎明時,生命的誕生延續了“秋”的生機,“秋”呼喊著“秀”,在腥風血雨中,她們染紅天邊的云……我們注意到,在全劇的“線性”展開中,出現了由三段雙人舞構成的一場戲,由“云”“秀”與各自的戀人,以及“秋”與自己的丈夫展開的雙人舞,成了“云”的記憶呈現著故事中的故事……若是沒有三段雙人舞讓詩劇之“線”有喘息的機會,這結構將趨于單調和平緩。這場戲設置在“娃”凍僵后而“秀”沉沒前,恰好是線性結構之“轉”處,使“詩劇”由此強化了“劇”的沖突。事實上,該劇的成功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紅軍群像氛圍營造得雄渾磅礴,二是人物性格細節刻畫得縝密機巧。后者往往能為前者錦上添花。看著這個升級版的《天邊的紅云》,我似乎覺得它更像蘇聯話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敘事構成;似乎還應該提一句的是,這種敘事構成也將再一次出現在兩位編導的下一部舞劇《八女投江》的創編中。
八、通過“女性視角”刻畫戰爭環境中的女性世界
《八女投江》是陳惠芬、王勇為遼寧芭蕾舞團創編的芭蕾舞劇。其實,他們之前創編的舞劇《藏羚羊》和舞蹈詩劇《天邊的紅云》,從動作形態風格上來看也不違芭蕾審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然同時也是在敘事構成方式上,我總是把《八女投江》視為《天邊的紅云》的進階,也可以說陳惠芬、王勇有了自己的舞劇編創風格。我認為,作為我們民族精神和氣節的象征,“八女投江”與寧死不屈的“狼牙山五壯士”一樣,是永垂青史的“八圣女”,這種人物設置對舞劇構思而言是一道不小的難題,好在知道這對夫妻編導創作過反映長征途中紅軍女戰士的舞蹈詩劇《天邊的紅云》,對于兩位如何在“類”的形象中塑造人物的個性是充滿信心的。[7]的確如此,該劇在獲得2014年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后,與廣東省歌舞劇院創演的舞劇《沙灣往事》一并成為那一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兩部舞劇—先是雙雙入選國家藝術基金對于優秀資助項目的“滾動資助”,再是于第十一屆中國藝術節中雙雙榮獲第十五屆“文華大獎”,接著又于翌年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是十部獲獎的大型舞臺劇中僅有的兩部舞劇。舞蹈評論家馮雙白認為,對編導而言,最大的困難是解決怎樣用芭蕾的形式表現抗日生活的問題,而非難在芭蕾能否被人接受:首先難在老題材如何創新的問題上,遼寧芭蕾舞團能否突破我們的審美期待;其次難在芭蕾的藝術風格如何與東北人民的性格特征結合起來并塑造生動形象的角色,人們眼中的“八女”更像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然而遼寧芭蕾舞團卻有更高的創作追求,即塑造八位女性的個性化角色形象,讓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能夠“復活”于舞臺。[8]編導沒有刻意表現抗日的外在搏斗場景,而是通過女性視角,放眼戰爭中的青春與愛情,那些美好的情感在那無情戰場的反襯下催人淚下。該劇并非僅有投江的場面,而是通過呈現八位女戰士的成長經歷,講述了抗戰英雄的生活以及愛情和家庭的故事,表達著對豐收的喜悅和對幸福的向往,也體現了一種美好的感情所遭受的懦弱者的背叛。[8]編導們要歌頌和贊美的正是“在潮水般涌來的敵人面前,八個正值最好年華的女人,帶著她們熱烈的青春、她們深切的愛情,還有她們堅守的信仰和尊嚴,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轉身……投進滾滾烏斯渾河……寧可戰斗到生命盡頭,也絕不選擇茍且和卑微。”[8]其實,馮雙白舞評中所言該劇“女性視角”(確切說是女性的“個體視角”)的舞劇“敘事構成”,正是對蘇聯話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有效借鑒。
九、成功地運用“芭蕾風范”張揚“抗聯精神”
在1986年,陳惠芬憑借《采蘑菇》《小小水兵》脫穎而出的第二屆全國舞蹈比賽,分別有兩個群舞作品表現“八女投江”— 一個是原沈陽軍區政治部前進歌舞團白淑妹等創編的《八女投江》(編導二等獎),另一個是總政歌舞團于增湘等創編的《八圣女》(編導三等獎)。賽后,兩個作品迥然不同的表現手法甚至引起了一場關于該用“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去表現該題材的討論。顯然,在評委會的認知中,《八女投江》要略高一籌,但當時的青年舞評家陳徽卻認為,在《八圣女》中,沒有故事般的情節設計,甚至沒有為其點綴的細節,無以稱為“典型”的證據,唯有難以忘懷的是暗藏在心底深處緩緩流動的情緒,隱喻象征配合以虛無迷幻,來換取最極致的真實,反以故事情節的淡化,重于情感的強化和升華,《八圣女》或許想要以此來實現它不一樣的理解和選擇。[9]重溫這段舞評并搜尋筆者記憶中的觀舞“意象”,我認為陳惠芬、王勇在創編女子群舞《天邊的紅云》時有這種取向。當然,從同名舞蹈詩劇《天邊的紅云》到芭蕾舞劇《八女投江》,兩位編導在情緒強化時并不拋棄情節,并且通過“細節”的拓展來完善“典型”的品格,今日的《八女投江》早已不可與《八圣女》同日而語了。筆者認為,分析芭蕾舞劇《八女投江》創作演出的成功背后,不難發現,拋開該劇的題材選擇與主題的發掘不談,作品較好地處理了三個主要關系:其一,軍事動作完美融合芭蕾風范。該舞劇是以展示抗聯女戰士為主題的,那么行軍、演練、戰斗是劇中不可避免的表現內容。如何將軍事動作納入芭蕾風范的“圖式”,并與之巧妙結合,對芭蕾舞劇編舞者在“語言”的理解和運用上有著極大考驗。該劇中,芭蕾舞優雅的足尖技巧與外開和挺拔的軍事動作相輔相成并有機結合,在展現芭蕾風范的同時,還宣揚了抗聯精神。但美中不足的是,在運用芭蕾語言“詠嘆”(雙人舞及其變奏)歌頌人物并對其加以強化的問題上,仍舊有提升和改進空間。其二,該劇關于“八女”人物共同性與個別性的關系上,有著完善的處理表現。在第一點中所提及的“關系”圍繞的是“語言提煉”,而“語言提煉”是作為輔助服務于“性格塑造”的。舞劇中人物個性的成功塑造,已經在前文的劇情敘述中涉及了一部分,總結來說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人物具體所代表的身份定位要明確;其次,人物之間的人際關系如何展開;最后,對人物間的互動性與聯通性需要有充足的考慮。其三,舞劇在主線敘事和“插部”呈現之間的關系,要有良好的處理方式。該劇的主線講的是“八圣女”的構成和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插部”在此對升華舞劇的內涵和個體人物性格特性上,就顯得非常重要。目前就整體而言,舞劇中關于主線敘述和“插部”的相輔相成的呈現方面,處理手法比較妥帖,但是,就該舞劇的提升空間來講,“插部”在主線中呈現的時間點和如何利用“插部”在主線中串聯進而營造一種“形式感”的結構這兩點是舞劇編導可以著重思考的問題,并以此來審視各個部分的“插部”在整部舞劇中的體量以及與主線之間的邏輯順序。[7]
十、芭蕾舞劇《花木蘭》姓“芭”也姓“花”
鑒于芭蕾舞劇《八女投江》獲得的巨大成功,遼寧芭蕾舞團相邀陳惠芬、王勇再創新作。于是,芭蕾舞劇《花木蘭》于2018年7月1日在沈陽首演。整部舞劇以芭蕾藝術的習常規構成為結構本體,兩幕的界限以中場休息間隔。如果讓我給這兩幕命名,第一幕(上半場)可稱為“家鄉·軍營”,而第二幕(下半場)則可稱為“軍營·家鄉”。可以看出,這兩位編導懷揣濃厚的軍旅情結,他們化不開的英雄情懷更是在此深扎。我們對比此前他們創編的舞蹈詩劇《天邊的紅云》和芭蕾舞劇《八女投江》,軍旅是現代的軍旅,英雄是群體的英雄。今觀芭蕾舞劇《花木蘭》謳歌的則是古代軍旅中的“獨行俠”。其實,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廣為傳揚之時,我們就有著以芭蕾舞劇來演繹“花木蘭”的期待,因為作為主題歌的《娘子軍連歌》反復吟唱:“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今有娘子軍,扛槍為人民……”比照中國共產黨引領的紅色革命武裝與花木蘭而言,筆者認為在花木蘭的“替父去從軍”中也隱喻著“扛槍為人民”的家國情懷,只是北朝民歌《木蘭辭》將這種情懷置于“唧唧復唧唧……”的淡淡吟唱中隱隱地敘說。筆者將第一幕“家鄉·軍營”中構成的三個場景分別稱為“戶織”“從軍”“ 鏖戰”。在第一場景中,“織女舞”作為底色,營造出生活的愜意和寧靜;緊接著的兩個場景,將底色分別鋪為“交戰舞”和“演兵舞”,在劇中引導敘事的功能角色則由李朔將軍來充當。舞劇中,第二個場景有個點睛之筆,即花木蘭不畏健碩的對手,在與之一對一的對抗中磨煉了意志,并提升了引弓射箭的本領,使她在此后的射敵酋、救李朔中立下首功。第二幕“軍營·家鄉”中的花木蘭,因立下首功而由“花射手”提升為“花將軍”,“萌情”“現身”“失親”“還鄉”是筆者對此前四場不同表演的高度概括和命名。英勇女將花木蘭在被譽以“花將軍”的美名后,和李朔將軍共赴生死、恪守邊關。黃沙孤煙,鐵馬秋風。患難、共情的歲月在二人之間碰撞出特殊的火花,看似缺少愛人間的歡情濃意,但卻有高于愛人間的相濡以沫。編導在“萌情”場景中設計的點睛之筆“鴻雁舞”,賦予鴻雁不畏艱險、跋山涉水的集中性動作,展現木蘭將軍開闊的胸襟以及對李朔將軍高山景行的欽佩與傾慕。緊接下來的第二幕、第三幕,情勢以戲劇性的節奏急轉直下,打破之前的所有美好。花木蘭首當其沖,中箭負傷,李朔將軍為之治療時,驚耳駭目,“女兒身”暴露;接踵而至的烽火連天,木蘭將軍負傷前行……李朔將軍英勇赴義,為救木蘭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下奪命寒箭。木蘭將軍含悲而起、卸甲殺敵……這才造就了最后第四幕中“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的“還鄉”。
2016年,該舞劇獲得國家藝術基金的扶持資助并在最終通過“合格驗收”,筆者認為,當我們論及芭蕾舞劇《花木蘭》,主要關注的其實并不在于演出的內容,即所謂的“演什么”,而在于“怎樣演”,即演出的表現形式。就該劇的“怎樣演”而言,我認為舞劇在以下幾個方面向我們展現了其作品的獨特性。第一,關于舞劇的性格塑造,編導以強有力的能力向我們展現了該劇姓“芭”又姓“花”。花木蘭以其坦率、堅毅的個性在芭蕾舞語言的挺拔性、伸展性中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并與之完美契合,向世界展示了用舞蹈語言講好中國故事的實力。第二,針對舞劇的劇情敘事而言,舞蹈編導將弓箭這一道具作為標志性的“節點”進行演進,花將軍在黃沙戰場的首立功勛、花將軍暴露女子真身、戰友逝世時花將軍的悲痛心境、花將軍決心反客為主的意志都與其密不可分,弓箭的四次出場對應舞劇情節中的起、承、轉、合而成為四個重要節點。第三,關于舞劇的意境營造而言,多樣化的舞蹈風格、情緒化的舞蹈氛圍和“織體化”的舞蹈敘事被創編者巧妙地融為一體,很好地詮釋了如何以舞演劇、劇在舞中。第四,關于舞劇中的動態設計,冷兵器時代特有的戰斗、動作配合肢體語言的動態呈現被創編者精準地捕捉、再現,通過表現訓練、交鋒、鏖戰中的較量、拼搏、廝殺,使得動作動機有了層次的遞進,從而得到高效、充分的發展;同時“制作精良”成為創編者的得力武器,進一步實現“藝術精湛”和“思想的精深”。[10]
當陳惠芬最初以《采蘑菇》中“小姑娘”的形象亮相舞壇,在此后舞蹈詩劇《媽祖》《天邊的紅云》和舞劇《八女投江》《花木蘭》的創編追求中,始終有一團“紅云”的意象在作引導,這也讓我聯想起慶祝新中國建立十周年之際由原廣州軍區政治部戰士歌舞團創演的大型舞劇《五朵紅云》,這便是深扎于“軍旅情結”中的“英雄情懷”!我們相信,陳惠芬、王勇未來的舞劇創編仍會這樣一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