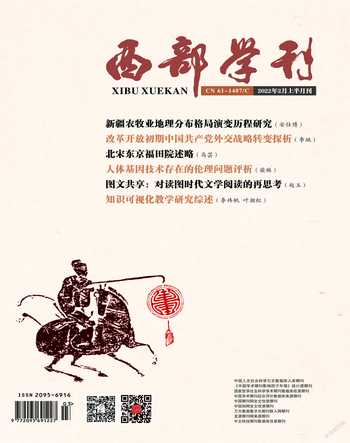環境健康風險背景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芻議
摘要:現行立法和司法解釋允許對于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但由于其救濟理念的滯后和具體制度的不完善,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應對環境健康風險的科學不確定性,預防對公眾的環境健康損害。為此,有必要基于風險預防原則,有序擴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范圍,細化完善相關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并實現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和風險評估制度的有效銜接。
關鍵詞:環境健康風險;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風險預防原則;比例原則
中圖分類號:D92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3-0060-03
隨著人們對自然認識和改造程度的加深,環境問題的科學不確定性越發突出。如何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應對不斷更新的環境問題,成為我國環境公共利益保護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是近年來我國保護環境公共利益發展最為迅速和有效的手段,本應成為環境健康風險防控的重要環節。但目前我國的法律從立法到司法實務,對潛在的環境風險均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成為我國環境公共利益保護領域的一個空白,本文現就此作一探討。
一、問題的提出
(一)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
2016年4月17日,央視新聞頻道《新聞直播間》節目報道,江蘇省常州市爆發了一起嚴重的環境污染致害事件。常州外國語學校搬入新校區后,發現其北側一個已經搬遷且正在進行土壤修復的化工廠所在地塊在施工的過程中散發出異味。學生家長自發組織九百余位學生進行了體檢,其中493名學生血壓指標檢測顯示異常,個別學生被檢測出淋巴癌、白血病等惡性疾病。4月25日,常州市政府發布消息稱,調查發現在常州外國語學校相鄰地塊施工修復過程中,新北區監管部門對原常隆地塊修復監管工作沒有落實到位,該地塊沒有按時完成土壤修復工程,修復施工單位沒有按照要求采取防護措施,而學校在該地塊尚未修復完工的情況下仍然進行了搬遷[1]。4月29日,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共同向常州市中院提起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江蘇長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蘇華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三被告承擔消除影響、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賠禮道歉、承擔原告因本訴訟支出的污染檢測費等法律責任。5月16日,常州市中院以“常州市政府即常州市新北區政府在本案訴訟開始前即對案涉污染地塊實施應急處理,并正在組織開展相應的環境修復”“兩原告提起本案公益訴訟維護社會環境公共利益的訴訟目的已在逐步實現”“案涉地塊于2009年由常州市新北國土儲備中心協議收儲并實際交付”等理由,于2017年1月25日做出了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判決①。
(二)榮華公司非法排污事件
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是我國近年來危害程度最深、社會影響力最大的環境公共利益受損相關案件,但其并非個例,我國還存在諸多社會影響力不及該事件,卻更為普遍的環境相關事件。2011年12月,武威市榮華工貿有限公司污水處理廠開始將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用于本公司投資建成的榮生沙漠公路兩側樹木的灌溉,并將生產廢水通過暗管排入沙漠深處。武威市涼州區發放鎮沙子溝周邊村民表示,榮華公司的排污行為已經對自己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不僅時常能夠聞到惡臭的氣味,賴以生存的飲用水和農業用水遭到污染,在未經任何處理的情況下,就呈現出肉眼可見的藍色,許多村民被迫搬離。后經生態環境部(現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聯合北京師范大學組成的技術組判斷,僅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3月6日,榮華公司每日平均排放971噸、累計排放271654噸工業廢水,其中有187939噸用于灌溉榮生沙漠公路兩側的樹木,83715噸通過鋪設的暗管排入了騰格里沙漠腹地。通過無人機航拍和GPS定位,榮華公司的非法排污行為導致騰格里沙漠中形成大小不等的污水坑塘共計23處,污染沙體面積達265.81畝②。事件發生后,沙子溝村村民因榮華公司非法排污行為產生的直接和間接損失,未能進入司法程序,也未得到任何賠償。
二、環境健康風險相關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不足
(一)舉證責任分配制度不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1230條的規定,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引起的損害賠償案件,應當由加害人承擔污染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這一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沿襲了《侵權責任法》第66條的規定,是完全的“舉證責任倒置”模式[2]。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全面加強環境資源審判工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環境保障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環境侵權解釋》)則要求受害人初步證明污染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關聯性”,即污染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因果關系存在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盡管在《民法典》生效后,《侵權責任法》將同時廢止,但《環境侵權解釋》和《環境保障意見》的規定相較于絕對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更具有合理性,而且在我國司法實務界和學術界也得到了普遍的認可。環境健康風險問題相較于普通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要解決的不是事后的救濟,而是在損害發生以前,對于損害發生的可能性進行評估和控制。故其證明對象事實上是一種“尚不明朗的事實狀態”,科學不確定性的程度明顯更高,承擔因果關系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勝訴的難度遠高于對方當事人。因此,相較于普通的環境侵權,環境健康風險相關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規則有必要更加嚴謹。
(二)對欠發達地區重視不足
環境問題的損害后果沒有國界之分,在一國之內更不會因為地區經濟水平的差距而存在區別,但事實上,經濟的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制約著對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地區所遭受到環境損害的重視程度,這些相對不發達的地區所遭受到的環境健康風險事件甚至環境污染事件多未能進入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程序。前述榮華公司非法排污事件即為眾多案件中極為普通又非常典型的一個案例,該公司非法排污給沙子溝村的生態環境以及村民造成的損害后果,包括后續潛在的環境健康風險均未受到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社會組織的關注,村民未能到任何賠償,不能不說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應對環境健康風險的缺失。
三、環境健康風險相關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則
(一)風險預防原則
風險預防原則是應對科學不確定性最為直接有效的法律原則,其經典表述源自1998年的《溫斯布萊德申明》:當一項活動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產生了威脅時,即使因果關系不能從科學上完全證明,也應當采取預防措施[3]。結合風險預防原則的定義可知,該原則的目的在于處理一定程度的風險危害、科學不確定性和該科學不確定性帶來的危害可能性能否成為拒絕或延遲行動的理由這三者之間的關系[4]。根據預防程度的不同,風險預防原則可以分為強風險預防原則和弱風險預防原則,前者是指只要某項活動有產生嚴重且不可逆轉損害的可能性,不論這種可能性的大小,都必須完全禁止該項活動的繼續進行;后者是指在禁止某項活動前,要對該項活動產生的風險所可能造成的損害結果和預防該風險所投入的成本進行損益比的衡量,如果禁止該項活動所需付出的資源小于或等于對該風險所指向損害結果的救濟成本,就應當停止該項活動的實施,反之該項活動則應當按照原計劃繼續進行。目前,國際社會認可并實施的風險預防原則大多屬于弱風險預防原則[5]。合理確定風險的等級并將其納入調整范圍,是目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應對環境健康風險的當務之急。
(二)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的核心在于通過法益間、目的與手段間的衡量,選擇對關系人和一般大眾造成損害最小的方法為之[3]。對環境健康風險進行有效的評估,確定對環境健康風險采取預防措施的標準是預防風險轉化為實際損害的必要前提。結合環境侵權案件加害人承擔的無過錯責任和目前立法選擇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原告即受害人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承擔的訴訟義務并不繁重,對提起環境健康風險相關的環境公益訴訟設置一定的風險預防標準并未超出其訴訟能力。因此,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選擇弱風險預防原則,并同時引入比原原則,根據對環境健康風險評估的結果,確定相應的風險預防的適用范圍,能有效緩解環境健康風險所可能產生的損害及其后果的嚴重程度。
四、環境健康風險相關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完善路徑
(一)擴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范圍
如前所述,目前我國有資格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主體僅限于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滿足一定條件的環保組織,這一規定的范圍過于狹窄,導致具有原告資格的主體遠不能滿足現有實踐中大量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需求,對于環境健康風險更是無暇顧及。在此基礎上,將環境健康風險納入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只會使欠發達地區的環境公共利益被忽視,不利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筆者認為,有必要賦予公民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這樣以來,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原告主體數量,減輕目前具有原告資格主體的訴訟壓力,避免原告數量不足導致對欠發達地區環境問題的忽視;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提高民眾參與環境保護、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的意識,切實保障公民的環境權。但出于防止濫訴的需要,和環保組織一樣,有必要對公民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做出一些限制,比如訴訟請求必須與自己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等。同時,有必要對不同主體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類型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分配,使其能夠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二)風險評估制度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有效銜接
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編著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理解和適用》中指出:“重大風險”是指以訴訟過程中涉及的有效證據材料和當前的科學技術能力作為條件,能夠判定對環境可能造成重大損害危險的一系列行為,不能準確判定具體環境損害行為可能性的情形不在此范圍[6]。盡管環境健康風險具有科學不確定性的基本特征,以現有的科技手段尚無法精確解釋該風險轉變為現實損害的原理和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對任何具有環境健康風險的行為提起相關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而無需對其進行評估。對風險的準確評估是對其進行有效防控的前提條件。環境風險進入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程序,并不要求僅有模糊的不安全感,而是要達到環境危險標準[3]。這就要求它最起碼有造成實際損害的可能性,有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且不可逆轉的損害。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了環境檢測體系,在此基礎上完善環境健康風險評估制度,明確風險的嚴重程度和可能涉及的人群,并將該信息在合理的范圍內向社會和公眾公布,有利于公眾對環境健康風險及時進行了解和分析,為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提供科學的依據。
五、結語
為了有效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不僅應當對已經發生的生態環境損害進行救濟,也應當對有可能造成重大損害的環境健康風險進行積極的預防。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是我國近年來社會關注度最高的生態損害案件,而榮華公司非法排污事件則是近年來社會發展中普遍發生的案例,環境健康風險相關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在上述兩個事件中的缺席足以說明我國相關制度的不完善。為了彌補這一缺失,有必要在我國環境立法中加強風險預防的理念,使“風險預防原則”成為環境立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同時,在風險預防理念的指引下,還應當對舉證責任分配、環境健康風險評估等制度做進一步的規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以更好地應對實踐中普遍存在的環境健康風險。
注釋:
①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蘇04民初214號民事判決書。
②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人民法院(2015)武涼刑初字第381號刑事判決書。
參考文獻:
[1]唐娟.常州通報外國語學校污染事件:相關責任人被立案調查[EB/OL].(2016-04-26)[2020-09-02].
https://www.sohu.com/a/71738594_123877.
[2]薄曉波.論環境侵權訴訟因果關系證明中的“初步證據”[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
[3]張旭東.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程序規則思考[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4).
[4]何香柏.風險社會背景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反思與變革——以常州外國語學校“毒地”事件為切入點[J].法學評論,2017(1).
[5]朱炳成.環境健康風險預防原則的理論建構與制度展開[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11).
[6]于文軒,牟桐.論環境民事訴訟中“重大風險”的司法認定[J].法律適用,2019(14).
作者簡介:張陳昕(1995—),女,漢族,甘肅武威人,單位為福州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