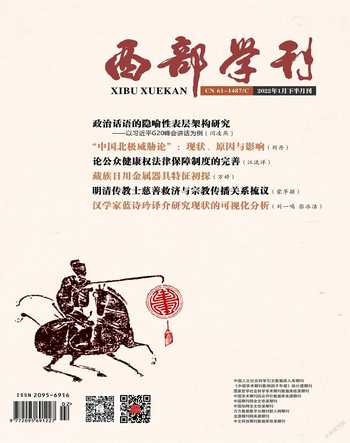女性群體形象污名化問題探析
孫影娟
摘要:女性群體形象的污名化問題由來已久,女性群體為抵制污名化付出了積極的努力。近年來出現(xiàn)的“Me Too”運動、“中華田園女權(quán)主義”等大規(guī)模的社會行動體現(xiàn)了女性個體在面對污名化時所選擇的不同的應(yīng)對策略。這些策略有的是被動接受,有的是主動抵抗,也有以“田園女權(quán)主義”為特征的極端應(yīng)對策略,但這一切并不利于“女權(quán)主義”的發(fā)展和傳播。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女性群體形象污名化應(yīng)對策略應(yīng)當(dāng)是:(一)注重提高女性個體的社會認同;(二)增加正面的群際接觸;(三)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四)社會層面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與社會秩序。
關(guān)鍵詞:女性群體;污名化;應(yīng)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H136;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2-0080-04
女性群體形象的污名化問題由來已久,互聯(lián)網(wǎng)興起后更是甚囂塵上。譬如,女大學(xué)生、女博士、剩女等話題,總能和“胸、二奶、性行為”等敏感詞牽涉一起,成為一種賺流量的熱門話題。我們的社會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女性群體為抵制污名化付出了積極的努力。然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復(fù)雜、多元的社會,過去女性群體為反污名所做出的努力以及經(jīng)驗總結(jié),對今日女性群體應(yīng)該如何更有效地抵抗污名化仍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一、女性群體形象的污名化現(xiàn)象闡釋
污名這一概念,早在1963年就由美國著名的社會學(xué)家戈夫曼(GOFFMAN E.)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xiàn)》中首次提出,并把它作為社會歧視的起點。他認為,由于個體或群體具有某種社會不期望或不名譽的特征,而降低了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污名就是社會對這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目前的界定趨勢是將污名概念從個體化向群際化轉(zhuǎn)向,從認知化向系統(tǒng)與制度化轉(zhuǎn)向。當(dāng)面對污名時,女性會有很高的風(fēng)險感到痛苦、焦慮、羞恥等負面情緒,并且污名也是妨礙女性群體取得社會支持的主要因素之一[1]。針對女性群體面對的污名化局面,外國學(xué)者提出了詳細的對應(yīng)策略,如行為認知療法(CBT)、支持小組(support groups)等,并對這些對應(yīng)策略的有效性通過問卷等方法進行了驗證。我國有關(guān)女性群體污名化的相關(guān)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并且集中在參與互聯(lián)網(wǎng)比較積極的年輕女性群體當(dāng)中。
在我國當(dāng)前的網(wǎng)絡(luò)傳播時代,女性污名的形成是媒介污名、公眾污名和自我污名三種污名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并且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推動下,有不斷擴大與加劇的趨勢。一方面,信息傳播速度的提升使得信息不再閉塞,先進思想的傳播提高了人們的思想境界,促進了社會對女性群體的了解,弱化了原有的一些女性污名標簽;另一方面,以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媒介,出現(xiàn)了更多針對女性群體的污名化,并且比起以往的污名化影響更加深遠。面對污名化,女性個體會出現(xiàn)諸如憤怒、害怕、悲傷等不同的情感應(yīng)激,這些情緒加上社會認同、社會地位、自我效能感、個人經(jīng)驗等其他因素,導(dǎo)致了女性個體選擇了不同的應(yīng)對策略來應(yīng)對污名化。
二、近年來應(yīng)對女性群體形象污名化的策略選擇
近年來出現(xiàn)的“Me Too”①運動、“中華田園女權(quán)主義”②等大規(guī)模的社會行動體現(xiàn)了女性個體在面對污名化時所選擇的不同的應(yīng)對策略。在這些應(yīng)對策略中,并非所有的應(yīng)對策略都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些極端的應(yīng)對策略非但沒有弱化對女性群體的污名化,甚至還加深了男女群體的群際偏見,激化群際矛盾,導(dǎo)致了更多女性污名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
(一)整體應(yīng)對策略
1.被動接受。女性個體面對污名化現(xiàn)象時被動接受,保持沉默的情況主要發(fā)生在社會民眾普遍認為女性群體社會地位較低的情況下。例如,在我國的古代,女性被視為是男性的附屬品,地位較為低下,女性對于身上的污名標簽主要就是持沉默態(tài)度。盡管害怕情緒對集體行動參與的影響暫不明確,但是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害怕與回避性反應(yīng)有關(guān)[2]。當(dāng)女性群體社會地位低下時,往往意味著女性擁有更少的資源,若主動抵抗污名化現(xiàn)象,除了效果不佳外,還可能要承擔(dān)更大的后果,這些因素導(dǎo)致在女性群體面對污名化時傾向于表現(xiàn)出害怕情緒而非憤怒情緒,最終選擇回避性反應(yīng)。
2.主動抵抗。1987年,KLANDERMANS和OMEGEMA提出,個體參與特定的集體行動或社會運動主要經(jīng)歷了4個階段:第一步,個體了解到某項社會運動的策略目標并對其產(chǎn)生同情,于是個體成為這項運動的潛在動員目標;第二步,個體正式成為這項運動的動員目標;第三步,個體產(chǎn)生參與集體運動的動機;第四步,參與社會行動。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認同、群體情緒和效能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自我效能感(sense of self-efficacy)是指個人對自己在特定背景中是否有能力去操作行為的期望,由美國心理學(xué)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在女性地位相對較高,女性群體擁有更多資源和話語權(quán)利的時候,女性個體的自我效能感更高,在面對污名化現(xiàn)象時,更傾向于表現(xiàn)出憤怒情緒,由于此時女性群體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支持,因此女性參與集體行動的積極性更高,更傾向于主動抵抗的行動策略。
(二)極端應(yīng)對策略——以“田園女權(quán)主義”為例
“中華田園女權(quán)”原本是指要求男女平等卻要男性承擔(dān)主要責(zé)任,以女權(quán)為借口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群體,現(xiàn)在“中華田園女權(quán)”所包含的范圍有所擴大,某些行動較為激進的女權(quán)主義也被冠以中華田園女權(quán)的稱呼,在極端情況下,“中華田園女權(quán)”甚至被錯誤地等同于女權(quán)主義。“中華田園女權(quán)”也是女權(quán)主義的一個分支,但是由于其行為比較激進,在維護女性群體權(quán)利、反污名的過程中常常忽略客觀事實,沒有結(jié)合實際情況,且較為缺乏邏輯和組織,因此被大部分人所反感和抵制。“中華田園”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中華田園犬”一詞,“中華田園女權(quán)”本身就構(gòu)成了對女權(quán)的戲謔,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對女權(quán)主義的污名化。本文所指的“中華田園女權(quán)”是指在百度貼吧、微博、豆瓣等主流社交媒體中,行為言論激進且忽視客觀事實的女權(quán)主義。在“是否能分清‘中華田園女權(quán)’和‘女權(quán)主義’”這個問題上,有56.67%的人表示無法區(qū)分,有43.33%的人表示能夠區(qū)分[3]。這就意味著,在過半數(shù)被調(diào)查者的眼中,“中華田園女權(quán)”實際上就代表了“女權(quán)主義”,于是“中華田園女權(quán)”等詞匯就成為了女權(quán)的負面標簽,這無疑是不利于“女權(quán)主義”的發(fā)展和傳播的。在微博語境中,“中華田園女權(quán)”往往代表著“霸道”“激進”“蠻橫”等,這些標簽同樣會貼在女權(quán)主義上,使得人們對女權(quán)主義形成新的刻板印象。
三、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女性群體形象污名化應(yīng)對策略反思
(一)注重提高女性個體的社會認同
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是指個體認識到他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社會認同、群體情緒(group-based emotion)、效能感(efficiency)是影響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三大因素[4]。女性群體若希望應(yīng)對策略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讓更多的女性個體參與到行動中是一個必要條件,只有參與人數(shù)足夠多,才能被社會所重視和關(guān)注。如何提高女性的社會認同,增加其參與集體行動的積極性就是關(guān)鍵。TAJFEL和TURNER在1986年提出社會認同理論,在這個理論提出之初就指出,若個體自己所在的群體帶有強烈的認同感,同時認為當(dāng)前的群際關(guān)系是不公平的時候,個體就更可能會參與到改變?nèi)后w現(xiàn)狀為目標的集體行動中。后續(xù)的研究發(fā)現(xiàn),情緒(特別是憤怒情緒)和效能感是衡量不公平感的重要指標。比起泛泛而談或是冷冰冰地講述一類寬泛的事件,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更具有真情實感,更能激起個體的情緒[5]。女性群體在應(yīng)對污名化的過程中,應(yīng)該將范圍縮小,以特定的事件作為中心來展開,這樣更能夠引起女性個體的共鳴,提高社會認同,使得更多女性加入到集體行動中。同時,對于女性個體來說,也應(yīng)該積極提高自身的社會認同,認識到自己也是女性群體中的一員,發(fā)生在別的女性身上的污名化現(xiàn)象并非與自己毫無關(guān)系,當(dāng)看到別的女性個體受到污名化的侵害時,要盡可能地提供幫助,這樣才能讓污名化現(xiàn)象逐漸減少。
(二)增加正面的群際接觸
19世紀50年代,社會心理學(xué)家奧爾波特(GORDON W.ALLPORT)從認知角度解釋偏見(prejudice),他認為刻板印象是人類思維中所不可避免的一種產(chǎn)物,是人類由于無知所產(chǎn)生的自我防御心理,基于這個理論假設(shè),奧爾波特隨后提出了群際接觸假說:如果在最合適的條件下進行群際接觸,會有效地減少群際偏差。從認知的角度上看,既然偏見是由無知所產(chǎn)生的自我防御心理,那么當(dāng)兩個群體之間的交流增加時,就會減少因為認知不足以及片面的信息所造成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從而減少污名化現(xiàn)象的發(fā)生[6]。在一個群體對外群體的接觸、了解較少的情況下,就可能會出現(xiàn)群體成員通過自己先前片面的經(jīng)驗或是內(nèi)群體成員的觀點和看法來判斷和定義外群體成員的情況,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就可能會導(dǎo)致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的發(fā)生。對于這種情況,應(yīng)該增加兩個群體之間的群際接觸,使得內(nèi)群體成員對外群體有全面、準確的認識和了解。不僅是直接的群際接觸可以弱化刻板化,想象的群際接觸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
與此同時,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群際接觸都會減少群際之間的刻板化,群際接觸策略的有效性在不同的情況下存在一定的差異,既可能弱化刻板化,也可能增強刻板化,若一開始接觸到的是目標對象的類別信息,則人們出于節(jié)省認知資源的目的,會傾向于使用一開始接觸到的類別信息對外群體成員進行判斷,這樣就增強了刻板印象;若一開始接觸到的是個體化信息,則刻板化降低。因此,良性的應(yīng)對策略應(yīng)該強調(diào)正面、有效的群際接觸,奧爾波特提出的關(guān)于有效進行群際接觸的四個條件分別為:群體間平等的地位、共同存在的目標、群際之間的合作以及權(quán)威支持,若缺少或嚴重違背其中一條,就會導(dǎo)致消極的群際接觸。在具體的應(yīng)對策略中,女性群體應(yīng)該增加與其他群體正面的接觸,增強群際之間的了解與認識,弱化因不了解和無知所造成的刻板印象,以此達到消除污名化的目的。
(三)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
污名化現(xiàn)象對女性群體帶來的傷害的多少,一方面來自污名化現(xiàn)象本身,另一方面來自于女性的自我認知。在經(jīng)歷污名化的時候,部分女性會害怕聽到他人談?wù)撚嘘P(guān)自己身上存在的污名標簽的事情,哪怕他人并沒有針對性。形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是這些女性腦海中存在的不合理的信念,有學(xué)者稱之為“自我污名”(internalized stigma/self-stigma)。自我污名與女性所感受到的焦慮情緒與不良行為甚至是自殺行為有密切的關(guān)系。要減輕這種污名化的影響,女性應(yīng)該修正腦海中不合理的信念,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許多研究已經(jīng)明確表明,外部手段的干預(yù)能夠有效弱化自我污名,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認知行為療法(CBT.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認知行為療法是一種通過改變不合理的認知而矯正不正常行為的治療方法,于上世紀70年代后期用于臨床。當(dāng)女性在面對污名化現(xiàn)象時,要時常留意不合理的認知,一旦識別出不合理的認知,就要及時改變它,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尋求外部的幫助。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對于女性群體應(yīng)對污名化至關(guān)重要,擁有正確的自我認知,就可以大幅度減輕污名化現(xiàn)象所帶來的傷害。
(四)社會層面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與社會秩序
戈夫曼指出,污名的存在并非為污名者的問題,而是社會規(guī)則和公共秩序的缺陷,污名是社會建構(gòu)的越軌標簽;同時奧爾波特指出刻板印象具有合理化(rationalizing)和合法化(justifying)的功能,宙斯特和巴納吉(JOST AND BANAJI)將刻板印象的合法化功能分為三個方面:自我合法化、群體合法化、系統(tǒng)合法化,其中刻板印象的系統(tǒng)合法化是指刻板印象為明顯體現(xiàn)偏見的社會制度形式提供合理性,使其看起來合法[7]。從這個角度上看,要弱化或消除女性群體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關(guān)鍵在于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和社會秩序,這就要求社會以及國家各級政府發(fā)現(xiàn)社會制度中所存在的弊端,采取措施對其進行修正,從而消除為使系統(tǒng)合法化所導(dǎo)致的刻板印象。
概言之,女性群體可以通過以下幾方面提高應(yīng)對策略的有效性:在行動過程中,注重提高女性個體的社會認同,增強女性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積極性;增加正面的群際接觸,有利于增進群際間的交流和了解,弱化因無知和思維惰性而導(dǎo)致的刻板印象和無名標簽;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減少自我污名所造成的傷害;國家和社會層面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和社會秩序。
注釋:
①Me Too(我也是),是女星艾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等人2017年10月針對美國金牌制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聞發(fā)起的運動,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jīng)歷,并在社交媒體貼文附上標簽,藉此喚起社會關(guān)注。
②中華田園女權(quán):網(wǎng)絡(luò)流行詞,是指一群表面上積極爭取“男女平等”,但是實際上卻想要獲得遠高于自身合法權(quán)利的特殊權(quán)利。并且無法正確理解“男女平等”,扭曲“男女平等”的意義的群體。有人認為中華田園女權(quán)的盛行,一部分原因就是女性對權(quán)利的過度解讀。
參考文獻:
[1]張瑾濤.新媒體時代國內(nèi)女性主義發(fā)展中的問題研究——以社會化媒體平臺中女性主義污名化現(xiàn)象為例[J].科技傳播,2020(21).
[2]薛婷,陳浩,樂國安,等.社會認同對集體行動的作用:群體情緒與效能路徑[J].心理學(xué)報,2013(8).
[3]萬珺.微博語境中“女權(quán)主義”污名化研究[D].海口:海南師范大學(xué),2020.
[4]高明華.偏見的生成與消解? 評奧爾波特《偏見的本質(zhì)》[J].社會,2015(1).
[5]吳欣桐,陳勁,朱子欽.管理研究中的女性形象——基于管理學(xué)國際期刊的文獻分析[J].外國經(jīng)濟與管理,2020(11).
[6]羅漢,鄒月華.媒介,話語與性別:虐童報道中女性形象研究——以“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為例[J].新聞愛好者,2020(10).
[7]翟晗.國家想象之鏡:中國近代“女權(quán)”概念的另一面[J].政法論壇,2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