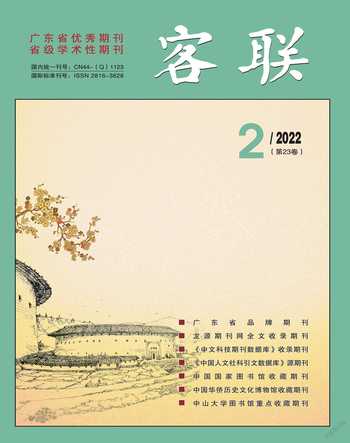朝鮮時代韓日民間繪畫的對比淺析
朱潔
摘 要:日韓作為東亞古國,在文化藝術發展都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外,但在發展中逐漸產生了本民族獨特的藝術特點。封建社會的封閉性使得韓國民畫和日本大津繪保留了濃厚的本民族的性格特征。韓國民畫內容豐富,整體流露著詼諧之美,日本大津繪則是崇尚簡潔之美。作為同時代的民間廉價繪畫,經過學者們多年的藝術研究,它們蘊含的藝術價值被不斷發掘,重新煥發了光芒。雖同屬民間繪畫,但是兩者之間也存在很多值得探討的差異性,通過此研究會讓讀者對日韓文化差異性有更深的理解。
關鍵詞:朝鮮時代;韓國民畫;日本大津繪;對比
同屬于東方文化圈的日韓兩國,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也出現了類似于中國民間年畫一樣的樸素的民間繪畫,比如韓國的民畫和日本的大津繪,這些藝術形式雖然都受到主流繪畫的影響,但是主要反映的是底層勞動人民的藝術需求,通過對這些樸素的民間繪畫的研究,可以更好的理解一個民族的性格,更深刻認知古代東方化圈的文化個體之間的差異,是非常有價值和必要的。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案例比較和分析,總結和歸納其中的異同點,希望可以挖掘出隱藏在民間繪畫之后更深的文化屬性,為后續的東方民間繪畫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韓日民間繪畫的人文背景
最先把韓國的民間繪畫稱為“民畫”的是日本學者柳宗悅。他在自己的論文《不可思議的朝鮮時代民畫》中首次嘗試提出這個概念,并且提出韓國的民畫有著不可思議的美,存在無意識的個性,他認為韓國的民畫有著與獨特的新鮮感和自由度。①民畫最繁榮的時期是朝鮮的中后期,時間大約是1700年-1850年,這段時間的朝鮮半島是一個封閉的封建社會,是韓國歷史上一個錯綜復雜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壬辰丙子之亂,本土的巫教和外來的天主教以及統治階層信奉的儒教和佛教之間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和爭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底層人民與統治階級的爭權奪利不同,他們更向往純粹的可以帶來福祉的信仰和追求,這為民畫的繁榮奠定了信仰基礎。
朝鮮時代是一個等級森嚴的歷史時期,人的貧富貴賤是靠出身來決定的,一般的老百姓毫無上升空間。在統治階級圈層中流行的文化藝術大多受中國影響的宮廷繪畫和文人畫,這些藝術形式對朝鮮的底層百姓來說是極為奢侈的,所以民畫的繁榮正好可以填補普通百姓對美的需求,這奠定了韓國民畫的群眾基礎。面對底層需求郁郁不得志的工匠、畫師和農民成為了民畫創作的主力軍,在民畫的世界里他們不但可以滿足對美的創作欲望,還可以獲得微薄的收入,針對百姓的基本的裝飾需求和祈福需求,大量進行同主題和系列主題的創作,韓國民畫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逐漸繁榮起來的。
日本的大津繪是日本江戶初期寬永年間在大津地區流行的一種民間繪畫,是為了滿足日本底層人民需求而出現的繪畫形式,大津繪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初期。江戶時代是日本最后一個封建武家時代(1603-1868),從年代上來看大津繪和民畫基本同屬于一個歷史時期,此時的日本也是奉行鎖國政策,同樣的等級森嚴,全民被嚴格分為四個階層: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這期間的日本文化主流思想以朱子學、陽明學、古學派、國學派和町人思想為主。17世紀后半葉,町人思想與文化迅速崛起,日本的宮廷藝術狩野、土佐派繪畫逐漸被華麗的“浮世繪”所取代,究其原因浮世繪描寫的是市井生活,更加貼近現實,大津繪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與浮世繪不同的是大津繪是描述市井生活以外的題材,雖然在精致程度上遠不及浮世繪,但卻更加適合底層人們的消費需求。
德川幕府時期島原之亂的時候日本禁止基督教的傳播,并發通告昭告天下,這次宗教爭端引發殉教者超過28萬人。當時的佛教又腐化并流于形式,陷入宗教迷茫期的平民轉向以享樂為人生目的,這是大津繪產生的宗教背景。在宗教改革最嚴苛的時代,持有大津繪的佛像畫可以免罪,此時的大津繪成為平民能夠欣賞、寄托情懷和祈福的心理象征。②大津繪與韓國民畫一樣,其創作者都是平民百姓和底層工匠,受眾群同樣是最底層的勞動人民。
二、功能與題材的比較
民間繪畫在不同的文化、地理和宗教背景之下,必然發展出適合本民族的功能與題材,韓國的半島文化長期受儒教的影響,在地理上多為山地丘陵,廣大人民崇尚自然、擁抱自然,在等級社會的統治之下發展出了自我滿足的詼諧的人文特征,繪畫自由而充滿了現實意義。日本遠離大陸,一直保持唐朝文化的影響,整個日本的封建統治也出現了有別于中國和韓國的集權形式,大津繪是在幕府統治時期的江戶時代發展起來的,帶有深深的浮世繪的烙印又區別于華麗的浮世繪,獨具特色。
韓國民畫從功能上來講主要滿足底層人們對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所以題材基本上是以民間祈福內容為畫題而進行創作,是以日常生活中實用為目的廉價繪畫。民畫并不像個人風格獨特的文人畫一樣的抒發胸襟之用,而是為大眾創作的具有集體意識的繪畫作品。韓國工藝民畫研究家超子庸認為,韓國所有的民間繪畫都可以稱為“韓畫”,按照技法可以分為純粹繪畫與工藝美術畫,韓國民畫具有無名性、實用性、工藝性、象征性以及獨特性。
民畫的題材在功能性的基礎上進行大量的、多內容的創作。底層人民在長期的艱苦生活里對美的需求是具體的,非虛假性的,所以描繪的東西基本都是真實存在的尋常事物,描繪時會表現韓國民眾的詼諧與愉悅、純真的精神世界。具體到民畫內容時,可以根據室內的裝飾需要和民俗要求進行分類。為了祈福辟邪的“有效性”,民畫的張貼位置基本上是約定俗成的。純粹的裝飾用畫基本以花鳥蟲魚為元素進行創作,象征著幸福美滿、夫妻恩愛;日月昆侖圖和一般的山水題材則象征著人們對自然的美好憧憬。在民俗的婚嫁儀式用畫中,牡丹圖和百子圖基本上是象征榮華富貴、多子多福;行樂圖和地宴圖張貼于喜慶熱鬧的婚禮上。在信仰滿足方面會張貼佛教圖、神像圖和俗信圖等,用來祭拜神靈。大眾祈愿和祝壽用的民畫, 每一年都固定貼在宮殿和高官的墻壁上。有祈求國泰民安的民畫,祈求十長生、虎圖、神仙圖和揚名韓國內外的魚龍變成圖, 還有祈求健康長壽的十長生圖, 祈求驅神、避邪、尋求安寧的圖以及十二支圖,虎、龍、龜、雞、鷹、太、鳳圖等。如果百姓家有崇尚學問之風,家中則可以使用書架圖和表示文房四寶的文房圖;還有勸善懲惡的表示倫理觀的孝涕圖和文字圖等, 都以教化為目的使用。大門上一般張貼高句驪名將乙支文德,其作用于中國年畫的門神相仿;民畫貼在窗戶上還可以擋風避雨。③
日本的大津繪功能和韓國民畫略有不同,除了裝飾用和祈福之用,在大津繪流行的年代京都附近的旅人會把大津繪作為土產帶到周邊地區以供留念或贈禮之用。學者柳宗悅認為,大津繪的“用之美”,不僅僅是欣賞之美,其具有的裝飾功能,更是一種獨到之美。④所以說用來裝飾民宅,是韓日民間繪畫的共同特點,大津繪主要裝飾的地方有佛壇、壁龕、墻壁和屏風。
大津繪在初期主要題材是佛教相關的內容,隨時時間的發展社會需求在不斷的變化,在各種的文化變遷中逐漸加入了更多的人物角色,題材也在不斷擴充。前期描繪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佛教神像,后來出現了神鬼、藤娘(歌舞伎)、武士和鳥獸為主要角色的題材,這些主要是為了滿足民眾對信仰的需求。在江戶時代的后期逐漸出現了特色的“護身符”大津繪,內容包括壽星、雷公、鷹匠等角色,每種角色都象征不同的寓意,這些角色在日本問政時期漸漸成為了大津繪的主要內容。在題材的高峰期大津繪出現了近百種不同的內容,但按類型劃分可以分為佛像畫、風俗畫、武者繪、美人畫、鳥獸畫等幾大類。在幕府統治末期,大津繪的題材基本定型,不再加入新的內容題材,但是民間的需求并沒有減少,但是藝術性和美術價值在不斷降低,直至消亡。
大津繪在18世紀之后,受到石天梅巖創立的石門心學的影響,開始對俗世間的奢侈和愚昧之風進行大量諷刺和批評,形式上以輕松幽默的風格對大眾進行說教,這對當時專制社會對民眾的壓制帶來的壓抑情緒起到了緩解作用。這樣的教化作用也是日韓民間繪畫的共同點之一。
三、繪畫特征對比
民間繪畫在韓日兩國的不同背景之下,各自發展出了獨特的繪畫特征,這些特征的物質基礎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兩種民間繪畫都是極為廉價的繪畫,都是用來滿足和豐富最底層百姓的精神世界的,他們的購買力非常薄弱,都是在物質生活極為窘迫的空隙中去追求內心的安寧,所以這些作品的制作者也只能通過大量的制作形成盈利,這就會極度壓低繪畫制作成本,所以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繪畫特征。
韓國民畫的造型特征可以用“詼諧”一詞去概括,在造型方法上和普通的韓國畫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基本流程也是先勾線造型在上色暈染,由于民畫的廉價性,所以在畫面的精致程度上沒有太大的講究,線條和用色的美不能按宮廷繪畫的審美標準去要求,反而凸顯出一種粗糙而樸質的民間自然之美。
在畫面空間上民畫并不講究透視關系,主要是采用傳統的國畫處理空間的辦法,比如在表現重點對象時會把比例放大,相對次要的角色會把比例縮小,做成主次關系;表現遠近時候可以通過元素的遮擋進行前后關系表達等,總體概括下來就是“上為遠下為近,后為遠前為近,小為遠大為近,疏為遠密為近。”如果都是近處的造型,則基本都是按正面直視的方法去描繪,整體畫面只是把元素羅列到一起,也就形成了畫面的多視點化。自由化的空間處理是民畫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少了其他繪畫的一些規矩,給民畫帶來了更加貼近自然的感覺。與大津繪的各種限制比較,民畫并不注重造型的簡潔性,反而會把很多的物品都組合到畫面上,沒有固定的章法,甚至會把不同的事物的元素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形象,不得不感嘆韓國民畫畫師的想象力的豐富和造型的果敢。
民畫的用色是基于傳統的陰陽五行理論進行傳承的,比如五色中青色(木)、紅色(火)屬陽,白色(金)、黑色(水)為陰,黃色(土)為中間色,這幾種色構成了民畫的基本用色,是與韓國古人信奉的宇宙哲學是相吻合的。⑤民畫中每種色彩都有寓意,青色象征著陽氣旺盛的東方,紅色代表草木茂密的溫暖的南方,白色代表日落的西方,黑色代表寒冷的北方,黃色則代表滋養萬物的大地。⑥這種用色理論基本與中國傳統繪畫一致,但與大津繪是有區別的。
從創作手法上來講,日本的大津繪造型手法簡潔、省略,但這并不代表粗略。這樣的造型手法是因為大津繪的繪制是非常講究效率的,畫師、工匠或者農民創作者利用閑暇時間進行制作,目的非常明確,需要盡可能短的時間滿足百姓對畫面質與量的需求,長久下來畫面上就舍棄了完全不必要的線條,留下的全部是幾代匠人沉淀下來的造型精華。柳宗悅就大津繪的省略手法發表了他的看法: “大津繪的省略不是粗略,呈現的只是精華; 不是畫下無用的外形,而是揭示虛無的存在。”⑦大津繪的空間表現手法和韓國民畫類似,基本上無視比例和明暗關系,造型也不是寫實手法,都注重寫意,對形象的刻畫都是集中在線條和用色上。
在用料上基本都是民間的尋常筆墨,常見的大津繪繪畫流程中是在繪制之時先涂一遍土黃顏色在紙上,再作勾線造型,后續的用色極為克制,主要以胡粉(白)、丹(朱紅)、粉綠、墨等礦物顏色為主色,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大津繪的畫面效果用墨非常精到,渲染畫面氣氛十分恰到好處,利用墨的干濕技巧和濃淡、輕重對比表現出高雅的視覺效果。
四、總結
整體看來,韓國民畫和日本的大津繪作為東方具有代表性的民間繪畫雖有共同之處,但也有各有千秋。兩者繁榮發展幾乎是同一個時代,都是封建專制的王權時代,底層人民生活在封建專制之下上流社會的奢華與他們毫無關系,民間繪畫成為他們豐富精神世界的為數不多的手段。
在功能上兩者都可以滿足底層人們的日常信仰活動和民間儀式活動。民畫基本上是韓國巫俗、佛教和儒教文化集合下的文化載體,除了承載了祈福作用之外還有教化之用,這一點上和大津繪功能也是基本一致,大津繪商品性更加突出,甚至有旅人作為純粹紀念品購買,大津繪后期則以可以隨身攜帶的“護身符”的方式持續發展了一段時間,也是一個特異之處。兩者的題材也基本上會是以宗教事物和山水蟲魚、美人、玩童等為繪畫元素為主,大津繪的鬼怪題材在韓國民畫之中是不常見的,同樣民畫之中自由組合、嫁接的富有想象力里的元素組合也是大津繪不具備的,整體上突出的詼諧的繪畫風格,自由靈動,大津繪注重傳承,很少出現傳統以外的繪畫事物。
在繪畫風格上,民畫崇尚自然,自由度高,內容豐富,畫面元素活潑,不拘泥于傳統,更像是底層人民思想的自由之地。大津繪注重簡潔明快,畫面除了必需之處毫無多余筆墨,簡潔有力,用筆純熟,很多時候是熟練工匠的無意識之作,所以其中韻味是工匠的沉淀之美,經驗之美,這是與民畫非常不同的。
通過對韓國民畫和日本大津繪的對比研究發現兩者的美,是基于各民族的性格和地域屬性的,韓國民族居住于半島與大陸緊密相連,深受傳統的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又不同于大陸文明的封建專制,很多時候保留了民眾的自由性,自然性,產生了詼諧之美。日本的大津繪是島國文明,更加封閉和壓抑,底層人民物質的匱乏,以及為盈利為目的的大津繪,把繪畫的簡略性降到了極致,不但可以降低筆墨成本,還能夠更有效率的大量復制,逐漸形成了簡約之美。大眾藝術是人民的藝術,對傳統民間繪畫來說勞動人民是藝術的需求者,也是創造者,研究傳統繪畫也是認知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希望本研究可以給后來者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
① (韓)李禹煥,《吏曹的民畫》[J],悅訴堂出版社,1977年,第17頁.
② (日)信多純一,祈り の 文化:大津繪模様.繪馬模様[M],京都市:思文閣,2009年7月,第33-37頁.
③? 李惠景,碩士論文《韓國朝鮮時代的民畫》[M],中央美術學院,2004年5月,第20頁.
④? (日) 柳宗悅: 《大津絵の価値》[J],的屋勝編: 《大津絵》,大津絵保存振興會1953年版,第 46-47 頁.
⑤ (韓)金鐘太,《東方畫論》[M],首爾一志社,1982年,第369頁.
⑥ (韓)任東權,《韓國民俗論稿》[M],首爾先明文化社,1973年,第87頁.
⑦ 歐陽秋子,《寫意性:中日傳統民間藝術共同的審美特征》[J],求索,2011年6月,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