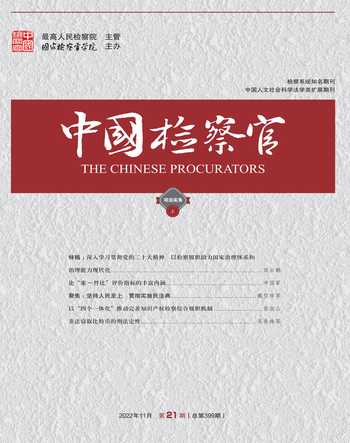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風(fēng)險的檢察應(yīng)對
李學(xué)東 何旭霞 周俊生
摘 要: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在適用中缺乏辯護權(quán)、對抗式訴訟模式等程序保障,可能出現(xiàn)公權(quán)力行使失當(dāng)、侵犯財產(chǎn)權(quán)、實體處理錯誤等風(fēng)險。司法機關(guān)主要通過參照適用普通刑事程序的訴權(quán)保障和嚴(yán)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來控制風(fēng)險,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與公正和效率價值平衡的要求不盡相符,需進一步完善,其關(guān)鍵是發(fā)揮檢察機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職能,突出審前階段利害關(guān)系人權(quán)利保障,以及完善提起介入機制,引導(dǎo)形成證明標(biāo)準(zhǔn)適用共識。
關(guān)鍵詞:司法風(fēng)險 訴權(quán)保障 證明標(biāo)準(zhǔn) 法律監(jiān)督
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以下簡稱“特別沒收程序”)是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重要法律手段,在創(chuàng)設(shè)時被寄予厚望,但并未廣泛適用。對此,實務(wù)部門和學(xué)界強調(diào)要擴大其適用范圍,但卻未深入研究制約其廣泛適用的實際原因。[1]實際上,特別沒收程序擴大適用的難點不僅是法律適用方法問題,更重要的是法官、檢察官在適用該程序時怎么做、怎么想的問題。因其擴大適用最終有賴于司法者積極主動作為,故筆者綜合運用座談?wù){(diào)研和判例分析的實證方法[2],探析司法者在特別沒收程序?qū)嵺`中的所行所思,研究破解制約其擴大適用的主客觀障礙,以期為推動程序適用提供指引。
一、特別沒收程序適用的潛在風(fēng)險
調(diào)研中,筆者發(fā)現(xiàn)司法機關(guān)對特別沒收程序風(fēng)險的防范和控制是貫穿其適用全過程的核心邏輯。這是因為當(dāng)事人的缺席連帶造成辯護權(quán)缺位、對抗式訴訟模式消解、公開審判限縮等問題,可能引發(fā)較大的司法風(fēng)險。
(一)公權(quán)力行使失當(dāng)?shù)娘L(fēng)險
一方面,適用特別沒收程序的案件,監(jiān)察、偵查機關(guān)負(fù)責(zé)在訴前階段的調(diào)查取證工作,檢察機關(guān)、當(dāng)事人缺乏參與其中、對取證活動進行監(jiān)督的程序機制,容易引發(fā)不規(guī)范取證、訴權(quán)保障不足等風(fēng)險。另一方面,由于對抗式訴訟模式的消解,控訴權(quán)的行使失去辯護權(quán)的制衡,既容易使檢察機關(guān)怠于行使訴訟監(jiān)督職能,也容易滋生不當(dāng)行使控訴權(quán)的問題。
(二)不當(dāng)侵犯財產(chǎn)權(quán)的風(fēng)險
特別沒收程序的核心是涉案財產(chǎn)的歸屬問題,在認(rèn)定犯罪事實的同時,往往牽涉民事法律關(guān)系,但刑事訴訟法對當(dāng)事人、利害關(guān)系人提供的程序保障,既低于普通刑事程序也低于民事訴訟程序。涉案財產(chǎn)的權(quán)利人面對國家機關(guān),在程序上僅有異議權(quán),難以形成實質(zhì)的平等對抗,導(dǎo)致涉案財產(chǎn)權(quán)被侵犯的風(fēng)險較普通刑事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大幅增加。
(三)實體處理錯誤的風(fēng)險
適用特別沒收程序案件的證據(jù)體系往往缺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多為“零口供”案件,本身證據(jù)審查和事實認(rèn)定的難度、不確定性就比較大,加之訴前取證活動缺乏當(dāng)事人、律師參與和有效的檢察監(jiān)督,其取證行為的規(guī)范性和可靠性弱于適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因而要達(dá)到排除合理懷疑的難度更大,偏離客觀真實的風(fēng)險更大。
二、特別沒收程序適用風(fēng)險的實踐應(yīng)對
調(diào)研中,可發(fā)現(xiàn)司法人員對以上風(fēng)險大多有清醒認(rèn)識,并有意識地通過參照適用普通刑事程序的程序保障機制來合理控制風(fēng)險。在操作層面,主要是通過強化利害關(guān)系人訴權(quán)保障和升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兩種方式來對沖風(fēng)險。
(一)強化利害關(guān)系人訴權(quán)保障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300條的規(guī)定,特別沒收程序中,涉案財產(chǎn)的利害關(guān)系人享有在法院公告過程中申請參與訴訟的權(quán)利,以及對違法所得提出異議和二審上訴等權(quán)利。“兩高”2017年《關(guān)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稱2017年《規(guī)定》),明確了法院向利害關(guān)系人送達(dá)的職責(zé)和利害關(guān)系人公告期滿的例外參與權(quán)——賦予了利害關(guān)系人更高規(guī)格的知情權(quán)和更完整的參與權(quán)。此外,法院在實踐中還會給予利害關(guān)系人更進一步的訴權(quán)保障。
在與法院座談?wù){(diào)研時,有法官提到,實踐中許多利害關(guān)系人不愿參加特別沒收程序,但法庭仍會敦促其積極參加,以免當(dāng)事人和公眾質(zhì)疑程序適用的公正性。從判例來看,法院積極敦促的傾向主要有兩種表現(xiàn):一是法院在立案受理后,主動詢問利害關(guān)系人是否參加訴訟,而不僅僅是通過法定的公告或者送達(dá)程序予以告知。如在王某某受賄申請沒收違法所得一案中,法院向被告人妻子直接送達(dá),征求其有無異議、是否參加庭審的意見。[3]二是法院強制利害關(guān)系人以訴訟參加人的身份參與訴訟。如在張某受賄申請沒收違法所得一案中,盡管被告人妻子對涉案財產(chǎn)沒收沒有任何異議,但法院仍傳喚其到庭參加訴訟。[4]
實踐中,有的法官在落實庭審實質(zhì)化上表現(xiàn)出一種比普通程序更加自覺主動的傾向,重視利害關(guān)系人參與權(quán)對追訴權(quán)的制衡作用和對實體公正的促進作用。檢察機關(guān)對加強利害關(guān)系人訴訟保障也持一種積極態(tài)度,2017年《規(guī)定》第12條明確將利害關(guān)系人相關(guān)情況作為沒收違法所得申請書的必備內(nèi)容。司法者對訴權(quán)保障的重視,主要是基于一種防范風(fēng)險的替代補償心理,意圖以此彌補特別沒收程序正當(dāng)性不足可能引發(fā)的司法風(fēng)險。如座談時有法官提到,之所以特別重視敦促利害關(guān)系人參加訴訟,主要是考慮特別沒收程序本質(zhì)上是一種未定罪沒收,相較于普通刑事審判程序而言,其財產(chǎn)沒收的決定并未建立在穩(wěn)固的定罪基礎(chǔ)之上,存在一定的司法風(fēng)險,故而對利害關(guān)系人的知情權(quán)和意見表達(dá)權(quán)等權(quán)利保障更加積極主動,有時甚至出現(xiàn)“過頭”的“強制”傾向。
(二)升格沒收違法所得案件證明標(biāo)準(zhǔn)
刑事訴訟法并未直接規(guī)定沒收違法所得案件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2017年《規(guī)定》第9、10條和第17條對犯罪事實的審查與對涉案財產(chǎn)性質(zhì)的審查分別規(guī)定適用“有證據(jù)證明”和“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這兩者的文字表述有所差異,但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都屬于“優(yōu)勢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范疇。[5]同時,審查涉案財產(chǎn)的性質(zhì)是審查認(rèn)定犯罪行為與涉案財產(chǎn)之間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性,屬于犯罪事實查明的一部分,因而應(yīng)將“具有高度可能性”理解為“有證據(jù)證明”的量化標(biāo)準(zhǔn),即只要達(dá)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就滿足“有證據(jù)證明”犯罪事實的要求。
2017年《規(guī)定》的證據(jù)標(biāo)準(zhǔn)并未被實踐完全接受。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特別沒收程序的庭審中,很多法官仍是按照普通刑事案件的審判流程進行,習(xí)慣于以“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嚴(yán)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來認(rèn)定沒收違法所得案件的事實,這導(dǎo)致對犯罪行為與涉案財產(chǎn)關(guān)聯(lián)性的審理間接適用了嚴(yán)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有法官提到,即便利害關(guān)系人或被害人未提出異議,但法院認(rèn)為案件的犯罪事實不清的,也會開庭審理,對案件的犯罪事實展開獨立調(diào)查,以確保達(dá)到嚴(yán)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如在潘某某貪污、受賄案中,法院在刑事裁定書中明確指出由于某一項受賄事實“無法形成證據(jù)鎖鏈”,故對該項受賄事實及違法所得不予認(rèn)定。[6]
升格沒收違法所得案件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傾向,也主要是受防范風(fēng)險的替代補償心理影響。如座談時有法官指出,雖然按照2017年《規(guī)定》,法庭無需按“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審查認(rèn)定犯罪事實,只需專注于審理違法所得是否應(yīng)當(dāng)沒收,但是在未查清犯罪事實的前提下進行違法所得沒收的處置,猶如“建房子沒有地基”,面臨較大的錯判風(fēng)險,故更傾向于選擇升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以求將沒收違法所得案件的錯判風(fēng)險控制在與普通刑事案件同一水平上。
三、特別沒收程序適用風(fēng)險應(yīng)對的完善建議
通過加強訴權(quán)保障和升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控制特別沒收程序的風(fēng)險,有利于實現(xiàn)實體公正,但同時也會加重特別沒收程序適用的司法成本,削弱其服務(wù)于追逃追贓的司法效益。立法者創(chuàng)設(shè)特別沒收程序,初衷是為解決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所造成的案件久拖不決、涉案違法所得遲遲無法追繳等問題,追求的是司法訴訟的效益價值。因此,應(yīng)從實現(xiàn)公正與效率平衡的價值目標(biāo)出發(fā),優(yōu)化訴權(quán)保障和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適用機制,以合理控制特別沒收程序的司法風(fēng)險,這其中的關(guān)鍵是發(fā)揮好檢察機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職能。
(一)完善審前階段利害關(guān)系人訴訟權(quán)利的保障體系
對抗式訴訟模式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有效機制。在當(dāng)事人缺席時,可以通過強化利害關(guān)系人訴權(quán)保障來構(gòu)建替代的對抗式訴訟模式,即賦予利害關(guān)系人“準(zhǔn)當(dāng)事人”或類似于民事被告人的訴訟地位,以此在特別沒收程序中“模擬”對抗式訴訟模式:檢控機關(guān)—利害關(guān)系人—審判機關(guān)。目前,司法實踐對利害關(guān)系人的訴權(quán)保障集中在審判階段,應(yīng)當(dāng)將此權(quán)利保障追溯至審前階段,即賦予利害關(guān)系人參與涉案違法所得的偵查、調(diào)查和審查起訴過程的權(quán)利,以完整“模擬”對抗式訴訟模式。這要求檢察機關(guān)嚴(yán)格落實人權(quán)保障職責(zé)要求:一是在訴前階段,要通過案件會商工作機制,敦促監(jiān)察、偵查機關(guān)在啟動程序時即查明涉案財產(chǎn)利害關(guān)系人情況、向其調(diào)取相關(guān)證言和告知相關(guān)情況。二是在審查起訴階段,要加強訴訟參與人權(quán)利保障情況的審查,必要時聽取利害關(guān)系人的意見,以嚴(yán)格保障其參與權(quán)、知情權(quán)乃至抗辯權(quán)等權(quán)利。
(二)健全合理適用沒收違法所得案件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工作機制
當(dāng)下司法實務(wù)部門對沒收違法所得案件事實的認(rèn)定采用嚴(yán)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混淆了特別沒收程序與普通刑事程序的性質(zhì):前者是對物之訴,后者是對人之訴。換言之,在特別沒收程序中,犯罪行為事實的認(rèn)定并不苛以當(dāng)事人刑事責(zé)任,而僅是作為沒收行為的事實條件,并且沒收行為不是刑罰,而是作為一種保安處分措施[7],不具有終局性效力,應(yīng)采用2017年《規(guī)定》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目前,我國刑事審判實踐存在適用嚴(yán)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慣性,檢察機關(guān)應(yīng)當(dāng)能動履職,進一步完善沒收違法所得案件的證據(jù)收集和訴訟監(jiān)督機制:一是在審前階段,要通過提前介入機制,引導(dǎo)監(jiān)察、偵查機關(guān)按照普通刑事程序的嚴(yán)格證明標(biāo)準(zhǔn)來調(diào)取證據(jù),盡最大努力實現(xiàn)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舉證責(zé)任,排除錯案風(fēng)險。二是在審判階段,要通過庭前會議機制加強與法院溝通,理性客觀看待沒收違法所得案件證據(jù)情況,推動法檢共同按照2017年《規(guī)定》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審查認(rèn)定沒收違法所得案件事實,避免對案件證據(jù)再作過高要求,以進一步提高特別沒收程序訴訟效率,更好發(fā)揮其反腐敗追逃追贓的制度效能。
*本文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2020年度檢察理論研究課題“職務(wù)犯罪案件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GDJC202012)階段性成果。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長、二級高級檢察官[510623]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三級高級檢察官[510623]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一級檢察官助理[510623]
[1] 參見韓曉峰等:《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證據(jù)審查相關(guān)問題探討——以涉外追逃追贓案件為視角》,《人民檢察》2022年第5期。
[2] 本文調(diào)研座談范圍為廣州地區(qū)監(jiān)察、偵查機關(guān)、檢察機關(guān)和審判機關(guān)的辦案人員,并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收集2018至2021年期間全國各地公開的適用特別沒收程序的案件26件作為分析樣本。
[3] 參見河北省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19)冀09刑沒初1號。
[4] 參見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20)云01刑沒1號。
[5] 參見裴顯鼎等:《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重點疑難問題解讀》,《法律適用》2017年第13期。
[6] 參見陜西省商洛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18)陜10刑沒1號。
[7] 參見朱孝清:《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幾個問題》,《人民檢察》2014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