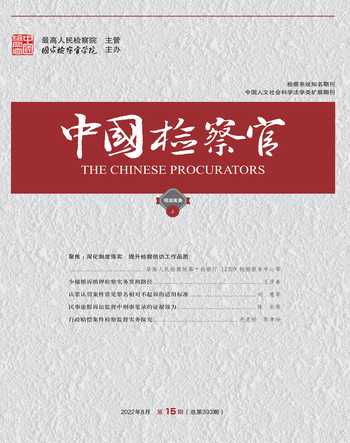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再審視
甘肅省人民檢察院蘭州鐵路運輸分院課題組
摘 要: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責任體系尚在探索階段。從實踐樣態來看,該領域還存在著模式選擇難以自洽,所受損失、支付價款與銷售金額之間轉化機制缺失,不同性質處罰之間抵扣、減免混亂,懲罰性賠償金的管理使用不盡合理等問題。為妥善解決當前實踐面臨的困境,應當重置以銷售金額為計算基數的標準,合理確定彈性倍數,構建以客觀因素為導向的減免事由。
關鍵詞:食品安全 民事公益訴訟 懲罰性賠償
一、現行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確定模式
(一)“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確定模式
民法典第1207條規定了“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計算模式,并對其適用要件進行了嚴格限定,只有當滿足“明知”為缺陷產品或者未采取補救措施,且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權嚴重損害的重大后果時才能適用該條文。但由于“相應的”計算標準賦予了司法人員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限,在實踐中很難把握合理限度。雖然其在條文構成上是法律規則的范式,然而與其他懲罰性賠償金計算模式相比則更多的起到一種宣示作用,實際發揮著法律原則的功效,適用比例較低。在計算時尚需結合“計算基數”與“計算倍數”兩方面的內容才能確定賠償數額,因此在相關單行法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只能優先適用單行法的規定。
(二)“二倍及以下”懲罰性賠償確定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第2款規定了“二倍及以下”的懲罰性賠償計算模式,要求經營者在主觀上為明知故意,且具有造成他人健康嚴重損害或致人死亡的后果。雖然該計算模式與民法典第1207條在主觀要件與結果要件上具有一致性,但規制主體卻不同,前者只規制經營者的銷售行為,后者在此基礎上還規制生產者的生產行為。此外,“二倍及以下”計算模式可同時主張“損失賠償+懲罰性賠償”,并對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行為可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即在計算懲罰性賠償金額時以實際損失與精神損害賠償為依據。
(三)“三倍”懲罰性賠償確定模式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第1款與《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皆規定了三倍的懲罰性賠償金計算模式,但前者要求經營者需具有“欺詐”行為,且在計算時以消費者“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價款作為計算基數,最低賠償金額為500元;后者則只需生產者或經營者具有主觀故意即可,計算基數以消費者所受損失為準,最低賠償金額為1000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第1款只規制經營者的經營行為,《食品安全法》第148條卻既規制生產者,也規制經營者。據此,相較于后者主觀故意明知的狀態,顯然前者欺詐的證明標準更高,但其最低懲罰性賠償金額卻明顯回落。該兩者之間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
(四)“十倍”懲罰性賠償確定模式
《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規定了支付價款十倍的懲罰性賠償計算模式,其在構成要件與最低賠償金額上與該條文中三倍懲罰性賠償保持一致,但在確定計算基數時卻是以“支付價款”為準,而非“所受損失”。該模式是目前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中確定懲罰性賠償最常采用的標準。
二、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確定模式選擇
如何妥善處理現行法律體系下不同懲罰性賠償確定模式之間的關系,有學者提出應依據“請求權自由競合說”自擇其一,[1]也有學者主張最好借鑒刑法中“想象競合犯”理論按賠償最多的一個論處。[2]但是根據法律沖突時的解決規則,一是“新法優于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最后一次修訂是在2013年,而《食品安全法》則在2018年,且兩者處于同一法律位階,所以在內容上發生沖突時應當以新法為準。二是“特別法優于一般法”。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其調整對象為“商品或者服務”,而《食品安全法》第2條卻規定其調整對象為“食品生產、儲存、運輸、經營、安全管理”,顯然此處的食品只能是商品的一個組成部分。之所以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中確定懲罰性賠償時優先適用特別法,是因為其充分考慮了食品生產及銷售的特殊環節,精準性更高、針對性更強。據此,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中主張懲罰性賠償時應當優先適用《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的規定。
此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所規定的三倍或兩倍以下計算模式的規制主體為“經營者”,并不包括生產者。雖然從實踐中來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的違法主體大多呈現出“生產經營一體化”的特征,但兩者相分離的情形也大量存在。此時如果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的規定來對經營者作出懲罰,而追究生產者的責任時卻適用《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的規定,顯然有違公平原則。也有觀點主張生產者的社會危害性遠勝于銷售者,所以對其予以十倍的懲罰性賠償,而經營者給予三倍的懲罰性賠償符合常理。但《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為該類情形預留了自由裁量的空間,其在制度設計上采取選擇性的立法模式,可供辦案人員根據具體情形在“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之間進行選擇,由此避免了根據社會危害性強弱對生產者與銷售者施以懲罰性賠償時依據不同條款所致使的窘境。
在選取《食品安全法》第148條作為計算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數額的依據時,應當對該條款中的“所受損失”做擴大解釋,既包括身體、健康權損失,也包括金錢利益損失。在實踐操作中還需妥善處理好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價款與所受損失之間的銜接轉化,在身體、健康權未受到損害或者損害結果輕微,可以忽略不計時,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款”與“所受損失”之間具有等價性。但是由于消費者的不特定性,往往很難精確確定具體的人數,所以需要精準化實現“銷售金額”與“所受損失”的對比及轉化。一般情況下,生產者的出售金額或者銷售者的銷售金額與消費者購買商品時所支付的費用具有一致性,但在部分案件中,兩者之間卻會出現一定的差異。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時會扣押尚未銷售的食品,該部分是否應當納入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實踐中存在不同的操作方法,但是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48條所規定的計算基數,其顯然屬于尚未銷售的食品,并未對消費者的身體及健康造成損害,也未對其金錢利益有絲毫影響,所以在計算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數時將被扣押食品納入其中違背了立法本意。
三、《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的適用困境
(一)“損失三倍”與“銷售金額三倍”的轉化
司法實踐中,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的前提是經營者的行為滿足民法典第148條與第149條所確定的“欺詐”要件,即:欺騙者具有雙重故意;欺騙與陷入錯誤、錯誤與意思表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欺騙行為具有不當性。目前利用三倍模式確定懲罰性賠償金一般都是在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單純的民事公益訴訟中采用該模式的情形較為少見。且絕大多數都是利用“銷售額”作為計算基數,這在一定程度可有效避免根據消費者“支付價款”或者“所受損失”確定懲罰性賠償金時不能窮盡受害人的情形。但在重慶市長壽區人民檢察院訴張可俊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3]中,檢察機關卻要求以“不特定眾多消費者所受損失”作為計算三倍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根據該案證據顯示,其中134盒保健食品可以確定具體的購買者,其他97盒難以確定其人。既然消費者具有不特定性,那么以其所受損失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計算基數至少在解釋邏輯上存在一定的障礙。
然而,利用銷售金額作為計算基數在認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難。一是調查取證難。大部分的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違法主體為“小商販”,其并無規范的收支流水記錄,很難精確確定銷售金額。一方面檢察機關只能通過被告人供述,另一方面以違法行為人的原材料購買記錄,并輔之以“通常工藝水平”所能生產的成品市場價來確定。但被告人供述在審判階段容易翻供,人民法院此時基于有利于被告人原則的考慮,往往會根據庭審過程中被告人供述直接確定銷售金額。二是食品生產、流通的多階段性決定了其銷售金額的可變性。實踐中一般以最后的銷售環節作為確定計算基數的標準,但也存在以生產或流通等環節的銷售額為標準的計算方式。三是多層級銷售前提下銷售金額認定的差異化。食品銷售環節往往存在多個層級的經銷商,此時在確定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數時是以一級經銷商還是最后一級經銷商的價款作為標準存在不同的處理方式。實踐中一般以最后一級經銷商即消費者支付價款作為計算基數,但也存在以生產者出售給一級經銷商時的價款作為計算基數,兼具考量多層級銷售時差異化規則前提下侵權人的權益保護,最終以最低銷售金額作為計算基數的處理方式。
(二)“支付價款十倍”與“銷售金額十倍”的轉化
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中主張十倍懲罰性賠償的情形實踐中較為常見。但是在確定計算基數時是根據銷售金額還是支付價款存在差異化處理方式,這種差異化的原因主要在于能否精確確定消費者人數。現行法律規定十倍懲罰性賠償金確立基數的“支付價款”模式是立足于私益訴訟的獨有特征,是以消費者作為賠償權利人而做出的制度設計,并未考慮檢察機關或者社會組織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樣式。在大部分案件中,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涉及的消費者為不特定的多數人,以支付價款作為懲罰性賠償金的計算基數較為困難。且存在立法解釋論與司法實踐之間的悖論,因此仍需在相關法律文書及釋法說理過程中做好支付價款與銷售金額之間的轉化。
(三)不同性質處罰之間的抵扣及減免
關于懲罰性賠償金與刑事罰金、行政罰款之間的關系,實踐中存在“共存論”與“扣減論”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人民檢察院訴羅某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案[4]中,人民法院認為刑事、行政、民事責任雖然在性質上有公私之分,但都歸屬于金錢罰,可以并存適用,并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應當參照行政罰款與刑事罰金的處理方式,在實踐中將懲罰性賠償金與刑事罰金進行抵扣。但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司法機關都將刑事罰金與懲罰性賠償金并存適用,并未進行抵扣。
四、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的完善路徑
(一)重置以銷售金額為主的計算基數
現行法律以“支付價款”與“所受損失”作為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金額的計算基數,是立足于消費者自身尋求權利救濟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并未考慮到公益訴訟損害后果擴散性的特殊屬性。雖然以銷售金額作為懲罰性賠償金額計算基數在調查取證、精準計算等方面尚存有一定的困難,但其在邏輯的自洽性、實踐的操作性上更具優勢。首先,將銷售金額作為懲罰性賠償金的計算基數,能夠充分發揮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的懲戒與威懾功能。通過增加違法成本的方式,在去除其獲利成本的同時威懾相似的潛在違法行為,從而彰顯懲罰性賠償的制度價值。其次,相較于支付價款與所受損失,銷售金額相對明確且容易操作。由于公益訴訟受害主體的不特定性,致使檢察機關或社會主體在確定懲罰性賠償金額時很難通過精準確定消費者數量的方式來確定其購買食品的金額及所受到的損失。且對于日常生活所需之食品,也鮮有消費者會索取票據或者留存相關證據。而此時生產者或銷售者的銷售金額已經相對固定,可以通過生產記錄、銷售憑據,稅務發票、供銷名單等進行論證、計算。[5]最后,銷售金額不同于不法利潤總額。也有學者主張參考《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條的規定以不法利潤總額作為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6]經濟學上關于利潤的定義是收入扣除成本價格和稅金的余額,如果單純以不法利潤總額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計算基數,生產者或消費者的違法成本則大幅下降,顯然難以實現重磅懲罰、威懾與警示之目的。
(二)合理確定彈性倍數
實踐中主張十倍懲罰性賠償金模式的情形最為常見,但也不乏存在一倍、二倍、三倍、五倍的情形。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中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確定既要實現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之目的,又要對違法行為人起到一種懲戒及警示作用。但是目前普遍存在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略低,作用未充分彰顯等現象。
在確定最低懲罰性賠償金額時,也突破了現行法律規定,譬如:在河北省阜平縣人民檢察院訴武某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案[7]中,檢察機關主張生產、銷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油條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共計人民幣500元,卻忽略了該條文模式下“賠償金額不足一千元為一千元”的強制性規定。在適用《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時絕大多數情形下只要求生產者或銷售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卻未主張賠償損失,顯然降低了違法行為人的違法成本。從該條文的表述來看,賠償損失為強行性規定,而懲罰性賠償為選擇性規定,顯然在主張后者的同時應當要求違法行為人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