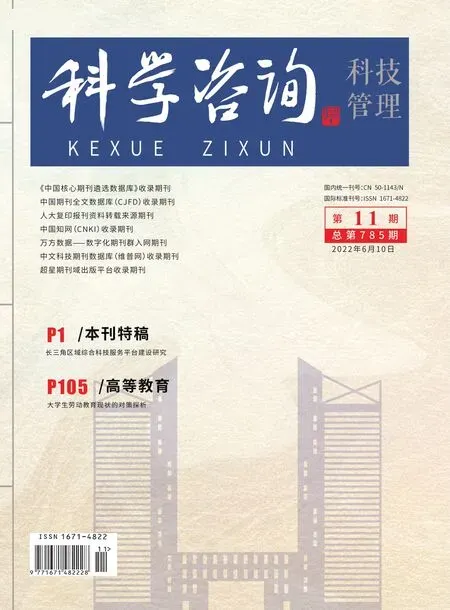結構式團體心理輔導提升女大學生自我客體化研究報告
劉海英,陳天剛,劉菲
(1.安徽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馬鞍山 243032;2.安徽省馬鞍山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安徽馬鞍山 243000)
一、研究背景
在性客體化環境中,女性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外表會被他人作為主要觀察和評估的對象,她們會內化一種第三者的視角,將自己當做基于外表被觀看和評價的物體來看待,Fredrickson和Robert把這一過程稱為自我客體化[1]。性客體化通常是指女性的身體部位或者性功能脫離本人,淪為純粹的工具或者被視為能夠代表女性個體本身[2]。研究表明,在性客體化環境中,女性會體驗到一種社會性焦慮,長時間的社會焦慮會導致抑郁情緒[3];自我客體化用第三者視角關注自己的身體屬性,想到的是“我看起來怎么樣?”,而不是從第一人稱的角度關注自身內在屬性,想著“我能怎么樣”或“我感覺怎么樣?”。這些思想認識容易形成女性對身體外在形象的習慣性監控。持續的自我身體監控,會引起外貌和身體安全焦慮,減少心流體驗,內部知覺遲鈍,身體羞恥等,心理學家米哈里齊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把一種將個人精力完全投注在某種具有挑戰性的活動上的感覺定義為心流體驗,心流產生同時會有高度的興奮及充實感[4]。自我客體化水平高帶來的消極體驗的積累,對女性的心理造成不利影響,進而容易引起進食障礙、抑郁、性功能障礙等心理問題[5]。自我客體化程度較高的個體可能有較低的心理安全感和較高的外表焦慮水平[6]。
可見自我客體化源自文化環境影響,產生對自我的片面思想認識,或者不合理的認知,帶來一系列的心身健康問題。筆者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女大學生自我客體化水平得分偏高人數,占總調查人數比例約為19%[7],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比例,對于這部分女大學生應給予積極的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輔導訓練。
健康心理知識教育幫助女大學生提高正確的思想認識,運動可以改善理想身體意向對女性吸引力的消極影響[8],關注身體的感受,會幫助個體注意內部知覺,增強心流體驗,從而增強女大學生從第一人稱的角度關注自身內在屬性。本次團體運動體驗內容選擇的是心理咨詢中的正念心理療法和舞動心理療法的相關練習,正念(mindfulness)指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覺察,有意識地不作判斷地覺察當下每一刻的經驗,是1979年美國卡巴金博士(Jon Kabat-Zinn,Ph.D.)于麻省大學醫學院所,結合東方禪修與西方醫學、心理學研究所創。正念練習包括正念呼吸、正念瑜伽、正念走路、正念禁語等,能夠幫助人提高內部覺察能力。舞動是一種舞蹈運動療法(DMT),是借由舞蹈和動作進一步到對情緒、認知、生理和個人的社會化整合的治療性應用。融合了TA(交互溝通分析)和Passo(派索的戲劇治療)于一體,是一種易被人接受的快速而有效的方式來探索和體驗人的內心世界,恢復心理能量的方式。親密舞動練習,幫助人覺察到自己的能力,通過非語言溝通模式和身體語言與自己建立連接,深度地理解和自我覺知,并建立與他人的連接,使人際關系更加令人滿意并富有意義,與他人的相處更有效率。
因此,我們在做針對降低女大學生自我客體化水平的教育工作中,注重實行雙管齊下,既要幫助女大學生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建議她們更多關注提升自我內在素質的內容,對強調女性外表特征價值的內容保持敏感,又要指導女大學生參與增強心流體驗的訓練活動,提高她們身體內部感知覺,使她們能夠感受到內在體驗對自我成長的價值重要性,讓她們把對身體外表的過度關注調節到適當水平,平衡對身體內外的照顧,尊重并接受自己的身體。
二、方法
(一)研究對象
通過志愿報名選取藝術設計學院12名女大學生,后脫落3人,9人完成團體活動,團體成員平均年齡20歲,最小18歲,最大21歲,大學二年級學生,其中7人為獨生子女,2人為獨生子女,6人來自城市,3人來自農村。
(二)團體過程
采用自編的女大學生自我成長心理健康教育知識手冊對團體成員進行知識教育,運用心理咨詢中合理情緒、正念和親密人際舞動等方法進行團體活動訓練。每次團體活動包括:教育知識學習約20分鐘,親密人際舞動練習約20分鐘,跟隨帶領者進行正念練習約40分鐘,提問和分享感受約30分鐘,最后一次是一整天7個小時的正念止語練習。共九次團體心理輔導活動,每周一次,歷時三個月,團體活動時長共計約24小時。
(三)研究工具
自我客體化量表(SOQ),采用由Fredrickson和Robert(1998)編制,趙方翻譯和修訂的自我客體化量表[9]。該量表包括5個與身體能力相關的項目和5個與身體外表相關的項目,共10道題目。要求被試對10個項目進行排序,最后用身體外表相關項目的得分總數減去身體能力相關項目得分總數,總分在-25到25之間,分數越高說明自我客體化水平越高。本研究所采用的自我客體化量表具有良好的區分度,校標效度為0.476,重測信度為0.82,具有較好的信效度。
(四)統計分析
采用SPSS20.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三、結果
(一)自我客體化前后測結果

表1 實驗組自我客體化團輔前后測數據分析
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女大學生自我客體化在前測組和后測組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t=2.299,p<0.05)。
(二)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
本次團體結束三個月后邀請團體成員集中進行了一次不記名的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成員對團體活動印象深刻,對團體的滿意度平均分在8分以上(總分10分),團體成員認為在團體中有所收獲。

表2
團體成員給本次團體活動滿意度評分時,三位成員給出了滿分10分,一位成員給出9分,三位成員給出8分,兩位成員給出7分的滿意度。當問“您認為有必要在女性中推廣這樣的團體嗎?”團體成員的回答都是認為有必要。問“如果再有類似團體體驗訓練,是否愿意再參加?”,7位成員表示愿意,兩位表示看情況。
四、討論
(一)結構式團體心理輔導可以提升女大學生的自我客體化水平
本次團體輔導根據提高女大學生對性客體化環境的合理認知,增強心流體驗,提高女大學生對身體的內部感知覺,促進女大學生現實交往能力提高為目標需要,在結合結構式團體心理咨詢方法的基礎上,對團體輔導形式和內容進行適當創新,把心理教育知識和主觀評估帶入結構性團體,靈活運用相關思想教育和心理治療方法,安排易于女大學生接受的訓練活動,根據量表測試結果和開放式問卷回答內容以及成員感受化的表達,表明團體取得較好的輔導效果[10]。健康心理知識教育幫助女大學生提高正確的思想認識,運動可以改善理想身體意向對女性吸引力的消極影響[8],關注身體的感受,會幫助個體注意內部知覺,增強心流體驗,從而增強女大學生從第一人稱的角度關注自身內在屬性。
本次團體研究主要通過前后測和三個月后回訪成員自我陳述,來進行結果評估,基本達到預期效果。同時,因為團體成員主要來自設計專業,對繪畫有一定的基礎,研究者增加了繪畫探索環節,在團體開始時征求成員同意,在每次團體活動結束后自愿用繪畫表達自己的感受,從成員提供的畫作發現最初畫作中規中矩表達想法偏多,后期畫作較多自由運用色彩表達內部感受。也可以主觀表明團體在幫助成員提高身體內部知覺和幫助成員解放認知束縛改善身心關系有效果。這些相對主觀的評估結果,也許不能作為嚴謹科學研究結果,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這些主觀效果的存在。
(二)結構式團體心理輔導中需要改進的地方
一是心理知識教育內容還需要更好地融合在團體訓練中。通過本次團體我們把女性心理知識教育納入團體內容之中,這個環節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對活動訓練,團體中成員對純文字知識的學習興趣不大,結合到活動中能夠讓成員更理解知識的含義,同時也更懂得運用知識提升自我。二是團體的分享環節需要加強。團體體驗訓練活動安排較多,成員很喜歡,但分享時間短,使體驗活動由感性到理性認識集體獲得有限,有些局限在個人體悟層面,團體結束后容易失去一部分感性經驗上升到理性認識的機會。三是增加了一次一整天的正念禁語練習,需要在時間和設置上進行適當調整。在團體成員的希望下增加了最后一次整天訓練,成員對練習投入很認真,因為是最后一次,活動安排在參加的學生成員放假回家的前一天,也沒來得及進行感悟分享,使本次非常有意義的體驗訓練教育體現有限。
(三)結構式團體心理輔導帶領者的影響
本次研究筆者作為結構式團體輔導的帶領者,同時也是學校老師,和參加團體的女大學生輔導員熟悉,既是帶領者和成員之間關系,也是老師和學生關系,這種雙重關系可能會影響參加團體的女大學生迎合老師的心理。作為女性團體帶領者,在進行團體正念練習的活動時,沒有自己現場說引導語,而是播放練習的音頻,而音頻中引導語是男性聲音,對于提升女性自我客體化水平的團體輔導,女性帶領者沒有在引導上體現,在對女性大學生團體成員的自我體驗上可能存在一定影響,需要更多研究探索驗證。
五、結束語
1.參加本次結構式團體輔導的女大學生的自我客體化水平前后差異顯著;
2.參加的女大學生團體成員在開放式問卷回答中,對本次團體輔導滿意度評分較高;
3.本次結構式團體心理輔導對女大學生在感受性和自由度上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