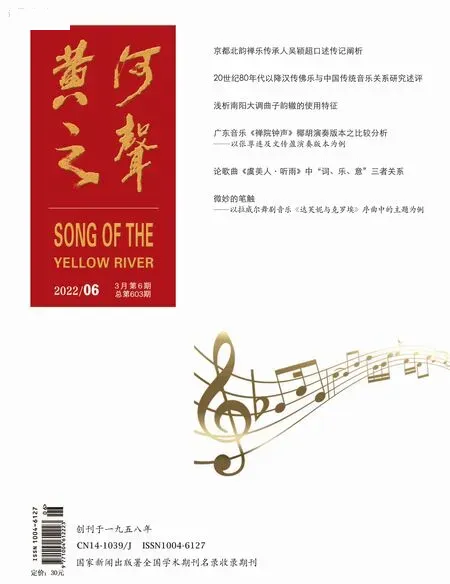微妙的筆觸
——以拉威爾舞劇音樂《達芙妮與克羅埃》序曲中的主題為例
崔登航
引 言
美術創作,不論素描、水彩或是油畫、國畫,“筆觸”都是鑒賞、觀察這類藝術作品的途徑之一,或許畫家在創作過程中并沒有刻意注意筆觸的形成,又或許“筆觸”已然成為了一種個人習得,總之“筆觸”在畫面中是客觀存在的、可被細致觀察的現實,進而在對不同歷史時期的美術作品進行分析研判中,美術學家會自覺關注“原作”的“筆觸”,從而對畫家所處社會環境、風格特征進行分析。對于藝術作品而言,其間的共通性不言而喻,也就是說不同的藝術門類之間自然存在一定的共同點,但也由于兩者的差異,會自然形成特殊的個性。音樂與美術之間的“鴻溝”在于一為具象,一為抽象,就像在談及“日出”的形象時,腦海中自然想到的是莫奈筆下的《日出》而非美國作曲家格羅菲筆下的《大峽谷組曲》第一樂章,同為“日出”,莫奈的《日出》,用細膩微妙的色差詮釋了實景投射到視網膜上的過程以及色彩的更替,格羅菲筆下的“日出”則更為傾向于體現太陽自東方升起的明暗對比。從這個簡單的例證中即可得知,畫家所關注的“筆觸”更為客觀,有一定的具體形象作為參照,甚至可以通過畫面的構成析出畫家所用畫筆的質地與型號,而對于音樂作品中“筆觸”的研究,則需具有更為形象性的色彩,依托樂譜與音響文本,構建較為立體的“音樂圖景”,是為兩者之間的共通。本文擬借助美術學對于“筆觸”的研究,以印象主義作曲家拉威爾筆下的舞劇音樂《達芙妮與克羅埃》序曲中四個主題的構建作為例證,探究這部音樂作品主題創作中的“筆觸”以及建構于古希臘文學藝術思維中“原欲”和“敬獻”之合。
一、對線條的勾勒
在對美術作品的鑒賞與觀察中,線條是最為基本的要素,所謂“線條”可以泛指藝術品外形輪廓的構成,包含曲線、直線、折線、粗線、細線、實線、虛線等等形態;音樂作品中的“線條”可以泛指旋律,亦為對音樂作品進行分析時必要的參考。對線條的勾勒,是畫家與作曲家創作藝術作品時必須經歷的過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賽諾斯曾斷言,音階必須總是遵循著‘旋律的性質’(the nature of melos)”①,即便是進入20世紀,對音樂作品中線條的勾勒雖不一定是創作過程的必須,但因旋律創作而生的線條勾勒過程,仍然是分析研判音樂作品的途徑之一。拉威爾筆下的《達芙妮與克羅埃》序曲,飽含對古希臘神話中阿波羅、達芙妮、丘比特、克羅埃的崇敬,并保持著一份“敬獻”的態度,因而在對“序曲”中多個線條的勾勒過程中,作曲家沒有使用任何一種源于十二平均律的大小調式,而是自覺選擇了源于古希臘的“自然調式”作為載體;即便如此,在拉威爾的筆下,仍然飄逸出符合古希臘時期審美意向的、優美綿長的線條。
《達芙妮與克羅埃》序曲中,包含四個相互關聯的主題,其所勾勒的形象包含“敬獻”、“克羅埃”、“達芙妮”與“愛欲”。這種對于形象的理解是抽象的,或許在作曲家本人的理解中,序曲中所出現的形象并非如此,但存在于其中的主題之間形成某種關聯,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對于古希臘時期音樂藝術發展歷程的回望——關于音樂、數字、諧音、四音列及各式各樣的自然音階。當然也有腦海中閃現地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及人,如同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曾說“人是萬物的尺度”②。

例1 舞劇《達芙妮與克羅埃》序曲中的四個主題
就上述呈現的主題而言,其所同時具備的核心材料源自“敬獻”主題中的縱向四度音程,另外三個主題均以此音程作為基礎派生而來,只不過除“敬獻”主題之外,其他三者均以橫向音高橫向運行為基礎,并可依據主題線條、音色、形態對其所表現的藝術形象進行解讀。
(一)關于“達芙妮”主題
這一主題出現于第5小節(排練號:1),由一支長笛演奏;由于長笛音色的圓滑及其氣柱的生成,使這一主題在具體形象上描繪了“初醒的達芙妮”;主題起始的兩小節,由#D引出的由慢至快再慢的音高與節奏的并行發展,使“初醒”時的呼吸得以凸顯,并在第二小節E音及其下行進入B音的過程,達成了一體化的深呼吸過程,同時也體現出深呼吸過程中由吸到呼的緊張度提升與緩解。如果說起始兩小節為呼吸,那么后續的四小節則為身體的蘇醒,就其線條運行而言,身體線條的變化成為了這四小節的核心要素。第3、4小節中包含兩個變化重復的過程,出現了含有十六分音符連綴與三連音連綴的兩個由同樣音高組織構成的片段,并在第6小節達到“起身”之象。起身的過程同樣伴隨著呼吸,由于第1、2小節對“呼吸”的詮釋,使第3、4小節對“起身”過程以及身體曲線的描繪更為細膩;從主題外形以及有關古希臘神話的描述中可以獲知,作曲家拉威爾筆下的“達芙妮”是身體曲線極具美感的月桂女神。
(二)關于“克羅埃”主題
“克羅埃”是舞劇文學劇本中虛擬出的男性形象;“克羅埃”實為“克羅埃地亞”,也就是克羅地亞的前身,其人種為南斯拉夫人的一個支脈。在古老的古希臘神話中,月桂女神達芙妮與太陽神阿波羅以及愛神丘比特之間存在著諷刺、愛慕、嫉妒等矛盾沖突,但在對于神話的描述中并無“克羅埃”之名,因而舞劇中的形象是虛構的。既為男性,凸顯陽剛之氣成為這一主題的特質。作曲家選用有著金屬音色的圓號為主奏樂器;圓號通常在管弦樂隊中擔任著中和弦樂組與木管組音色的作用,在此使用圓號之意除了描繪男性形象之外,亦有中和音色之用。
從這一主題的外形來說,唯有第1、2小節分別下行與上行的五度音程具有“克羅埃”形象的指征,在這 兩小節之中的其他成分則來源于“達芙妮”主題。

例2 “克羅埃”主題與“達芙妮”主題的類似成分
從上例中可以發覺作曲家微妙而細致的安排,舞劇中的“克羅埃”追求著女神“達芙妮”,追求本身即帶有“心”的感應,這是一種單純而美好的愛意,雖然在兩神相愛的過程中,或許會有很多不確定要素的存在,但彼此相知相愛、情投意合地感覺,需要通過旋律要素之間的呼應關系予以獲得,方可尋得在上例中所見——“你中有我”。
在對古希臘文學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神-原欲-人”三位一體的結構框架構建了古希臘文學的特質,這種特質體現了一種由“神”轉化為“人”的人本意識;既為人,即擁有著七情六欲等凡間之“品”,進而在描繪“神”的過程中,為了讓神性與人性得以吻合。作曲家的任務是在主題要素的塑造與展開過程中,將這種具有修辭意義的旋律進行分別應用于不同的形象塑造過程中。在“達芙妮”主題中,這一要素的主旨是為了體現“達芙妮”身體曲線的優美,而在“克羅埃”主題中,則應當是為了體現“克羅埃”對“達芙妮”的愛與念。
(三)關于“愛欲”主題
因愛生欲,這大概是古往今來的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中慣常涉及的命題,如表現主義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在《春之祭》中的“原始之欲”,古希臘遺存至今的裸身雕塑以及比才《卡門》中的“野性之欲”,無不體現出“欲”作為對藝術形象的描繪過程中,廣泛涉獵的內心反應。
就此曲中的“愛欲”主題而言,通過音高的橫向進行來描繪“愛”與“欲”的表征及狀態,是在主題的構建過程中需要著重考量的問題。既然是描寫“男歡女愛”,又是一種建構于古希臘美學之下的關乎“原欲-神-人”結合之“欲”,在其主題內部,實則產生的一種包容呼吸、身體、動作與人物之間的交合之美。

例3 “愛欲”主題中多個要素的綜合
上述譜例所含內容,分別源自“達芙妮”主題與“克羅埃”主題,雖然某些音高進行更改了原本的音序,但基本保持了原主題片段的特征。在這一飽含“愛欲”之情的旋律進行中,一方面保留“人物”類主題的要素,一方面增加級進式的音高進行,促使兩者“惺惺相惜”,目的在于詮釋“達芙妮”與“克羅埃”在一個時空之中的耦合,這種耦合包含著“呼吸”、“擁吻”與“愛撫”。
二、“敬獻”與“原欲”之合
通過上文的講述,可以發現不論劇中的男主角還是女主角以及他們的“交合”,都離不開“敬獻”;“敬獻”與“原欲”之間的關系,通過音樂作品本體,似乎無法實現結合,但對于“神”的“原欲”而言,古希臘文學仍然以“人”為其文明的出發點和對象;在古希臘神話中,則將“神”的秉性貼合到“人”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思想環境以及有關哲學的討論中,特別是顯現于古希臘神話中的“神”與“人”具有同樣的情欲,甚至連肉身也可相通。“神”的思想行為皆與“人”貫通,因此“人”所具有的一切能力“神”都擁有,又因“神”的能力往往高于“人”,因而對于“神”的描繪更為夸張,這就像“藝術來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一般。在關于此曲的分析中,筆者認為“敬獻”與“原欲”一為心理狀態,一為人神之本能,在一部舞劇序曲中即達成了交合。
(一)由“敬獻”主題而派生出的其他主題
此曲中的“敬獻”主題由混聲合唱團演唱,首次出現位于第8-10小節,但這一主題最早的雛形出現于全曲第6-7小節,由圓號演奏。從這一主題的外形來看,使用橫向二度與縱向七度音程所構建的主題雛形,可以視為對“達芙妮”“夢中初醒”的提示,同時也是對“敬獻”的初次呈現。
對于真正意義上的“敬獻”主題而言,所包含的要素可以總結橫向二度與縱向純四度的結合,與其“雛形”的進行方式相同,均以兩拍為一個單位原樣重復,進而停滯下來。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敬獻”主題除了作為一種樣態存在于音樂之中以外,還成為了全曲其他主題生成的基本資源。
以“敬獻”主題為基礎,另外三個主題中的進行要素均源于這一主題,而對于“敬獻”主題自身而言,除作為全曲主題性要素的資源庫之外,其自身也蘊含著存在于古希臘文學藝術之中的理性精神,這一點與上文所述“原欲”達成了統一。
(二)“原欲”與“敬獻”中的神性與人性
“原欲”是人的社會屬性,是理性的基礎,而“敬獻”則意味著人對神的崇拜。在古希臘文學藝術的觀念之中,人神本無區別,也就是說人所具有的一切屬性——社會屬性、情感屬性、理性精神等等在神的領域仍然存在,只不過由于肉身和“意念之軀”本不對等,為了使“人”的心理狀態切合于作為文學作品的神話,文學家在此其中“借神喻人”,仍以人的種種行為作為神話形成的基礎。謝華在《古希臘文學——原欲與理性的統一》一文中寫道:“象征理性的日神精神與象征原欲的酒神精神共同構成了古希臘文學的兩股水流。”③從這一觀點所引申的內容來看,“日神”與“酒神”作為“神”的代表,象征著人與神在精神層面的兩種特征,這既表現為人的習得,也可表現為“神”異化為“人”之后所具備的屬性。在舞劇《達芙妮與克羅埃》中,作曲家將人的“原欲”和“敬獻”,化為主導動機的貫穿,以人化的神作為描繪主體,促使兩者在同一時空中發生了交合;“敬獻”則更多地將視角投向于人,因為只有當人作為祭拜主體時,“神”的光環才會顯現;雖然這部舞劇更多地將故事情節的發展處理成為人化的神,但“敬獻”作為一種存在于舞劇之中的“暗線”,自始至終或明或暗地顯現于全劇的各段音樂之中,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作曲家自身對于“敬獻”一詞內涵的深刻理解。
一部舞劇的生成,首先應有故事梗概和文學劇本等文字性內容,而后才有舞劇音樂、舞美場景和舞蹈動作的生成。對于舞劇音樂而言,如何通過音高、節奏、線條等要素刻畫人物,成為了作曲家所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自巴赫首次使用“簽名動機”,瓦格納開創符號性(人物性)主導動機以降,作曲家在包括歌劇、舞劇、音樂劇的音樂創作實踐中,利用人物性格、相貌特征乃至時代背景,依托文學、美術中刻畫人物的方式,對具體形象進行藝術化處理。不同之處在于,美術作品中形象的具體性、文學作品中語言的具體性,與音樂作品中形象的抽象性形成了鮮明對比,作曲家在創作符號性(人物性)主題時,需要充分考量所需描繪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征,在與時代背景充分結合的過程中,方可尋求音色、音高、節奏等要素的綜合作用。
拉威爾筆下的“達芙妮”與“克羅埃”,在神性與人性并存的刻畫實踐中,依托繪畫技法中的“筆觸”,促成了人物形象的個性存在,雖對于主題而言,作曲家僅完成了對線條的勾勒,但對于全劇音樂的對立統一以及矛盾沖突的生成、激化與化解,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注釋:
① [美]托馬斯·克里斯坦森.劍橋音樂理論發展史[M].任達敏譯,上海音樂出版社,2011,11:96.
② 普羅泰戈拉《論真理》,轉引自鄭克魯《外國文學史》(上)[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③ 謝華.古希臘文學——原欲與理性的統一[J].美與時代,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