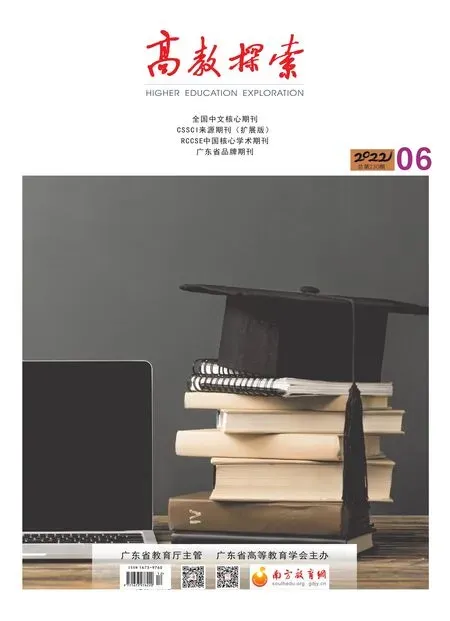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路徑與成效研究*
張清玲 劉寶存
在全球化的今天,隨著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越來越緊密,與其他國家展開教育合作越發受到各國和高等學校的重視,高等教育的區域化合作與交流也成為一種全球性趨勢。[1]作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和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以及總人口位居世界第三位的東盟,為了應對區域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和順應全球化趨勢的要求,促進東盟意識和區域認同,提升東盟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一直在積極全面推進高等教育的區域化發展。那么,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到了什么樣的程度?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如何開展合作?東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參與者,是中國的重要合作伙伴,對于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上述問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迫切性。
一、研究問題與分析框架
簡·奈特(Jane Knight)認為區域化是區域經濟和社會文化不斷聯系和互動的演變過程,[2]而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可以被定義為:在一個被稱為區域的地區或框架(通常稱為區域)內,在高等教育行為體和系統之間建立更為緊密的協作和聯盟的過程。[3]為了全面系統了解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包括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到了什么樣的程度,以及在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背景下我國如何開展與東盟的高等教育合作,本文采用簡·奈特的FOPA(Functional,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簡稱FOPA)模型[4]來分析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形成與發展的路徑,并通過其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程度理論來分析東盟高等教育現階段的區域化發展程度。
(一)FOPA 模型視角下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分析框架
簡·奈特于2012年提出了FOPA模型來分析研究高等教育區域化的發展[5],并在2013-2017年逐漸完善了該模型(圖1)[6]。FOPA模型主要由功能、組織和政治路徑組成(圖1)。這三種路徑相互關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7]。該模型強調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是各國政府、高等學校或組織在特定區域或框架內密切協作和建立聯盟的動態過程,可以適用于世界不同地區不斷變化的高等教育區域化進程。[8]本文以簡·奈特提出的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FOPA模型為分析框架,分析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路徑。

圖1 FOPA模型及相互關系

表1 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三大路徑及主要表現形式
(二)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程度
簡·奈特認為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程度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或者程度[9]。第一階段是指建立合作、協作和伙伴關系階段,在該階段,高等學校之間建立了開放、自愿、非正式的關系,開展大量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活動。第二階段是指協調、一致性和結盟階段,在該階段,有組織的網絡、聯合教育計劃、高等學校和系統之間的伙伴關系提高了高等學校間合作的成效。第三階段是指融合和和諧階段,在該階段,區域質量保障體系、資歷資格框架、區域期刊索引、學分轉換體系和統一的學期校歷等的建立,使得區域內部建立了更強和更具戰略性的聯系。第四階段是一體化、共同體和相互依存階段,是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最高程度。在該階段,區域內部通過區域層面的協議和機構建立了更正式、制度化和更全面的聯系和關系,形成更穩健和可持續的區域工作方式和影響力,如形成共同的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空間。可見,高等教育區域化程度從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代表著區域化發展程度呈現出越來越高的遞進關系。本文按照簡·奈特的這個理論評估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程度。
二、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功能路徑
根據簡·奈特的FOPA模型,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功能路徑是指促成高等教育機構之間進行實際互動的一系列框架、項目和計劃等,主要表現形式包括高等教育系統整合和合作項目。[10]從區域化的功能角度出發,這些措施為東盟高等教育系統之間的連接、區域協調和人員流動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中,高等教育系統整合具體包括東盟資歷參照框架(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Framework,簡稱 AQRF)、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框架(ASEAN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簡稱AQAFHE)、東盟大學網絡質量保障(ASEAN University Network-Quality Assurance,簡稱AUN-QA)、東盟學分轉化體系(AS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雙聯制學位計劃(Dual Degree Program)、東盟學年/學期校歷(Academic Calendar—Years and Semesters)和館際互借體系(Inter-Library Loan Systems)等。合作項目主要包括學生國際流動計劃(ASEA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for Students Programme,簡稱AIMS Programme)、跨境合作教育項目(Cross-Border Programs)、東盟學院(SEAMEO College)、大湄公河次區域聯盟(GMS—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Uni Consortium)、東盟研究生商業經濟計劃(ASEAN Graduate Business Economic Program)、東盟大學人權網絡(ASEAN University Human Rights Network)、東盟在線數字圖書館(ASEAN Online Digital Library)和東盟區域學術期刊索引(ASEAN Regional Research Citation Index)等。以下將主要具體介紹東盟區域資歷參照框架、東盟質量保障體系和學生國際流動計劃。
(一)建立東盟資歷參照框架
為推動區域內教育系統之間的銜接與溝通和人員互動交流,東盟制訂了與各成員國都能銜接的東盟資歷參照框架,并通過多種途徑來積極推進各成員國資歷框架和東盟資歷參照框架的對接。[11]東盟資歷參照框架于2015年全面推行,作為區域資歷共同參照框架,為東盟各成員國高等教育體系之間的銜接提供了參考和依據,也為東盟各成員國的學歷和資格證書的互認和頒發提供了規范和標準,[12]從而使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資歷框架對接成為現實,進而可以有效消除區域各級資歷參照框架的互認壁壘,更好地推進東盟區域人員的流動以及東盟共同體的建設。東盟資歷參照框架包括八個資歷級別,每個級別對應知識和技能、應用能力、責任感三個不同的指標,其中6-8級為高等教育階段。[13]此外,東盟還成立相關部門負責和支持東盟資歷參照框架的實施,處理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政策或技術問題,協調相關工作和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和保障。同時,為了確保本國資歷框架與東盟資歷框架能夠更好地接軌,東盟各成員國還專門成立了國家東盟資歷參照框架委員會。[14]
(二)建立東盟質量保障體系
為了確保東盟資歷參照框架中的高等教育資歷對接得到社會認可和有效實施,東盟確立了兩個區域質量保障機制:一是東盟大學網絡質量保障;二是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框架。兩套質量保障體系使區域內資歷框架得以有效運行,有利于加強區域高等教育合作,并達到提高教育質量以及提升區域競爭力和國際化程度的目的。
為了達到高等教育的高標準以及保證其高質量,早在1998 年,東盟就制定和實施了《東盟大學網絡質量保障》。《東盟大學網絡質量保障》的內容框架主要包括政策、標準、方針、基準程序、評估標準和指標等,其中包括8項評估標準和53項評估要求。[15]此外,為了構建高等教育學分轉換與學歷互認體系,東盟不斷完善東盟大學網絡質量保障機制,以此進一步促進區域高校師生的自由流動,推動東盟高等學校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為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合作與交流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質量保證。因此,AUN-QA的未來被認為是東南亞高等教育的集體未來。
東盟于2013年建立了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框架。該框架一共有40條,主要由四部分內容組成,包括外部質量保障、外部質量保障標準和流程、內部質量保障和國家資歷框架。[16]通過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框架,東盟逐步完善資歷認證程序,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構工作的信譽,加強東盟各成員國教育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并進一步提升東盟區域高等教育的質量。
(三)制定東南亞區域學生流動計劃
為了促進東盟區域范圍內學生的流動,東盟設立了推動區域學生流動的項目,例如東盟學生國際流動項目、東盟學生交換項目(AUN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東盟學習獎學金(ASEAN Studies Scholarships)項目等。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2010年正式啟動的AIMS項目,參與該項目的每個成員國的教育部負責為本國學生提供獎學金資助。[17]AIMS項目的目的是通過區域內人才流動與合作培養促進文化交流與融合,通過構建共同空間支持東南亞地區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在2010-2011學年至2018-2019學年間,參與AIMS項目的國家從3個增加到9個,學校從23所增加到77所,每年參與的學生從150人增加到4150人,交流學科也由5個增加到10個。[18]
三、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組織路徑
根據簡·奈特的FOPA模型,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組織路徑主要是成立一些網絡和組織以及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并通過這些組織架構的變革更系統地促進區域化。[19]在組織路徑方面,東盟主要成立了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簡稱SEAMEO)、東南亞高校聯合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簡稱 ASAIHL)、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Region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SEAMEO-RIHED)、東盟大學網絡(ASAEN University Network,簡稱AUN)、東盟+3大學網絡(ASEAN +3 University Network)和大湄公河次區域高等教育協調工作組(GMS Higher Education Coordinating Task Force)等。這些新的組織或機構負責制定宏觀政策、制度、共同行動綱領和預期目標、具體的合作機制、運行、規則與規范,通過相互合作,以實現東盟高等教育的區域化發展。以下將主要具體介紹東南亞高校聯合會、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和東盟大學網絡。
(一)成立東南亞高校聯合會
東南亞高校聯合會正式成立于1956年,是一個非政府組織,最初由東南亞8個國家的公立大學提出建立。該聯合會的宗旨是協助成員國高校通過相互幫助加強自身實力,提升其在教學、研究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國際聲譽。截至2019年,該聯合會的成員發展到28個國家的254所高校。[20]東南亞高校聯合會每年都會舉辦2次國際學術會議,由成員國輪流主辦。2019 年 12 月 8-10 日,泰國斯利帕圖大學(Sripatum University)在斯里蘭卡主辦了第43屆東南亞高校聯合會國際會議,會議主題為“振興高等教育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分主題包括:(1)運用創新技術改進高等教育;(2)通過課程變革增強高等教育活力;(3)整合學術界和工業界以促進可持續發展。[21]
(二)成立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
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成立于1959年,1993年成為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的下屬區域中心,致力于推進東南亞地區高等教育系統的合作、協調和發展,協調和創建東南亞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共同空間。[22]SEAMEO-RIHED的遠景目標是構建一個充滿活力、戰略和政策研究驅動的區域中心,并通過實現以下五個目標促進東盟高等教育的相互理解、合作和協同發展:(1)賦予高等學校自主權;(2)發展和諧機制;(3)推進高等教育系統管理的知識前沿;(4)培養全球化的人力資源;(5)促進大學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23]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每個目標都包括相應的若干舉措,例如,通過學生和研究流動計劃、區域實習方案等舉措來實現培養全球化的人力資源的目標。SEAMEO-RIHED通過各種項目推進各項目標的實現,主要包括研究訪問(Study Visits)、學生流動(Student Mobility)、國際獎學金(Internationalization Award)、學分轉換體系以及質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等。自1993年起,SEAMEO-RIHED開始制定并實施五年發展規劃,目前實施的第五個五年發展規劃(2017-2022年)把聯盟和發展(Alignment and Development)、合作與協同(Cooperation and Synergy)、研究(Research)、信息門戶(Information Portal)等4個關鍵領域作為重點領域。SEAMEO-RIHED 每年發布一份年度報告,對該年度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合作和發展進行總結和反思。
(三)成立東盟大學網絡
1995年東盟大學網絡正式成立,各國教育部長簽署了《東盟大學網絡憲章》,有關大學校長(或學區長、副校長)和AUN董事會簽署了《東盟大學網絡協議》。東盟大學網絡旨在通過促成東盟成員國大學在高等教育重點發展領域與方向的合作,推動東盟各國高校之間的緊密聯系與互動,推進東盟的認同與團結。[24]據統計,截至2020年,AUN有30所成員大學,分別來自泰國(5所)、馬來西亞(5所)、印度尼西亞(4所)、新加坡(3所)、菲律賓(3所)、越南(3所)、緬甸(3所)、柬埔寨(2所)、文萊(1所)和老撾(1所)。[25]東盟大學網絡始終把推動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擺在核心位置,2017年第9屆AUN校長會議提出了東盟大學網絡2017-2021年的戰略重點(AUN Strategic Focus 2017-2021),[26]包括課程和學習方法的進步(Advancements in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Approaches),東盟大學網絡質量保障,學生技能培養、展示和經驗(Students’ Skill Enhancement,Exposure and Experience),科研合作(Research Collaboration),大學網絡平臺(University Networking Platforms)。
四、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政治路徑
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政治路徑是指將高等教育倡議列入決策機構議程的政治意愿和戰略,通過啟動發展規劃和重大項目,開展政策對話等途徑推動高等教育的區域化發展。[27]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政治路徑主要體現在《東盟宣言》、《東盟憲章》、《東盟共同體后2015年愿景》、《東盟2020愿景》、《2004-2010年萬象行動計劃》、《東盟教育5年工作計劃(2011-2015)》、《東盟教育5年工作計劃(2016-2020)》、《新的教育議程:SEAMEO的七個優先事項(2015-2035)》、《七個優先領域行動綱領》、高等教育戰略發展規劃、東盟首腦峰會、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會議等方面。以上政治路徑明確指出高等教育在提升東盟認同意識、人力資源開發及科學技術發展上的重要性。[28]與此同時,各成員國在提升教育質量,提高教育透明度和加強良性互動等方面達成共識,并使之具體體現在東盟制訂和頒布的下列高等教育計劃和戰略中。
(一)制定《2004-2010年萬象行動計劃》
《2004-2010年萬象行動計劃》是在2007年第2次東盟教育部長會議和第42次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會議上通過的。《2004-2010年萬象行動計劃》制定了建設東盟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三大共同體的具體目標、策略和可操作性措施。其中,社會文化共同體目標涉及的東盟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包括:(1)促進東盟意識和區域認同;(2)保護和發展東盟文化遺產;(3)推動婦女和青年人進入勞動力大軍;(4)開發勞動人力資源;(5)促進東盟科學與技術發展;(6)擴大高等教育機會,提高公民文化素質。[29]《2004-2010年萬象行動計劃》重在強化東盟區域認同,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建設,創建高等院校數學與科學合作研究網絡,提高東盟高等教育的質量,并逐步擴大東盟與伙伴國家的教育合作與交流,從而進一步提升東盟各成員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和影響力。[30]
(二)制定東盟高等教育5年工作計劃
《東盟教育5年工作計劃(2011-2015)》的第三個優先事項是推動跨境流動和教育國際化,旨在重點推進區域內學生和教師的流動以及各種教育培訓項目的國際化。該優先事項包括3個子項目:分享區域資源知識和增進學生流動的相互關聯性;加強支持各級學生交流和獎學金的活動;制定區域交流計劃,重點通過區域戰略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31]
《東盟教育5年工作計劃(2016-2020)》的第六和第七個目標是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目標,主要是圍繞“建立協調的東盟質量保障機制”,“協助高等學校建立東盟質量保障機制”,“加強大學、工業和社區之間的聯系”和“增加東盟內部國際學生的數量”設計了11個子項目,并對這些子項目的成效考核指標和預期結果、主導國家和合作方以及時間節點等都一一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和要求。[32]
《東盟教育5年工作計劃(2021-2025)》的第三個目標是提高區域高等教育發展能力,通過提供靈活、創新、多學科、跨境教育和研究合作,加強高等教育機構在終身學習中的作用;通過戰略、機制和獎學金,持續并加強東盟在高等教育協調方面的能力。[33]
通過制定和實施以上三個5年高等教育工作計劃,東盟不僅強化了在區域高等教育合作與交流中的主導作用,而且還擴大了區域高等教育合作伙伴,拓寬了合作范疇,并對進一步推動高等教育區域化進程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制定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戰略
在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2015年發布的《新的教育議程:SEAMEO的七個優先事項(2015-2035)》中,高等教育就是其中的優先發展戰略領域之一。在與之相配套的《七個優先領域行動綱領》中,在促進高等教育與研究協調發展方面制定了以下8個發展戰略:(1)構建東南亞大學在關鍵領域的研究和發展(R&D)實踐共同體;(2)加強學術和工業界的聯系;(3)利用研究與發展(R&D)開發高等教育開放教育資源;(4)加強和擴大東盟國際學生流動項目;(5)開發東盟學分轉換框架;(6)協調和發展衛生專業的質量保障;(7)推動SEAMEO中心政策研究網絡發展和制度化;(8)促進本區域及以外地區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相互認可和流動性。東盟高等教育發展戰略是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風向標和指南,為了確保這些戰略規劃從政治共識落實到具體實踐中,每一個戰略都具體化到項目,并明確規定負責執行項目的主導國、實施機構以及時間節點,[34]增強各國成員高等教育體系的透明度和可對比性,保障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可持續性。
五、結語: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程度評估與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建議
(一)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程度評估
自2015年12月東盟共同體正式成立以來,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取得了較大成效。根據簡·奈特對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程度的描述以及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現階段的具體表現形式,可以確定目前東盟高等教育的區域化發展正處于融合與和諧發展階段,并向一體化、共同體和相互依存階段努力邁進中。此外,簡·奈特認為,高等教育區域化的各種路徑依據其成熟程度顯示出不同的特征,如非正式或正式,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臨時性或有意性,漸進性或大規模飛躍,內部驅動或外部驅動,被動性或主動性、戰略性。[35]根據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現狀來看,其區域化發展越來越趨向正式化、自上而下、有意性、飛躍性、外部驅動以及戰略性。由此可見,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日益成熟,這說明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通過功能、組織和政治這三大路徑的共同推動,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并具備向一體化、共同體階段邁進的基礎。
同時,客觀地講,東盟各國社會政治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宗教、文化差異顯著,教育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利益訴求差異各不相同,這些都影響著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也正是認識到東盟各國之間的差異和不平衡,東盟共同體不同于歐盟這一超國家組織的統一性,強調彼此之間尊重差異前提下的團結合作,保持和諧合作的關系,照顧彼此各自的利益訴求,重視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協調。雖然東盟的最終目標是進一步推動區域一體化,逐步發展成為類似歐盟那樣的超國家組織,但是東盟松散多國聯合體的本質決定了它沒有超越國家權力的機構,無法在短期內實現歐盟那樣的一體化,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也是如此。
(二)對我國與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建議
東盟共同體建設促進了東盟各國內部的協調和合作,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使各國逐漸建立統一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空間,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上走向一體化,同時也啟動了許多超越國家層面的東盟項目,這就要求我國與東盟國家的高等教育合作,不僅要推進國家之間的合作,而且要面向東盟層面開展合作。基于FOPA模型對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路徑的研究,可以對于我國加強與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提供如下三點啟示和建議。
第一,推動我國高等教育資歷與東盟高等教育資歷的互認,并建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框架”。根據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功能路徑分析,區域資歷參照框架的建立可以為區域各國高等教育體系之間的比較、互動、互認以及連接提供技術保障,我國應盡快建立國家資歷框架,并對照東盟資歷參照框架的內容,為推動我國國家資歷框架與東盟資歷參照框架的互認提供技術指導,以及進一步提高我國高等教育資歷與東盟高等教育資歷的可比性和可轉換性。此外,還要建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框架”,確保資歷對照和學分轉化的對等性以及獲得社會的認可。
第二,加強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以及東盟大學網絡的對話與合作。根據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組織路徑分析,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以及東盟大學網絡對推進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合作發揮著關鍵性作用。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不僅是影響東盟成員國內部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政府組織,還是代表東盟成員國與區域外國家開展高等教育合作與交流的重要平臺。而東盟大學網絡通過不斷推進東盟各成員國在高等教育與科學技術研究優先發展領域的合作,進一步強化了東盟高校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將東盟各成員國的學術資源和優勢整合起來。因此,我國一方面要積極加強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高等教育與發展區域中心的對話,另一方面又要深化與東盟大學網絡的合作。在目前的AUN30+3(中國、日本、韓國)中,我國與東盟大學網絡合作的高校數量并不多,截至2019年只有廣西大學、貴州大學、云南大學、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等5所高校。[36]因此,我國應該擴大高等院校與東盟大學網絡的合作,同時根據東盟大學網絡戰略重點,有針對性地開發與之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合作項目。
第三,積極關注東盟高等教育發展5年計劃以及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做好戰略對接,創造共同的高等教育合作空間。依據東盟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的政治路徑分析,東盟十分重視并積極推行高等教育5年發展規劃及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因而我國要進一步分析和研究東盟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與計劃的具體內容,深刻把握東盟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和優先領域,拓展我國與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空間。基于此,我國要及時關注東盟發布的《東盟教育5年工作計劃(2021-2025年)》中有關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與規劃,同時還需繼續關注東盟《新的教育議程:SEAMEO的七個優先事項(2015-2035)》中的高等教育與研究優先發展領域,以及與之相配套實施的東盟高等教育與研究協調發展的8個發展戰略,指導我國頂尖高校設計與東盟高等教育戰略與規劃相關的合作與交流項目,重點研究東盟在研究與發展(R&D)、東盟國際學生流動項目和東盟學分轉換框架等戰略方面的進展,尋找和創建共同合作空間,有效地促成多層面、深層次、可持續性的高等教育合作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