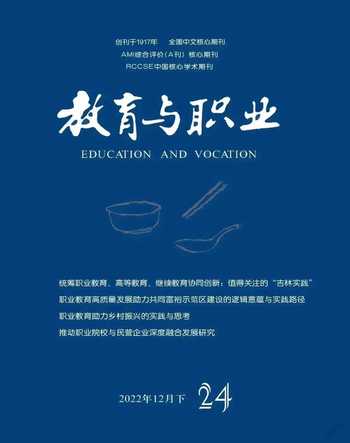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理論內(nèi)涵、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與實(shí)踐進(jìn)路
蔣小燕 張晨 韋慶昱
[摘要]推動(dòng)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是建設(shè)高質(zhì)量教育體系的必然之舉。基于高校職責(zé)視角分析,當(dāng)前高職院校發(fā)展存在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有待提升、社會(huì)服務(wù)功能有待延展、科學(xué)研究能力有待加強(qiáng)、國際交流合作有待拓展等現(xiàn)實(shí)困境。因此,推動(dòng)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需要深化人才培養(yǎng)改革,進(jìn)一步豐富社會(huì)服務(wù)內(nèi)涵,提升科學(xué)研究能力,穩(wěn)步擴(kuò)大國際交流合作,從而更好地承擔(dān)新時(shí)代高等職業(yè)教育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時(shí)代責(zé)任。
[關(guān)鍵詞]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理論內(nèi)涵;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實(shí)踐進(jìn)路
[作者簡介]蔣小燕(1969- ),女,江蘇宜興人,常州工程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江蘇 ?常州 ?213164)張晨(1974- ),女,江蘇常州人,江蘇聯(lián)合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常州衛(wèi)生分院,研究員。(江蘇 ?常州 ?213000)韋慶昱(1974- ),男,江蘇泰興人,常州工程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研究員。(江蘇 ?常州 ?213164)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2022年度全國教育科學(xué)“十四五”規(guī)劃重點(diǎn)課題“職業(yè)院校專業(yè)群集聚效應(yīng)的形成機(jī)理及提升路徑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DJA220479)和2019年度江蘇省教育系統(tǒng)黨建研究會(huì)重點(diǎn)立項(xiàng)課題“高職院校黨建工作質(zhì)量評價(jià)體系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9JSJYDJ010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hào)]G717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文章編號(hào)]1004-3985(2022)24-0065-05
加快建設(shè)高質(zhì)量教育體系是建設(shè)教育強(qiáng)國和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必然要求。在我國教育體系中,高等職業(yè)教育承擔(dān)著優(yōu)化高等教育結(jié)構(gòu)和培養(yǎng)大國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作用,而高職院校作為高等職業(yè)教育實(shí)施的重要載體,自然成為推進(jìn)高等職業(yè)教育實(shí)現(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同時(shí),推進(jìn)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也是落實(shí)職業(yè)教育立德樹人根本任務(wù)的客觀要求,更是推動(dòng)高職院校實(shí)現(xiàn)主動(dòng)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之需。鑒于此,本研究擬從高校職責(zé)的視角切入,探討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理論內(nèi)涵、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及實(shí)踐進(jìn)路等具體問題,以為豐富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研究提供理論支撐與實(shí)踐基礎(chǔ)。
一、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理論內(nèi)涵
自《國家職業(yè)教育改革實(shí)施方案》提出“推進(jìn)高等職業(yè)教育高質(zhì)量發(fā)展”以來,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受到了學(xué)界的廣泛關(guān)注,相關(guān)研究在推動(dòng)高職院校落實(shí)立德樹人根本任務(wù)、推進(jìn)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和數(shù)字化升級(jí)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客觀而言,現(xiàn)有的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內(nèi)涵是什么、高質(zhì)量發(fā)展有何特征、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實(shí)施路徑有哪些,回答好這些問題對于促進(jìn)高職院校實(shí)現(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推動(dòng)高等職業(yè)教育提質(zhì)增效都有所助益。
20世紀(jì)80年代,美國學(xué)者邁克爾·波特提出了戰(zhàn)略定位理論。他認(rèn)為,企業(yè)競爭戰(zhàn)略的核心內(nèi)容是做好自身戰(zhàn)略定位。基于此,朱正茹提出,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是指高職院校整合各類資源而選擇的錯(cuò)位發(fā)展,最終帶來高質(zhì)量的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技術(shù)服務(wù)以及品牌。甘華銀則提出,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包括全方位和多層次兩個(gè)層面。全方位指高職院校應(yīng)當(dāng)在人才培養(yǎng)、科技創(chuàng)新、社會(huì)服務(wù)等方面推進(jìn)高質(zhì)量發(fā)展,而多層次則指高職院校要從整體到局部、從宏觀到微觀來實(shí)現(xiàn)自身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肖冰提出,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是一場組織變革,旨在提高組織效能,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組織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可見,目前的研究側(cè)重學(xué)理性,未能運(yùn)用一個(gè)科學(xué)有效的分析框架來探討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問題,難以完整涵蓋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特征全貌。因此,本研究認(rèn)為,應(yīng)結(jié)合當(dāng)前高職院校發(fā)展的實(shí)際情況,運(yùn)用動(dòng)態(tài)、全面的視角來審視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問題。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應(yīng)是在經(jīng)濟(jì)、教育等領(lǐng)域全面高質(zhì)量發(fā)展背景下一種促進(jìn)高職院校主動(dòng)作為并持續(xù)增強(qiáng)其職責(zé)的新型院校發(fā)展理念,旨在通過自身高質(zhì)量發(fā)展來擺脫諸如人才培養(yǎng)、專業(yè)設(shè)置、產(chǎn)教融合等方面的困境,最終促進(jìn)高職院校更好地承擔(dān)社會(huì)職責(zé),進(jìn)而達(dá)到提升國家人力資本素質(zhì)的目的,確保國家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實(shí)現(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
二、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面臨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
黨的十八大以來,大力發(fā)展職業(yè)教育已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國家和地方政府陸續(xù)出臺(tái)的系列宏觀政策及改革舉措推動(dòng)了我國職業(yè)教育邁入高質(zhì)量發(fā)展新征程。職業(yè)教育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是一項(xiàng)涉及多維度的復(fù)雜的系統(tǒng)工程,高職院校作為職業(yè)教育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載體,其高質(zhì)量發(fā)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huì)面臨一系列挑戰(zhàn),需要認(rèn)真面對。
(一)“三教”改革緩慢,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有待提升
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是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面臨的首要任務(wù),其關(guān)鍵在于推進(jìn)教師(主體)、教材(客體)、教法(內(nèi)容)三者的深入改革。但從改革的實(shí)際情況來看,高職院校的“三教”改革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一是師資隊(duì)伍建設(shè)未能較好地滿足育人需求。據(jù)2016—2020年的《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顯示,“十三五”期間高職院校在校生數(shù)量持續(xù)增加,高職院校生師比呈逐年上升趨勢,2016年為17.73∶1,2020年為20.28∶1。這也使得有限的高職院校教師隊(duì)伍面臨更加繁重的教學(xué)任務(wù),難以滿足育人需求。二是課程體系改革未能較好地契合育人需求。高職院校課程目標(biāo)與職業(yè)崗位適配度不高,課程內(nèi)容開發(fā)時(shí)企業(yè)參與意愿不強(qiáng),課程內(nèi)容與企業(yè)需求脫節(jié),對企業(yè)、教師等主體的課程評價(jià)意見關(guān)注度不高。三是教學(xué)方法改革未能較好地適應(yīng)育人需求。盡管高職院校進(jìn)行了以項(xiàng)目教學(xué)法、任務(wù)驅(qū)動(dòng)法、案例教學(xué)法等為代表的多輪教學(xué)方法改革,嘗試構(gòu)建開放性的教學(xué)格局,但教法改革的實(shí)際成效收效甚微,傳統(tǒng)講授法仍然占據(jù)主要地位。
(二)服務(wù)意識(shí)不強(qiáng),社會(huì)服務(wù)功能有待延展
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我國高校的社會(huì)服務(wù)職能迅速發(fā)展,高職院校的社會(huì)服務(wù)功能也日漸成熟,但仍面臨嚴(yán)峻挑戰(zhàn)。一是社會(huì)服務(wù)領(lǐng)域不夠全面。《國家職業(yè)教育改革實(shí)施方案》明確指出,高職院校要“重點(diǎn)服務(wù)企業(yè)特別是中小微企業(yè)的技術(shù)研發(fā)和產(chǎn)品升級(jí),加強(qiáng)社區(qū)教育和終身學(xué)習(xí)服務(wù)”。但實(shí)際上,高職院校在服務(wù)社區(qū)教育方面關(guān)注不夠、投入不多,取得的成效遠(yuǎn)低于政府預(yù)期。因此,未來高職院校要以社區(qū)教育為突破,拓展社會(huì)服務(wù)領(lǐng)域空間。二是社會(huì)服務(wù)協(xié)同機(jī)制不健全。高職院校社會(huì)服務(wù)牽涉面較廣,包括政府、行業(yè)企業(yè)、其他院校及本校相關(guān)處室或二級(jí)學(xué)院等,利益主體多元化。而現(xiàn)有的內(nèi)部協(xié)調(diào)機(jī)制往往不能滿足不同主體的價(jià)值取向,造成跨部門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能力弱化,導(dǎo)致各種推諉現(xiàn)象時(shí)有發(fā)生。三是社會(huì)服務(wù)資源要素面臨短缺。近年來,高職院校生源數(shù)量快速增加,導(dǎo)致師資力量面臨攤薄風(fēng)險(xiǎn),進(jìn)而造成社會(huì)服務(wù)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四是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開展社會(huì)服務(wù)資源不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以及數(shù)字化經(jīng)濟(jì)的推動(dòng),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xué)已成必然趨勢,但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開展社會(huì)服務(wù)所需要的諸如課程、信息、平臺(tái)等資源要素卻嚴(yán)重短缺,影響了高職院校社會(huì)服務(wù)效能的發(fā)揮。
(三)科研團(tuán)隊(duì)薄弱,科學(xué)研究能力有待加強(qiáng)
高職院校同普通高校一樣,承擔(dān)著科學(xué)研究的社會(huì)職責(zé),肩負(fù)著以科研創(chuàng)新推動(dòng)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重要使命。但長期以來,高職院校的科研定位不清、知識(shí)域狹窄、技術(shù)創(chuàng)新能力薄弱,尤其是我國教育邁入高質(zhì)量發(fā)展階段以來,高職院校科研短板愈加凸顯。一是高級(jí)別研究項(xiàng)目立項(xiàng)數(shù)偏少。高級(jí)別研究項(xiàng)目是反映一所高職院校科研產(chǎn)出的重要指標(biāo),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xiàng)目為例,通過對2021年度和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一般項(xiàng)目評審結(jié)果公示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可知,全國高職院校2021年入選項(xiàng)目數(shù)量為88個(gè)、2022年入選項(xiàng)目數(shù)量為96個(gè),立項(xiàng)率均不到4%。可見,立項(xiàng)項(xiàng)目數(shù)量雖有提升,但高職院校立項(xiàng)數(shù)量占總體立項(xiàng)數(shù)的比例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同樣,在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高級(jí)別研究項(xiàng)目立項(xiàng)情況也不容樂觀。二是高水平科研團(tuán)隊(duì)建設(shè)存在薄弱環(huán)節(jié)。受科研成果排名因素影響,團(tuán)隊(duì)成員更熱衷于“單兵作戰(zhàn)”,團(tuán)隊(duì)科研凝聚力不強(qiáng),未形成科研合力。同時(shí),團(tuán)隊(duì)成員來源單一,缺少跨學(xué)科教師的學(xué)術(shù)支持,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等相對落后,研究成果與團(tuán)隊(duì)研究主題的關(guān)聯(lián)性不強(qiáng)。此外,科研團(tuán)隊(duì)的經(jīng)費(fèi)管理制度、激勵(lì)機(jī)制等在執(zhí)行過程中存在偏差,團(tuán)隊(duì)文化建設(shè)滯后,團(tuán)隊(duì)科研產(chǎn)出效率低。三是高層次科研平臺(tái)建設(shè)成效緩慢。科研平臺(tái)包括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工程研發(fā)中心、技術(shù)轉(zhuǎn)移推廣中心、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是高校科研創(chuàng)新體系建設(shè)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教師科研能力提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目前大部分高職院校科研設(shè)備老舊,科研平臺(tái)層次偏低、數(shù)量少,同時(shí)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不夠深入,資源共享利用率整體不高。
(四)協(xié)同融合不夠,國際交流合作有待拓展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推進(jìn),高職院校積極順應(yīng)高等職業(yè)教育國際化發(fā)展的趨勢,堅(jiān)持“引進(jìn)來”與“走出去”并舉,促進(jìn)高職教育與世界職業(yè)教育的協(xié)同融合,進(jìn)而推動(dòng)我國高職教育世界影響力的穩(wěn)步提升。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隨著世界產(chǎn)業(yè)布局的調(diào)整,加之后疫情時(shí)代經(jīng)濟(jì)復(fù)蘇較為緩慢,“十四五”期間高職院校國際交流與合作任重道遠(yuǎn)。一是優(yōu)質(zhì)職教資源輸出能力參差不齊。近年來,高職院校開發(fā)并輸出的專業(yè)教學(xué)標(biāo)準(zhǔn)和課程標(biāo)準(zhǔn)數(shù)量雖然在持續(xù)增加,但總體的開發(fā)能力還處于較低水平。據(jù)《江蘇省2022質(zhì)量年度報(bào)告》顯示,該省90所高職院校2021年開發(fā)被國(境)外采用的專業(yè)教學(xué)標(biāo)準(zhǔn)數(shù)量為269個(gè),平均每校不足3個(gè)。二是師生國際化水平提升存在瓶頸。據(jù)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xié)會(huì)《CEAIE2021年度職業(yè)院校國際化發(fā)展報(bào)告》顯示,高職院校大部分專業(yè)具有海外學(xué)習(xí)經(jīng)歷的師資占比低于20%,教師在國(境)外專業(yè)性組織擔(dān)任職務(wù)情況也不容樂觀。同樣,來華留學(xué)生招生數(shù)量處于較低水平,高職院校學(xué)生赴境外深造意愿減弱和參加國際競賽機(jī)會(huì)較為缺乏。這與院校地理位置、專業(yè)發(fā)展水平和學(xué)生家庭收入狀況等有較大關(guān)系。
三、推進(jìn)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實(shí)踐進(jìn)路
面對以上挑戰(zhàn),高職院校必須探索人才培養(yǎng)、社會(huì)服務(wù)、科學(xué)研究等領(lǐng)域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具體實(shí)踐進(jìn)路,重構(gòu)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內(nèi)涵重點(diǎn),進(jìn)而增強(qiáng)高職教育的適應(yīng)性,“加快實(shí)現(xiàn)與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內(nèi)生嵌入式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①,才能真正推進(jìn)高職院校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
(一)深化人才培養(yǎng)改革
隨著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shù)深入應(yīng)用,產(chǎn)業(yè)行業(yè)對職業(yè)院校畢業(yè)生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能力結(jié)構(gòu)、技能習(xí)得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掌握更為復(fù)雜的智能化設(shè)備操作與維護(hù),還要具備持續(xù)的學(xué)習(xí)能力,通過不斷的知識(shí)更新來保持行業(y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所需要的生產(chǎn)能力,這也成為高職院校人才培養(yǎng)需要應(yīng)對的挑戰(zhàn)。一是以學(xué)生未來就業(yè)崗位為主導(dǎo),緊貼企業(yè)崗位需求設(shè)計(jì)開發(fā)人才培養(yǎng)課程體系,選取結(jié)構(gòu)化和序列化的典型崗位任務(wù)重組教學(xué)內(nèi)容,確定合適的教學(xué)方式,形成“崗”與“課”對接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二是最大限度地實(shí)現(xiàn)技能競賽要求和人才培養(yǎng)規(guī)格相接軌,確保學(xué)生具備未來就業(yè)崗位所必需的專業(yè)能力(技能)、職業(yè)素質(zhì)和知識(shí)。同時(shí),將備賽訓(xùn)練與實(shí)踐教學(xué)相結(jié)合,實(shí)現(xiàn)“課”與“賽”在標(biāo)準(zhǔn)、內(nèi)容等維度的融通互補(bǔ)。三是圍繞1+X證書制度等新要求,在課程體系、課程內(nèi)容、課程資源、課程實(shí)施等方面進(jìn)行改革,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書證融通”,大力提高學(xué)生核心競爭力、創(chuàng)新能力和綜合素質(zhì),助力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出彩人生。總之,應(yīng)通過“崗課賽證”綜合育人“打通復(fù)合型技術(shù)人才的培養(yǎng)環(huán)節(jié)”②,豐富高職學(xué)生成才路徑,幫助他們更好地應(yīng)對就業(yè)變化并獲得技能水平提升。
(二)豐富社會(huì)服務(wù)內(nèi)涵
誠如威斯康星大學(xué)校長查爾斯·范海斯所言:“服務(wù)應(yīng)該是高校唯一的理想。”在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轉(zhuǎn)變、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大調(diào)整的背景下,高職院校依托人才、設(shè)備等資源開展社會(huì)服務(wù)顯得極為必要。一是以服務(wù)人民群眾的知識(shí)更新拓展高職院校社會(huì)服務(wù)外延。如前所述,社區(qū)教育和終身學(xué)習(xí)服務(wù)應(yīng)是高職院校服務(wù)對象之一,因此,高職院校要以打造社區(qū)教育項(xiàng)目工作室為抓手,培育整合社區(qū)項(xiàng)目(課程)資源,開發(fā)包含公民素養(yǎng)、誠信教育、人文藝術(shù)、科學(xué)技術(shù)、職業(yè)技能等在內(nèi)的在線學(xué)習(xí)資源,滿足人民群眾對優(yōu)質(zhì)社區(qū)教育的需求,有力支撐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建設(shè)。二是以深化產(chǎn)教融合為主線推進(jìn)高職院校社會(huì)服務(wù)縱深發(fā)展。“開展科技研發(fā)服務(wù),助推中小微企業(yè)發(fā)展,是高職院校社會(huì)服務(wù)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③基于此,高職院校要以深化產(chǎn)教融合為主線,以項(xiàng)目為合作紐帶,積極為行業(yè)企業(yè)提供技術(shù)開發(fā)與服務(wù)、技能培訓(xùn)、學(xué)歷教育等服務(wù)項(xiàng)目,從而賦能區(qū)域行業(yè)企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同時(shí),通過開展社會(huì)服務(wù)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資源參與高職院校人才培養(yǎng),進(jìn)而增強(qiáng)職業(yè)教育的適應(yīng)性。三是以構(gòu)建高效的協(xié)作機(jī)制促進(jìn)高職院校社會(huì)服務(wù)能力提升。增強(qiáng)社會(huì)服務(wù)功能是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重要保障,構(gòu)建高效的協(xié)作機(jī)制是一項(xiàng)復(fù)雜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協(xié)調(diào)好不同參與主體的利益訴求,建立利益共享、風(fēng)險(xiǎn)共擔(dān)的多主體合作機(jī)制,在價(jià)值認(rèn)同的基礎(chǔ)上形成參與合力,推動(dòng)社會(huì)服務(wù)提質(zhì)增效,從而更好地促進(jìn)高職院校履行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促進(jìn)國民素質(zhì)提升等重要職責(zé)。
(三)提升科學(xué)研究能力
開展科學(xué)研究是提升高職院校高等性的重要路徑,也是促進(jìn)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源泉。高職院校應(yīng)跳脫出科研錦標(biāo)賽的局限思維,牢牢堅(jiān)持應(yīng)用型科研定位,以生產(chǎn)技術(shù)知識(shí)和教師實(shí)踐性知識(shí)為重點(diǎn),以科研成果來支撐更好地履行人才培養(yǎng)、社會(huì)服務(wù)等社會(huì)職責(zé),“努力將自身打造為‘雙高計(jì)劃中所描述的‘技術(shù)技能創(chuàng)新服務(wù)平臺(tái)”④ 。一是以項(xiàng)目驅(qū)動(dòng)為導(dǎo)向,挖掘不同類型教師的科研潛力。高職院校應(yīng)梳理不同類型教師的科研需求,在此基礎(chǔ)上分類制定科研激勵(lì)政策。例如,針對青年教師可以提供專家指導(dǎo)、參加學(xué)術(shù)會(huì)議等必要的科研支持,幫助青年教師快速提升項(xiàng)目申報(bào)能力與水平;針對博士學(xué)歷教師群體,則可以通過搭平臺(tái)、壓擔(dān)子、定任務(wù)等方式激發(fā)其參與科研項(xiàng)目申報(bào)的熱情,進(jìn)而形成濃厚的科研氛圍。二是以跨校合作為突破,組建高水平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針對高職院校現(xiàn)有科研團(tuán)隊(duì)?wèi)?zhàn)斗力不強(qiáng)、科研績效不顯著等情況,鼓勵(lì)組建跨校、跨學(xué)科的科研共同體,以政策、資金、知識(shí)等支持方式來鼓勵(lì)企業(yè)技術(shù)人員、普通高校高層次人才等與高職院校教師開展合作研究,實(shí)現(xiàn)優(yōu)勢互補(bǔ);同時(shí),積極破除科研團(tuán)隊(duì)成果評價(jià)“重論文”的傾向,加大對指導(dǎo)學(xué)生競賽獲獎(jiǎng)、科研成果轉(zhuǎn)化、咨詢報(bào)告等其他形式成果的認(rèn)可度,以此提升教師參與科研的積極性,處理好教師科研需求與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之間的矛盾,促進(jìn)高質(zhì)量科研成果產(chǎn)出。三是以提質(zhì)增效為目標(biāo),加大對科研基礎(chǔ)設(shè)施設(shè)備建設(shè)的投入。科研基礎(chǔ)設(shè)施設(shè)備是開展高層次科研的基礎(chǔ)條件和重要保障,在推進(jìn)職業(yè)教育高質(zhì)量發(fā)展進(jìn)程中,高職院校要加大對以科研平臺(tái)為代表的科研基礎(chǔ)設(shè)施設(shè)備建設(shè)的投入,為教師取得高質(zhì)量科研成果奠定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四)擴(kuò)大國際交流合作
在國際交流合作過程中,我國高職教育雖然在促進(jìn)青年技能養(yǎng)成、確保人人享有教育機(jī)會(huì)等方面貢獻(xiàn)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高職院校應(yīng)強(qiáng)化制度設(shè)計(jì),“推動(dòng)形成與新時(shí)代國家戰(zhàn)略相適應(yīng)的高職教育國際化發(fā)展的新范式”⑤。一是整合資源,多方共建海外人才共育平臺(tái),加快培養(yǎng)愛華友華的國際青年。二是多維探索,拓寬職業(yè)教育資源輸出渠道。增進(jìn)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職業(yè)教育標(biāo)準(zhǔn)、制度、需求等方面的了解,教育行政部門統(tǒng)籌高職院校開發(fā)專業(yè)標(biāo)準(zhǔn)、課程標(biāo)準(zhǔn)等優(yōu)質(zhì)職教資源,依托“走出去”行業(yè)企業(yè)廣泛開展職教資源輸出,穩(wěn)步提升我國高等職業(yè)教育標(biāo)準(zhǔn)在世界上的認(rèn)可度。三是內(nèi)外聯(lián)動(dòng),多措并舉促進(jìn)師生國際化水平提升。圍繞“引進(jìn)來”與“走出去”相結(jié)合,一方面積極組織師生參與各類線上培訓(xùn)項(xiàng)目,推動(dòng)師生融入不同國家文化,提高師生跨文化交際能力。另一方面,高職院校理應(yīng)完善相關(guān)政策,形成多元的經(jīng)費(fèi)投入機(jī)制,鼓勵(lì)教師赴(國)境外高校訪學(xué)、深造、參與學(xué)術(shù)會(huì)議等,鼓勵(lì)教師在國際組織任職,擴(kuò)大高職院校的國際影響力。同時(shí),加大來自職業(yè)教育發(fā)達(dá)國家的海外高端人才的引進(jìn)力度,帶動(dòng)高職教師綜合能力的提升,助推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shè)。
[注釋]
①王亞鵬,唐柳.高職教育適應(yīng)性:內(nèi)涵、目標(biāo)、邏輯及機(jī)制[J].職業(yè)技術(shù)教育,2021,42(28):40.
②楊磊,朱德全.“1+X”證書制度下職業(yè)院校課程體系的邏輯框架[J].貴州社會(huì)科學(xué),2021(8):107.
③岑家峰.新時(shí)代高職院校社會(huì)服務(wù)現(xiàn)狀及能力提升路徑研究——基于廣西高水平高職學(xué)校質(zhì)量報(bào)告的分析[J].職業(yè)技術(shù)教育,2021,42(18):48.
④李政.職業(yè)本科教育的學(xué)科建設(shè):大學(xué)職能的視角[J].江蘇高教,2022(3):113.
⑤祝成林,吳立保.新時(shí)代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發(fā)展的轉(zhuǎn)向、挑戰(zhàn)與路徑[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22(3):96.
[參考文獻(xiàn)]
[1]朱正茹.錯(cuò)位發(fā)展:新時(shí)期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戰(zhàn)略選擇[J].中國職業(yè)技術(shù)教育,2019(31):5-9.
[2]甘華銀.新時(shí)代高職院校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困境與突圍[J].教育與職業(yè),2020(7):34-39.
[3]肖冰.高質(zhì)量發(fā)展背景下高職院校組織變革研究[J].中國高等教育,2021(Z1):72-74.
[4]羅堯成,劉桐.教育部人文社科高職研究項(xiàng)目立項(xiàng)分析[J].中國高校科技,2018(Z1):77-80.
[5]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xié)會(huì). CEAIE 2021年度職業(yè)院校國際化發(fā)展報(bào)告[EB/OL].(2021-10-29)[2022-10-31].http://www.ceaie.edu.cn/article/23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