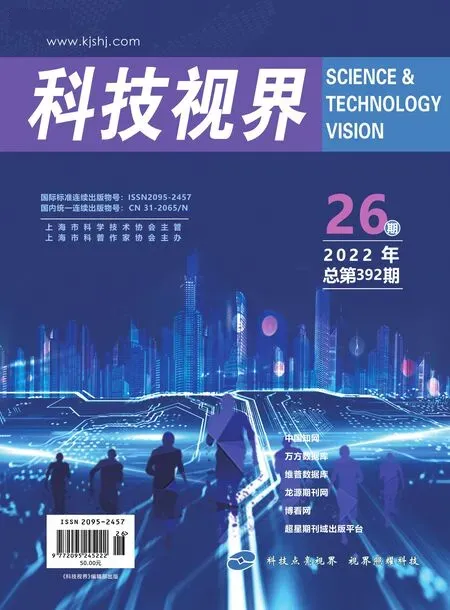在“全流程大項目”思路下構建電競課程體系探究
方 俊 楊金霞 張 博 胡肖璇 張紅蘭
(北京京北職業技術學院,北京 101400)
0 引言
自2003年電子競技作為國家體育總局確認的第99個體育項目,至2008年重新調整為第78個項目,“電子競技”正式步入“官方認可”視野以來,國內電子競技事業一直蓬勃發展。
2021年以來,電競產業的數字化優勢仍然在持續,各地對行業提出了規范化的要求。從各個省市公開的政府網站中可查閱到的相關政策實施意見頻出,如2021年1月廣州市天河區印發《廣州市天河區關于扶持游戲產業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的通知;3月北京市海淀區印發《關于促進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科技創新片區海淀組團產業發展的若干支持政策》;4月江蘇省蘇州市印發《關于促進太倉市電競產業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6月上海市靜安區發布《靜安區關于促進影視、電競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8月國家新聞出版署下發《關于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通知》;以及到目前為止電競作為正式比賽項目進入杭州亞運會。
2017年6月由華體電競主編的《電子競技場館建設標準(征求意見稿)》發布。2018年8月由聯盟電競起草的《電子競技場館運營服務規范》發布。2019年8月“2019全球電競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上發布了首個《電競場館建設規范》和《電競場館運營服務規范》。2020年人社部發布《國家職業技能標準—電子競技員》(職業編碼4-13-99-01)、《國家職業技能標準—電子競技運營師》(職業編碼4-13-05-03)。2021年4月由完美世界發布了《電子競技賽事運營職業技能等級標準1.0版》。
由此可見,電子競技已擺脫“蠻荒時代”,進入體制化、系統化、規范化發展階段。
1 電競行業與專業特點分析
1.1 行業特點
以現象級MOBA端游“英雄聯盟”為例,該項目于2011年正式進入中國至今僅有十多年光景,而同樣在國內成為現象級的手游“王者榮耀”電競比賽的發展也只有幾年的時間。可見電競行業相比于其他傳統行業,仍屬于新興行業。各載體項目的角色調整、數據平衡與版本更新頻繁;各電競俱樂部此消彼長、興衰更替;明星選手不斷新老迭代;每年行業規模與用戶量屢刷新高;種種跡象表明電子競技的蓬勃發展,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向全社會詮釋其新興行業的特征。產業鏈與人才培育體系雖已成形但仍處于不斷調整與完善中[1]。
1.2 專業特點
教育部于2016年9月發布了職業教育專業增補目錄,明確了《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專業的開設許可并于2017年起執行。
行業的特點影響甚至決定了專業特點,首先“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是一個新專業。根據教育部職成司提供信息顯示,2017年的專業開設檢索結果為19條,而2021年則達到144條。雖然開設本專業的院校數量逐年增加,但現存的且較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新時代背景下新專業本身一系列的短板,具備諸如“節奏快、變化多、吃政策”等特征的專業在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勢必無法像傳統專業那樣,有諸多原理、公式、模型等“亙古不變”,顯然“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專業不便從現有的傳統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和方案中借鑒,需要探索出一條全新的道路。
所以能夠確定的是,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專業特點的研究和明確,構建有別于傳統專業并能適用于電競專業的科學、合理、全面、正確、高效的課程體系以保障人才培養質量,對為行業和企業輸送人才、對職業標準制定和優化,甚至對社會經濟發展都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2 人才培養探究與課程體系構建
2.1 人才培養思路
在明確行業及專業背景和特點之后,建立更科學、合理且契合行業特點的電競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專業課程體系,是人才培養建設與推進的重要一步。
從電子競技生態結構分析,“電子競技賽事”始終是整個生態的核心。即如果各種類型、級別賽事取消,整個電競生態隨即瓦解。所以在人才培養模式和方向上,緊緊抓住“電競賽事”這一核心要素,構建整個人才培養體系,通過課程打通整個賽事流程各階段、環節和元素等,如此便符合了電競產業生態的結構特征和滿足了以賽事為核心的行業崗位人才需求。
以賽事為核心的電競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可視為在效仿一家專業承辦電競賽事公司的運營模式:一個電競專業班級相當于一家賽事公司,學生在校三年的學習過程即相當于賽事公司在執行一場大型電競賽事,賽事公司在賽事執行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和流程便可演化為不同學習階段和學習項目,每個流程、環節或崗位對應的職業能力要求亦可演化為對應的知識、技能和素養。于是三年期人才培養過程視為一場“全流程大項目化”的電競賽事的思路便順理成章。同時充分認識到企業在市場中所遵循的“生存法則”而產生的制度、管理、流程優勢亦可借鑒至電競專業人才培養,使人才培養過程具備“企業行為”特征,高效、機動、靈活。
2.2 課程體系構建
課程體系是人才培養實現的重要載體,所以在人才培養模式的思路設計上,緊緊抓住“電競賽事”這一核心,以培養學生賽事能力為目標,圍繞賽事構建整個課程體系。為了更高效地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打破傳統學科課程體系構建的思維模式,以能夠完成具體的電競賽事落地為目標。
根據實際的賽事執行,將人才培養這一“全流程大項目”分為“賽前、賽中、賽后”三個大型“輪崗項目”,即學生需要以“輪崗的方式”走完三個項目的流程,當完成了三個項目之后也象征著學生完成了整個校內的學習生涯。整個“大項目”包含賽前學習項目、賽中學習項目、賽后學習項目;每個學習項目又包含若干學習“子項目”,同時每個學習子項目實施又以工作任務為導向的任務驅動法開展若干學習任務進行學習。
這樣帶來的好處是一方面能夠比較完整的實現電競專業與市場需求對接,隨著市場內容的進一步細分,課程體系也可以進一步細化。另一方面產業鏈由于外因發生的調整,在課程體系結構中也可以快速聯動,不會影響其他相關課程;不像傳統課程體系結構那樣,某一門課程取消開設之后就不得不考慮知識的連續性和系統性。
這一構建形式,能使項目化課程內的各教學任務“靈活多變、適應性強”,能與行業同步發展,可移植性高。通過創新課程體系,幾乎所有項目化課程均是電競賽事中的一個元素或一段流程,所有課程均配備實際操作環節,理實一體化教學率幾乎接近100%,學生每完成一個學習任務的成果,馬上會成為下一個學習任務所需要的基礎,以此環環相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學生學習效果。
3 實施策略
具體實施中,以培養電競賽事職業能力為目標,借鑒“企業行為”,構建“全流程大項目化”的人才培養模式;深化“崗課賽證”,制訂電競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按照崗位職業能力要求,創建“三個平臺、多項能力、輪崗實踐、一專多能”的教學體系;以學生為中心開展教學,創建以工作任務為導向的“情境教學+綜合實訓+頂崗實習”教學模式,實施基于項目化課程的理實一體化授課方式。借鑒企業的市場行為模式確定專業的學習組織形式。
根據“電子競技運營師”職業標準中的技能等級要求,對接全流程賽事具體工作任務,并逐一落實到“緊密聯系、環環相扣”的項目化課程中,并將崗位任務中的能力要求拆分到每個項目化課程的具體知識點、技能點和素養點上,培養學生綜合能力;通過學生自辦賽、承辦賽、參加賽的形式檢驗項目化課程設計與崗位對接的合理性、各項目銜接的邏輯性、項目化課程內部知識結構的科學性與正確性,輔以“第二課堂”建設強化學生思政素養,實現“課程思政”與教育教學同向同行;學生在完成項目化課程學習之后不僅掌握了知識、技能,培養了素養,還能夠得心應手的參加“電子競技運營師”的職業資格取證考試,為實現“1+X”證書制探明了道路。學生在實現“崗課證”融通的基礎上,亦具備參加職業技能大賽的基本能力,最終實現在“崗課賽證”之間建立“相輔相成、相互印證、齊頭并進”的綜合性橋梁。
如此,“全流程大項目化”人才培養模式中所有學習任務均來自真實賽事執行流程,使學生在真實的學習情境中綜合運用前一學習項目或任務中掌握的知識和技能,解決本項目或任務的具體問題,進而形成扎實的崗位知識和崗位技能,感受真實的工作氛圍,體驗真實的企業文化,最終掌握職業知識和職業技能,形成就業所必需的職業能力,培養出成品型人才,實現“零距離”就業的人才培養目標。
4 實施效果
創新型人才培養方案和“大項目化”課程體系構建,較好實現了一個全新的專業與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更好的接軌,課程體系架構更加靈活、更加具體、更具有可執行性,學生學習成果與工作崗位需求可更好的對接,“專業背景匱乏”的師資亦能夠快速適應新專業并完成教學任務,設計和建設“性價比”更好、使用效率更高、更緊密結合教學過程并能將理論付諸實踐的實訓場所。如此,方案具備了更加科學、完善的“教、學、做、考、評、改”的閉環屬性。
通過對在校班級、實習班級、畢業班級的整體數據統計分析來看[3],能夠有效規避當前電子競技專業人才培養在培養模式、培養方向、培養經驗等方面積累不足的問題;能夠最大限度地緩解新專業在辦學和建設方面存在的師資問題、課程問題、教材問題、教法問題等方面的矛盾。同時,在構建此創新人才培養內容時,系統性實施課程改革、教法改革、教材改革、“第二課堂”建設、學生社團建設等[4],能夠及時、動態、扎實貫徹《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和北京市《關于深化職業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等文件要求,保障人才培養能力和水平;在較好實現與立德樹人同向同行、深入探索“崗課賽證”融合育人模式、創新發展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模式、持續深化教師、教材、教法改革等方面,為電子競技行業人才培養積累了明確、系統、規范的階段性成果與經驗,且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和移植性,能夠作為同類院校或相近相關專業建設與人才培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