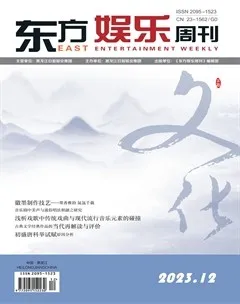張暖忻電影探索路徑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王慧萍
[ 關鍵詞] 張暖忻;女性形象;女性意識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一掃昨日沉積,迎來了多元煥新的創(chuàng)作格局。在各放異彩的影片爭鳴中,張暖忻以獨特的銀幕氣質(zhì)與敏銳的藝術感受成為中國電影史中一顆寶玉明珠。統(tǒng)觀張暖忻僅有的幾部電影作品,獨特而各具魅力的女性形象是影片重要的敘事主體,也是作者鮮明的個人印記。銀幕內(nèi)的女性形象與銀幕外的“女性導演”身份合力構成了張暖忻電影中潛在的女性意識。然而,無論是導演本身對于性別身份的不看重,還是其更為強烈而多元的藝術訴求,都使得這份女性意識顯得更為幽深朦朧。
一、審美重塑中的個體自述
作為“第四代導演”的理論宣言,《談電影語言的現(xiàn)代化》的橫空出世,實質(zhì)是中國電影在觀念、思想上滿足現(xiàn)代焦慮與革新訴求后的一次累積爆發(fā),也是中國進入新階段時各種社會思潮涌動、氣象更新所凝聚的一次明文表征。這種求新、求變的訴求隨后從理論走向了實踐,從文字走向了銀幕,從張暖忻自身走向了“沙鷗”與“李純”。
非職業(yè)演員所具備的全新審美與個性氣質(zhì)深化進故事角色之中,“沙鷗”從外到內(nèi)完成了一次“銀幕新人”的塑造。張暖忻在選角時曾陷入兩難的抉擇:到底是“選專業(yè)演員,然后訓練她打排球”,還是“選擇排球運動員,培養(yǎng)她演戲”[1]。基于對“生活流”“紀實性”的美學追求,張暖忻最終選定了曾是排球運動員的常姍姍。而在常姍姍的自述中,在定她為“沙鷗”一角后,攝制組中就出現(xiàn)了不少質(zhì)疑,“總而言之,嫌我長得不好看”[2]。張暖忻則認為這種對于形象外貌上的挑剔是“出于一種習見的、有些陳舊了的審美觀念”[1],而在破除這些審美傳統(tǒng)的同時,她所想要抓住的是來自常姍姍的性格美、精神美。“有勁”“有性格”“真實性”,此類人格上的魅力在超越傳統(tǒng)審美標準之時,也順勢符合了影片中沙鷗這一形象所蘊藏的個人激情與執(zhí)著堅韌。
在這之前的多數(shù)體育題材電影當中,往往會將競技比賽中個人的源驅力引導向國家維度,而作為運動員對于勝利的天然渴求被忽視。《女跳水隊員》宣揚只有拋開個人得失利益,建立起為祖國、為人民這一崇高思想后,一個運動員才會變得更為堅強和勇敢。在《女籃5 號》中,林小潔剛出場就是一個將個人前途和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脫軌”角色,而最終在男主人公田振華的領導與教育下回歸到了集體主義的軌道上。與之不同的是,沙鷗在警惕“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便勇于直言“誰不想當冠軍,誰就不是好運動員”,顯示出天然的個人競技意識,以及對于冠軍榮譽的渴求。借助這一從內(nèi)到外都嶄新的銀幕形象,導演將個體從早期的詢喚中釋放出獨立的精神人格。
在《青春祭》中,初到傣鄉(xiāng)的李純總是身著一身藍灰色工裝,游離在那群美麗自然的、穿著筒裙的傣族姑娘之外。相較于花哨豐富的傣族服裝,此時李純單一、暗沉的服飾以去性別化的方式隱喻著一套截然不同的審美體系。無論是“不美為美”“勞動為美”,還是“樸素為美”,“美”在漢族傳統(tǒng)文化與時代語境中被認為一種與道德、政治息息相關的符號,被裹纏在其中的除了美好的女性身體之外,還有女性對美的渴望和追求。以服飾為顯性符號的直觀美麗沖擊著李純陳舊的觀念。在意識到“美原來那么重要”后,李純開始了對自我、對性別的反觀與審視。最后,李純穿上了傣族的筒裙,在異鄉(xiāng)通過另一個民族的服飾完成了審美的重塑。偏居一隅的地理與文化共同構建了一個夢一樣的歷史時空,同時也成為“自我意識”重生的沃土,隨著美的重新回歸,人性脫離重負,得以短暫地張揚自由。
學者王玲珍認為,以張暖忻為代表的這一代女性導演在經(jīng)歷失語的十年后,往往通過銀幕上他人的故事迂回展現(xiàn)自己的“女性個體視點,強調(diào)女性主觀經(jīng)驗和情感的再現(xiàn)模式”[3]。張暖忻的影片最終也“成為一種創(chuàng)作者個人氣質(zhì)的流露和感情的抒發(fā)”[4]。《沙鷗》和《青春祭》中對人物內(nèi)心、回憶的視覺化展現(xiàn),意識流為線索的敘事方式,以及內(nèi)心獨白等設計,以都使得導演的主體位置與銀幕上的女性形象完成疊印與重合。沙鷗與李純都被重塑為一個全新而自覺的女性個體,不忌憚自己對勝利或美的多重欲望,而這種“自我意識”也正是同樣歷經(jīng)十年壓抑的張暖忻所投射在銀幕上的個體私語。
二、愛情抉擇下的時代隱痛
自《北京,你早》開始,這種導演的主觀自述似乎逐漸退回到一個更為客觀的立場。大時代下,小人物成了張暖忻電影當中新的主題。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一切舊的、固有的、單一的觀念模式逐漸被撼動、瓦解,而許多更為新興多元的事物與思想浮現(xiàn)出來,新舊元素被同時放入這一時期的社會之中,相互碰撞摩擦產(chǎn)生劇烈的反應,身處異動與轉變的人們也隨之變得躁動不安、彷徨糾結。在張暖忻的影片中,各類女性角色不僅對這一錯動更為敏感,她們所陷入的愛情抉擇在作為影片情節(jié)主體的同時,也成為千萬個躁動靈魂的生動隱喻。
二選一的愛情模式甚至可以算作導演鐘愛的一個敘事“母題”。沙鷗在“結婚”與“拿冠軍”當中取舍,李純則朦朦朧朧地搖擺在大哥與任佳之間。在后續(xù)的幾部作品當中,艾紅與鄒永強分手后投入了克克的懷抱,本來是董事長情人的梁小姐卻又不自覺被袁方吸引。然而,不同的是,售票員艾紅的情感變化與得失取舍進一步成為《北京,你早》中的敘事焦點,她在抉擇中的所思、所想、所為也正像一面鏡子,折射出時下青年的價值取向與心理變化。
鄒永強和起初的艾紅一樣,盡管有著對新事物的向往和躁動,但都屈從于職業(yè)體系所安排的既定路線。“車二代”鄒永強難以脫離支撐起整個家族的體系結構,而艾紅則是苦于缺少邁入另一個世界的敲門磚。在一切仿佛都無力改變、求變無門后,克克隨機而又偶然的出現(xiàn)成了艾紅走向幻夢生活的一個契機。對艾紅來說,掙扎在克克和鄒永強之間,其實就是焦灼在新與舊的兩種生活之中。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傳統(tǒng)的生活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興價值觀念的沖擊和碰撞,而張暖忻觀察到,此時的大多數(shù)青年就如銀幕上的艾紅一樣“都面臨著自身固有位置的傾斜”[5]。
在以主旋律為基調(diào)的《南中國1994》中,更為出彩的依舊是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其中,梁秘書陷入的是物欲和情欲的兩相抉擇。從一出場就已經(jīng)化身“妞妞”的梁憶帆已然選擇了一種物欲做主導的生活。隨后,梁憶帆與袁方之間又涌動著真實而自然的男女情欲。然而,當袁方闖入梁憶帆的秘密二樓后,背景墻上巨大的董事長畫像就如整個富足豪華的別墅一樣,構成了此刻董事長不在場的在場,也喻示著物欲世界對個體的分裂和傾軋。影片最后并未清楚地交代梁憶帆的去向,然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女性角色的身上看到一種回答。原本善良勤勞的女工金翠花為維護自尊憤然出走,而最終卻以一襲性感衣裙、艷麗妝容的形象返場,這和她與梁憶帆的相遇則形成了一種鏡像式的對照。男女之間的性別關系被經(jīng)濟關系取代,在日益膨脹的物欲下,女性群體的社會處境及思想觀念在經(jīng)濟文化與物質(zhì)思潮的沖擊下面臨著傾斜和置換。
張暖忻擁有著敏察時代的女性感受力,同時又癡迷著大時代下的小故事,因而在她鏡頭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承擔著時代錯動的分裂與徘徊。然而,同樣作為面臨著多個選擇而催生出多重欲望的女性形象,相較于艾紅來說,梁小姐身上的女性的主體力量大為消減,艾紅迎面時代的進程大膽前進,而梁小姐卻沉溺于物質(zhì)金錢,難以做出符合自己真實情欲的選擇,我們從這樣一種女性力量的削減與被剝奪中可以捕捉到張暖忻作品中女性視角的漸趨弱勢。
三、銀幕探索中的女性意識
作為在20 世紀80 年代十分活躍和突出的女性導演群體的一員,張暖忻及其電影創(chuàng)作在“女性電影”的視野下總是處于尚有缺憾的一方。“女性電影”作為一種源自西方的學術思潮,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漸與“反電影”或“少數(shù)電影”等具有顛覆力量的概念內(nèi)涵緊密融合[6]。因此,以“女性電影”為研究支點的評論家往往期待一種更為自覺、女性內(nèi)觀視角更為明顯、父權意識形態(tài)批判力度更大的女性電影,力圖尋找作為“邊緣的或反電影(anti-cinema)嘗試者與挑戰(zhàn)者”[7]的中國女性導演。顯然,張暖忻電影當中的女性形象并非一類邊緣人群或者擁有反抗力量的存在,其中的女性意識往往只被視作“女性朦朧、含混的自陳、影片特定的情調(diào)與風格”[7]。
在吳冠平對話張暖忻的訪談中可以看到,張暖忻并不想刻意地去強調(diào)女性的立場,而是以“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和我自己的藝術體驗去完成創(chuàng)作”[8]。張暖忻的這一性別觀念有其歷史淵源和文化語境。張暖忻導演所在的是一個由政府參與、由上至下地推進和實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意義上的男女平等”[7] 的時代,“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一樣能做到”的語錄及觀念深入人心,而銀幕內(nèi)的文化建設則與官方話語高度一致,性別特質(zhì)的話語書寫不斷被遮蔽、被忽視。因襲在這樣一個語境中誕生的女性文化,張暖忻的創(chuàng)作沒有成為一種基于性別自省的自覺探索。不僅如此,張暖忻對藝術、文化和時代的訴求在壓抑數(shù)年后顯然更為迫切,女性意識便在各方的平衡和考量中退居一旁。我們可以從《云南故事》當中樹子這一失衡的女性形象看出張暖忻在電影創(chuàng)作當中所力求把握的多重元素。
《云南故事》可以看作《青春祭》在新階段的一次變奏,影片講述了一個戰(zhàn)敗后被留在中國的日本女人樹子的故事,一個國家近40 年的歷史風云被高度濃縮在了這一女性形象身上。從日本戰(zhàn)敗這一歷史節(jié)點開始,樹子經(jīng)歷了遣返政策的實施、中日建交等重大事件,就像是一個浮標借以淺淺錨定歷史深海的崎嶇坎坷,她的命運書寫的其實是政治文化的變遷,女性自身的成長轉變和情感的波動起伏則變得十分被動。
由此,樹子成了一個被國家話語、歷史敘述沖淡后顯得空洞又漂浮的女性形象。但這也凸顯出導演在創(chuàng)作中如何將個人藝術訴求與“主旋律”相融的這一課題。在之前的影片中,張暖忻并非將政策、國家意志以一種教條化的方式進行宣傳述說,而是選擇貼近大眾,反映現(xiàn)實社會,展現(xiàn)時下生活狀態(tài),致力于達到一種能夠在社會底色當中奏響的“主旋律”。因此,“如何被大眾喜歡”則又使得張暖忻將創(chuàng)作的天平放在了藝術與商業(yè)之間,然而越發(fā)趨于主導地位的商業(yè)性也使得張暖忻在電影探索上顯得有心無力。云南的故事續(xù)寫到1993 年已經(jīng)難以再是一個純粹的、抒發(fā)個人意志自由的“異托邦”神話,女性身體承載的也不再是審美意識的重生,樹子游離在兄弟之間的愛情故事已成為一種女性的敘事奇觀。與此同時,樹子所天然攜帶的美麗、善良、情感等美好品質(zhì),更像是一個完美女性的抽象化身,成了滿足男性想象的觀賞品。除此之外,由于《云南故事》的一部分資金是由臺灣公司提供的,資方規(guī)定男女主人公需要由臺灣明星出演[9]。因此,在云南村寨生活的日本遺孤樹子有著濃厚的臺灣地區(qū)口音,這不僅與她所處的族群環(huán)境格格不入,也不符合角色國籍身份的設定,在樹子這一女性角色的身上重疊混雜了銀幕內(nèi)外多處相異的話語,女性主體由此再度被各方消解和分割。
在張暖忻于時代的探索中,電影商業(yè)性的日益凸顯使得張暖忻越發(fā)努力地在藝術性與大眾性之間形成對話,但在《云南故事》中,女性主體被各方消解,女性視角被男性視角置換遮蔽,在主旋律與商業(yè)性成為主流電影越發(fā)奏響的強音之際,張暖忻卻難以在其中的縫合與平衡中尋找一個回歸自我、對話觀眾的路徑。
四、結語
在張暖忻的影片中,充滿人性真情的女性形象成為張暖忻銀幕探索的重要部分和獨特標志,成就了其真實而動人的美學風格,同時在社會的不斷發(fā)展變化過程中,張暖忻借用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歷史、民族、時代展開對話,以期回答文化、電影藝術等宏觀層面的議題。但這位女性導演并沒有對自身進行強有力的性別身份建構,也沒有對女性的身體、情感和命運進行向內(nèi)的自省和剖析,這導致張暖忻女性書寫的脆弱性。因此,在后期的創(chuàng)作中,女性主體和視角便讓位給了由更為強勢的宏觀話語與趨于男性視角的大眾趣味所構成的外部世界。然而在當下,女性主義、女性電影的邊界正在不斷拓寬,甚至開始與商業(yè)性、大眾性接軌,進而試圖進入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結構之中。再度審視張暖忻導演的這一條在女性與觀眾、國家之間力趨平衡的探索路徑,或許能夠為女性電影的顯現(xiàn)和創(chuàng)作提供更有力的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