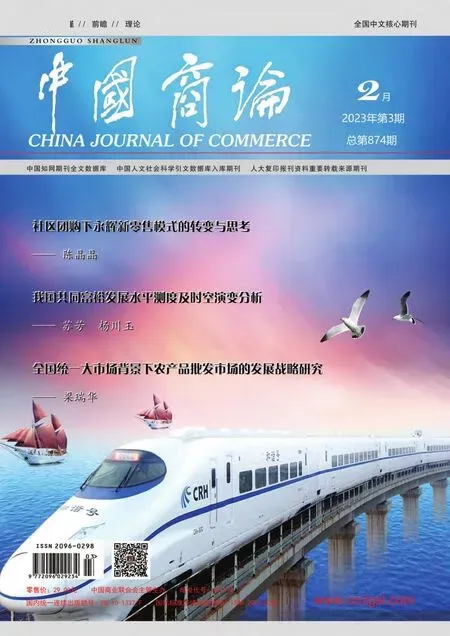新冠疫情前后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黃思穎
(華南師范大學數學科學學院 廣東廣州 510631)
由于國內與國際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人民幣匯率也在不斷波動。2010年6月,我國宣布繼續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出現明顯升值,而2015年8月我國進行下一輪匯改時,人民幣出現了貶值,匯率上升。直至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發后,人民幣又開始出現小幅度升值,匯率下降。
2010年1月—2021年11月的人民幣匯率波動情況如圖1所示。

圖1 人民幣匯率波動情況
人民幣匯率是衡量我國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若人民幣發生貶值,會使我國國內經濟形勢面臨很大壓力。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素分析,國內很多學者使用不同的模型做過相應的研究,但其方法大部分為基礎的計量經濟學模型。例如,李浩寧(2021)使用VAR模型探究了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素;李禧龍(2021)使用多元線性回歸討論了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素。
目前,探究新冠疫情發生前后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變化的文獻不多,故本文為了探究各變量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采用RT方法對變量重要性進行分析,依此建立了加入新冠疫情影響前后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1 數據準備
本文選取貨幣供應量(x1)、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x2)、國家外匯儲備(x3)、中美利差(x4)、中美CPI差值(x5)作為變量研究人民幣匯率(k)變動的影響因素。選取的數據為2014年1月—2021年11月的月度數據,本文的所有相關數據均來自choice金融終端。由于貨幣供應量和國家外匯儲備的數據較大,為了防止回歸時產生較大誤差,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取自然對數的處理。
2 模型建立與分析
2.1 OLS回歸
為了初步查看回歸效果,本文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研究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素,建立的初始模型如下:

對數據進行OLS回歸,得到的回歸結果為:

該模型的R2=0.807669,F=74.74886>F0.05(5,89)=2.317,故認為人民幣匯率與上述變量間總體線性關系顯著。但其中,x2、x5前的參數估計值未能通過t檢驗,說明模型中存在問題,因此需要再對模型進行檢驗與改進。
2.2 多重共線性檢驗與逐步回歸
2.2.1 相關系數熱力圖
由前文的初步分析可以猜測,模型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需要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本文計算得出各解釋變量間的皮爾遜相關性熱力圖如圖2所示。

圖2 相關性熱力圖
由此可以發現,貨幣供應量和中美利差、PMI與中美利差、PMI與CPI差值等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比較大,因此該模型存在多重共線性,具體還需進一步檢驗。
2.2.2 變量重要性分析
本文采用機器學習方法中的集成學習回歸方法對各變量的特征重要性進行分析,從而更加客觀判斷各變量的重要性,利用RT進行回歸學習,為變量重要性得分創建條形圖以直觀觀測(見圖3)。

圖3 RT方法計算變量重要性條形圖
由圖3可以發現,lnx3對y的影響最大,且顯著大于其他變量,也就是說,國家外匯儲備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程度最大。其次是貨幣供應量、中美利差、CPI差值及PMI,且PMI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顯著小于其他變量。
2.2.3 逐步回歸
由于本文所選的變量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構建回歸模型。
考慮到國家外匯儲備對匯率的重要影響,本文考慮先保留lnx3,再逐個加入其他變量進行逐步回歸。保留lnx3時,其回歸函數為:

其R2=0.681289,F=198.8002,可見國家外匯儲備對人民幣匯率的解釋力度很大,結合前文變量重要性的分析,顯然可以確定該變量不能刪除。
因此,依據逐步回歸的思想,在固定保留lnx3的基礎上,逐個加入其他變量,發現加入x5,即中美CPI差值時效果最佳,其R2上升為0.780291,回歸函數為:

結合前文變量重要性的分析,可以說明中美CPI差值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較大,且加入模型后不會出現多重共線性的現象。
因此,本文保留x5,在此基礎上逐個加入其他變量,發現加入lnx1,即貨幣供應量時效果最佳,其R2上升為0.806719,回歸函數為:

因此,在原有模型的基礎上增加lnx1變量,可以增加模型的解釋力,且不會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
此時,若再引入其他變量,模型的解釋效果會下降,且變量無法通過t檢驗。這說明在本文所選的五個變量中,lnx1、lnx3以及x5就可以對人民幣匯率k有很強的解釋力,且變量之間不會存在多重共線性。綜上所述,此時該模型擬合結果最佳:

2.3 異方差性檢驗與修正
除了去除多重共線性的干擾之外,還需要對該模型進行異方差檢驗,避免模型出現異方差性,從而影響模型的評估效果。
因此,本文采用eviews7.2進行檢驗,其檢驗結果如圖4所示。

圖4 懷特檢驗結果
顯然,在檢驗結果中,0.0385<0.05,故可以認為模型存在異方差性,因此需要對異方差性進行修正。本文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以提高參數估計的精度。
為了選取效果最好的權數進行加權最小二乘法,本文通過了很多嘗試,最終選擇了

作為權數進行加權回歸,其回歸結果為:

此時的R2上升為0.861269,F=188.3153,說明該模型的擬合效果很好。此時再對該模型進行懷特檢驗,其P值為0.3665>0.05,已經不存在異方差性。因此,本文最終建立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綜上,在該模型中,最終僅保留了貨幣供應量、國家外匯儲備及CPI差值三個變量。從模型效果可以發現,這三個變量可以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較好的解釋說明,且該模型滿足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的基本假設,對被解釋變量有很好的解釋度。
3 考慮新冠疫情影響的模型
3.1 變量重要性變化分析
為了考慮新冠疫情對國家匯率的影響,本文將2020年開始的數據進行分析,繪制變量重要性條形圖(見圖5)。

圖5 RT方法計算變量重要性條形圖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各變量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程度有了很大改變,可以說明在新冠疫情爆發后,各變量的重要程度也相應發生改變。
3.2 加入虛擬變量的OLS回歸
為了解新冠疫情對模型的影響,本文引入虛擬變量D。2020—2021年的數據中,令D=1;2014—2019的數據中,令D=0。
由于lnx3依舊是重要變量之一,本文同樣選擇優先保留lnx3,再逐個加入解釋變量,按照與前文同樣的方法進行逐步回歸,再同樣進行異方差檢驗,可得到其P值為0.0497<0.05,可以說明該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因此,該模型的最終回歸方程為:

觀察結果可以發現,斜率差異系數在統計意義下為顯著,說明在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發之后中美CPI差值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機制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2019年末,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美CPI差值每增加1%,人民幣匯率比2019年之前多增長0.006796。
4 結語
綜上所述,貨幣供應量、國家外匯儲備及中美CPI差值這三個變量都對人民幣匯率具有顯著的影響。其中,貨幣供應量與人民幣匯率呈正相關關系,國家外匯儲備與人民幣匯率呈負相關關系,而中美CPI差值與人民幣匯率呈正相關關系。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后,以2019年為節點,中美CPI差值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機制有所改變,各個指標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且整體來看,人民幣匯率有所下降,即人民幣出現升值的趨勢。
根據結論進一步完善外匯儲備的管理制度,合理對外匯儲備進行管理及建立健全的貨幣政策,使國家外匯儲備、貨幣供應量及CPI處于較為合理的水平,對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