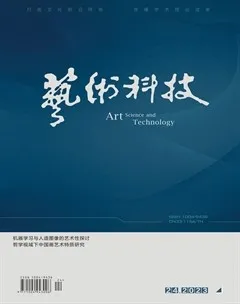清代男耕女織年畫的圖像研究
孫云麗 張力麗

摘要:目的:男耕女織年畫包括農耕與紡織兩大類,文章結合清代歷史對當時的耕織年畫進行分析,主要探究耕織年畫的藝術特色及成因,從中感受到我國傳統民間藝術歷久彌新的魅力。方法:通過文獻調研法和圖像學方法,對這類年畫進行收集、歸納與梳理,比較同一主題下不同年畫的異同之處,從題材、功能、構圖等角度分析其圖像元素與造型特點,探析圖像設計背后的思想內涵。結果:文章闡述了耕織年畫的畫面內容,分析了男耕女織這種生產模式在清代盛行的原因,探討了男耕女織年畫圖像在政治社會中的價值與意義。男耕女織年畫以描繪事實為主,從宮廷至民間,其中蘊含的承襲關系影響深遠。耕織年畫具有教化民眾與科普耕織技術的作用,作為具有象征意義的民俗符號,在農耕文明時期扮演著重要角色。結論:此類年畫是珍稀的民間藝術品,深受民眾喜愛,值得對此進行研究,并在當今社會傳承與發揚,同時其是研究清代農業史記、藝術史、經濟史、民間生活與習俗等多方面的寶貴資料,更是民眾對穩定生活的渴望,是統治者對民眾施行教化的一種方式。
關鍵詞:男耕女織年畫;圖像;清代
中圖分類號:J21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24-00-03
0 引言
我國的農耕文化歷史悠久,以農事活動為主題的圖像起源較早,各個朝代都有大量表現耕織、畜牧等活動的圖像。它們分散存在于畫像石、墓室壁畫、農書、風俗圖像之中,印刷技術的成熟使清代年畫盛行。在種種農耕圖像載體當中,年畫是最具有民間氣息的,其取材于民間,在農村的普及度較高,是研究農耕文化的典型藝術代表,反映了耕織在當時社會的重要性,同時是人們了解清代文化和社會機制的一種途徑。
1 男耕女織年畫圖像分析
男耕女織相關主題的年畫體裁豐富,涵蓋貢尖、門畫、三裁、歷畫、中堂、橫批、燈畫等。年畫的體裁形式是根據張貼的位置與功能來制作的,從體裁可以看出,這類年畫散布在民眾居所的各個角落,通過對這些年畫進行分析,以小見大,能深入了解清代的耕織發展與各地民眾的習俗。
1.1 耕織年畫內容
從畫面內容來看,主要有耕織勞作、喜慶豐收與祭拜神像這三大類。
耕織勞作類大多取材于人們熟悉的勞動場景,把所有季節性活動或耕織全過程合并到同一個場景中,形成系列化的勞動情形,并采用圖像與文字相結合的方式對畫面內容進行說明。男耕類年畫反映了男性從事田間勞作,包括耕地、播種、鋤地、蹲苗、收割等10余種勞動生產過程,附帶扛、捧、推、挑等搬運動作。女織類年畫呈現的是女性進行各類紡織活動,并帶有育兒活動。典型的是清末楊家埠世興畫店的《男十忙》與《女十忙》,兩張為一套,運用分層排列的構圖方式和鮮明的動態打破時空限制,采用云線分割場景和扁平化的繪畫技法,具有概括性與系統性。耕織年畫除了描繪常見的耕織勞動之外,還會根據當時的社會道德需求對畫面內容進行延伸,女性從紡織場景延伸到教子場景,加入了三娘教子等具有普世性的戲曲情節,放置于畫面中心位置,引導女性遵從“相夫教子”的道德準則,場景描繪也更加精細。
豐收類年畫主要是表現稻谷、蔬菜或瓜果的收獲場景,體現當時物種的豐富,整個畫面洋溢著勞動者的喜悅,慶豐收年畫皆有題詩,勉勵農人勤勞不誤農時。谷物豐收年畫的共同特點是在畫面中表現豐收場上人們的忙碌與和睦,其中穿插描繪碾場、揚場、裝袋、入倉等情節,婦人在一旁照顧孩童,老人或觀望或指揮,一片祥和之景。這類代表作有《同慶豐年》《莊稼忙》《農人自樂》等。
天津楊柳青《莊稼忙》與山西曲沃《男十忙》(見圖1)都描繪了收麥子的場景。《莊稼忙》可分為近景、中景、遠景三個部分,最前方散落著石磙、木叉子、鐮刀等11種農具以及壺和碗。在一塊平整的場地上,還沒有脫粒的小麥平鋪在地上,旁邊是兩個中年農夫,一人手持木锨揚麥粒,一人手持笤帚掃去糠草。畫中人物形象俊美秀麗,色彩樸素雅致。曲沃《男十忙》對場景進行了分割,一張豐收主題的年畫中包含了不同的子主題,楊柳青的豐收年畫著重對豐收這一大場景進行描繪,并沒有子主題的拓展與場景的分割,畫中男性都著短衫短褲,寬松利落,便于干農活。
神像年畫中的神仙取自道釋諸神以及人們想象出的各行各業的保佑神。在耕織技術并不發達的年代,耕織受天氣、病蟲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較大,人們通過祭拜神靈來祈求風調雨順和豐收。常見的神像畫面主神多為土地神、倉神與蠶神,還有與農耕相關的牛王、馬王、圈神等。紡織在小農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民間養蠶人家有貼蠶花年畫和祭拜蠶神的習俗。蠶神以女性形象為主,稱為蠶花娘娘、蠶姑、蠶皇老太等。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蠶神的供奉具有地域特點。江蘇、上海、浙江一帶供奉蠶神“馬頭娘”,亦稱馬明王。江蘇桃花塢《蠶花茂盛》畫面正中的馬頭娘坐在花斑白馬上,頭戴花冠,身穿裙袍,雙手捧著一盤圓潤的蠶繭,后有一侍女舉“馬明王”旗跟隨,四邊有著銅錢紋樣。山東濰縣萬盛畫店神祃《蠶姑宮》由上至下分為四個部分,頂端題詞,上端刻印蠶姑宮神龕,里面端坐著蠶神嫘祖及左右兩位陪神,嫘祖手上有一潔白碩大的蠶蟲,以香案隔開人與神的世界,下有民間婦女側身飼蠶,底部的高宅大門刻著萬盛畫店的名稱,兩側婦女帶著孩童采摘櫟葉,新絲上市時節,蠶農會張貼《蠶姑宮》祈求新絲賣個好價錢。
民間農業與紡織業信仰的神祇繁多,蠶神信仰是一種典型的多神崇拜體系,同一地區可能存在人神信仰、動物崇拜、佛教信仰、道教信仰等多種形式并存的狀態,一戶蠶農可以有多種信仰,這種多元共生的信仰圖式源自人們世俗功利的動機,尋求神祇的多重保護。
1.2 耕織技術與工具
我國傳統農具特別是大田作業農具,在秦漢時代已基本完成,農具的大類相對穩定。到隋唐五代時期,我國傳統農具發展格局基本形成[1]。年畫中所用的農具與前朝農具相比鮮有創新,清代是中國歷史上農業技術專業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如梯田耕作和灌溉系統的推廣,使農民能夠在陡坡和干旱地區耕種。這些創新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時期人口糧食問題。相比之下,紡織業起步較晚,清代各地《女十忙》年畫中所繪的紡織工序相差無幾。據清中葉陜西鳳翔《女十忙》的描繪,已經出現從軋棉、彈花、搓棉條到整經、織布的全過程,其中在軋棉這一環節,僅需一人便可將棉花從棉籽和棉纖維中分離出來,并保持棉纖維的整潔。從工具進步來說,清代紡織工具相較之前所用人力更少,機器的改良對提升紡織效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從各地年畫中可以看出紡織操作的簡易性和紡織工具在民間的普及程度。
1.3 地域差異與表現
年畫作為一種民間藝術,不論在表現內容還是色彩、體裁、用線、精細程度等方面都有地緣性。年畫的題材更多受當地經濟、文化、社會民俗等因素的共同影響,體裁則根據當地的建筑形制另具特色,如北方年畫包括炕畫,而南方沒有火炕,自然不會有炕畫,年畫的人物造型夸張或寫實,色彩強烈明亮或柔和細膩。
區域環境的不同使年畫題材多樣,江南地區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桑養蠶,拉絲織布,蠶繭儼然成為江南地區發展經濟的關鍵。養蠶農戶將“蠶貓避鼠”這類年畫貼在蠶房門上、窗子上或蠶匾上,一方面,蠶繭嬌嫩,貓能捕鼠保護蠶繭;另一方面,蠶月之時,貼此類門畫有閑人止步之意。清代《男十忙》在不同地區受建筑環境和民俗影響,有不同的張貼部位和裝飾功能,出自河北武強的《改良男十忙》是窗花體裁,長橫幅形制,有四小幅,單幅的窗花里表現一個季節中代表性的勞作景象。由于我國北方冬季氣候寒冷,為了抵御寒風,窗戶會被糊上白麻紙,并用木頭將窗戶分割成大小不同的窗格子,購入年畫后,將其依次裁下,對窗子進行裝飾。
2 男耕女織生產模式的成因
男耕女織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家庭農業經濟模式,這種勞動分配模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秦漢時期,大多數女性并不進行家庭紡織生產,明代的江南地區,男耕女織的趨向已很明顯,到了清代中期,男耕女織得到充分的發展與普及。這種模式在清代成為農村主導性的勞動分配模式,有以下三點原因。
2.1 以性別為引導的社會分工
傳統農業社會生產效率低下,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大,對體力的需求較大,男性身體更強壯,體力更充足,勞動強度較大的田間農活分配給男性,勞動強度較小的家庭勞動分給女性。男性一般承擔著耕種土地、播種和收割作物等勞動密集型生產職責,女性需要照顧其他家庭成員的飲食起居。紡織是一項足不出戶就可以完成的生產勞動,更適合女性。在男耕類年畫中,女性一般會出現在田間地頭為勞作的親人送飯,或在糧食豐收的時候做一些輔助工作,常常會有小孩出現在女性身旁,暗示女性所承擔的教育子女的責任。
2.2 紡織的經濟效益高
至清代,棉紡織業成為我國產值最大的手工業[2]。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形成了農戶既要耕種維持家庭生計的糧食、蔬果與棉花又要喂養禽畜的格局,但江南地區人多地少的形勢迫使民眾進行商品交換以維持家庭溫飽。
清代不同時期的布價與米價均存在波動,這種波動受到自然災害、田價、銀錢比價、賦稅等多方面的影響。一石米大約可換10匹布,當時一個成人婦女使用單錠手搖車一天勞作10至12小時可紡紗5兩,一匹布則需要4天紡紗,日成一匹是正常的織布效率。一匹布在單人使用單錠手搖車勞作的情況下,5天就可完成,而一石米需要一畝稻谷脫殼而得,種一畝稻谷的周期為5個月左右,10匹布一人至多兩個月便可完成。康熙年間,米價下跌,布價上漲,是棉紡織勞動收益最高的時期,紡織生產的盛行也是生產需要的結果。這種高經濟效益使紡織題材被引入木版年畫的生產,成為重要題材之一,借用年畫這種圖像形式再現并推廣紡織技術。
2.3 統治者理想社會的映射
乾隆時期,我國人口爆發式增長,人口的激增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巨大壓力,也是提升農業生產力的主要動力。男耕女織不僅能滿足人民的衣食需求,也關系到社會的穩定。統治者采取一系列農業政策鼓勵農民開墾土地,引進新技術提高作物產量。有定期對地方官員進行巡查考課的行政制度,對官員的政績進行評定,而農桑墾殖、水利興修等是考課的重要內容之一[3]。同時,直接將農民耕織效益納入百官的考核中,由此催生了勸農文、勸農詩、鄉約告示等文字形式的農政文獻,各地年畫、竹枝詞、器物上的農事圖豐富多樣,這些文與圖的興盛足以說明統治者恢復和推動生產的積極性,也映射出統治者心中民眾衣食無憂的理想社會。
以上多方面原因,促進了清代男耕女織生產模式穩定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男耕女織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并經常在文學、藝術和民間傳說中被描繪出來。
3 耕織圖像的顯與隱
在耕織年畫中,從視覺表象可以感知人們耕織勞作的簡樸生活以及對農事豐收、家宅安泰的祈福愿望。畫面具有扁平化與真實性的特點,教化表達則是隱性的。《鄉言解頤》中“新年十事”云:“掃舍之后便貼年畫,稚子之戲耳。然如《孝順圖》《莊稼忙》,令小兒看之,為之解說,未嘗非養正之一端也。”[4]這里提到了年畫對少兒的美育功能,統治者也通過圖像敘事的方式強化思想傳播。
3.1 民眾生活愿景的圖像化
藝術源于生活,耕織類年畫的創作離不開鄉村生活的沉淀。清代民間年畫的創作者中有農民,他們中的大多數農忙時在田間地頭干活,農閑時拿起刻刀進行年畫創作,亦筆亦耕兩不誤,刻繪出的年畫在立意、構圖、色彩方面都具有民俗的意味,真實展現了鄉間生產生活的狀態,也表達了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愿景,期盼天下太平,風調雨順,金銀滿囤,期盼為官者體恤民情。常見的《春牛圖》能夠預告來年降雨量、農作物收成等信息,神牛的背上經常馱著一只種有搖錢樹的聚寶盆,聚寶盆和搖錢樹代表著物質的豐富,兩邊飛來的鳳凰借指社會太平。滿足民眾訴求的年畫是一種將人們的愿景圖像化的呈現方式。
3.2 社會秩序的教化隱喻
耕織年畫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的采桑銅紋壺,描繪的是最原始的耕織畫(面。之后經過不斷發展,到宋朝形成了成熟的耕織圖體系,民間耕織年畫與宮廷發行的耕織圖卷并不是毫無關聯的,楊柳青《農人樂》畫面左下角的豐收與焦秉貞《耕織圖》中的登場在人物姿勢和景物布置上相仿,近處的麥垛、木梯以及農夫用木杈遞稻谷,從視覺元素的一致性可見官方的重農思想對民間畫師的創作產生了影響,并提供了一個創作方向。年畫圖像中的和諧穩定是統治者祈求的社會狀態,耕與織既是民生之本,又是清代男子與女子德行的體現。當這種道德教化藏于圖像之中時,統治者與臣民之間就具有了契約關系,將其變成一種人們都應該期許的公共秩序。因此,男耕女織不僅是一種生產活動,還是一種社會道德和契約的踐行。
4 結語
要理解年畫藝術,就必須研究與其相關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主觀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耕織木刻版畫的留存,為研究清代農業歷史提供了圖像資料,起到了佐證的作用。通過對這些民間圖像進行分析,可以深入了解當時農業社會的風俗文化、性別角色與分工。木刻版畫藝術作品真實地描繪了當時的生產生活場景,展現了當時的主流價值和理念。
參考文獻:
[1] 周昕.中國農具通史[M].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175-178.
[2] 郭衛東.印度棉花:鴉片戰爭之前外域原料的規模化入華[J].近代史研究,2014(5):72-85.
[3] 王加華.教化與象征:中國古代耕織圖意義探釋[J].文史哲,2018(3):56-68.
[4] 李光庭.鄉言解頤:卷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2:23-24.
作者簡介:孫云麗(1998—),女,江蘇鹽城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
張力麗(1979—),女,山東煙臺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