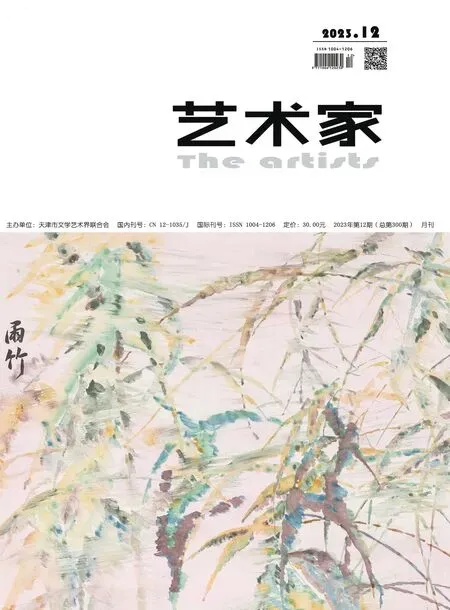音樂劇《血色湘江》中“韋江”的藝術形象塑造及詮釋
——以詠嘆調《名字》為例
□田昀艷 黃 興
音樂劇《血色湘江》以湘江戰役為背景,以紅34 師師長陳樹湘為創作原型,講述了在湘江戰役中執行后衛任務的部隊掩護中央機關和兄弟部隊強渡湘江,最終全部壯烈犧牲的感人故事。這部劇中的“韋江”是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動展現了軍人就算戰死沙場也滿心歡暢的革命英雄氣概。
本文以男高音詠嘆調《名字》作為切入點去研究音樂劇《血色湘江》中“韋江”藝術形象的塑造和詮釋,從音樂分析和演唱分析角度,對詠嘆調《名字》所包含的音樂特點、演唱特點、舞臺表現等進行研究,希望對聲樂學習者演唱該唱段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一、對“韋江”藝術形象的戲劇塑造
(一)“韋江”勇敢睿智、信仰堅定的軍人形象
劇中,韋江所在的中央二縱遭到了敵軍的猛烈攻擊,導致韋江與部隊走散失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一路護送懷有身孕的朱大姐躲避敵人的追蹤和攻擊;在部隊進入山巒迷路后,作為壯族的紅軍戰士的他想到了求助于當地老鄉,并獲得了瑤家同胞的糧食補給;在部隊走出重巒疊嶂的密林之后,與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再次打響。部隊在這場戰斗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此時,閩西籍紅軍戰士“賴老石頭”對以往戰役的勝利和如今戰局的不利之間的對比,師團領導的犧牲以及自己一路從班長升到營長折射出戰損的恐怖,無不透露出“賴老石頭”對當今戰局的失望和悲觀情緒,而韋江對此的回答竟是“越是挫折越是要堅定信仰”的強音。
由此可見,在面臨激烈的戰況、軍心的動搖、錯綜復雜的地理環境時,韋江沉著冷靜,信仰堅定,把悲傷轉化為前進道路上的不竭動力,更堅定了為革命事業奉獻的信念,投身于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用自己所有力量來兌現誓言。這是身為軍人和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韋江展現給我們的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質。
(二)“韋江”寬厚溫暖、體貼深情的親人形象
在劇中,朱大姐一直在說“不要救我,不要救我”。此時韋江與朱大姐的二重唱中,韋江道:“你的丈夫,我們英勇善戰的師長,已經壯烈犧牲在湘江邊上,他是我親如兄弟的戰友,他把你托付在我的身上。你的孩子已經失去了父親,你怎么忍心再讓他失去親娘。”韋江一句又一句溫情且溫柔地訴說著內心的心聲。
他給予朱大姐無微不至的關懷,深情地勸說想要自殺的朱大姐,希望她為了革命的勝利、為了犧牲在湘江邊上的丈夫和戰士們、為了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勇敢地活下去以及朱大姐自殺后,韋江的內心的苦痛,使“韋江”這一人物形象更有血有肉、真實生動。他對朱大姐細膩體貼,關懷備至,表現出親人般的深情厚誼。韋江對革命戰友不拋棄不放棄,始終堅持關懷和真情勸導,展現出了偉大的戰友情和血濃于水的親情,將一個溫柔卻有著堅定信念的親人形象展現得淋漓盡致。
(三)“韋江”紀律嚴明、嚴于律己的戰士形象
在戰局失利和戰士傷亡巨大的情況下,軍心動搖,戰士們戰斗意志出現搖擺。當韋江得知“紅米飯”脫離隊伍,想要回到家鄉時,韋江唱到“你承認要脫離隊伍,你可知道戰場的紀律,軍法無情”,說著便掏出了自己的手槍指向了“紅米飯”的額頭。在韋江的步槍指向“紅米飯”的同時,“賴老石頭”為了保護“紅米飯”也將自己的槍指向了韋江。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緊張的人物關系以及對比更凸顯出韋江對軍隊紀律的堅守。面對戰友的退卻,部隊軍心的不穩定,為了確保部隊能夠繼續前行,為了穩定軍心,韋江表現出一位戰士應有的素質,時刻以軍人的要求與作風貫穿到自己的一言一行。
二、對“韋江”藝術形象的音樂塑造
在音樂劇《血色湘江》中,韋江重要的唱段共有5 首,涵蓋重唱、獨唱、對唱,其中詠嘆調《名字》是劇中唯一一首獨唱。此部分將通過對音樂劇《血色湘江》中人物“韋江”的一首詠嘆調《名字》來對其藝術形象的音樂塑造進行分析。
(一)旋律分析
第1~4 小節為引子,清新柔和的旋律以P 力度奏出,曲子進行在D 大調二音、三音、五音反復進行,鋼琴右手的柱式和弦進行營造出一種靜謐的氛圍。旋律線條緩慢悠長,增強了D 大調旋律感,穩定調式調性。第5~6 小節旋律線條以八分音符加八分休止組成,旋律線條八分休止進行,使韋江寫下紅軍戰士們名字的這個動作更加形象,并在p 力度的演唱下,以樸實的語言、旋律進行的似斷非斷烘托出他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如圖1)。

圖1
在音樂進入第13 小節,鋼琴伴奏織體較之前出現明顯變化,由之前四分音符的進行變成六連音的旋律進行。左手伴奏織體也由之前建立在D 大調主音上的和弦進行轉變為F 大調主音和中音交替變換的連續六連音的組合。旋律進行由之前結束在小字一組向結束在小字二組變化。旋律的向上推進音樂線條的流動和感情迸發,直接推動旋律走向B 樂段(如圖2)。

圖2
第21~37 小節為B 樂段,旋律線條以F 大調主音向下級并反向跳進至屬音C 音,左手伴奏織體依舊是連續的六連音,右手由之前單音旋律進行變換為和弦進行,使音樂發展更厚實,情感更加激昂(如圖3)。第29 小節快速的下行級進加跳進將音樂發展推至高潮,力度由之前的p 變成f,左手伴奏織體以由之前的連續六連音轉換成以十六分音符為主的F 大調主和弦反向上下行快速進行。這一樂段是前一樂段的升華,在連續八小節的高聲區旋律進行下,最后結束在高音區G 音上(如圖4)。

圖3

圖4
第38~43 小節為6 小節尾聲,拍號由之前4/4變為2/4,旋律強弱對比更加強烈。旋律線條由高音區A 音向下級進,再以三連音的形式從F 音向下跳進,最后在F 大調主和弦分解中結束于主音F 上。鋼琴伴奏織體為和弦柱式進行,富有結束感,使情緒得到升華(如圖5)。

圖5
(二)和聲分析
第1~4 小節是樂段引子,建立在D 大調的基礎之上的主和弦與二級和弦的交替進行,旋律進行以主音D 為低音,穩定了D 大調的調式調性。左手單音伴奏上行走向,加之右手以和弦伴奏織體進行,以弱力度進入為全曲打造了靜謐的開頭,并為后半部分高昂情緒的迸發奠定了感情基礎(如圖6)。

圖6
第9~12 小節五級和弦、六級和弦、二級和弦及主和弦以和弦轉位形式使其半音下行平穩進行,最后主和弦的進入使樂句結束感增強(如圖7)。第13 小節后為轉調樂段,為前一樂句主導動機的變化重復,和弦進行也從前一樂句的單音進行變為六連音的快速進行,和弦的變化也更加復雜,由此建立在副音級基礎上的和弦交替進行,如Sii2--T--DTiii--TSvi 以及重屬和弦DD7 的使用,使整首曲子更有民族性和色彩性(如圖2)。

圖7
第21~37 這一部分副和弦的使用更加巧妙,和弦的轉位使半音化進行平穩。樂句之間的結束如第29 小節采用F 大調和弦屬七和弦以十六分音符快速下行的樂句半終止,無論是從音響效果、情緒爆發,還是樂句之間的連貫都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如圖8)。建立在副和弦上的快速進行加右手柱式和弦進行,對樂曲的進行、高昂情緒的迸發起著催化劑的作用。

圖8
第38~43 前三小節和弦進行均為副和弦柱式進行,最后以S--T 柱式和弦結束全曲(如圖5)。
(三)節奏分析
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連續使用。在全曲開始,此段中鋼琴左手旋律均為八分音符與四分音符的交替組合,右手伴奏織體除了引子的八分音符與附點二分音符的平穩進行,其余小節右手均為全休止。
六連音的充分使用。之后的伴奏織體的運用較之前出現明顯變化,左手連續的六連音的使用代替了平穩的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右手采用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長時值音符,快速六連音與長音之間的相互輝映使整曲的情緒高昂、激動,變得更有力,情緒更飽滿。右手以快速的十六分音符組合代替六連音,加上踏板的使用,連續的大附點節奏型的使用,使樂曲情緒在之前的鋪墊下得到迸發。
結尾處伴奏織體發生變化,用琶音的形式以及八分音符下的和弦結束全曲(如圖2、圖4、圖5)。
三、對“韋江”藝術形象的詮釋
在結合韋江藝術形象的戲劇塑造和音樂塑造的前提下,筆者從氣息的運用、字音的歸韻、情感的把握三方面,對“韋江”藝術形象的詮釋進行分析。
(一)氣息的運用
詠嘆調的開始類似說中帶唱,唱中帶說,夾敘夾議,用宣敘調的感覺來表達這段內心獨白、沉思和情懷。因此,樂曲開始時,我們需要在較弱的力度下,采用適中的音量,將氣吸到肺的底部,同時將聲音保持在高的位置上,讓每個字在高位上配合氣息自然地發出。
隨著音樂線條向前流動,情感逐漸飽滿,第21~29 的氣息運用較之前的運用更夸張,整個肋骨周圍的肌肉向外擴開,此時的后腰要更有力,能夠隨著音高上升將氣息這個“底盤”穩住(如圖3)。
第30~37 小節是整曲的高潮樂句。連續的高音不僅對歌唱者技術有較高要求,還考驗歌唱者氣息的穩定。在29 小節的八分休止中,樂句中的換氣也十分重要。此樂句中的全部換氣均在弱起,因此,演唱者必須在弱起之前換氣,將氣息快速吸入肺部,以保證有充足的氣息保證后半部分高強度的演唱(如圖4)。最后38~43 小節為整首詠嘆調的尾聲部分,此時的氣息可以運用得更從容。氣息要在敘述性的樂句中緩緩送出(如圖5)。
(二)字音的歸韻
詠嘆調開始的第一個樂句“點、橫、撇、捺、豎、折、彎、劃”,這一句中五個元音的變化就全部包含其中(如圖1)。對于“an”的發音,在保證腔體豎著打開的同時,演唱者要盡可能地突出“a”母音。此句中的后鼻音“eng”非常重要,如果不注重字音的歸韻就會唱成“en”,這樣歌曲的整體情緒從剛開始就會被破壞。因此,演唱者需要更注重咬字的干凈利落,在咬住字頭時,要快速歸韻。
“以”“歷”“史”這幾個字都在換聲點附近,且這幾個字都是窄母音,演唱者要遵循窄母音寬唱的要求去積極地咬字(如圖9)。在窄母音與寬母音之間的快速換字,演唱者一定要在保持窄母音的明亮集中的音色基礎上,做到咬字位置的統一與聲音的連貫。

圖9
副歌部分的“以、記”兩字都在a2、g2,且這兩個字都是窄母音“i”音,演唱中要在深呼吸的支持下,“i”中帶“yu”快速歸韻,才能夠在高音部分站穩,不會出現“緊摳撐”的現象(如圖4、圖10)。

圖10
(三)情感的把握
演唱者在演唱中要將紅軍戰士無所畏懼、百折不撓、永不退縮的精神貫穿全曲。“點、橫、撇、捺、豎、折、彎、劃”名字筆畫的書寫飽含深情與堅定。“趙、錢、孫、李,諸姓百家”此時的情緒要較之前更抒情。“一個姓氏代表著一個家”,感情更加深刻,眼神更加堅定,與第一樂句形成一定程度的對比。“從以歷史的名義都記下到就算我們的尸骸被埋進黃沙”這一整個樂段中,演唱者要將紅軍戰士不畏懼犧牲、敢于同強大的敵人抗爭的紅軍精神的表達出來。最后一句“紅軍戰士,英雄的名字,會被人民記下”轉化為內心的獨白,演唱者要將情緒、情感傳遞給舞臺上的紅軍戰士,傳遞給臺下的觀眾(如圖5)。
本文以對“韋江”藝術形象的戲劇塑造為開端,從軍人形象、親人形象、戰士形象等方面探究“韋江”的戲劇塑造,并以此為基礎,通過分析“韋江”唱段《名字》的音樂本體,結合自身演唱的藝術實踐,總結分析《名字》的演唱感悟和要點,希望能為今后演唱此作品的演唱者提供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