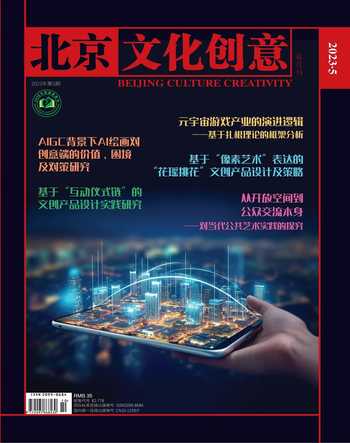傳統文化跨文化傳播背景下“魯班工坊”走出去路徑探究
曾淑媛 汪星星
摘要:“魯班工坊”是我國職業教育跨文化傳播發展的樣板,為跨文化傳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現實語境。由著名工匠魯班生發出的符號化聯想也為現代職業教育賦予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能量,使得魯班代表的工匠精神伴隨著“魯班工坊”的“走出去”在不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落地生花。本文主要探究“魯班工坊”的文化符號建構,并借由內向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和國際傳播這六種傳播類型對“魯班工坊”的海外傳播實踐進行解讀,以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海外傳播實踐提供學理支撐。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 魯班工坊 文化符號 傳播類型
一、跨文化傳播理論及其相關應用
(一)跨文化傳播理論
學界普遍認為,“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理論是美國學者愛德華·T.霍爾(Edward T. Hall)在其1959年發表的著作《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正式提出的,而跨文化傳播的實踐歷史卻可以被追溯到人類社會初期。①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西方學者將跨文化傳播從更為宏觀的人類學知識譜系中剝離出來,通過從語言學、教育學、傳播學、政治學、文學等不同角度切入,拓寬學術領域、深化學科范疇,使之形成了較為規范的跨學科理論體系。②值得強調的是,西方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冷戰之后歐美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語境之下的。因此,有關“跨文化傳播”的相關研究,西方學界主流側重于關注它是如何在特定語境中影響人類交流活動的,并強調因東、西方的主、客體身份所帶來的“差異”和“沖突”而形成了二元對立局面。③
而后,20世紀80年代,跨文化傳播研究被引入我國學界,并再次經由多學科視角的匯入形成了交叉研究。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交流與合作不斷加深拓展,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學者們將積極響應國家政策與時代發展的需要作為研究出發點,針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術熱情高漲。但是,“跨文化傳播”作為舶來的學術理論概念,在立足于中國的本土化研究過程中,因其長久此以往的“二元對立”學術慣性,不可避免地讓學者們落入西方研究框架的窠臼。同時,國內的多數研究仍處在用既有西方理論對本土案例進行闡釋的階段,還未觸及對理論核心的更新和再發展。除此以外,在闡釋的過程中仍集中在以物質文化為重點的文化內容推介上,而以物質文化為媒介的跨文化傳播被受眾接受并不一定代表著其文化理念被認同。④在研究內容上,國內僅有少數學者關注跨文化傳播學理層面,并主要集中于將推動文化“走出去”作為研究目的進行討論。總體而言,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從國家軟實力、媒體傳播力、文化輻射力幾方面出發,屬應用型研究,對于“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對外傳播”以及“對外文化傳播”幾種研究取向則界限模糊。因此,在中國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通過對本土實踐、理論的深度探究,探索關于“中國故事的世界表達”和“中國理論的世界闡釋”有一定研究價值和意義。
(二)跨文化傳播理論應用:“一帶一路”背景下政府主導的跨文化傳播
有別于“冷戰”之后形成的以歐美國家為中心的“全球化”,在平等與合作的新型理念指導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跨文化傳播的理論重構提供了新的機遇。學者蘇婧與劉迪一認為,與主流西方二元對立、凸顯主客體的思想內核不同的是,“一帶一路”作為國家之間的頂層倡議,倡議的是恢復不同文化主體之間關系的內在特性,即在保留各自文化核心特征的基礎上,主張多元共存而非同化同質。在此語境之下萌生的跨文化傳播相關討論和實踐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于國家的軟實力建設和傳播,典型案例之一是在漢語國際教育領域已有多年發展經驗、并在海外合作國家收獲良好口碑的孔子學院。而被稱為職業教育領域的“孔子學院”的“魯班工坊”,近年來發展迅速,同樣為中國文化的跨文化傳播做出了貢獻。
二、跨文化傳播的平臺:“魯班工坊”現狀概述
“魯班工坊”是以“大國工匠”精神為依托,由天津市率先主導推動實施的職業教育國際知名品牌,它搭建起我國職業教育與世界國際教育接軌的橋梁,旨在培養一批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熱愛和平、德技雙修的具有國際合作精神、適應合作國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術技能型人才。①“魯班工坊”的名稱取自我國春秋末期著名的發明家和工程師魯班,他被后世尊稱為中國工匠師祖。魯班本人所代表的工匠精神和創新智慧,加上其所處時代應運而生的“兼愛”“非攻”的班墨文化,使得“魯班工坊”這一職業教育品牌的命名既能體現傳授技術技能的功能性作用,又能展現植根于厚重歷史文化背景的深遠內涵。②
如果說“孔子學院”是現代中國教育“走出去”的開拓者,那么“魯班工坊”則為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打開了“新窗”。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教育充分發揮了其夯實基礎的先導作用。“魯班工坊”不僅鼓勵各國分享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和成果,搭建互利共贏的職業教育國際化平臺③,還作為中國在境外創建學歷教育和技術培訓的合作載體,在國際職業教育合作和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上具備里程碑式意義,豐富了我國跨文化傳播的內涵和具體實踐。④
自2016年首個魯班工坊投入使用以來,該模式行之有效,至2022年,我國已在亞、非、歐三大洲19個國家建成20個魯班工坊,全球化布局已然開啟,⑤并為世界職教貢獻了“中國方案”。“魯班工坊”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旨在以境外辦學和國際合作辦學為主要方式,為沿線國家和國內外相關產業輸出我國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培養優秀技術技能型人才,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與智力支撐。⑥“魯班工坊”既面向市場、利用市場手段,又以國家宏觀調控為抓手,使得此模式兼具四重功能,分別是:培養優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功能,推進職業教育國際合作實體化的社會功能,服務“一帶一路”并與歐亞經濟對接合作的經濟功能,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成熟的中國特色教學模式的文化功能。⑦四種功能彼此相融、相互促進,使得“魯班工坊”的跨文化傳播迸發出新的發展可能性。
三、跨文化傳播的內容:“魯班工坊”的文化符號建構
“魯班工坊”作為一種“走出去”的中國職業教育模式,始終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出現,其名稱由“魯班”和“工坊”連綴而成,二者作為獨立的符號有著專屬的傳統文化意涵,當合二為一時又使得以“魯班工坊”為名的職教品牌煥發新的生機。與此同時,它的文化內涵也隨著越來越多所“魯班工坊”在海外的建成而不斷演繹,不僅為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打開了新思路,也為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傳播路徑。
(一)“魯班工坊”作為文化符號
“符號”在人類文化形成和傳播的過程中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①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文化符號更是承擔著展現文化軟實力、傳遞核心價值觀念的載體功能,并輔助國家主體形塑國家形象、建構文化身份、增強文化自信。從20世紀初,現代符號學奠基人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語言學的視角下提出所有符號都包含“能指”和“所指”兩部分②,到20世紀中葉,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從文化的本質入手,提出人與動物的不同是能否利用符號和以符號為手段,闡釋已有事物,③到20世紀60年代,以尤里·洛特曼(Ю?рий Ло?тман)為代表的莫斯科—塔爾圖學派推動了“文化符號學”的理論建構,④到20世紀下半葉,羅蘭·巴特在索緒爾語言學角度的符號學的啟發之下,拓寬了結構主義的研究疆域,認為“人只是結構中的一個符號”,從人的主觀意志出發,賦予事物意義,才能達到“結構”的目的,并以敏銳的時代目光剖析了各種文化現象,可謂是意義分析的利器。⑤至此,文化結構主義的形成標志著文化符號學的成熟。⑥總體而言,將符號理論引入文化研究領域,為學者們觀察世界和研究歷史提供了嶄新的思考角度,基于此,本部分也將分析“魯班工坊”的符號意義。
有關于魯班的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傳播歷史,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學術研究領域內,魯班都不再單一地代表具體歷史人物形象,而是作為特定的文化符號承載了深刻意涵。魯班又名公輸盤、公輸般,尊稱公輸子,是春秋戰國時期魯國著名工匠。據現存的文字記載和口述文藝,有關魯班的歷史可劃分為以下階段:在先秦和漢初,魯班事跡的記載多基于歷史事實。而漢魏至唐代,魯班形象及事跡則逐漸傳說化。⑦在現有的學術研究領域中,與“魯班”傳說相關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匠精神”與魯班形象的共通性上,并以魯班這一歷史人物作為切入點,深入剖析“工匠精神”的歷史演繹和文化內涵。⑧
“魯班”作為典型的中華文化符號,在民間傳說中多被描述為木匠行業祖師爺和神圣的技藝傳授者,深受中國各族人民的喜愛。在此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文化符號“魯班”才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著形塑文化身份、增進民族團結、加強文化自信的作用,有利于進一步建構文化認同體系。⑨除此之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倫理思想深入人心,類同祖先作為一種符號以血緣關系為紐帶整合起一個區域的文化認同,作為手工業祖師爺的魯班也以擬親緣的方式串聯起手工業從業者的情感聯系,用文化符號“魯班”喚醒“根基性情感”,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感提供重要動力。⑩愛爾蘭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符號則是想象共同體的媒介,因此,民族共同體實質上是符號共同體。?故而,“魯班”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與其背后的“工匠精神”的文化內涵和“大國匠心”的文化認同連結起來,形成了穩固的“文化認同—文化行為—文化符號”的映射關系。
“魯班工坊”通過文化符號“魯班”來建構具有標識性的文化身份,深層融合現代教育和傳統文化,以職業教育的國際品牌形式傳遞我國主流價值觀,有助于形成具有競爭力的跨文化傳播。從名稱上看,“魯班工坊”由“魯班”和“工坊”連綴而成。前者是代表著技術技能領域的高超技藝、精益求精和創新精進的匠人精神的文化符號,后者則強調工作環境的小而精和工作流程上的雅且細。除此之外,“魯班工坊”的品牌標志也是重要的視覺符號。其標識設計主要由圓形和方形組成,寓意“天圓地方”。“魯班工坊”的漢隸四字以金鑲玉的理念呈現,并成為該標識的視覺中心,以此凸顯中國傳統文化和技藝的輸出對于“魯班工坊”的重要性。①其背景融合了祥云、書本、階梯和滴水檐四種傳統紋樣,在彰顯教育理念的同時寓意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國門,邁向世界,不忘初心,面向未來。②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不僅體現在“魯班工坊”的名稱上,還反映在視覺設計上。因此,“魯班工坊”不僅在推進國家文化符號體系建構的過程中實踐了跨文化傳播,還以其多元的文化吸引力拓寬了國際文化傳播途徑。
(二)“魯班工坊”作為跨文化傳播的媒介平臺
“魯班工坊”作為一種以技藝相傳為表現形式的文化傳播,本質上是本民族文化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鑒和融合。在跨文化傳播中,傳播主體在本族文化背景下進行編碼,通過媒介將本民族文化傳達給受眾,受眾在本土文化背景下進行解碼,傳受雙方的文化差異制約著解碼的有效性。③對于“魯班工坊”而言則不存在這種問題。得益于相對接近的地理位置、經由歷史發展而帶來的文化上的接近性,不僅使解碼成功的可能性增大,也使得傳播的阻礙減小,有助于“魯班工坊”這一職業教育國際品牌充分發揮其文化傳播的作用。
綜上所述,“魯班工坊”作為一種文化傳播形式具有一體兩面的特質。“魯班工坊”不僅從名稱上通過文化符號“魯班”來建構具有標識性的文化身份,更以職業教育作為跨文化傳播的媒介平臺傳遞我國主流價值觀。伴隨著更多所魯班工坊在境外院校扎根,其符號的內涵必將經歷不斷演繹的過程,其文化意涵也將隨著傳播路徑的多元化而逐漸豐富。
四、跨文化傳播的具體實踐:“魯班工坊”蘊含的六種傳播類型
“魯班工坊”在實踐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主要利用了人類傳播的六種傳播類型,即內向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和國際傳播。“魯班工坊”目前已通過這六種傳播類型建立起了踏實穩固的傳播渠道,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有豐富的借鑒意義。因此,本部分將結合“魯班工坊”在海外實踐跨文化傳播的成功案例,拆解其使用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并對應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內向傳播奠定傳播基礎
內向傳播(又稱為自我傳播、人內傳播)是傳播活動的基本類型,它是人在意識世界中不斷調動新輸入的外部信息與人腦中積淀的內部信息,進行一系列的符號化操作,諸如運用概念,進行判斷、推理,最終形成決策,以便指導自己后續言行的內在過程。在此基礎上,人類開展人際傳播、大眾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等活動。④
“魯班工坊”通過直接的面對面課堂教學和文化推廣活動,將中國文化與工匠精神的形態和理念傳遞給受眾。以英國“魯班工坊”開展的國際化中餐烹飪專業人才培養為例,縱然中華美食文化源遠流長,“中餐熱”也在世界遍地生花,但外國受眾普遍對中餐烹飪的原料、調味、用具等存在認識盲點,為解決這一問題,英國“魯班工坊”提供了多種解決方案。首先,他們創立了中餐烹飪藝術培訓模塊,通過系統性的講解和演示,教師將中餐的原料、調味、用具等方面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并引導他們親自動手操作。其次,他們運營面向公眾開放的產教融合“魯班餐廳”,通過實踐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中餐烹飪的實際操作和菜品創新。同時,在“魯班餐廳”的裝潢設計中,融入了魯班鎖、魯班傘等具有文化內涵的設計元素,讓受眾們沉浸式地體驗魯班工藝,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⑤受眾接觸這些信息后,經由味覺、視覺、觸覺等過程進行信息處理,并針對信息內容向魯班工坊的工作人員提出疑問。在溝通的過程中,受眾的認知不斷調整與適應,而后實現認知和諧,傳授雙方從而實現意義共享,在中國文化元素理解上達成一致,受眾也完成了對中國文化和“魯班工坊”從個人接受外部信息到在人體內部進行信息處理活動的完整內向傳播過程。
(二)人際傳播助推二次傳播
文化是一套符號和認知的系統,魯班工坊將文化符號所承載中華文化加以推廣,讓世界各國人民能夠認識、了解以及認同中國文化和工匠精神,使中外雙方能夠實現相互理解,建立意義的共享,其主要途徑便是人際傳播。目前,魯班工坊主要通過直接的課堂教學、文化推廣活動等人際傳播形式推廣中國文化和工匠精神,受眾經由內向傳播成功認知魯班工坊及其所代表的工匠精神,進而自發地將中國文化介紹給身邊的親朋好友,再次完成了人際傳播活動,魯班工坊的跨文化傳播影響力得以擴大。在此過程中,相關參與人員的跨文化認知能力和跨文化交際意識直接影響著跨文化人際傳播的效果,這就需要跨文化人際傳播的參與者不僅具備堅實的漢語言文化知識,而且需從認知、情感、行為三個方面不斷提升跨文化交際能力,才能在他者文化中順利完成傳播過程。故與其他幾種傳播類型相比,人際傳播的效果更為直接,是魯班工坊實踐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群體傳播促進文化認同
群體傳播是一種具備傳播主體多元和非制度化、非中心化特點的傳播形態,群體成員的參與、互動及分享不但可以促進意義在空間上的彌散,而且可以促進情感在時間上的延續。①國際學生作為雙文化個體有更復雜的文化知覺和文化知識結構,因而更容易受第二種文化環境的影響。在群體傳播中,國際學生個體通過主動管理和調整認知來積極尋求身份認同,并在群體中獲得的積極情感從而滿足其自身的基本心理需要,最終接受新文化語境下的自我身份 。②
在線下教學課堂群體中,課堂文化很大程度影響著課堂成員的心理和行為。因此,良好的課堂傳播生態環境對中華文化的跨文化傳播起到重要作用。魯班工坊定期組織中國教師和技術人員,為當地教師開展技能培訓,同時也會邀請對方來中國進行實地交流,這種線下互動教學是“魯班工坊”在進行群體傳播時的具體實踐。教師可以通過研究國際學生的課堂傳播運行過程和接收信息的意識、態度及行為,探討有效的班內傳播策略。在此過程中,以班級或學校為單位開展國際學生跨文化教育對達成群內共識起到重要作用。
(四)組織傳播推廣品牌活動
組織傳播是指一個組織使用其特有的組織媒體工具和傳播措施來進行的傳播,其目的是形成組織氛圍,凝聚組織力量,展示組織影響,促進組織內部、組織之間和組織外部的良性互動。③組織傳播把傳播作為描述和解釋組織的一個途徑,組織、受眾和媒介三大要素構成組織傳播,其中媒介是組織傳播活動中“傳受”之間的橋梁和中介,受眾是組織傳播中特定的受眾群體,組織是維系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的傳者主體,也是組織傳播活動的核心所在。④就組織傳播的主體而言,“魯班工坊”將政府視為其進行跨文化傳播的傳播主體,依托政府間的戰略合作為“魯班工坊”的有效性背書。同時采用非政府組織形式,借助職業院校間國際合作以及企業間需求間校企合作,搭建起世界范圍內職業院校技能交流切磋的平臺,也與世界共享了中國職業院校技能的標準和形成模式。⑤簡言之,我國以“魯班工坊”為傳播媒介建設了全球性國際職業教育交流平臺,并在平臺內部凝聚國際各方力量,積極開發國際議題,從而向國際共享中國職業教育智慧。
(五)大眾傳播拓寬傳播路徑
大眾傳播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傳播方式,是文化的引領者,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軟實力。⑥具體的大眾傳播媒介是由一些機構和技術所構成,并由專業化群體依托這些機構和技術,運用如報刊、廣播、電影等技術手段向廣泛受眾傳播內容所使用的工具⑦。在魯班工坊進行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常常借助電視節目、報紙、廣播等媒介將魯班工坊的相關信息以新聞的形式傳達給受眾,受眾會綜合新聞報道情況,構建自己心目中的魯班形象及工匠精神。因此,大眾媒體如何報道魯班工坊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民眾對魯班工坊形象的認知和建構。在融媒體時代,魯班工坊與時俱進,于2023年2月,正式啟動“魯班工坊”網絡傳播項目,運用新媒體技術手段豐富大眾視聽體驗,聚合多方面受眾為中華文化打造立體化、多維化的傳播空間,讓更多跨文化故事得以廣泛傳播。
(六)國際傳播助力民心相通
國際傳播指的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而實施的跨文化信息交流與溝通。在國際傳播的過程中,由外向內的傳播是指將國際社會的重要事件和變化傳達給本國民眾。由內向外的傳播則是指把關于本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向國際社會傳達。①
在宏觀層面上,魯班工坊從具體情境出發,在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中心的國際傳播中,結合受眾自身的政策、利益等因素,通過建設體驗館、參與舉辦世界職業教育大會等國際交流合作項目促進民心相通,充分利用能讓全體受眾共享并具有較強傳播感染力的因素調動受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在微觀層面上,無論是外派至境外“魯班工坊”的中國教師還是深耕本地職業教育的當地教師,都秉持著“以誠待人,以心換心”的原則相互尊重、相互促進、相互啟迪。為了提高溝通效率和增進中外友誼,幾乎所有外方教師都注冊了微信,雙方教師因地制宜改進培訓內容,②以期培養更多專業技術人才,為中外務實合作提供新的典范。
五、結語
“魯班工坊”依托于我國自古聞名的魯班工匠精神,積極實踐了六種傳播類型,現已成為中國文化進行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③從名稱上看,“魯班工坊”不僅通過“魯班”的符號化聯想來建構具有標識性的文化身份,更以“工坊”這一彰顯職業教育色彩的媒介傳遞我國主流價值觀。隨著越來越多家“魯班工坊”在境外院校扎根,它所代表的符號也經歷了不斷演繹的過程,其文化意涵也將伴隨著傳播路徑的多元化而逐漸豐富。“魯班工坊”在踐行跨文化傳播的具體實踐中也恰如其分地運用了傳播的六種類型,更大程度地發揮了跨文化傳播的效用,為其他跨文化傳播組織,尤其是教育主體,提供了發展思路。
Abstract:? “Luban Workshop” is a Chinese educational brand that can provide a new context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mpowered by the craftsman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well-known craftsman “Luban”, “Luban Workwhop” and its artisan spirit have been initiated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ural symbol construction of “Luban Workshop” and interprets i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through six types of communication: internal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group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asonable and reliable work to support for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uban Workshop,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