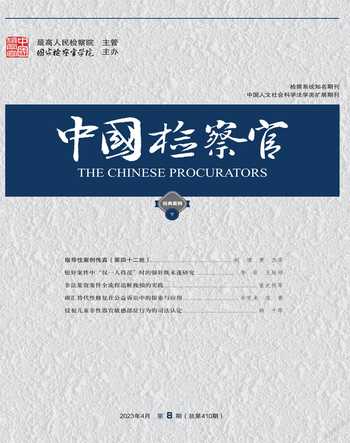涉“外嫁女”權益保護民事生效裁判監督重點及完善舉措
劉小勤 張傳廣
摘 要:涉“外嫁女”土地及相關權益糾紛案件往往涉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問題。在對以村民自治為由裁定駁回起訴的生效裁判開展檢察監督時,應重點審查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主體、標準以及人民法院受案范圍。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應從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高度加大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力度,發揮民事生效裁判監督的糾偏、創新、進步、引領作用,準確適用民事檢察復查制度,切實保護“外嫁女”等婦女權益。
關鍵詞:“外嫁女”權益保護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村民自治 復查 民事抗訴
一、基本案情及辦案過程
馬某某姐妹2人出生后戶籍一直在某村民組,婚后均未遷出。丁某某與馬某某結婚后,丁某某將戶口遷入該村民組,其2人的兩個孩子也落戶于該組。2008年,因土地被征收,某村民組獲得一定補償土地用以建造安置門面房。經村民代表會議討論確定,馬某某等5人為“外掛戶”和“出嫁女”,不享受村民待遇,不參與房屋分配。后經鎮政府協調無法達成一致,馬某某等5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案涉分配方案的確定系村民自治,該案不屬于法院民事訴訟審理范圍,裁定駁回起訴。馬某某等人申請再審,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后裁定撤銷原審裁定,指令某縣人民法院繼續審理。但再次審理的一審法院、二審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仍以相同事實、理由駁回起訴。
馬某某等人認為法院裁定錯誤,遂申請檢察監督,要求確定其村民組成員資格,并撤銷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某市人民檢察院以與生效裁定同樣的理由作出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后馬某某等人于2020年6月提出復查申請。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依法受理后進行了調查核實,確認馬某某等人均在該村民組落戶且生活,遂向法院提出抗訴,認為相關法律法規對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明確規定,不屬于村民自治范疇,且依據辦案當時適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第63條,村民代表會議作出的決定侵害村民權益時,其可以申請撤銷,人民法院應予審理。
2020年12月14日,經審判委員會討論,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采納抗訴意見作出再審裁定,再次撤銷某縣人民法院、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某縣人民法院審理。后某縣人民法院作出再審判決,認定馬某某等人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并確認案涉分配方案無效。[1]
二、案件辦理中的檢察監督重點
本案表面為馬某某等人能否參與門面房分配的糾紛,實質則涉及馬某某等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認定問題。法院對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問題的裁判意見直接關乎村民切身利益,尤其是“外嫁女”等特定群體權益的平等保護,在開展此類案件檢察監督時,檢察機關要重點審查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標準和集體組織是否越權作出決定,以及在成員權益受侵害時,人民法院應否受理審查當事人的起訴。
(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是否屬于村民自治事項
村民自治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一般情況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作出的決定如果不違反法律法規、未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應當得到尊重并在實踐中予以執行。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問題,部分辦案人員認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表象是身份的確認,實質上的訴求是對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組集體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等,該訴求爭議應該交由“村民自治”解決。另有觀點認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關涉到其能否依法享有附著于成員身份上的相關權益,一旦成員資格身份被否定,意味著相關民事權益就會被剝奪,由此形成的民事爭議應該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2],不應將其交由“村民自治”解決。
承辦檢察官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一般牽涉到集體經濟組織財產權利、財產收益分配等,與村民個人利益密切相關,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69條即明確了認定成員身份時,應依照法律、法規相關規定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7條第2款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該規定明確了村民自治的邊界,是實踐中確定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有效性的重要依據。而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4條,涉及村民利益的九項事項屬于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范圍,其中并無關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規定,雖然其中第(七)項為“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但僅涉及組織成員的權益,并不涉及組織成員的身份認定問題。另外,《安徽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第8條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認定列出了具體的五項標準,該五項均是以戶口所在地為判斷標準,符合五項條件之一的,均應認定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中第(一)(二)項標準分別為“本村出生且戶口未遷出的”“與本村村民結婚且戶口遷入本村的”,本案馬某某等5人即與該標準相符,其中丁某某為“與本村村民結婚且戶口遷入本村”,其他4人均為“本村出生且戶口未遷出的”。根據上述規定,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方面,相關法律法規并未授權集體經濟組織自行認定,而是直接確定了認定標準,因此,認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屬村民自治事項的觀點,與現行法律法規規定相違背。
(二)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受侵害產生的糾紛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的范圍
實踐中,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作出決定,將部分人員排除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外,進而使其無法享受相應的財產權益,此類情形并不鮮見,對于由此產生的糾紛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范圍,也存在不同觀點。結合以下三點理由,承辦檢察官認為,此類糾紛屬于民事訴訟審理范圍。
一是此類案件有具體的爭議事實和訴求。如在本案中,馬某某等人戶籍在該村民組,村民組以村民代表會議形式決定房屋分配,以“出嫁女”和“外掛戶”等理由將馬某某等5人排除在外,馬某某等人有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參與房屋分配權利等具體訴求。二是此類案件訴請的權益有法律明確規定,符合有權利必有救濟的要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征地補償權等權利屬于法定權利。依據辦案當時適用的《物權法》第63條第2款(現為民法典第265條第2款),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或者其負責人作出的決定侵害集體成員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集體成員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婦女權益保障法》)第55條亦明確,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的,或者因結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戶,侵害男方和子女享有與所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平等權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36條亦規定,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成員作出的決定侵害村民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本案中,馬某某等5人主張的是法律明確規定的權利,依上述法律規定,其享有起訴權利,并應當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救濟。縣人民法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相關事項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為由限制、排除當事人依法可以享有的訴訟權利,未能全面準確理解《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相關規定和精神,亦未適用前述《物權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對村民尤其是對婦女權益的特別規定,未對馬某某等人是否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作出司法確認,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三是司法實踐為此類受損權益設置了明確的救濟類型和渠道。本案歷次訴訟中都是以“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案由立案受理,正確界定了馬某某等人起訴的爭議性質。辦案當時適用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人民法院對于承包地征收補償費用分配糾紛應當依法受理。第24條規定,依照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土地補償費分配時,“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更明確要求,要充分認識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重要意義,依法保護“外嫁女”等的合法權益。綜上,本案爭議涉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屬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該起訴有明確的被告、具體的訴訟請求及事實和理由,符合民事訴訟起訴條件,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
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若發現生效裁判存在此類以村民自治為由不當排除當事人訴權,明顯損害婦女兒童等合法權益的,應通過抗訴或者再審檢察建議方式監督法院及時糾正錯誤的生效裁判,改變不符合立法精神導向的司法處理方式,保障農村“外嫁女”等依法應當享有的訴權,使得其受損害的權利得到及時救濟。
三、涉“外嫁女”民事生效裁判監督的完善路徑
(一)加大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力度,推動法律及相關決策部署落實
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婦女權益保護,黨的十八大以來,就維護婦女權益、促進婦女全面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更高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也進一步明確,不得以未婚、結婚、離婚、喪偶、戶無男性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同時,該法律還增加了婦女土地及相關權益的規定,特別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土地承包經營、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權利確認和救濟措施,從立法上保障農村婦女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
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應按照法律規定及相關決策部署要求,加大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力度,對于涉及婦女土地及相關權益的民事生效裁判案件,切實發揮民事檢察監督職能,構筑婦女權益保護屏障。
(二)按照民事精準監督要求,促進統一裁判標準
“外嫁女”糾紛本質上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爭議,其通常體現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財產及收益分配權等爭議。[3]本案的訴訟過程表明,關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主體問題,實踐中存在明顯不同的觀點,正確處理好此類典型問題,有利于統一裁判標準,推動法律正確實施。
民事生效裁判監督是民事檢察的基礎性工作及核心內容,也是實現民事精準監督的關鍵發力點。根據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的規定,檢察機關發現民事生效裁判符合再審條件的,應當通過抗訴或者再審檢察建議方式開展監督。本案辦理過程中,承辦檢察官對近期本省有關法院審理同類案件、檢察機關辦理類似案件情況進行了梳理分析,發現實踐中存在較為明顯的類似案件不同處理的情形,而且本案一、二審法院均兩次以相同理由認為其不屬于人民法院審理范圍,省高級人民法院與下級法院對案件處理有明顯不同觀點。為發揮案件在司法理念上的糾偏、創新、進步、引領作用,統一裁判標準,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決定以抗訴方式對該案開展監督,針對人民法院拒絕對損害“外嫁女”等權益的村民會議決定進行司法審查的錯誤傾向,通過抗訴督促人民法院糾正錯誤裁定,有利于推動解決農村“外嫁女”權益司法救濟缺失的突出問題,契合民法典頒布實施和婦女權益保護立法修改精神,也做到了“精準發現、精準審查、精準監督”。[4]
本案辦理的意義還在于充分發揮司法的導向作用,以抗訴監督促成公正裁判,彰顯當事人各項民事權益應受到平等保護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以法律權利體系規定為行動指引和邊界,推動和引導相關單位、組織依法作出決定,不得違反法律規定減損他人權益、增加他人義務。
(三)注重運用民事檢察復查制度,暢通申訴救濟渠道
對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調解書,同級檢察機關審查后作出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當事人認為存在明顯錯誤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請復查一次,此即民事檢察復查制度。該制度源于2013年最高檢原民事行政檢察廳和原控告檢察廳會議紀要,經過實踐完善后,于2021年8月1日在《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中得以正式確立。這項制度的設立進一步完善了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有利于彌補“同級受理”存在的不足,暢通權利救濟渠道,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目的是讓權利保護更加充分、更加有效,與民事檢察兼具公權力監督和私權利救濟兩種屬性相適應,也有利于強化檢察機關內部上下級間的領導和制約。[5]
本案中,馬某某等人在市檢察院作出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后,向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提出復查申請,安徽省人民檢察院發現上下級法院對同一問題處理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見,同時市檢察院未支持馬某某等人的監督申請可能存在錯誤情況,遂按照復查程序受理該案,在審查過程中開展了一系列調查核實工作,并經檢察官聯席會議討論,認為市檢察院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錯誤,遂以適用法律錯誤為由向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同時撤銷下級檢察院的決定,最終促成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本案、審判委員會審議采納監督意見,再審法院判決認定馬某某等人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并確認案涉分配方案無效。
通過民事檢察復查并精準抗訴,既實現了該案的徹底糾正、維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消除了信訪隱患,也推動全省層面解決法院系統類似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促進法律統一實施,后續亦未出現與此案件不同的裁判意見。同時,實現了檢察系統內部自我監督糾正,發揮對下指導作用,彰顯民事檢察復查的制度價值。
*本文為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民事精準抗訴及抗訴跟進監督機制研究”(GJ2020C27)、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民事訴訟精準監督研究”(AJ202013)的階段性成果。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部副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230022 ]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部二級檢察官助理[230022 ]
[1] 參見袁中鋒、張傳廣:《檢察抗訴幫外嫁女討回分房資格》,《安徽法制報》2022年6月9日。
[2] 參見趙風暴:《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的幾點思考》,《人民法院報》2022年9月1日。
[3] 參見馮小光:《民事檢察權對民事審判權的監督制約》,《民事檢察工作指導》(總第2輯),中國檢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頁。
[4] 參見馮小光、趙格、賈文琴:《深入貫徹實施民法典 加強民事生效裁判精準監督——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十八批指導性案例解讀》,《人民檢察》2022年第19期。
[5] 參見華錳:《民事檢察復查制度的沿革與完善》,《中國檢察官》202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