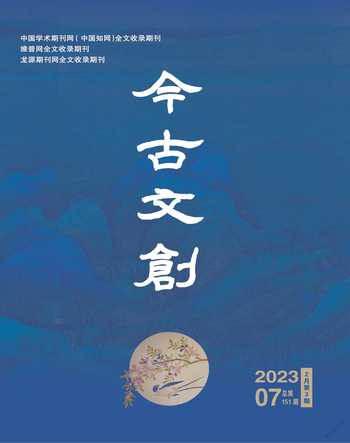識解視域下的譯者創造性翻譯研究
【摘要】 識解是人們選擇用不同方式對同一個情境進行概念化的認知能力。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對一個語言表達式有不同的理解和有意識地翻譯,這種有意識的做法帶有譯者的創造性翻譯。認知語言學中的識解理論則為人們主觀思維的分析提供了可行的方案。本文以潘家洵翻譯《玩偶之家》為研究案例,主要從識解理論中的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詳略度這四個維度,對比該譯本的初譯本和復譯本,以期探討認知在翻譯過程中對譯者的影響。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識解;翻譯;玩偶之家
【中圖分類號】H059?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7-01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7.032
一、引言
認知語言學以體驗哲學和認知科學為理論背景,在反對以喬姆斯基為代表主張的轉換生成語法的基礎上而誕生,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認知語言學反對語言天賦說,認為語言的生成使用等機制可以通過人的認知加以解釋,認識能力是人類知識的根本。與形式語法觀點不同的是,認知語言學認為語義不只是客觀的表達,而是主觀和客觀的結合,因此認知語言學研究語義還涉及包括個人主觀看法以及心理等因素。
“意義”在國內外都是個古老的話題,一直為哲學家、語言學家和翻譯家密切關注的研究課題。蘭蓋克[1]對“意義”作出新的理解:從本質上講,意義是一種心理現象,與個人認知活動緊密相關,因此意義包括表面意思和隱喻含義,通過激活、整合人腦中相應的認知域和知識框架,就能獲得意義,因而意義具有主觀性。翻譯向來注重對原作的理解和對意義的表達,而意義的呈現很大程度上和譯者的主觀理解密切相關。因此識解可以為翻譯研究所用,本文將基于識解概念,從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詳略度這四個維度結合翻譯個案進行討論。
二、識解與翻譯研究回顧
目前國內關于認知與翻譯的研究集中在對翻譯的概念和案例分析兩大類,研究的主題多聚焦識解的主觀性、意象圖式模式與等值翻譯、識解機制的四或五要素來研究翻譯。
首先是討論識解的主觀性。王寅[2]從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詳略度這四方面分析翻譯的主觀性,認為意義是體驗的概念化,即從體驗和識解兩個角度來解釋意義。王明樹[3]、王明樹和文旭[4]基于主觀化理論,分別從視角、情感和認識情態三個層面,以及六維度提出翻譯中的“主觀化對等”概念。王寅[5]以認知翻譯學為理論基礎,用認知語言學所提出的用以解釋語言表達主觀性的識解機制,來討論在譯入語語境中識解原作的意圖和意義。
其次是討論翻譯中的“等值”問題。宋德生[6]用意象圖式模式來討論翻譯的等值問題,等值只是經驗結構的相似。他指出文化的可譯性來自人類經驗結構的相似,而后者是龐大的意象圖式網絡,并作為媒介連接匹配譯文的不同文化意象。金勝昔[7]提出了實現原文和譯文認知等效憑借最大關聯和最佳關聯兩個途徑。最大關聯指譯者將原作者識解維度的操作復制到譯文里,譯入語讀者得以獲得原文讀者的感受。最佳關聯是指譯者按照譯文讀者認識維度的操作來處理譯文,建構語言的表達。
再者提出翻譯即認知重構。肖坤學[8]提出譯文表達就是識解的重構,并指出翻譯的第一步是譯者對原作者識解世界的解讀,繼而以符合譯文讀者識解運作的方式來重構原文情境。肖坤學和金勝昔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從識解維度解讀的翻譯注重譯者對作者的理解和讀者接受這兩方面。譚業升[9]提出翻譯轉換的認知實質是識解的轉換或重構,這種識解重構是翻譯體系中的核心能力。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將識解維度運用于翻譯過程的解讀,識解概念以及不斷發展壯大的認知翻譯學,對解讀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特意使用主觀性和創造性的表達,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
三、識解與創造性翻譯
蘭蓋克[1]138提出“認知語法的分析以識解為基礎,識解是指人們用不同方法對同一場景進行概念化的認知能力”,具體來講是“指人們通過確定不同轄域、選擇不同視角、突顯不同焦點、權衡不同精細度來觀察事態和解釋場景的認知能力,是形成概念體系、語義結構和進行語言表達的必經之路” [1]212。蘭蓋克認為,識解包括轄域、突顯、視角、背景、詳略度,它們能解釋人們面對相同場景時產生不同語言表述的因素。王寅將其五要素歸納整合為四要素,將“轄域”和“背景”合并,即“識解”包含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詳略度這四項內容。識解為人類主觀性的分析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同時也可以應用于翻譯認知過程的闡釋[5]54。認知在譯者翻譯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識解對于翻譯現象可以作出比較完整的解釋。本文收集潘家洵翻譯的易卜生戲劇《玩偶之家》的初譯本和復譯本,將分別從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詳略度這四個維度加以分析。
(一)轄域和背景
轄域指語言表達式背后所關聯的體驗和概念域,包括參照體和突顯物。人們的語言表達式和對文本意義的準確理解均受限于轄域,轄域一方面提供對不同語言表達式的直接經驗來源,并作為與之相關的多個語言表達式的背景知識庫,就涉及百科性的文化背景知識。一方面,百科知識作為一種背景性參照,能夠幫助主體去使用被激活的相關知識域,并將該知識域的內容前景化,而被激活的最大內容就是認知域中的最大轄域,而未被激活的轄域則被后景化[10]57。另一方面,背景這一視點為文化翻譯學派所強調,在翻譯中尤其強調譯者對原作和譯入語語境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掌握。翻譯涉及兩種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轉換,也可以說是從源域到目標域的轉換,隱喻便可以納入當中進行討論。以潘家洵在《玩偶之家》中文化意象詞的翻譯:
例1
英譯本:But now I must get clear of it all.
潘譯本:現在我想洗手不干事了。
例2
英譯本:I am open to all sorts of outside influence.
潘譯本:說我心軟意活,棉花耳朵。
例1是柯洛克斯泰與娜拉在私下見面時表明的心聲。柯洛克斯泰曾經想要以娜拉借債的名義來打擊海爾茂夫婦,但后來為洗清自己的名譽而進入海爾茂所在的銀行任職。潘家洵將“get clear of it”翻譯成“洗手不干”,極具中國文化特色。而“洗手不干”這個成語引出了清朝一則典故,來源自文康的《兒女英雄傳》。與“洗手不干”相近的近義詞有脫胎換骨、改邪歸正、洗心革面,因此從意圖和意象中都能夠表達出人物的神情。這個詞蘊含中國文化特色,從源語向譯入語的轉換。
例2是海爾茂不愿意自己公司的事情遭妻子指手畫腳,并且讓自己淪為職員間的笑話,因此堅決不肯被說服。潘家洵將原文中的 “be open to all sorts of? influence”有意識地用上了中國的典故并將其翻譯成“心軟意活,棉花耳朵”,讓中國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一句歇后語“棉花耳朵——耳根子軟”,簡明扼要地說明他怕老婆。譯者注意到文化隱喻的不同,有意識地選擇傾向目的語讀者的翻譯策略,因此也實現了從源語、文化向譯入語文化意象的轉換。
(二)視角
繼描述范圍與背景之后,就應該考慮從哪個視角來進行觀察。視角是人們對事體進行觀察描述所選擇的一種角度,體現了觀察者和該場景之間的一種相對關系。蘭蓋克將觀察者定義為可以理解語言表達式意義的體驗者,即說話人和聽話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場景進行觀察和描述,相應的就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語言表達式通常會激活一個最佳視點來作為它們意義的一部分,選取視角的不同會導致認知參照點的不同。參照的不同就意味著概念化的差異,反映在語言層面就是語言表達的不同,如詞匯的使用和句型的選擇和時態語態轉換、敘述角度等等。泰爾米[11]68認為視角就是觀察某個事物或場景的空間和心理角度,包括有位置、距離和方式這些因素。因此,視角就涉及主體觀察認識事物的立場態度和時空角度、價值取向等心理因素。以潘家洵《玩偶之家》中初譯本和復譯本為例來看敘事角度的轉換:
例3
英譯本:A bell rings in the hall outside. Presently the outer door of the flat is heard to open. Then Nora enters, humming gaily. She is in outdoor dress,and carries several parcels, which she lays on the right-hand table. She leaves the door into the hall open, and a Porter is seen outside, carrying a Christmas-tree and a basket, which he gives to the Maid-Servant who has opened the door.
初譯本:外廳里有鈴響。立刻就一聽見外面的門開了。娜拉很高興的嘴里哼著走了進來。他穿著出門的衣服,把手里的幾包東西放在右邊桌上,他把通外廳的門敞著,看見外面站著一個挑夫,把手里拿的一顆圣誕樹和一只籃子遞給開門的女仆。
復譯本:門廳里有鈴聲。緊接著就聽見外面的門打開了。娜拉高高興興地哼著從外面走進來,身上穿著出門衣服,手里拿著幾包東西。她把東西擱在右邊桌子上,讓門廳的門敞著。我們看見外頭站著個腳夫,正在把手里一棵圣誕樹和一只籃子遞給開門的女用人。
例3為第一幕的場景描寫。整段從第三句到最后一小句,舊譯本原封不動地按照英譯本的語言順序直譯出來,并無任何斷句。這種并列式語句讓人物的動作看起來是同時并列進行,給人閱讀以展現一長串描述性動作,作為背景幕后,對讀者而言沒有任何關注焦點。復譯本則將英譯本的最后一句話拆分成三個小句。每一個小句的結束隨即將讀者引向另一個討論的對象。潘家洵在最后一個小句的處理上頗為用心,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腳夫,這與下面正文娜拉和腳夫的對話是相照應的。因此,從復譯本對這第一幕的場景設置來看,潘家洵將人物動作的邏輯連貫與引起讀者關注的方式使得譯文的對象更加集中。場景的作用不再是靜態的描寫,而是激發讀者關注的動態畫面。因此,潘家洵將讀者作為第一視角進入戲劇的情節,更加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
(三)突顯
“突顯”直接反映了人們從主觀意志上對某個事物或事件的最感興趣和最具吸引力的部分。人們認知的不對稱性也影響了語言表達的不對稱性,因此語言使用者常常將注意力所聚焦的對象突顯出來,為了達到最具思維和表達的目的,滿足最具對語境理解的需求,就會將觀察對象的某個部分突顯強化出來,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結構。蘭蓋克指出兩種突顯模式,即勾勒包括側顯和基體兩個要素、射體和界標組合。射體和界標組合同時也構成了圖形與背景的關系。圖形背景模式是認知能力中最基礎的特點,往往也和物體的運動有關,往往運動的物體較之靜態的對象更容易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因此得以突顯成為主要焦點,也稱為射體,而其余次要焦點則視為界標,成為背景。
以上文中的例3來看,原先的舊譯本中第4句開始,潘家洵在翻譯英譯本所有內容時,出現了兩次以“他”為主語的人稱改動,而其余以謂語動詞為主的小句則可以默認為其主語也是文中的“他”,即女主人公娜拉。因此在舊譯本中,所有動作的施事者都聚焦在女主人公娜拉身上。娜拉顯然成為整個句段的焦點人物被突顯出來。但在復譯本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譯者在視角上有意識所作出的調整和改動。從最后一個小句直到句末,視角不再聚焦在女主人公娜拉身上,而是以讀者為第一視角。讀者成為該句段的施事者和被突顯的對象,其余對象則被弱化和虛化處理。因此突顯與視角也是密切相關的,復譯本中的這種處理對比原文而言,其實更加符合原文要傳達的意思。
(四)詳略度
詳略度是指說話人能夠決定以詳細程度的不同對某個場景或對象進行描述。詳略度和突顯密切相關,由于說話人不同的意圖和目的,最能夠表達其意思的內容往往會被更加詳細地表述出來,從而被突顯出來,其余內容則會被省略和忽略掉。在翻譯中,改寫的現象是以往翻譯研究關注較多的一個熱門話題。以“五四運動”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外譯中翻譯現象為例,兩個時期的翻譯都呈現出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趨勢,因此翻譯的實用性功能甚至超過其藝術價值,而為了符合意識形態的需求,譯者會有意識地增加或者刪減原文中的內容,并且改動原文的意義。潘家洵對《玩偶之家》原文中“The Joint Stock Bank”的翻譯有兩次的變化,他把原先初譯本中“銀行”的譯文重新翻譯為“合資股份銀行”。原先舊譯本中譯文的概念更加泛化,也并沒有追求更加精準的翻譯,但是后來復譯本的譯文則更加符合現當代的概念認知,翻譯更加準確,內容更加翔實。
四、結語
認知語言學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翻譯研究中翻譯家研究是近年來國內不斷關注的話題,而認知、識解等概念為翻譯家研究,尤其對于探索和分析譯者創造性翻譯背后的原因提供了一個合理而科學的理論支撐。對同一部文學作品,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理解,而同一個譯者前期翻譯和其后期翻譯又有不一樣的理解和呈現。譯者不同的理解就導致了不一樣的語言表達,這其中包含了譯者各種創造性的想法。識解就能夠從不同的維度來解析譯者各種創造性翻譯的意圖。
參考文獻:
[1]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王寅.認知語言學的“體驗性概念化”對翻譯主客觀性的解釋力——一項基于古詩《楓橋夜泊》40篇英語譯文的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3):211-217.
[3]王明樹.翻譯中的“主觀性識解——反思中國傳統譯論意義觀[J].重慶大學學報,2009,(4):144-147.
[4]王明樹,文旭.“主觀化對等”在翻譯中的應用——以李白詩歌《送友人》英譯為例[J].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9,(5):63-65.
[5]王寅.認知翻譯學與識解機制[J].翻譯研究,2013,(1):52-57.
[6]宋德生.認知的體驗性對等值翻譯的途釋[J].中國翻譯,2005,(5):21-24.
[7]金勝昔,林正軍.識解理論關照下的等效翻譯[J].東北師大學報,2015,(2):119-123.
[8]肖坤學.識解重構: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譯文表達[J].外語研究,2013,(4):81-86.
[9]譚業升.翻譯能力的認知觀:以識解為中心[J].中國翻譯,2016,(5):15-22.
[10]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Vol. 2)[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作者簡介:
余雨露,女,重慶永川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