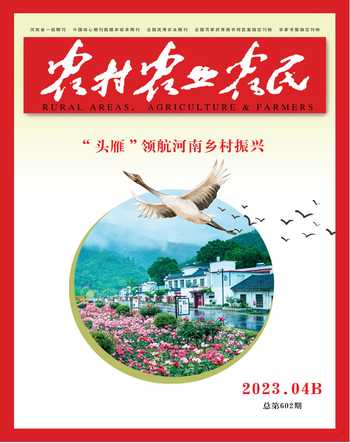新時代家風治理的維度透視
沈維君 徐寒建
摘 要: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邏輯起點。本文圍繞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剖析家風建設的“公共精神培育”“規范約束”“道德教化”三個功能要素與“自治”“法治”“德治”三個維度的內在邏輯。以浙江省諸暨市為例,探究婦聯組織作為牽頭部門,把家風建設融入基層治理的具體實踐。從實踐看,實現家風建設的治理創新,還需要從數字化、制度化、多元化治理等多方面進行構建,進而促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
關鍵詞:新時代;家風建設;基層治理;婦聯組織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家風建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報告明確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注重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首次將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寫入黨代會報告。家風建設不只是家庭的事情,還是整個國家高效、有序治理的需要,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著力點。在構建基層治理體系的發展語境中,深入研究如何激活家風建設的內在治理功能,如何實現治理有效等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也是實踐創新的需要。
一、家風建設的治理功能與“三治融合”的內在邏輯
本文根據王淑琴提出的家風建設“公共精神培育”“規范約束”“道德教化”三個治理功能進行分析,研究家風建設與“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邏輯。
(一)家風建設的公共精神要素,體現自治的核心
公共精神是公眾參與公共事務、對公共規則的認同、維護公共利益的倫理精神。家庭作為一個共同體,是培育公共精神的重要場域。在傳統社會,生產生活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單位,“家本位”思想是傳統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家庭成員對自己家庭及家族負有責任,強調以家庭家族的集體利益為最高利益。因此,在傳統社會,在家訓和族規的教化之下,公共事務的處理變得容易起來。以家庭和家族為主的倫理共同體,是維持傳統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力量。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在非農化、市場化的沖擊下,人際關系開始疏離,鄉村共同體逐漸式微,公共精神開始缺失,人們更多地關注個人利益,對不涉及個人利益的公共事務往往不夠關心。面對新形勢,要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重構新時代家風內涵,對家庭成員進行觀念引導,促進公民道德向善,培育公共精神,激發村民自治的積極性和活力。“中國村民自治試圖喚醒村民在公共領域的公民精神、自治精神和公共精神,從被動接受向主動參與轉變, 從依賴他者到成為主動者轉變。”可見公共精神培育,與自治的核心內涵不謀而合。
(二)家風建設的規范約束要素,契合法治的功用
在傳統社會,家風依托于血緣共同體,注重家族和家庭成員之間的身份差異,如長幼有序、尊卑有別,根據身份規定形成行為規范。正如梁漱溟提出的,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傳統社會主要以“禮”進行內部秩序的規約。費孝通提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公共秩序的維持無須仰賴國家法律,而是僅依靠“對傳統規則的服膺”,即所謂“禮治”。近代以來,傳統社會的“三綱五常”包含著愚忠愚孝、喪失獨立人格等糟粕。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傳統家風中的精髓仍具有時代意義,在建設現代家風中需加以鑒別。家風作為非正式制度,是一種內在精神,也是外在的硬性規范約束,包括家訓、家規、族規等行為規范,其規則意識的內涵和社會秩序構建的本質,與法治的功用相契合。2020年5月28日,“優良家風”寫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這是法治的進步。2022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首次就家庭教育進行專門立法,從法律層面將家庭教育從“家事”上升為“國事”。
(三)家風建設的道德修養要素,反映德治的本質
《大學》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在古代社會,強調只有在加強個人道德修養的基礎上,才能遞進式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是人接受教育的起點,家庭對一個人的品德形成、道德養成、價值觀培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傳統社會的家風建設具有宗法性,注重對有親緣關系的家庭成員、家族成員的人文禮俗和道德倫理的教養,主要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儒家文化中的“八德”。傳統家風就是家庭(家族)成員在家長的長期影響和教導下,逐漸積淀和形成相對穩定的見習,其蘊含的價值取向內化于家庭(家族)成員的思想之中,作為無形力量,潛移默化熏陶著人們,間接維護了社會秩序。現代社會,優良家風作為“傳家寶”,是傳播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重要渠道。家風不僅僅影響家庭成員,還影響著黨風、政風,乃至整個社會風尚。“作風—家風—國風”和“個人—家庭—國”是有機統一的。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家風建設的道德教化功能有助于減少社會治理成本,道德在社會治理中屬于社會自我管理,成本遠低于法律,可通過培養誠實、守信、團結、互助等美德,有效避免或化解矛盾糾紛。
二、新時代家風建設助推基層社會治理的具體實踐
本文選取浙江省諸暨市為研究對象,作為全國“楓橋經驗”的發源地,諸暨婦聯創造性地運用新時代“楓橋經驗”,把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融入基層治理。基于此,對案例進行客觀分析,圍繞自治、法治、德治三個維度進行剖析。
(一)解決治理載體的問題:自治強基,加強隊伍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男性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鄉村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留守在農村的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農村婦女成為鄉村治理的新型主力軍,對家風建設起著重要作用。諸暨婦聯從組織架構、資源整合、能力培訓等方面,不斷加強婦女隊伍建設。
一是建立五級聯動網格。建立“市—鎮—村—網格—服務小組”五級組織架構,多層面嵌入基層治理。以“全科網格+婦聯執委”“全科網格+巾幗志愿服務隊”等形式,讓婦女隊伍、婦聯陣地與轄區網格緊密融合,將婦聯的服務延伸到婦女群眾組織的最小單元。
二是整合巾幗志愿力量。婦聯組織充分利用“聯”的優勢,整合巾幗志愿者資源,廣泛參與到美麗鄉村建設、文明建設、矛盾化解、幫扶濟困等工作中。諸暨已引導孵化700余支“七彩玫瑰”巾幗志愿服務隊、15000余名巾幗志愿者參與到基層治理的各個方面。
三是組建專業家庭教育隊伍。家庭是第一課堂,家庭教育隊伍的專業化水平很大程度決定了家庭服務的質量和水平。通過實施婦聯隊伍賦能計劃,對婚姻家庭輔導員、家庭教育講師團、家庭教育指導員進行培訓,增強婦女組織服務群眾、參與治理的能力。
(二)解決治理手段的問題:法治保障,構建和諧家庭
家風建設中,既要發揮其道德屬性,又要注重制度保障,讓法律制度與公序良俗凝聚合力。宏觀層面,國家出臺一系列的相關政策法規。微觀層面,聚焦家事,以家庭化解服務為切入點,完善保障機制,維護婦女合法權益,促進家庭平安、社會和諧。
一是深化家事調解機制。實施婦聯組織“聯網、入格、進戶”制度、“四必訪”制度、婦情家情預警等機制,對重點關注對象定期走訪、動態管理,實現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的目的。
二是建立“1+X”調解品牌陣地。市級層面,成立“西施娘家人”工作室,吸納律師、心理咨詢師等專業又熱心的調解人員。鄉鎮層面,打造“楓橋大媽”“江大姐調解室”等子品牌建設陣地。
三是延伸調解陣地。利用駐點市矛盾調解中心、打造網絡“云”陣地、婚姻登記處設立家庭調解室、深化鎮街村級家庭矛盾調解組織建設等多種方式,延伸調解服務,構建多元化問題解決渠道。重點搭建村級“楓橋式婦女之家”平臺,在一線解決涉及群眾關心的權益問題和實際困難。
(三)解決治理主體思想精神層面的問題:德治育心,弘揚向善新風
家風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通過加強家風建設,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諸暨市利用活動評比、激勵措施等方式,把家風傳承落實到日常言行之中,在弘揚家庭美德的同時,營造出崇德尚賢的氛圍,增強群眾的參與感和獲得感。
一是選樹“最美家庭”等先進典型。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道德榜樣通過自身所承載的道德精神以及文化認同傳遞著正能量。尤其是身邊的榜樣,更能喚醒人們內心的情感共鳴、思想認同。
二是建立“有德者更有得”的禮遇機制。市婦聯招募愛心單位聯動,為最美家庭推出金融、教育、文化、旅游等禮遇項目。如公交公司推出一年內免費乘公交禮遇,雖物質上獎勵不多,以精神鼓勵為主,但樹立了“好人有好報、德者有所得”的價值導向。
三是廣泛開展家教宣傳。家教是立德樹人的重要力量,依托家庭教育講師團隊,向社會公眾開辦線上線下家庭教育公益課堂,不定期邀請家庭教育專家開展專題講座,向社會傳播正確的家教觀念和知識。
三、未來的方向和展望
我們通過對諸暨市案例的調研分析,發現了一些實踐短板。比如鄉風文明建設中,群眾的內生動力還不足,長效機制還需要健全。家風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在新時代背景下,要更好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實現治理創新,還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數字化治理:打通供給和需求渠道
隨著社會的深刻變革,家庭結構、家庭規模、家庭觀念發生了新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家庭建設的新期盼新需求”。因此,準確把握家庭的需求,是堅持人民至上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有效性的首要條件。在此過程中,可以利用大數據的強大支撐,全面掌握、精準分析家庭動態信息,以數字化手段實現高效精準管理。如浙江舟山以“家庭”為切入口,建設 “普陀幸福云家”應用場景,以家庭檔案庫和婦女志愿者庫這兩個數據庫為基礎,設立志愿服務臺、求助臺、報料臺等,以數字化訂單制形式解決個性化需求。
(二)制度化治理:推進家風積分制管理
在具體操作中,以家風文化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模式,主要是依托非正式制度的軟治理,利用文化、道德、觀念等柔和的方式,達到教育、引導、約束等功能。但如果非正式制度缺乏具體的制度支撐,則難以發揮長效作用。村規民約作為村民自治的重要規范,普遍存在形式化的問題,結構千篇一律,內容簡約模糊,缺少對于具體事務的處理細則,約束作用不強。因此,鄉村治理中可以實行家風積分制、指數化管理,作為配套制度,激發群眾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積極性。如浙江浦江推出“5+1”模式的“好家風指數”評價準則,實現村民日常行為量化管理,為鄉村共同體建設注入持久的動能。
(三)多元化治理:開展協同合作
要更好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作用,需要多元治理主體參與,調動職能部門、地方政府、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健全聯動協同機制。如浙江富陽推出家事多元共治系統——“家和碼”,建立“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精準服務”的家庭建設工作機制,首次正式將家庭建設工作納入黨政議題,建立了區委政法委和區婦聯牽頭負責、區級相關部門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多元共治工作體系。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9-11-06(004).
[2]王淑琴.家風建設: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益滋養[J].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3(02):39-45.
[3]李文釗,張黎黎.村民自治:集體行動、制度變遷與公共精神的培育——貴州省習水縣趕場坡村組自治的個案研究[J].管理世界,2008(10):64-74.
[4]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7.
[5]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3:1-2.
[7]王燁,陽葉青.從道德與法律關系看社會治理[J].人民論壇,2014(35):122-124.
[責任編輯:朱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