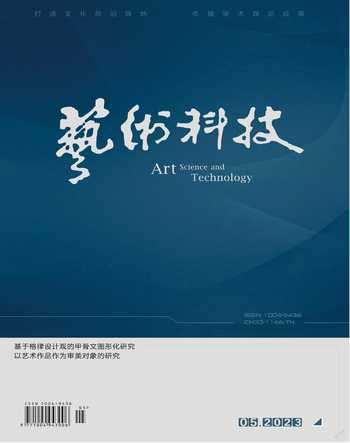系列電影的公式化難題研究
景晨雨 宋曉利
摘要:敘事學的一個研究方向是歸納與尋找敘事的規律,試圖尋到一套通用的敘事語法,而系列電影常常會產生固定的敘事框架,這些固定的框架使故事具有明確的主題與意義,一方面起到了鞏固系列電影特點、增強品牌效應的作用,另一方面限制了導演敘事的自由度,使得系列電影容易出現公式化的缺陷,無法跳脫前作的束縛,因此如何戴著鐐銬跳舞成為系列電影創作不得不解決的問題。20世紀以來,日本產出了大量的長系列電影,如《哆啦A夢》《男人真辛苦》《完全笨蛋》系列,日本導演在系列電影的公式化方面有著相對成熟的應對方式。基于時代因素,日本大量系列電影受資方和題材的制約,在公式化的影片結構中傳達不變的精神內核已成為日本電影的常態。《哆啦A夢》的劇場版系列和《名偵探柯南》《蠟筆小新》一同被稱為日本動畫電影的三棵常青樹。但《名偵探柯南》逐漸滑入爆米花電影的范疇,在票房上升的同時,口碑不斷下降,《哆啦A夢》系列電影則實現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消除了先前的劇場版危機。文章以《哆啦A夢》系列電影為例,從故事形態學的角度解構其敘事框架與人物職能,探究系列電影如何在系列框架的束縛下創造新經典。
關鍵詞:《哆啦A夢》;敘事;系列電影;公式化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5-0-04
0 前言
2023年3月,最新的《哆啦A夢》年度電影《哆啦A夢:大雄與天空的理想鄉》在日本上映。作為系列作品的新開端,筆者借此機會回顧50周年紀念的《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其質量無疑是近幾年來《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一個高峰。事實上,近幾年的《哆啦A夢》系列電影擺脫了以往的原創魔咒,重制和改編作品的占比大幅減少。即使是作為《哆啦A夢:大雄的恐龍2006》重制版的《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也只是化用題材而非完全重制。“新”不僅意味著新的恐龍品種,還意味著這部作品延續曾經的故事,是新的故事。從前劇場版的大量伏筆這次被放在明面上,與彩蛋和情懷共同呈現。電影兼顧新老觀眾的觀影體驗,老觀眾能看到情懷,新觀眾也可以全身心投入劇情,劇情脈絡簡單,情節頗具趣味性。作品對生命進化的科普深入,對人與自然的思考十分深刻,但卻以簡單的方式表現出來,無論是兒童還是成年人都可以收獲獨屬于自己的快樂。
1 《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時代困境與改變
任何電影的敘事都是與其思想內核牢牢結合的。探究《哆啦A夢》系列電影及其敘事,必須先了解電影的思想內核。電影中的伊甸島可以說是飽受天災摧殘的日本列島本身,電影不可避免地體現了日本人的生命觀、價值觀及時代特色。
1.1 藤子·F.不二雄時期的《哆啦A夢》
原作者藤子·F.不二雄在逝世前監制了《哆啦A夢》系列的17部電影作品,從這17部作品中能看出時代背景對電影的深遠影響。第一部電影是1980年的《大雄的恐龍》。這個故事是《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開山之作,并沒有過多展現社會關系,而是將筆墨重點放在人物之間的情感及弘揚愛與善的思想上,由此塑造了《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思想內核和經典的人物形象。
之后的《哆啦A夢》系列電影開始表達對社會現象的反思。在藤子·F.不二雄時期的第一階段,電影對天皇制度的抨擊要比對工具理性的抨擊更加激烈。首先是1985年的《哆啦A夢:大雄的宇宙小戰爭》,其從主體角度展現了當時日本向內高壓統治的恐怖氛圍,1986年的《哆啦A夢:大雄與鐵人兵團》則以客體視角表現狂熱的民族中心主義,即納粹主義的毀滅性與反人類性,抨擊日本的軍國主義制度。鐵人兵團以神的名義開始戰爭,是當時日本借天皇權威作為侵略合法性依據的體現,這種權威摧毀了日本人民的自我思考能力。女主角莉莉露因為盲從指揮官和神,行為與自身的認知產生了沖突,通過靜香的開導才獲得內心的自由,從而擺脫自上而下的權威束縛。影片中鐵人兵團的制度象征著當時日本實行的病態制度,即將對國內民眾的剝削轉變為對他國人民的剝削,以實現所謂的日本的幸福。日本將這套西方殖民制度與本土的天皇制度相結合,造成了病態的個體與社會。這一階段的批判大多是直白的反戰思想宣揚,以及對天皇制度的辛辣諷刺。
藤子·F.不二雄對日本社會的思考在《哆啦A夢:大雄的創世日記》中達到了頂峰。與之前的大長篇敘述一個故事的形式不同,《哆啦A夢:大雄的創世日記》由數個小故事組成,大雄等只是牽涉其中而非主要角色。創世初期,大雄便抹除了神的權威,而后解構了從石器時代到現代世界主流的神話內容,諷刺了愚昧、落后的習俗。在影片前半部分,大雄希望創造一個烏托邦,人類歷史上的悲劇卻依舊重演。影片后半部分,大雄的宣言讓人神的界限被打破,從此新世界的人民與神同等,再無高下之分。影片對工具理性的反思更具有顛覆性,工具理性乃至人類文明本身,都不一定是地球演化的唯一答案。如果世界不過是造物主的惡作劇,那么一只昆蟲創造文明也完全合理。《哆啦A夢:大雄的創世日記》可以說是藤子·F.不二雄思想的集大成者。
1.2 后藤子·F.不二雄時代的《哆啦A夢》電影
近幾年《哆啦A夢》電影的內核思想是一致的:每一個孩子都擁有才能,只要鼓勵與理解他們,他們就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在《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中,大雄與小楸具有相似點,影片對兩個人的成長作了平行對比,大雄翻不好單杠,小楸不會飛行。在影片前期,大雄放任小楸自由成長,但隨著劇情的發展,開始焦躁地嘗試教小楸飛行。這里大雄突破了以往孩子的形象,以家長的形象出現。大雄在小楸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將自己丟失的自信寄托在小楸身上。翻單杠是不起眼的小事,但象征著大雄無法實現的目標,隱含著大雄落后于同齡人的自卑心理。大雄將自身的期待過多地投射在小楸身上,最終造成了與小楸的決裂。這個情節是影片隱藏在觀照人與自然、人與歷史、電車難題之下的深層表達,即關注現代家庭中家長與孩子的關系,家長是否了解孩子,是否過多地投射了自己的期待,是否讓孩子承擔了過多的壓力。
《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對此給出了答案——陪伴與理解。靜香敏銳地察覺到了二者決裂的根本原因,大雄也幡然醒悟。他不再恐懼,因為他獲得了最珍視的人的認可;他不再為小楸的未來焦慮,因為他明白了焦慮無法解決問題,理解小楸才是正確的做法。他來到小楸的身邊,首先開始翻單杠的訓練,告訴小楸它并不孤單。
平成年代已經過去,令和年代的日本面臨著少子化、老年化的危機,年輕人開始成為家庭支柱。正是因為處于這樣的時期,家庭矛盾大量爆發,新時代的《哆啦A夢》重拾了藤子·F.不二雄的思想,以兒童都能看懂并喜愛的大冒險作為表層敘事,重點關注環保、未來、歷史等宏大的主題,但其內核卻著眼于當代日本社會,關注日益嚴重的家庭矛盾,實現了《哆啦A夢》電影的一大轉型,這也是時代變化的必然結果。
2 《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敘事框架
2.1 敘事的基本原理
2017年開始,連續4年的《哆啦A夢》電影都是原創作品,這打破了以往一年重置、一年原創的習慣。但即使是打著重制版名號的作品,也在劇情上作出了一定的改變,這些原創作品逐漸撕下了低質量的標簽,回到了藤子·F.不二雄時代的制作水準。《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作為近幾年《哆啦A夢》電影的代表,成功挽回了《哆啦A夢》系列電影日漸下滑的口碑。
但這并不能改變《哆啦A夢》系列電影公式化的狀況,其遵守著固定的影片邏輯。弗拉基米爾·普羅普《民間故事形態學》一書總結了民俗故事的結構,其采用的方法是研究民俗故事與其他類型故事結構的差異,以及民俗故事的特點。弗拉基米爾·普羅普認為,民俗故事大多是民間傳說、神話與童話故事,其敘事淺顯,要講述的道理也大多相似,但因為地域與文化不同,人物變化多樣。因此,民俗故事不應通過單個人物進行分析,而應基于人物的職能與行動來分析。人物的形象可能是無限的,人物及其負擔的職能是有限的[1]。筆者以《哆啦A夢》系列電影為例進行分析。
例1:在《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中,大雄被胖虎、小夫嘲笑,于是夸下海口決定尋找恐龍蛋,并求助哆啦A夢。
例2:在《哆啦A夢之大雄的冒險》中,大雄考試失利,認為在魔法世界他會更加聰明,于是求助哆啦A夢。
這兩部影片的情節、人物、背景各不相同,但結構如出一轍,即主人公受挫,希望擺脫困境,求助他人。在這個結構中,將大雄換成任何一個角色都可以成立。而《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成功公式化就在于其固定了每個角色的職能,如此,在構思劇情時,能夠輕易確定各個角色的行為,劇情應該被哪個角色觸發。在此基礎上的創作,無論是照搬經典還是創新,都比從頭創作來得容易。
普羅普談及民俗敘事中的人物形象時,將其劃分為侵犯者、贈予者、助手、公主及其父親、委托者、英雄與假英雄,并且把敘事發展的可能劃分為31種行動,角色可能超出自身的形象范圍或一個角色同時擁有多種職能。對于如今的電影敘事來說,這種分類比較落伍,但依舊有著鮮明的指導意義。普羅普之后的克洛德·布雷蒙認為,身份職能的應用不僅僅在民俗故事中,其幾乎可以運用于任何敘事,但必須糾正這一理論中的必然因素[2]。必然性,即主人公必然接受考驗,經過考驗后必然成長。對于民俗故事來說,這種必然性使故事具有明確的主題與意義;對于電影來說,這種必然性則摧毀了電影的多樣性。
但《哆啦A夢》系列電影卻大量運用必然性因素,即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將故事的結局限定好,只是過程有所變化。在這一點上,《哆啦A夢》系列電影應當是受日本系列電影的影響。早期,日本有大量的系列電影,如著名的《男人真辛苦》系列。主人公作為浪子,來到一個城市,愛上一名女性并試圖追求她,隨后因為一些事情離開了城市,與這名女性的戀情也不了了之。《男人真辛苦》系列電影將近48部,每一部都有著相同的劇情構架,卻在日本大受歡迎,雖然評論家對其大肆抨擊,但每部電影的票房都大獲成功,原因是影片中展現的美好社會給予了觀眾一絲慰藉[3]。《哆啦A夢》系列電影同樣如此,通過公式化的影片結構,傳達不變的愛與夢想、善良的精神內核,其并不需要過多的改變。對觀眾來說,《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職能便是為其提供心靈的避風港。因此,在劇情構架、主題傾向、人物職能明確的基礎上,要盡可能多變,渲染情緒,調動觀眾的情緒。
2.2 《哆啦A夢》系列電影中人物的職能
下文分析《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中主要角色的職能及劇情架構,將其與《大雄的恐龍》對比,以明確導演如何在固定架構中再創作。
新舊版本中人物的基本職能如下。
大雄:影片的主人公,在劇情中常常扮演弱者、委托者,是一切矛盾的解決者與引發者。
哆啦A夢:贈予者與助手。在影片中負責幫助主人公行動,解決常理上不可能的請求和委托,是劇情發展的合理性擔當。
胖虎與小夫:侵犯者與助手,負責推動主人公行動,是最初矛盾的發起者,也是劇情中期矛盾的發起者。
靜香:助手與導師,是主人公成功的推動力。
恐龍:新舊恐龍的基本職能沒有變化,即公主的形象,是主人公行動的理由和動力。在舊版中,恐龍保持自我形象;在新版中,恐龍同時承擔著主人公的職能,大雄與恐龍互為對照,彼此學習,恐龍從被動的接受者變為主動的尋求者。
偷獵隊:只在舊版本中出現的人物,其為純粹的侵犯者。
時空搜查隊:時空搜查隊作為電影的大背景與最終的收尾人員,在舊版中只起到使主人公行動合法化與為主人公行為收尾的作用。在新版中卻成為矛盾的進一步觸發者,推動電影劇情達到高潮。
通過新舊人物的對比可以看出導演在系列電影框架下的再創作,大雄等五人形象塑造完善,于是在敘事上著重改變未曾形成角色定式的恐龍、反派、時空搜查隊等的形象,以側面展現原有人物的經典性格并展現其新性格。這種繞開定式角色,側面描寫的手法在系列電影中較為常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于《真三國無雙》系列。由于三國中的經典形象如劉備、曹操等形象完善,因此創作者繞過這幾個角色,塑造如張星彩、關平等未形成定式的角色,使其人氣超過了原有角色。但《哆啦A夢》系列電影不能創造新主人公,因此導演使用這種繞開定式角色的手法,主要是為了在展現經典角色典型性格的同時,通過其與新角色的互動揭露角色的新性格,塑造立體的人物形象[4]。
2.3 新舊電影的劇情情節與構架對比
通常,電影劇情可以分為三段:前奏、發展及高潮。與中國電影的敘事結構不同,日本電影慣于放大細節,充分展現人物的成長脈絡,而將高潮放在尾部,以達到使觀眾情感在短時間內爆發的目的。《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也是如此,電影的前奏部分是大雄找到恐龍蛋撫養小楸長大,發展部分是大雄五人組共同到白堊紀幫助小楸尋找伙伴,高潮部分則是將恐龍從隕石的撞擊中救出。
在影片的前奏部分,劇情架構并未完全脫離舊版,或者說是在有意致敬與模仿舊版,甚至照搬大量臺詞。這一方面戳中了舊版觀眾的情懷,另一方面也使劇情變得薄弱。而大雄與胖虎、小夫的打賭,從舊版的用鼻子吃面條改為用眼睛嚼花生等,也使新舊版本在敘事結構上保持了一致。
在發展部分,新舊版劇情最大的不同是時空警察的設定。時空警察以往作為正派角色登場,而新版中則放了一個煙幕彈,作為原作重制版,觀影者會不自覺代入舊版劇情,導演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時空警察吉爾以反派的形象登場,變成可怕的白猿與蝙蝠,其綁走小夫、胖虎和帶走基地中的恐龍標本無一不在暗示其恐龍偷獵者的身份,這大大優化了觀影體驗。
影片高潮部分的鋪墊較長,相較于舊版,新版更注重伏筆的回收,前期使用的朋友巧克力是胖虎逃脫的關鍵,時空警察抓捕大雄使用驗證卡證明了大雄的行為是歷史的一部分,大雄墜海被神似皮助的蛇頸龍救助等情節不僅回收了伏筆,還解釋了此前的電影。導演今井一曉認為,這是相對于《哆啦A夢》的世界觀的一次嘗試。這種嘗試挑戰了原著《哆啦A夢》的設定,增強了作品的曲折性,是較為成功的。從拯救恐龍開始,環環相扣的情節讓觀眾充滿了緊張感,而這緊張感在小楸終于飛翔于天空的那一刻完全釋放了出來,實現了電影情緒與結構上的閉環。
電影的最后,小楸展翅飛翔,象征著生命的進化,大雄也成功翻過單杠,完成了作為人的成長。電影全片沒有一個字的說教,卻將主題完美地表達了出來。
3 《哆啦A夢》系列電影擺脫敘事困境的原因
《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創作從1980年至今已經過去了43年,電影的數量超過40部。作為系列電影,《哆啦A夢》近年來逐漸擺脫了公式化的敘事困境與日漸下滑的口碑,其原因有二。
3.1 對系列電影的再定位
創作者認識到了電影日漸低齡化與搞笑化的問題,因此將重心轉向成人市場,在影片中加入符合青少年喜好的內容,還通過在社交網站傳播成年人關注的話題,提高討論度。小學館和東寶將哆啦A夢定位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使其常與時尚元素一起出現在傳媒上。盡管《哆啦A夢》永遠是以兒童為主要受眾的作品,但更加成人化、復雜的構圖與演出手法以及更深刻的內涵在新時代的系列電影中得到了展現。
3.2 劇情的原創化
從《哆啦A夢:大雄的恐龍2006》開始,《哆啦A夢》系列電影一直遵循一年原創、一年翻拍的規律。而近四年的《哆啦A夢:大雄的金銀島》《哆啦A夢:大雄的南極冰冰涼大冒險》《哆啦A夢:大雄的月球歷險記》都是原創作品,《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也有大量原創內容。同時其發展策略側重貼合流行元素,最為明顯的是《哆啦A夢:大雄的南極冰冰涼大冒險》中的“雪球地球”概念,其科學性得到了學者的肯定。
由此可以看出,系列電影擺脫公式化構架的關鍵在于重新定位受眾群體與貼合流行元素,使電影現代化,滿足時代需求。
4 結語
從早期的《哆啦A夢》系列電影到現在,可以看到其主題逐漸從對封建社會和古板制度的批判演變成對家庭矛盾、社會困境的反思,《哆啦A夢》系列電影作為日本社會的一面鏡子,隨著時代的變化,其傳達的文化內涵也不斷變化,成了日本文化生長的一塊土壤。從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豪言開創神話電影新宇宙起,我國的電影事業正嶄露頭角,吸收《哆啦A夢》系列電影的成功經驗,將我國特色文化內容轉譯為現代文化,是實現文化的跨時間跨語境傳播、創造中國電影系列IP的關鍵一步。
參考文獻:
[1] 劉云舟.電影敘事學研究[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3-12,72-80.
[2] 弗拉基米爾·普羅普.故事形態學[M].賈放,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24-59.
[3] 四方田犬彥.日本電影與戰后的神話[M].李斌,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70-85.
[4] 余安安.巴什拉的夢想詩學與哆啦A夢的夢想世界[J].名作欣賞,2014(9):157-160.
作者簡介:景晨雨(1998—),男,江蘇南通人,碩士在讀,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數字媒體藝術理論與實踐。
宋曉利(1981—),女,山東青島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從事文化產業經濟、文化產品的策劃與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