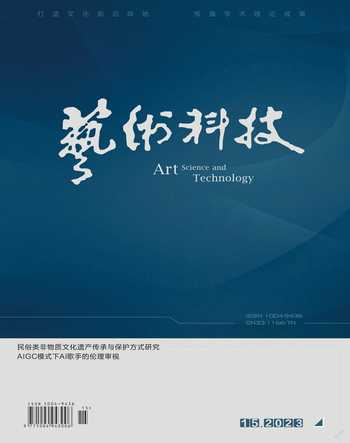社交媒體中的話語抵抗策略研究
摘要:作為當下流行的文化符號,“摸魚”從誕生伊始就與打工人的工作狀況和社會心態緊密聯系。赫勒認為,工作是有雙重屬性的,作為類本質活動,它可能是人錨定自身意義、尋求價值實現的一個途徑,但是這并不能否認勞動作為日常活動,具有讓人疲憊、倦怠的成分,“摸魚”行為就是緩解勞動消耗,實現勞動力再生產的一種方式。文章利用爬蟲軟件,抓取知乎平臺上關于“摸魚”現象的討論,并借助費爾克拉夫的批判話語分析方法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進行話語分析。研究認為,在“摸魚”文本中,打工人與資方被塑造為對立的權力兩級,并且呈現出愈發激烈的意識形態沖突。“摸魚”人所生產的文本反映了其對自身工作狀況、勞動權益的憂慮與不滿,但這并沒有轉化為改變現實的動力,而是流于后現代式的戲謔,成為一種消極被動的話語抵抗。文章認為,“摸魚”這一流行文化符號反映了當下職場打工人對工作環境存在的憂慮,受制于諸多現實壓力,打工人難以直接在現實環境里表達不滿,因此在網絡趣緣社群進行話語抵抗成為普遍的選擇之一。當然,“摸魚”人的話語抵抗并不是高烈度、對抗性質的,大多數“摸魚”人在網絡吐槽后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從這個層面上講,“摸魚”行為成為打工人自身再生產的一個途徑。
關鍵詞:“摸魚”;知乎;話語分析;抵抗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15-0-03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赫勒曾經對工作下了以下定義,她認為,“我們在雙重意義上使用‘工作這一詞:一方面,它指謂特定類型的日常活動,另一方面它指謂直接的類活動……馬克思常常使用兩個詞來表明這一區別:他稱日常活動為‘勞動,而用‘工作專指類本質范疇”[1]。赫勒的意思是,工作具有雙重屬性,作為類本質活動,它可能是人錨定自身意義、尋求價值實現的一個途徑,但是這并不能否認勞動作為日常活動,具有讓人疲憊、倦怠的成分。
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是,當代人的工作時長并未隨著技術進步而顯著縮短。凱恩斯曾經暢想,隨著機械設備被大規模引入勞動場所,在21世紀初,人類每日只工作4小時便可以實現社會物質的極大豐富。然而現實是,加班之風盛行,一些國內互聯網企業每周的工作時長竟然超過了60小時。或許正因為如此,“摸魚”和圍繞著“摸魚”行為而產生的文化現象正受到年輕人的熱捧,并逐步演化為一種流行的文化符號。
1 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摸魚”雖是一個新梗,但卻是人類社會的老現象。德塞圖在《日常生活實踐》一書中,便介紹了法國企業雇員中普遍的“摸魚”現象,他將之稱為“假發”,即雇員們裝作為老板工作,實際上偷偷忙自己的事情[2]43。在互聯網的使用語境中,“摸魚”指的是“偷懶,不務正業,不干正事,或在集體活動中不出力”[3]。
本研究使用爬蟲軟件收集了知乎平臺“摸魚”話題下的所有提問和回答。截至2022年6月10日,共收集相關提問及問題描述114條,回答3877條。
數據分析主要分為三個步驟。首先,利用爬蟲及中文分詞庫,對3877條回答樣本進行中文分詞,并統計詞頻。在停用詞表中,加入了常用量詞、連詞以及和主題相關而必然出現的詞(如“摸魚”)。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初步確定了知乎平臺上有關“摸魚”問題相關回答的核心問題及概念:針對打工人與老板、企業為代表的資本方形成的二元對立呈現以及解構式的消極抵抗。其次,結合回答契合度、代表性、完整度等因素,篩選出214條代表性文本,并利用話語分析的質性研究方法對其中的典型文本進行解讀。
2 區分“我們”和“他們”:外部群體和內部群體的話語建構
在社會心理學領域有關群體行為的相關研究中,社會認同理論被認為是重要理論。詹金斯認為,社會認同是由具備內在規定性的群體認同與外在規定性的社會分類兩方面組成的。處于群體中的個人“通過社會分類,對自己的群體產生認同,并產生內群體偏好與外群體偏見”[4]。梵·迪克將這一理論揉入批判話語分析,衍生出了話語中的群體認同策略,在“摸魚”文本中,它體現為對“我們”這一內部群體和“他們”這一外部群體的定義與區隔。
……老一輩人,掌握著資本,掌握著話語權,緊緊握著,不肯放手。他們吃了時代的紅利,在風口上起飛,卻嘲笑我們努力奔跑的是不會飛的豬……
——知乎用戶 生活小浪浪
這段文本第二句句首的“他們”是一個回指代詞,指稱的是首句中的“老一輩人”這個先行詞。作者在這里構造出了分處于權力兩級的兩大群體,作為“他們”的“老一輩人”掌握了社會中的大多數資源——這些資源不光包括物質資源(資本),還包括象征符號的資源(話語權),而“我們”則被塑造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這段文本也同樣包含兩個定向行為過程的分句——“他們吃了時代的紅利”和“他們……嘲笑我們”。正如費爾克拉夫所言,“哪種過程類型被選來表示一個現實過程,這可能具有文化、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5]167。在這段文本中,作者強調了行為者依據自身目標行事的能力,而將“我們”置于被動地位,這是權力關系的體現。
此外,這段文本包含一些深植于文化語境中的習焉不察的隱喻,如“掌握著資本……緊緊握著,不肯放手”“吃了時代的紅利”等。當我們使用隱喻來表示事物時,哪怕是無意識的,“我們是在以一種特定方式建構我們的現實”。將資本隱喻建構為一種可以手持的實體器物,或許可以說是為便于理解而進行的簡化,但這一隱喻同樣剝奪了資本所擁有的內在邏輯,將其降格為一種喪失生命力的物件,同時也暗示了一個更具操縱力的主體的存在。
而“吃了……紅利”一句則將“紅利”視作可以為主體補充養料的食物,這是漢語中利用概念實體與食物間的毗鄰性進行轉喻的一種常見模式。但“時代的紅利”這一說法將“老一輩人”得以“在風口上起飛”的原因歸之于個體難以控制的時代背景,這無形中消解了對“老一輩人”成功合法性的認同,并為后文“我們”被嘲笑為“不會飛的豬”進行了開脫和辯解。
總體而言,在“摸魚”人創造的話語體系中,“我們”被塑造為處于權力弱勢地位,通過自身勞動創造價值(努力奔跑),卻無法得到相應回報(不會飛)的普通人形象;而“他們”則處于權力譜系的高階地位,掌握著社會的絕大多數資源。
3 戲仿與狂歡:后現代式的話語解構
如加拿大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哈琴所言,戲仿是后現代主義“轉向游戲、拼貼、虛擬、仿擬、破碎、嘲諷等敘事話語”[6],從而區別于以往一切文化藝術風格的典型特征。由于包括戲仿在內的任何仿擬必定存在一個臨摹的原本,因此決定了戲仿文本不可能是單一的存在,而是一種特殊的復合文本,也因此,關于戲仿文本的討論離不開關于文本互文性的討論。
巴庫廷將互文性的空間關系區分為兩個向度:互文性的水平向度及垂直向度。其中戲仿文本以及構成其理解背景的原文本主要構成了一種垂直的互文性的關系,“這些文本歷史性地連接在一起”,沒有對原文本的掌握,對戲仿文本的理解就無從談起。此外,戲仿文本的互文性還可以被看作它與習俗(文類、話語、風格、行為種類等)的潛在復雜關系。比如巴庫廷在討論文類的時候,注意到文本不僅能以直接套用的方式繼承這一文類的習俗,還可能通過如譏諷、模仿的方式對其進行“再次強調”或者“混合”[5]95,這便是戲仿所選用的文類、話語風格所具有的互文性。
實際上,知乎熱門話題《摸魚學導論》正是對傳統教學過程中所應用的知識話語結構進行的戲仿。可以借助對其戲仿機制的解析,來考察戲仿文本與作為歷史、背景的原文本之間的戲謔性張力。
戲仿文本最明顯的特征之一便是對源文本的“格式化”,即將現實主義文本夸張變形成一種游戲性文本,即巴庫廷所說的沿用文類風格形成的互文性,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正是對中世紀騎士小說的戲仿,其中的章節設置、情節轉承等文本格式都刻意模仿了當時流行的騎士小說。
《摸魚學導論》是對諸如《心理學導論》《社會學導論》等教科書文本體系的模仿,具體而言,《摸魚學導論》戲仿地構建了自身的內容體系結構和標準化規范,如內容的選擇、組織,語言表達、教學時間、課后練習等,同時也包含對課堂教學話語中多模態符號的吸收和借鑒,如PPT這類結合了圖像與文字的展示單元。
在顯性格式方面,作者完全按照正規課程的教學單元流程設置。在首節課程里,戲仿者煞有其事地交代了開課說明及開課目的,并將課程的考核評分標準、學分情況等予以說明,甚至安排了這節課程后的大小作業。而在內在的語言格式方面,戲仿文體也通過格式化的語言實現了一種狂歡效果,“評分標準:本作業占期末總評成績的0%”。雖然語言格式完全仿照正規的教學語言,但通過粉碎原文本中的意義鏈條和價值邏輯,戲仿文本進行了“形式大于內容”的幼稚化敘事,完成了對原文所承載的意義及價值的解構。
4 討論:“避讓但不逃離”的話語抵抗策略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在“摸魚”人的互聯網討論中,存在著彼此對立的權力兩級——資方與打工者。“摸魚”人借助社交媒體生產的語料一方面宣泄著對現實工作環境中不平等權力關系的不滿與牢騷,另一方面借助各種后現代手法對這一難以動搖的權力構型進行戲謔與解構。
法國學者德塞圖的理論為理解“摸魚”話題及其相關討論提供了進路。德塞圖將“摸魚”視作個體日常的抵抗行為,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個體“透過以無數可能的方式利用外來資源來發明自身”[2]84,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就是在各種權力間尋求平衡,而這往往不得不借助于一種戰術——抵制。
當打工人在各類網絡論壇交流起“摸魚”經驗,分享起“摸魚”心得,這種抵制就由個體的現實行為轉化為一種話語抵抗,并借助網絡趣緣群體形成了儀式化連接。當然,作為德塞圖所言的戰術行為的“摸魚”更多是尋求特定目標的實現或者最低限度的自主性,是“在機制內尋求著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既服從既定規則,又在規則內尋求個人的運作空間”[7]。
“摸魚”人的抵抗是隱蔽、非公開的,“有活干活,沒活就看下新聞,眼角余光一直瞟著門口,領導一進來馬上切換Excel,裝模作樣地敲幾下鍵盤,眉頭緊鎖”。根據36氪發布的《2022職場摸魚報告》,有九成的受訪者通過將“電腦保持在工作頁面”或“時刻觀察領導動向”進行“摸魚”,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戈夫曼將這類行為命名為“假裝干活”。他寫道,“在許多機構中,不僅要求工人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的產量,而且還要求他們時刻準備著造成此時正在努力工作的印象”[8]。
雖然戈夫曼并不熱衷于用權力關系來解釋這類體面策略的成因,但他給出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與德塞圖相接軌。他認為,假裝工作是“地位低的人的特殊負擔”,對于打工人而言,工作空間是微觀政治與權力關系的載體,其中最典型且具有戲劇張力的一對權力關系便是雇主與員工的關系。不難理解,對于員工而言,在領導面前展現出恭順且敬業的形象,不僅是一種主動的印象管理,也在表達著自身對這種權力關系的服膺(起碼不是公開抵抗),以及對工作場域內各種規則和知識的承認與尊重。只有當領導消失,既有的權力空間讓位于一個相對自由的后臺空間或者匿名化的網絡空間時,真實的個體才終于浮出水面,體面策略也轉變為“摸魚”以及肆無忌憚地解構。
5 結語
本文聚焦網絡論壇中“摸魚”現象的相關討論,通過對“摸魚”人在知乎平臺上所分享語料的分析,筆者認為,“摸魚”這一文化符號的流行反映了當下職場打工人對工作環境存在的憂慮。受制于諸多現實壓力,打工人難以公開直接地在現實環境里表達不滿,因此在網絡趣緣社群運用各種話語抵抗策略進行自我表達與情緒宣泄成為他們重塑自主性空間的方式之一。但這種話語抵抗也往往流于后現代式的戲謔與解構,在文本狂歡中,“摸魚”話題的參與者很難對勞動相關的嚴肅議題展開認真的討論。本研究從話語分析的方法入手,探討了“摸魚”人常用的話語抵抗策略及其折射出的社會問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能充分考察話語抵抗策略這一概念的歷史與進路,未對當下社會打工者所面臨的社會困境進行深入研究。未來研究或可從這些角度進一步展開。
參考文獻:
[1] 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58.
[2] 米歇爾·德·塞托.日常生活實踐:實踐的藝術[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43,84.
[3] 大倪. 2022職場摸魚報告[EB/OL]. 36氪-后浪研究所,https://www.36kr.com/p/1589594793970185,2022-01-28.
[4] 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06(3):475-480.
[5] 諾曼·費爾克拉夫.話語與社會變遷[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95,167,200.
[6] 劉濤.語圖論:語圖互文與視覺修辭分析[J].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71(1):28-41.
[7] 練玉春.論米歇爾·德塞都的抵制理論:避讓但不逃離[J].河北學刊,2004(2):80-84.
[8] 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5.
作者簡介:李清貴(1994—),男,湖北十堰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社交媒體、數字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