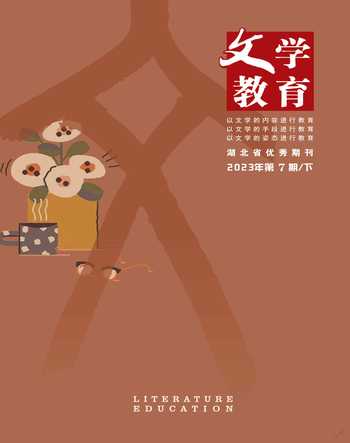《三國(guó)演義》中對(duì)敵思政教育與場(chǎng)域方式研究
阮云志 龐妍
內(nèi)容摘要:學(xué)界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研究主要著眼于己方成員之間,但在實(shí)踐中還包括對(duì)敵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三國(guó)演義》中各方勢(shì)力的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最終形成三足鼎立的情勢(shì)具有巨大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可以分為化敵為我、化敵為友或化敵為無(wú);場(chǎng)域方式包括請(qǐng)入、走出和臨陣。《三國(guó)演義》中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場(chǎng)域方式研究,對(duì)于總結(jié)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歷史經(jīng)驗(yàn)、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視域和指導(dǎo)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實(shí)踐,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和現(xiàn)實(shí)意義。
關(guān)鍵詞:《三國(guó)演義》 對(duì)敵 思想政治教育 目的 場(chǎng)域
長(zhǎng)期以來(lái),受思想政治教育經(jīng)典定義——“一定的階級(jí)、政黨、社會(huì)群體按照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念、道德規(guī)范,對(duì)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jì)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huì)、一定階級(jí)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huì)實(shí)踐活動(dòng)”[1]影響,國(guó)內(nèi)學(xué)界普遍誤認(rèn)為,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只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己方成員。然而,深入研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實(shí)踐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些)人按照一定的期望,有意識(shí)、有目的地對(duì)另一個(gè)(些)人的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思想觀念、現(xiàn)實(shí)行為、行為傾向施加影響的實(shí)踐活動(dòng)”,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僅“包括對(duì)本階級(jí)、政黨、社會(huì)群體等內(nèi)部成員”而且包括“對(duì)友、對(duì)敵、國(guó)際乃至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
文學(xué)來(lái)源于現(xiàn)實(shí)又高于現(xiàn)實(shí),《三國(guó)演義》作為歷史演義小說(shuō)的經(jīng)典之作,“更加側(cè)重寫智慧,勇氣和力量的描寫還在其次”[3]。因此《三國(guó)演義》中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僅有利于了解我國(guó)古代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而且有利于推動(dòng)我黨當(dāng)前和今后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實(shí)踐,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學(xué)術(shù)研究視域。
一.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
三國(guó)時(shí)期,漢室衰微,群雄四起,各方之間,或時(shí)敵時(shí)我,或時(shí)敵時(shí)友。《三國(guó)演義》對(duì)此進(jìn)行了極其生動(dòng)、形象的文學(xué)演繹。通過(guò)對(duì)《三國(guó)演義》的全面系統(tǒng)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敵我或敵友轉(zhuǎn)換,并非完全取決于客觀形勢(shì)和各方實(shí)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方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狀況。其中最典型的是開(kāi)始幾無(wú)實(shí)力可言的劉備。他輾轉(zhuǎn)寄人籬下、半生顛沛流離、可謂命運(yùn)多舛,然其憑借漢室皇叔之名,高舉復(fù)興漢室之旗,盡展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之能,或化敵為我,或化敵為友,或化敵為無(wú),最大限度削弱敵勢(shì)、壯大己力,最終成就一方帝業(yè)。由此可見(jiàn),思想政治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實(shí)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政治目標(biāo),直接目的是使盡可能多的敵方人員在政治思想、心理傾向和實(shí)現(xiàn)行為上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保持一致,或盡可能排除來(lái)自他們的阻礙,從而削弱敵方、壯大己方。
(一)化敵為我
在一定的時(shí)空范圍內(nèi),由于不同的政治勢(shì)力,其政治目標(biāo)相對(duì),政治利益沖突,或者政治判斷不清或有誤,導(dǎo)致在政治立場(chǎng)上相互成為敵對(duì)方。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為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biāo),排除或減少來(lái)自對(duì)方阻礙,除了可采取軍事對(duì)壘等“大棒”手段外,還可采取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化敵為我的“胡蘿卜”策略。所謂化敵為我,是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通過(guò)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使敵對(duì)方或敵對(duì)方的部分成員尤其是重要成員成為己方成員,為我所用,從而達(dá)到削弱敵方、壯大己方的目的。《三國(guó)演義》中此類成功實(shí)踐比比皆是。
一是贈(zèng)之以利、導(dǎo)之以行。對(duì)于敵方見(jiàn)利忘義之類的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贈(zèng)之現(xiàn)實(shí)的物質(zhì)利益、闡明虛擬的期得利益,進(jìn)而勸導(dǎo)其采取看起來(lái)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實(shí)際上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行為方式行事,往往能夠達(dá)到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想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第三回,李肅為董卓勸呂布?xì)w順,先是獻(xiàn)上寶馬金銀,又采用導(dǎo)之以行的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使呂布投于董卓。“肅取金珠、玉帶列于布前”,且勸呂布認(rèn)丁原為父沒(méi)有前途,再訴說(shuō)董卓仰慕之情,謂之曰“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后又揶揄其“功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為耳”。[3]16呂布思緒良久,最終砍下丁原首級(jí),拜董卓為義父。
二是生擒活捉、親解其縛。第十二回,曹操見(jiàn)許褚威風(fēng)凜凜,在對(duì)戰(zhàn)中生擒活捉,收其為都尉。起初曹操的部下典韋與一壯漢大戰(zhàn)一天不分勝負(fù),曹操并不知道其為何人,命典韋接連詐敗兩天,壯漢在沒(méi)有防備的情況下連人帶馬落入陷阱,為操所擒。“操下帳斥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衣之,命坐,問(wèn)其鄉(xiāng)貫姓名”[4]58。得知此人就是許褚后,曹操表達(dá)對(duì)其的欽佩之情,“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3]58遂諸引百人俱降。
生擒活捉之后,親解其縛、解袍衣之這一行為輔之以其它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往往能使被擒之猛將頓生感動(dòng)、心悅誠(chéng)服。第十五回,孫策在設(shè)計(jì)生擒敵方劉繇之部下猛將太史慈后,采用言行感化的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成功地使其心悅請(qǐng)降。且說(shuō),為應(yīng)孫策來(lái)攻,太史慈自請(qǐng)為先鋒迎敵被其主劉繇所拒,遂不喜而退。后混戰(zhàn)之中,與策酣戰(zhàn),策喜其勇,設(shè)計(jì)生擒,解投大寨,策親自出營(yíng),喝散士卒,親釋其縛,解袍衣之,請(qǐng)入寨中,并謂之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慈見(jiàn)策待之甚厚,遂請(qǐng)降。[3]76
以上諸例,或贈(zèng)之以利、導(dǎo)之以行、或生擒活捉、親解其縛,最終都成功實(shí)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目的,使教育對(duì)象成功地轉(zhuǎn)化為己方成員,大大削弱了敵方力量,壯大了己方的力量。
(二)化敵為友
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中,化敵為友是最理想的狀況,通常可用于敵弱我強(qiáng)、敵困我順、敵心有怨、敵或思變等情勢(shì)下。在敵強(qiáng)我弱或敵我相當(dāng)、共同面臨第三方更強(qiáng)之?dāng)硶r(shí),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為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biāo),可以采取其它適當(dāng)?shù)膶?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如闡明雙方政治境遇的相似性和第三方強(qiáng)敵的共同性,或者用行為示范方式展示化敵為友后雙方政治境遇的可期向好變化,以期達(dá)到化敵為友的政治目的。《三國(guó)演義》中矛盾和沖突較為激烈,兩軍徹底聯(lián)合的情況并不多見(jiàn),但對(duì)于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來(lái)說(shuō),將敵人轉(zhuǎn)化成友軍共同聯(lián)合抗敵也不失為一個(gè)理想的目的。
一是言語(yǔ)說(shuō)服。第四十二回,曹操已占據(jù)一半天下,兵力強(qiáng)盛、糧草充足,親率八十三萬(wàn)大軍(“詐稱一百萬(wàn)”)一路追攻劉備之軍。劉備退守江夏,曹軍虎踞江漢、直取江陵,不但劉軍危在旦夕,而且東吳也將唇亡齒寒。雖孫劉“自來(lái)無(wú)舊”甚或互有戒備之心、些許敵意,然在此情勢(shì)之下,雙方都不得不認(rèn)真考慮“誰(shuí)是我們的敵人?誰(shuí)是我們的朋友?”這個(gè)革命的首要問(wèn)題[5]。諸葛亮正待借自東吳來(lái)探虛實(shí)之人的順風(fēng),前去江東說(shuō)服東吳;孫權(quán)從魯肅謀,命其往江夏以吊喪劉表之名,行對(duì)劉備思想政治教育之實(shí),探其“往結(jié)東吳”之意。因之,諸葛亮即隨魯肅親赴東吳,先面見(jiàn)群臣、舌戰(zhàn)群儒,繼言激孫權(quán)、陳情局勢(shì),再智激周瑜、堅(jiān)其戰(zhàn)心,后草船借箭、借瑜東風(fēng),最終致曹操在赤壁之戰(zhàn)中遭受了沉重打擊,為今后三分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關(guān)鍵的政治和軍事基礎(chǔ)。
二是行為感化。三國(guó)之中,敵我友關(guān)系瞬息萬(wàn)變。第十四回,兵敗于曹操的呂布無(wú)處棲身,往投時(shí)任徐州牧的劉備,兩者合而為友。后劉備奉曹操假天子詔討伐袁術(shù),張飛自薦留守徐州,期間張飛酒間無(wú)端暴打呂布岳父曹豹,布怒而夜取徐州,自領(lǐng)徐州牧,從而使呂劉由友我關(guān)系瞬間轉(zhuǎn)化為敵我關(guān)系。然布又意欲化敵為友,遂采用守備宅門、還其家眷的行為感化式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最終既達(dá)到奪人之地,又實(shí)現(xiàn)化敵為友的政治目的。
三是言行結(jié)合。第八十六回,鄧芝受諸葛亮所托,走出去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去往吳國(guó)說(shuō)服孫權(quán)拒魏向蜀。孫權(quán)在進(jìn)門處立油鼎、擺大刀,意欲嚇退鄧芝。鄧芝運(yùn)用曉之以理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分析魏蜀吳三國(guó)其中利害,同時(shí)表現(xiàn)得大義凜然,曰:“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愚將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絕說(shuō)客之名也。”言訖,便撩衣下殿,往油鼎中跳。[3]422以此行為言語(yǔ)相結(jié)合的方式,不但使孫權(quán)“急命止之,請(qǐng)入后殿,以上賓之禮相待”,而且最終說(shuō)服孫權(quán)派使“入川通好”。
(三)化敵為無(wú)
很多形勢(shì)下并不能讓自己的敵人直接歸順,或者成為友軍進(jìn)行幫助,故還存在一種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化敵為無(wú)”。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與其受教育的對(duì)象雖然不能成為一體,也不能成為友軍,但是對(du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不再存在威脅。“化敵為無(wú)”的“無(wú)”,可分為無(wú)為式存在、虛無(wú)式存在以及阿斗式存在。
一是化敵在敵之軍方為虛無(wú)式存在。敵方,從軍事角度可以分為敵之軍方(亦可稱為敵營(yíng))和敵之地方或敵之民方。化敵在敵之軍方為虛無(wú)式存在,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通過(guò)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身在曹營(yíng)心在漢”,不為敵對(duì)方獻(xiàn)智效力。第三十六回,劉備一直以來(lái)以仁義之心聞名,徐庶作為劉備的謀士,其智謀被曹操嫉妒,操軟禁了庶的母親并偽造信件讓庶歸降操。旁人勸備借操之手殺庶之母以使其死心塌地追隨備,備不肯做如此不仁不義的事情,遂放庶前往救母。終使庶感言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shí)為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shè)一謀”[3]180。備的行為使得庶與自己的母親都將備認(rèn)作當(dāng)世之英雄,庶也不再為操貢獻(xiàn)一計(jì)。通過(guò)言語(yǔ)、行為等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對(duì)象雖處于敵方陣營(yíng)之中,但卻不為敵營(yíng)獻(xiàn)智效力,從而實(shí)現(xiàn)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化敵在敵營(yíng)之虛無(wú)式存在的政治目的。
二是化敵在敵之民方為無(wú)為式存在。化敵在敵之民方為無(wú)為式存在,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通過(guò)一定的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使本屬于敵之軍方的軍事人員轉(zhuǎn)化為敵之地方的非軍事人員,從而使其在軍事上不愿或不能有所作為。第八十七回,諸葛亮采用言行感化的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將被縛的孟獲之將領(lǐng)以及手下蠻兵均去除束縛,并放他們歸去與家人團(tuán)聚,且贈(zèng)其酒食衣物。此可謂,“釋放敵將,以攻其心”[6]。士兵將領(lǐng)深感孔明之恩,不愿再追隨孟獲有所作為。第九十一回,驃騎大將軍司馬懿“深有謀略”,又總督雍、涼兵馬,“倘訓(xùn)練成時(shí),必為蜀中之大患”,是故諸葛亮從馬謖計(jì),派人于洛陽(yáng)、鄴郡等處散布謠言道懿欲反,并假借懿之名義張貼興師謀反的布告,通過(guò)謠言傳播者和揭榜或閱榜者對(duì)魏國(guó)新帝曹睿進(jìn)行上行思想政治教育,加上睿原本對(duì)懿就“素懷猜忌”,終使懿被“削職回鄉(xiāng)”、貶為庶民,從而不能有所作為。
三是化敵在我營(yíng)之阿斗式存在。化敵在我營(yíng)之阿斗式存在,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通過(guò)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使從敵營(yíng)請(qǐng)入或自入“我”營(yíng)的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忘記自己的陣營(yíng)歸屬和歷史使命,只顧享樂(lè),“樂(lè)不思蜀”。第一百一十九回,蜀國(guó)滅亡,司馬昭已得魏國(guó)政權(quán),蜀國(guó)后主劉禪行至洛陽(yáng),司馬昭設(shè)宴待之。席間表演魏、蜀之舞,蜀官皆悲痛,唯劉禪(阿斗)嬉笑顏開(kāi),司馬昭問(wèn)其是否思蜀,劉禪答曰“此間樂(lè),不思蜀”[3]588。這正是樂(lè)不思蜀典故的由來(lái)。后人都知阿斗樂(lè)不思蜀,其實(shí)其父劉備也曾樂(lè)不思蜀過(guò)。第五十五回,周瑜弄假成真使得劉備真的娶得孫權(quán)之妹,權(quán)意欲“以華堂大廈,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遠(yuǎn)孔明、關(guān)、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荊州可圖也。”[3]267備也確實(shí)享樂(lè)其中,全然不想回荊州。
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的場(chǎng)域方式
《三國(guó)演義》所描述的是中國(guó)古代,沒(méi)有今天的網(wǎng)絡(luò)虛擬環(huán)境與高科技聯(lián)系方式,因此所有的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在一定的現(xiàn)實(shí)物理空間中進(jìn)行。除了臨陣對(duì)戰(zhàn)或在對(duì)方不知情的情況下混入、潛入、潛伏外,敵我存在的現(xiàn)實(shí)物理空間基本都是相對(duì)獨(dú)立的,因此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實(shí)施的場(chǎng)域方式,也就可以相應(yīng)地分為請(qǐng)入、走出和臨陣,其中走出包括走出到敵方和走出到第三方場(chǎng)域范圍內(nèi)。
(一)請(qǐng)入
請(qǐng)入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將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請(qǐng)”進(jìn)自己的陣營(yíng),在自己的主場(chǎng)對(duì)敵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根據(jù)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行為方式,請(qǐng)入可分為禮賢進(jìn)入和強(qiáng)制“進(jìn)”入。
一是禮賢請(qǐng)入。禮賢請(qǐng)入,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以禮賢下士的姿態(tài)和行為將敵方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請(qǐng)入己方,使之感動(dòng)誠(chéng)服。第一種情況是從敵場(chǎng)禮賢請(qǐng)入我場(chǎng)。第六十五回,馬超原是東川張魯手下,魯聽(tīng)信奸人之言懷疑超欲兵變。劉備軍中降將李恢自薦至超處作說(shuō)客,成功將超勸降。備見(jiàn)超,親自接入,以上賓之禮待之。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云霧而見(jiàn)青天!”[3]324第二種情況是場(chǎng)域轉(zhuǎn)換——敵場(chǎng)變?yōu)槲覉?chǎng)后,原敵方將領(lǐng)不愿歸順,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可禮賢請(qǐng)而順之。第六十五回,劉璋投降,劉備入主成都,百姓迎門而接。備至公廳,升堂坐定。郡內(nèi)諸官,皆拜于堂下;惟璋舊部黃權(quán)、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備急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3]325并親自登門,請(qǐng)二人出仕。二人感備恩禮,乃出。
二是強(qiáng)制進(jìn)入。是指用捆綁、俘虜?shù)葟?qiáng)制方式使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進(jìn)入己方場(chǎng)域,目的是對(duì)之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十二回,劉備將曹操手下“請(qǐng)”回軍營(yíng),采用言語(yǔ)說(shuō)服曹操手下替自己說(shuō)話。話說(shuō)備假意欲與操和解,用計(jì)監(jiān)押了操手下劉岱與王忠,將二人“請(qǐng)”入劉備軍中,設(shè)宴款待二人,訴說(shuō)自己對(duì)操赤誠(chéng)忠心道,“備受丞相大恩,正思報(bào)效,安敢反耶?”[3]131遂放二人歸營(yíng),二人感懷劉備不殺之恩,替他在操前用家人之名擔(dān)保備不會(huì)造反,從而為備防御操爭(zhēng)取了時(shí)間。
(二)走出
走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自己或委派他人走出己方場(chǎng)域,到敵方場(chǎng)域中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可分為派己方謀士用面談、書(shū)信或借助榜文等方式將思想政治教育內(nèi)容帶入敵方場(chǎng)域以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走出面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己方自身或委派與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有舊交的手下直接前往,用面談方式對(duì)其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十回,陶謙的說(shuō)客陳宮采用曉之以理的方法對(duì)曹操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時(shí)曹操“文有謀臣,武有猛將,威鎮(zhèn)山東”,乃派人去瑯琊郡接操父曹嵩。嵩攜家小四十余人及從者百余人“道經(jīng)徐州”,太守陶謙欲結(jié)交操“正無(wú)其由”,遂“出境迎接”、設(shè)宴款待,并派都尉張闿率兵五百護(hù)衛(wèi),不料闿護(hù)送途中貪圖財(cái)物,將嵩一行殺害。曹知而遷怒于謙,起兵報(bào)仇,誓殺盡城中百姓以泄其恨。陳宮與陶謙交厚,又心系百姓的性命,便日夜兼程至操處進(jìn)言曰,“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義之輩;尊父遇害,乃張闿之惡,非謙罪也。且州縣之民,與明公何仇?殺之不祥。望三思而行。”[3]48第十四回,曹操派滿寵走出,與徐晃面談以對(duì)其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且說(shuō)曹操與楊奉大戰(zhàn),見(jiàn)楊奉手下徐晃“威風(fēng)凜凜”,頓生招納之意。曹行軍從事滿寵與晃有一面之交,遂自薦往說(shuō)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于楊、韓之徒?曹將軍當(dāng)世英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jiàn)公之勇,十分敬愛(ài),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zhàn),特遣寵來(lái)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yè)?”寵見(jiàn)晃不舍舊主,乃又進(jìn)勸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3]68晃乃從之,隨寵投操。
二是送出書(shū)信。礙于雙方敵對(duì)關(guān)系,并不是任何情況下都具備在敵場(chǎng)對(duì)敵進(jìn)行在場(chǎng)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便利條件,因此有時(shí)送出書(shū)信至敵場(chǎng)對(duì)敵進(jìn)行非在場(chǎng)式思想政治教育不失為一個(gè)較好的方法。第二十二回,劉備為防曹操大軍來(lái)攻,欲求救于袁紹,然與紹“未通往來(lái)”,“今又新破其弟”袁術(shù),雙方實(shí)處于敵對(duì)狀態(tài)。后從陳登言,請(qǐng)?jiān)僦辽袝?shū)、與袁紹三世通家又師于備的鄭玄作書(shū),差孫乾投遞于紹,紹覽之自忖,“玄德攻滅吾弟,本不當(dāng)相助;但重以鄭尚書(shū)之命,不得不往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伐曹操。”[3]109
三是發(fā)出榜文。送出書(shū)信仍然需要具備寫信之人與敵首或敵將有舊之類的便利條件,而且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對(duì)象往往是敵首或敵將等敵方特定個(gè)體。若無(wú)此便利條件則需要派員至敵場(chǎng)口宣或張貼榜文或者箭射榜文至敵場(chǎng)以對(duì)敵之不特定多數(shù)人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第十九回,曹操與呂布對(duì)戰(zhàn),得知呂布不得軍心,便張貼榜文射入敵場(chǎng),以對(duì)敵眾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榜文曰:“上至將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lái)獻(xiàn),或獻(xiàn)其首級(jí)者,重加官賞。為此榜諭,各宜知悉。”[3]98第二十二回,袁紹應(yīng)劉備之請(qǐng)起兵助攻曹操,對(duì)戰(zhàn)之前命陳琳草擬檄文張貼于各州各郡及關(guān)津隘口,陳情形勢(shì)、列操罪惡、罵操三代、重金懸賞,其效果是,使紹發(fā)兵名正言順,使操見(jiàn)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jué)頭風(fēng)頓愈。”[3]111
(三)臨陣
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場(chǎng)域,除了上述一方進(jìn)入另一方場(chǎng)域之外,還有一種是兩者臨陣共場(chǎng)。臨陣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可分為臨陣言語(yǔ)式和臨陣行為式。
一是臨陣言語(yǔ)式。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在陣前用言語(yǔ)感化或恐嚇?lè)绞綄?duì)敵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臨陣改變行為傾向或作出對(duì)己方有利之行為。第十八回,呂布攻打劉備,備守城不出。布將張遼來(lái)攻,關(guān)羽知其“有忠義之氣”,遂在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身于賊?”[3]92遼“低頭不語(yǔ)”而退,張飛欲追,羽止之曰,“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頗有自悔之心,故不與我等戰(zhàn)耳。”[3]92關(guān)羽以一言而退強(qiáng)敵,此可見(jiàn)臨陣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之功效。第六十五回,馬超在城門前與劉璋喊話,璋驚倒,欲投降。話說(shuō)馬超敗于曹操后依附漢中張魯,劉備入川后、意取劉璋時(shí),超自薦攻備救璋,不期被諸葛亮用計(jì)招降于備。降后自薦前往喚璋出降,及至城下,立馬鞭指璋曰,“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zhí)迷,吾先攻城矣!”[3]324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意欲“開(kāi)門投降”,被眾人勸阻。后備又派幕賓簡(jiǎn)雍走入城中當(dāng)面對(duì)璋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言備“寬宏大度,并無(wú)相害之意”,終致璋“決計(jì)投降”。
二是臨陣行為式。臨陣之際,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用自己的行為,如能勝而不勝,能殺而不殺,能辱而不辱等,對(duì)敵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使敵明白如其繼續(xù)對(duì)抗則必?cái)o(wú)疑。第二十七回,關(guān)羽當(dāng)初投降曹操時(shí)與操有約,它日但知?jiǎng)湎侣浼葱姓?qǐng)辭尋備,然當(dāng)羽得備書(shū)而欲辭行時(shí),操故意閉門不見(jiàn),羽不得不轉(zhuǎn)友為敵,過(guò)五關(guān)斬六將。但羽之目的只在尋備,并非殺敵,因此過(guò)關(guān)斬將臨陣行為式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意在警告敵將,擋吾者死,放我者生。對(duì)敵眾則通過(guò)臨陣言語(yǔ)式進(jìn)行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羽殺東嶺關(guān)守將孔秀后謂敵眾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wú)干。”[3]134結(jié)果是,眾軍俱拜于馬前。殺黃河渡口關(guān)隘守將秦琪后謂敵眾曰,“當(dāng)吾者已死,余人不必驚走。速備船只,送我渡河”。[3]136結(jié)果是,軍士急撐舟傍岸。
《三國(guó)演義》雖然存在作家加工,但主要還是以歷史為本,是一部充滿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意蘊(yùn)的書(shū)籍。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不同,則方式有別。為了將敵人轉(zhuǎn)換為我方陣營(yíng),為我所用,可以贈(zèng)之以利、導(dǎo)之以行、或生擒活捉、親解其縛;為將敵人轉(zhuǎn)化為我方友軍,可通過(guò)言語(yǔ)說(shuō)服或行為感化,有時(shí)還可以言行結(jié)合;無(wú)法將敵人轉(zhuǎn)為我方或友方時(shí),還可化敵為無(wú),消除敵人威脅。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場(chǎng)域方式上,可以是請(qǐng)入,也可以是走出或臨陣。其中,請(qǐng)入,既可以是禮賢請(qǐng)入,也可以是強(qiáng)制“請(qǐng)”入;走出,既可以是走出面談,也可以是送出書(shū)信或發(fā)出榜文;臨陣,既可以是臨陣言語(yǔ)式,也可以是臨陣行為式或兩者相結(jié)合。研究《三國(guó)演義》中的對(duì)敵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目的和場(chǎng)域方式,不僅有利于我們總結(jié)中國(guó)古代對(duì)敵進(jìn)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實(shí)踐智慧和成功經(jīng)驗(yàn),還可以為當(dāng)前和今后我國(guó)對(duì)國(guó)內(nèi)外敵對(duì)勢(shì)力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xiàn)
[1]張耀燦等.現(xiàn)代思想政治教育學(xu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6.
[2]阮云志,武端利.思想政治教育內(nèi)涵和外延的重新審視[J].求實(shí),2012,(5):78-80.
[3]張國(guó)風(fēng)著.說(shuō)不盡的經(jīng)典 三國(guó)演義 歷史的智慧[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9.(07):5.
[4][明]羅貫中.三國(guó)演義[M].長(zhǎng)沙:岳麓書(shū)社,2001(09).
[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
[6]李飛,周克西編著.《三國(guó)演義》與經(jīng)營(yíng)管理[M].北京:北京體育學(xué)院出版社.1988:234.
基金項(xiàng)目:陜西省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年度項(xiàng)目“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革命精神譜系研究”(2021B001);陜西科技大學(xué)博士科研啟動(dòng)基金項(xiàng)目“大眾思想政治教育視野下中國(guó)夢(mèng)宣傳教育研究”(BJ15-18) 【注:項(xiàng)目主持人均為阮云志】
(作者單位:陜西科技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陜西省交通醫(y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