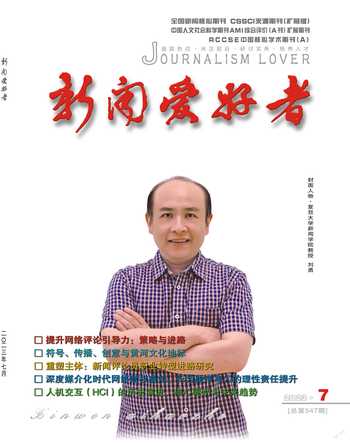把握新媒體傳播規律,提升主流媒體網絡評論引導力
顏云霞 朱秀霞 翟慎良
【摘要】提升新聞輿論引導力是主流媒體在當今復雜多變的輿論環境中發揮職能作用、彰顯自身價值的必然選擇。主流媒體的網絡評論,則是其引領思想、引導輿論、凝聚共識的重要載體。提升主流媒體網絡評論引導力,需著眼新媒體傳播的需求規律,高度注重網評時效;遵循新媒體傳播閱讀規律,加快網評媒體融合步伐;把握新媒體傳播偏好規律,善于運用網評的情感要素;探索新媒體傳播圈層規律,加強網評與用戶間的互動交流。
【關鍵詞】新媒體;主流媒體;網絡評論;引導力;傳播規律
習近平總書記在“2·19”講話中指出,要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切實提高黨的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1]其中,提升新聞輿論引導力作為重要的分解目標,是主流媒體在當今復雜多變的輿論環境中發揮職能作用、彰顯自身價值的必然選擇。網絡評論是指“網絡傳播中的意見性信息”[2]。所謂主流媒體網絡評論,主要指的是由主流媒體生產、在網絡上傳播的,對新聞事件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等現象和問題表達判斷與思考的意見性信息。主流媒體的網絡評論是其引領思想、引導輿論、凝聚共識的重要載體。本文結合近年來主流媒體網絡評論的相關實踐,梳理和提煉新媒體傳播的四種規律,以期為提升主流媒體網絡評論引導力提供建議參考。
一、著眼新媒體傳播需求規律,提升網絡評論“時效力”
在依托互聯網技術所形成的媒介生態環境中,評論一直是受眾對新聞產品的剛需。尤其是熱點事件、重大事件發生后,優秀的網絡評論作品往往能形成刷屏效應。原因在于: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更新迭代,傳播者與受傳者的界限早已模糊,曾經被動的受眾正在成為信息生產和傳播的主力軍,由此帶來信息數量的幾何級增長。面對汗牛充棟且瞬息萬變的信息流,人們不再滿足于信息本身,而更渴求對信息加以情感交流、意義解讀與價值評判。人們不僅關注“發生了什么”,更關注“應該怎么看”。相較于其他新聞產品,網絡評論具備態度鮮明、觀點新銳、文風多變等特征,有著更強的思想性與批判性,更好地滿足了受眾的新聞需求。
受眾的注意力資源是有限的,總是被最新、最熱、最重要的事件所俘獲。根據心理學的“沉錨效應”,對這些最新、最熱事件的“第一解讀”,往往能像沉入海底的錨一樣,讓公眾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和認識。如今“人人都有麥克風”,誰發聲早誰就有更大概率錨定輿論風向,成為輿論的“領舞者”。故而,網絡評論的“時效力”就是輿論的“引導力”。作為網絡評論隊伍的專業選手,主流媒體能否引領輿論關鍵在于,能否第一時間回應社會關切、解答公眾疑惑。快發聲、早發聲,就能搶占先機,站在輿論風暴的上風口;慢發聲、晚發聲,就會貽誤時機,成為輿論的跟隨者,甚至喪失話語權。
受眾對“怎么看”的需求有些是顯性的、即時的,表現為大事、要事、新事發生之后的極度關切,有些則是隱性的、未來的,如對多個新聞事件背后是否聯系的疑惑,對某一長期現象原因和走向的猜測等。這就意味著,網絡評論的“時效力”不僅要體現在速度上,做到事后快速反應、及早發聲,還體現在預判上,做到預先設置議題、鎖定輿論“風口”,傳播積極正面的思想。如針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新聞,“團結湖參考”發表觀察類評論《什么職務最危險?政協副主席》(2015-01-19)、《余遠輝栽在哪里?秘書長魔咒還在繼續》(2015-05-23)等,結合一系列新聞事件分析特定階段的反腐側重點,闡釋全面從嚴治黨的意義,引導受眾思考,“創造性”地滿足受眾的新聞需求,做足輿論引導的提前量。
新媒體時代是一個“爭分奪秒”的時代。一個新聞事件發生后,尤其當涉及社會分歧和社會矛盾,抑或攸關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時,受眾有第一時間尋求解讀與闡釋的普遍心態。對此,主流媒體網絡評論必須快速反應,作出觀點闡釋,幫助受眾理順事實信息、厘清認識思路,進而占據話語主動權,影響輿論走勢。但也要注意,由于信源模糊、碎片傳播、報道失范等原因,新聞反轉現象時有發生。面對事實不清或疑點頻發的新聞事件,主流媒體網絡評論既要有“倚馬可待”的反應能力,也要有“讓子彈飛一會兒”的判斷定力,以避免輿論反轉的反噬。
二、遵循新媒體傳播閱讀規律,提升網絡評論“融合力”
碎片化、娛樂化、視聽化,構成了當下新媒體語境下新聞閱讀的三大典型特征,也成為主流媒體網絡評論需要遵循的閱讀規律與生產邏輯。
移動閱讀的碎片化,決定網絡評論必須抓人眼球,能在短時間內激發受眾的閱讀興趣。對主流媒體而言,就要打破紙質媒體時代的思維慣性,實現與新媒體“流量思維”的對接融洽。首要的就是標題制作,如果標題不能吸引讀者點開網評全文,內容即便再好也是失敗的。好的標題,不僅要恰當地概括網評的核心觀點,還要擊中社會情緒、撓到受眾癢處。如2022年底,一些地方將防疫作為工作出發點,層層加碼,濫用權力,為難群眾,以致讓防疫變了形。“浙江宣傳”微信公眾號發表題為《“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2022-11-29)的網評,該標題簡練而有力,直指問題要害,引發大眾強烈共鳴。此外,一些主流媒體所推出的網絡短評形式,也是適應碎片化閱讀的有益探索。如人民日報新媒體品牌欄目《你好,明天》、新華社的《新華微評》等,用百來字評析熱點新聞事件,往往起到“四兩撥千斤”的奇效。
移動閱讀的娛樂化,意味著受眾會有意無意地回避嚴肅內容,但并不意味著他們不需要嚴肅內容。如前所述,承載著思想和觀點的網絡評論仍然是網絡世界的剛需,而一些網評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主要還是因為話語體系的固化,其嚴肅有余、活潑不足,教化過多、感化不夠的弊端在新媒體語境中被進一步放大。面對當前客觀存在的主流與非主流兩個輿論場、官方與非官方兩種話語體系,主流媒體要學會融通兩種話語,不能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簡單地批評批判,要多些“說話”、少些說教,多些平等交流、少些居高臨下,多些真實體會、少些不痛不癢,用網友聽得懂的語言、肯接受的方式,進行共情對話、同頻對話。比如,“俠客島”微信公眾號多用輕松、調侃的語言寫時評,用幽默、詼諧的語氣談論政經大事,讓人愿讀、愛讀。
移動閱讀的視聽化,則對網絡評論的傳播方式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媒體時代,網絡評論可以是一篇文章,也可以是一個動畫、一張海報、一段視頻。如2020年2月,云南大理扣押重慶口罩一事引發熱議,新華網推出《大理,你“欠理”了!》,配發的海報上面“大理”二字,伸出了勾住口罩的黑手,形成了“無理”,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網絡評論的視頻化發展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重要趨勢,在這一過程中形象化、通俗化、即時化和分層化是其能夠快速融入用戶信息接收方式的必由選擇。[3]
三、把握新媒體傳播偏好規律,提升網絡評論“情感力”
麥克盧漢認為,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的層面上,而是堅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4]數字媒介技術作為一種“感官技術”,天然地與感情和情感聯系在一起。[5]故而,在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新媒體時代,具備較高情感喚醒程度的信息更易被轉發和分享。[6]面對感性技術的沖擊,主流媒體網絡評論必然要作出相應的調適,不能再延續過去紙質評論時追求莊重、回避情感的做法,既要做到以理服人,又要實現以情動人,要承認、接納、重視、善用評論中的情感要素。
作為意見性話語的網絡評論,情感并不會損害它的思想性與引導力。應該看到,情感是網絡評論寫作的起點與燃料。所謂“心由情動,文由情發”,“心動”而后“筆動”。一篇自帶一種“不吐不快”“非寫不可”沖動的網絡評論,往往具有較強的生命力、感染力,其背后是作者的情感與思緒,更是責任與擔當。如上觀網評《在章子欣家守了幾天之后,我想替沒有被看見的痛苦辯護》(2019-07-16),作者直言:“這些天來,面對鋪天蓋地的‘網絡暴力,我認為有必要替那些沒被看見的痛苦做一些辯護。”文章從記者視角出發,以在場者的身份書寫,筆觸樸實而感性,讓讀者充分感受到作者對網絡暴力的極度憤懣、對當事家庭的深切同情,并由衷反思“鍵盤黨”的行為。
情感力量是網絡評論重要的價值增量。一篇網評若能換位思考,體味受眾的情感,感受他們的苦與樂,就容易獲得更具普遍性的認同,從而被轉發、被分享。正如克勞斯所說的,理解觀點采納的更好方式是將其視為一種道德情感的運作。[7]換言之,懂得才能贏得,網絡評論當有“共情”能力,善于同頻對話。如全網刷屏的《嘲諷“小鎮做題家”是一個危險信號》(2022-07-16),站在“小鎮做題家”的視角,充分肯定“每一個奮斗不息的學子背后,都是晝夜不息的逆風奔跑”,對隨意給某一群體貼標簽的做法提出尖銳批評,贏得了高點贊、好口碑。
需注意的是,情感不能浮在網絡評論的表面,而要與觀點和論證融為一體,更不能濫情泛情,出現“情感驅逐邏輯”的尷尬局面。主流媒體網絡評論生產要學會恰當地進行“情感設置”、適度地運用“情感策略”,既要觸動情緒、飽含深情,也要有所克制、警惕煽情,講究情感與理性的適配,注重有節制、有節奏的表達。
四、探索新媒體傳播圈層規律,提升網絡評論“運營力”
進入新媒體時代,“關系黏性成為內容生產和傳播的新動力”[8]。互聯網以其強大的連接屬性,使得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個體通過網絡彼此相連,又在類似的興趣條件下不斷聚合,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圈子。與傳統社會中基于血緣、親緣形成的關系連接相比,當下的圈層本質是不同個體價值觀的聚合。[9]在此背景下,主流媒體網絡評論的輿論引導需注重“運營力”的提升,即與用戶建立緊密而鞏固的關系。原因有二:一則圈層是個體基于價值認同而凝聚在一起,對主流媒體網評高度認同的圈層,可助推主流輿論的二次傳播;二則圈層塑造了主流媒體與用戶的良好關系,更有利于其了解用戶的真實訴求,進而改進自身內容和傳播策略。通過良性互動、形成閉環,主流媒體網絡評論就能更具生命力、傳播力、影響力。
一方面,要打造網絡社群,擴大“朋友圈”。網絡社群是網絡生態系統中主體因子在不同關系引導下形成的群落,主要呈現兩種狀態:圈式聚合結構和鏈式聚合結構。[10]前者強調網絡社群成員間的“共性”,如依托現實關系的家族群、同事群,依托興趣愛好的購物群、科技群等;后者則強調網絡社群成員間的“個性”,典型的如微博的“熱搜榜”。故而,主流媒體也可通過兩種途徑建立自己的網絡社區,一是設立讀者QQ群、微信群等,與讀者建立直接聯系。如“團結湖參考”在獲得粉絲數突破性增長之后,很快設立了兩個讀者QQ群:普通讀者群與大學生研究群,成為黏住粉絲的有益嘗試。[11]二是在微博等社交平臺構建話題,主動設置議題,鼓勵受眾參與討論,協同主流媒體助推輿論走向。這是較少有人做過的嘗試,需要有很強的把控和平衡能力。
另一方面,要加強雙向互動,實現“社交化”。“沒有互動的新媒體就沒有靈魂”[12],強互動是新媒體區別于傳統媒體的重要特征。主流媒體網評要通過新型平臺建設強化與用戶之間的交流互動,包括留言互動、直播互動、短視頻互動等。輿論引導的社交化,不僅可以增強主流媒體的親和力,也能降低信息誤讀的風險,促進更高程度的認同。[13]如“浙江宣傳”,經營好評論區是其吸引受眾、破圈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該微信公眾號精心挑選平臺留言,與網民平等互動、親切交流,在提升受眾參與感、活躍度的同時,實現了輿論的二次發酵,放大了正面聲音的傳播效果。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充斥海量信息的新媒體平臺,好的內容未必就一定能獲得較高的閱讀量。于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而言,“內容為王”固然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也不能忽視“關系”在新的傳播生態中的作用與影響。如今,主流媒體幾乎都已構建起“兩微一端一網一抖”的全媒體傳播矩陣,但輿論引導力的提升不是簡單依靠資金投入、技術升級就能實現的,還需要在熟悉網絡主體行為特征的基礎上,激活自身與用戶、用戶與用戶之間的社會關系,形成各具特色、價值趨同的網絡社群,從而為主流輿論的社群化擴散提供有效渠道。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N].人民日報,2016-02-20(01).
[2]胡文龍.中國新聞評論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403.
[3]唐冰.新聞評論視頻化:傳播特質與發展趨勢[J].中國出版,2022(11).
[4]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58.
[5]宋乃馨,張雪魁.數字媒介與新聞生產的情感革命[J].青年記者,2023(3).
[6]Pfitzner,R.,Garas,A.,&Schweitzer,F.(2012).Emotional divergence influences information spreading in Twitter.ICWSM,12,2-5.
[7]莎倫·R.克勞斯.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與民主商議[M].譚安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161.
[8]彭蘭.傳統媒體轉型的三大路徑:移動化、社交化、智能化[J].新聞界,2018(1):36.
[9]喻國明,郅慧.理解認知:把握未來傳播的競爭重點、內在邏輯與操作路徑[J].新聞界,2023(3):68-75.
[10]彭蘭.從社區到社會網絡:一種互聯網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拓展[J].國際新聞界,2009(5):89-94.
[11]蔡方華.以“小而美”躋身新媒體紅海:“團結湖參考”的轉型之路[J].新聞與寫作,2015(7):18-21.
[12]之江軒.沒有互動的新媒體就沒有靈魂[EB/OL].https://mp.wei
xin.qq.com/s/W3DOZZB6kCpMiuf-wpEb7Q.
[13]金玉萍,劉建狀.新型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力提升的理念革新:網絡生態系統視域下[J].中國編輯,2021(12).
(顏云霞為《傳媒觀察》主編助理;朱秀霞為鄉村干部報社辦公室主任;翟慎良為鄉村干部報社總編輯,中國新聞獎新聞評論一等獎獲得者)
編校:董方曉